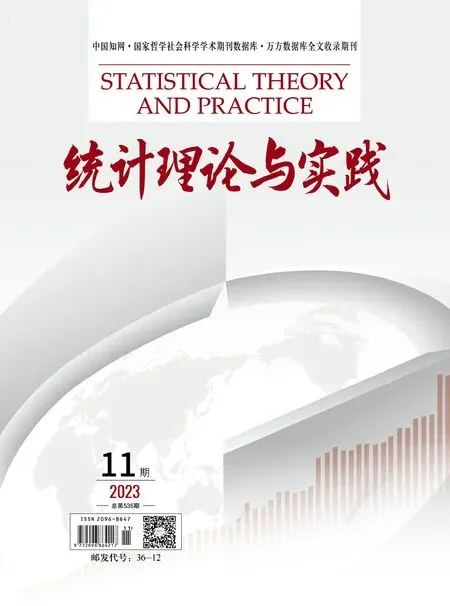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研究
——基于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的門檻效應分析
李安琪 姚作為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 廣州 510053)
一、引言
數字經濟是依靠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支撐的經濟新形態,而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依靠上述技術對自身的生產營銷與經營管理進行再創新的過程(龔雅嫻,2022)[1]。企業作為逐利個體,運用數字化轉型技術提升品牌資產價值是其目標之一,而現有文獻鮮有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的關系。因此,進一步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對企業自身價值管理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品牌資產是涉及企業品牌管理以及營銷活動的成果。企業使用新型信息技術,一方面作用于品牌管理成本,即通過互聯網渠道降低生產要素成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企業創新(黃群慧和余泳澤等,2019)[2],從而降低品牌成本。另一方面影響企業的營銷方式。企業不僅可以通過消費體驗視角嘗試打開品牌價值共創方式(王滿四和霍寧等,2021)[3],也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構建品牌虛擬形象,提升品牌資產(邢彥輝和樊雪琛,2020)[4]。
本文實證分析了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的關系,并考察了企業的營銷投入與創新能力對數字化轉型影響品牌資產的門檻效應,研究結果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舊可靠。此外,按照不同分類將樣本分組后進行了異質性分析。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以下兩方面:(1)將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納入一個分析框架,補充了數字化轉型的作用與品牌資產影響因素的文獻。(2)通過分析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在數字化轉型影響品牌資產關系中的門檻效應,為企業管理者提供借鑒。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
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中,企業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基于企業的動態能力(Warner 和Wager,2019)[5],將數字技術和業務流程相結合的組織變革(Liu 和Chen等,2011)[6]。這一變革為組織自身、顧客以及利益相關者群體都帶來了顛覆性影響。
首先,從企業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數字化轉型過程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營銷成本,提升了企業的聲譽和品牌影響力。數字化轉型要求組織重新定義自身的戰略和愿景,以促進在技術、人力資本、組織文化等方面的重構(Gurbaxani 和Dunkle,2019)[7],促進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人力資源利用率的提升(張志朋和李思琦等,2023)[8]、數字化管理部門職能的優化以及企業數字化戰略與企業文化的深度融合等,這勢必會壓縮企業經營成本和營銷成本。同時,企業運用新型數字技術進行個性化營銷,增強了與顧客的有效互動(吳瑤和肖靜華等,2017)[9]。在此過程中,企業的數字化營銷轉型也極大地降低了企業的營銷成本,其利用互聯網為媒介工具也提高了企業的品牌影響力。
其次,從顧客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數字化轉型的過程是企業通過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業務和營銷上的創新,優化流程來強化顧客體驗和顧客價值(姚小濤和亓暉等,2022)[10],通過滿足顧客的需求和影響顧客的心理作用于購買意愿以及購買行為。可見,企業的經營與數字技術結合的過程,使顧客與品牌的關系更加緊密。Keller 和Aaker(1992)[11]早就提出,強勢品牌的優勢在于該品牌與顧客建立了深度關系,這能夠提升顧客對品牌的信任,進而增加品牌資產。現有研究中,也有學者指出在數字時代,要強化消費者體驗對品牌價值創造的重要作用[3]。
最后,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利益相關者角度下的品牌資產不僅僅是生產利潤,更多的是關注價值創造(張燚和張銳等,2010)[12],以及利益相關者與品牌之間的相互作用(Duncan 和Moriarty,1999)[13]與互動程度。現有研究中,有學者考察了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價值創造(白福萍和梁博涵等,2023)[14],這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劉向東和米壯等,2022)[15],也為本文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品牌資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礎。
綜合看,現有研究主要結合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和品牌資產的部分構成進行分析,尚無直接將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聯系起來的文獻。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為了能夠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變革,對企業內部而言降低了企業的經營和營銷成本,提升了與顧客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互動,對企業外部而言改善了企業形象和聲譽,提升了品牌資產。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品牌資產。
(二)營銷投入的門檻作用
營銷投入往往被認為是一把雙刃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營銷活動投入加大,企業可以利用新型信息技術促進營銷轉型,如企業依托新型互聯網技術,提升與顧客的交流與互動(Yoo 和Donthu 等,2000)[16],深度挖掘用戶需求,并利用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提升顧客產品體驗,促進企業與顧客、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共創[9]。在此基礎上,顧客能夠更快地了解和熟知產品,進而促進企業品牌資產提升。同時,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需要企業使用大量資金進行研發以及業務全流程優化,而過多的營銷投入勢必會擠壓這一部分資金,擠占企業既有資源,資金的使用效率無法提升,已有研究發現過度的營銷活動會從不同維度降低品牌資產(江明華和董偉民,2003)[17]。因此,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會因為營銷投入的變化而變化,適當的營銷投入是這個過程中應該考量的問題。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營銷投入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正向影響中存在門檻效應。
(三)創新能力的門檻作用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依賴的是企業的創新能力。已有研究證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降低企業內部的溝通成本(戚聿東和肖旭,2020)[18],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更能節約成本,進而激勵企業加大研發資金投入(趙波和郭子宇等,2023)[19]。具體而言,數字化變革與員工創新的相互作用已經被諸多學者證明,而員工創新是企業創新的縮影,企業通過與員工、顧客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價值共創,提升品牌資產。因此,數字化轉型需要依賴企業創新水平,并在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中起作用。創新能力強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促進作用更大。需要指出的是,同一行業的企業創新能力以及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創新能力千差萬別。由此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會受到創新能力作用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3:企業創新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正向影響中存在門檻效應。
三、數據來源及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8—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對初始數據做如下篩選:剔除樣本中的ST、*ST 公司;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剔除財務狀況異常的公司;對企業層面的連續變量進行1%和99%水平的Winsor 縮尾處理。此外,本文對標準誤均按照公司層面的聚類處理。本文公司層面的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 數據庫,上市公司的年報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
(二)變量設置
1.自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
現有研究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測度標準不一,對其測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種:(1)黃群慧和余泳澤等[2]從互聯網普及率、相關從業人員、相關產出和用戶數四個方面測度互聯網綜合發展指數。(2)祁懷錦和曹修琴等(2020)[20]、王立平和李蔓麗(2023)[21]選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部分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度量企業的數字化水平。(3)劉政和姚雨秀等(2020)[22]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數據,總結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4)吳非和胡慧芷等(2021)[23]、袁淳和肖土盛等(2021)[24]利用Python 軟件對上市公司的年報和公告進行文本分析和詞頻統計,對詞頻統計結果進行對數化處理得到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
本文參考吳非和胡慧芷等(2021)[23]的方法,按照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及數字技術五大分類構建數字化轉型關鍵詞匯庫,并對企業年報進行文本分析和詞頻統計,對詞頻統計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以此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具體步驟如下:(1)構建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性詞語。(2)利用Python 軟件對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年報進行爬蟲,并將爬取的文件轉化為txt 格式。(3)對所得年報進行文本分析和詞條統計,并進行對數化處理,以克服原始數據的右偏分布特征,最終得到數字化轉型指標。
2.因變量:品牌資產
現有文獻對品牌資產的測度主要基于財務要素、市場要素、消費者要素的某一種或者將其綜合起來進行考量(盧泰宏,2002)[25]。本文綜合財務和市場要素,并參考邵偉和劉建華等(2022)[26]的做法,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salesit表示i 企業于t 時間段所獲得主營業務收入;E(salesit)表示i 企業于t 時間段所獲得主營業務收入的預測值,根據計算所得;ADi(t-1)和PROMOi(t-1)分別表示i 企業于t-1 期的廣告費用和促銷支出,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借鑒邵偉和劉建華等的做法,采用營銷投入和管理費用作為ADi(t-1)和PROMOi(t-1)的代理變量,變量滯后一期是為了控制營銷投入和管理費用的結轉效應;Δ Assetsit表示i 企業在t 時期的總資產增長率;HHIit表示i 企業在t 階段的產業集中度;μind、year、μi以及εit分別表示行業效應、時間效應、個體效應以及隨機干擾項。
3.門檻變量: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
借鑒劉艷博和耿修林(2021)[27],錢麗華和劉春林等(2015)[28]的研究,選用上市公司利潤表中銷售費用來衡量營銷投入(Minvest)。創新能力(Innvoate)選用上市公司專利數量的自然對數值作為代理變量。
4.控制變量
本文在進行線性回歸估計時,選用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現金比率(Cash)、股權集中度(TOP)、獨立董事占比(Ind)、董事會規模(Boardsize)、所有制代理變量(Soe)等作為控制變量。回歸所涉及的變量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度量
(三)模型構建
為了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線性回歸模型:
考慮到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和品牌資產存在非線性關系,借鑒Hansen(1999)[29]的門檻面板模型,分別考察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是否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存在門檻效應。因此,本文分別構建關于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的單一門檻面板回歸模型:
其中,γ 為待估計門檻值,I(·)為指示函數。當Minvest≤γ 時,I 取1,否則取0。當門檻變量超過門檻值時,通過構造F 統計量來判斷門檻效應是否顯著,觀察P 值取值,若P<0.1,則拒絕原假設,表明至少存在一個門檻值。假設兩個門檻值,即δ1、δ2為待估計門檻值,構建雙重門檻面板回歸模型:
四、回歸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
本文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上市公司的品牌資產指標BE 的平均值為0.161,并大于其中位數。這表明,在本文所選取的樣本中,上市公司品牌資產呈右偏分布,部分企業的品牌資產較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Digital)的平均值為5.189,最小值和中位數均為0,說明部分企業尚未開展數字化轉型或進程較慢。企業的營銷投入(Minvest)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4.882 和9.952,均大于0,說明企業對營銷投入的意愿較強。企業創新能力(Innvoate)的標準差為367.21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7178 和0,說明企業創新能力差別較大。此外,本文進行了變量的相關系數檢驗。總體而言,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都比較小,盡管存在相關系數的絕對值大于0.5 的情況,但表2 中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 均遠低于10,說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分析
表3 報告了被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與解釋變量品牌資產(BE)的基準回歸分析結果。為了驗證假設H1,在控制時間效應、個體效應的基礎上,依次加入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如列(1)至列(7)所示。可以看出,無論加入何種控制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均顯著且為正,假設H1得到驗證。

表3 基準回歸檢驗結果
從控制變量看,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股權集中度(TOP)、獨立董事占比(Ind)、董事會規模(Boardsize)的回歸系數均顯著。具體而言,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規模越大,品牌資產越大。資產負債率(Lev)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財務杠桿越大,品牌資產規模越大,能夠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有一定的合理性。股權集中度(TOP)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股權集中度越高,品牌資產的規模越容易做大。獨立董事占比(Ind)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為正,說明獨立董事規模占比越高,形成決議的事項越有利于企業發展,對品牌資產的擴大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現金比率(Cash)對品牌資產(BE)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現金的持有量在提升企業流動性的同時,也抑制了企業對建設自身品牌資產的能力,二者的影響相互抵消所致。所有制代理變量(Soe)對品牌資產(BE)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對自身品牌資產的影響并無直接相關性。
(三)穩健性檢驗
1.變量的穩健性
考慮到變量選取的準確性,本文采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方法來考察變量是否穩健性。借鑒祁懷錦和曹修琴等(2020)[20],王立平和李蔓麗(2023)[21]的做法,選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附注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項中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部分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來度量企業的數字化水平。表4 列(1)和列(2)報告了以無形資產占比的數字化轉型為核心解釋變量,分別控制相關變量與不控制相關變量的結果,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1)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證明了假設H1。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2.調整時間窗口
鑒于數字化轉型前后的時效性,本文以資本市場劇烈震蕩的2015 年為時間點,分為2010—2015 年、2016—2020 年兩個樣本期間,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 列(3)、列(4)。研究表明,分時間回歸后,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2)的系數分別為0.030、0.059,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樣本期間內,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品牌資產,再次證明了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此外,在2016—2020 年期間,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2)的系數更大,說明資本市場回歸理性后,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加快,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更大。
3.估計方法穩健性
本文在檢驗估計方法穩健性時,分別采用混合OLS模型估計法、隨機效應模型估計法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5 列(1)、列(2)。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的回歸系數分別在5%以及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本文的核心結論依舊得到支持。

表5 內生性檢驗結果
4.內生性討論
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可能與某些不隨時間變化的誤差項相關,這會導致參數估計的結果出現偏誤,因此需要討論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分別將核心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滯后一期和使用廣義矩估計法(GMM法)構建工具變量,以討論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1)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
考慮到滯后效應緩解可能的內生性以及時滯問題,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變量滯后一期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 列(3),滯后一期的企業數字化轉型變量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與研究假設H1吻合。
(2)使用線性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使用廣義矩估計法(GMM法),以緩解模型的內生性偏誤。為保證GMM法的有效性,進行兩個檢驗:其一是檢驗誤差項是否二階序列相關;二是過度識別Sargan 檢驗。二者p 值都大于0.1 時,才滿足要求。從表5 列(4)的結果可以看出,AR(2)和Sargan 檢驗的p值分別為0.925 和0.602,因此,GMM 估計結果有效,即工具變量有效。
(四)異質性檢驗
本文基于企業規模、所有制以及利潤率大小,將企業分組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見表6。具體而言,首先,生成企業規模變量的中位數,將企業規模大于中位數的企業與小于等于中位數的企業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列(1)、列(2)。可以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大規模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對提升品牌資產的能力更強。其次,列(3)、列(4)分別報告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對品牌資產的影響,可以看出,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系數為0.002,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對品牌資產的影響較大。最后,列(5)、列(6)分別報告了高利潤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從回歸結果看,高利潤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系數為0.002,相較于低利潤企業而言,高利潤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更顯著。

表6 異質性檢驗結果
五、進一步分析
為了進一步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Digital)與品牌資產(BE)的關系是否受到營銷投入(Minvest)與創新能力(Innovate)的影響,本文運用Stata 軟件,進行門檻面板模型回歸。
(一)企業營銷投入的門檻效應
表7 報告了營銷投入(Minvest)的門檻檢驗類型、F 統計量、p 值以及門檻值等。可以得出,營銷投入的單門檻和雙門檻p 值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存在雙門檻效應。從門檻估計值看,營銷投入的兩個門檻估計參數分別為0.021 與0.114。此外,本文也進行了不控制相關變量和控制相關變量的門檻面板回歸結果,回歸結果均顯著。表明在低營銷投入(Minvest≤0.021)時,在控制相關變量的基礎上,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的回歸系數為0.013,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營銷投入較低時,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有正向影響。在中等營銷投入(0.021<Minvest≤0.114)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為正,說明營銷投入中等時,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具有促進作用。而在高營銷投入(0.114<Minvest)時,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系數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營銷投入過高導致企業流動性降低,營銷活動效率下降,與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帶來的正向作用相悖,二者影響相互抵消所致。綜上所述,企業的營銷投入具有雙重門檻效應,要將其控制在一定范圍內,才能發揮出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最大效應,這印證了假設H2。

表7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
(二)企業創新能力的門檻效應
表7 報告了企業創新能力(Innovate)的門檻檢驗結果。具體而言,創新能力的單門檻和雙門檻檢驗p值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其兩個門檻估計參數分別為2.298 和4.543。此外,本文在不控制變量與控制變量的情況下分別考察了企業創新對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關系的門檻回歸結果。總體看,隨著創新能力的提高,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提升效率增大。具體而言,當企業的創新能力較低(Innovate≤2.298)時,數字化轉型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為正。當企業的創新能力處于中等水平(2.298<Innovate≤4.543)時,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系數為0.049,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當創新能力較強(4.543<Innovate)時,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為0.073,仍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創新能力越強,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正向影響越大,與假設H3相符。
六、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使用2008—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數據,考察了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品牌資產的關系以及營銷投入和創新能力的門檻效應。實證結果表明:首先,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穩健性檢驗中,通過替換變量和改變估計方法后,結果依舊可靠。在考慮了內生性以后,研究結論依舊成立。其次,營銷投入具有雙重門檻效應。在其小于第一門檻值或介于兩個門檻值之間時,營銷投入促進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正向影響,但營銷投入高于第二門檻值時,過高的營銷投入擠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正向影響,營銷活動效率降低,門檻效應不再顯著。創新能力具有雙重門檻效應。企業創新能力越強,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促進作用越大。最后,數字化轉型對品牌資產的影響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差別不大;規模較大以及利潤較高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對品牌資產的影響更大。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是企業要注重全產業鏈創新,打造品牌核心競爭力,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全產業鏈創新體現在技術創新更加包容化、管理模式更加智能化、服務更加精準化等方面。要通過信息技術等手段整合全要素、優化全流程,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二是企業要制定科學的數字化營銷策略,優化銷售模式,提升品牌資產。要深度融合線上和線下兩個渠道,創新體驗式、場景式消費。隨著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線上消費人群占比越來越大,企業要針對不同的消費人群,制定差異化營銷戰略。三是企業營銷要與平臺經濟深入融合。企業與平臺經濟的連接是數字化轉型的一環,利用好平臺經濟新模式有利于優化企業營銷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