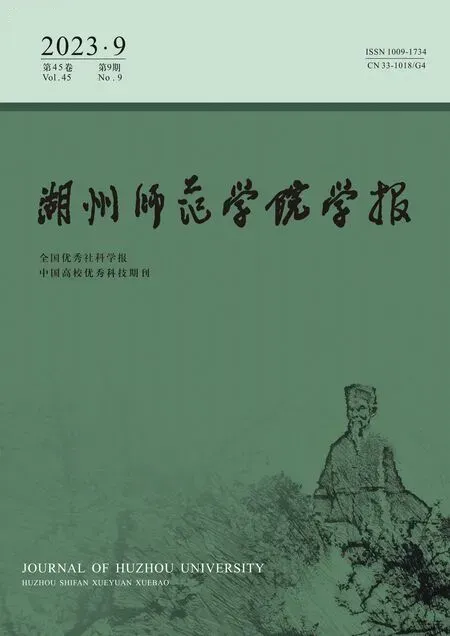現實語境、生成邏輯與實踐樣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維探析*
楊磊鑫,葉榮國
(安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穩,一個民族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同困難作斗爭,是物質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對壘”[1]16。可見,精神之于人、之于國、之于民族、之于未來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精神”的重要性做了新的考量,突出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2]22-23。在新的征程上,多維度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定位其語境、厘清其源流、探尋其實踐樣態,對切實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增強全民族精神風貌與力量具有重大意義。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現實語境
新時代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持續深入,中國夢穩步推進。既然如此,為何還要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回答這一問題,需要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現實語境。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
作為共同富裕的一體兩面,物質共富和精神共富同頻共振、缺一不可。單方面的物質富足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內在規定,也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強大動力。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內蘊精神生活極大豐富的現實期許。馬克思主義幸福觀認為,從物質需要的滿足中獲得快感是人的動物性體現,或者說是人的自然屬性,而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對精神交往的需要和精神世界的豐富正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重要體現,即“對科學的向往、對知識的渴望、他們的道德力量和他們對自己發展的不倦的要求”[3]107,可見,真正的幸福是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統一,是實現人全面而自由發展。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意味著我們的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人民基本的物質文化需要得到滿足,“物質幸福”得以普遍實現,人民對高質量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轉而成為矛盾的一方。如果說過去人們追求的是衣、食、住、行等生存性需要,是“體之要”,那么現階段人們注重追求的是文化學識的豐富、道德修養的提升、視野胸懷的寬廣、審美品位的高雅等發展性需要,是“心之要”,這些都與精神生活相關。特別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物質層面的絕對貧困,具備“個人硬實力”之后,人們更加注重“個人軟實力”的提升,即滿足感官欲望的同時,更加注重審美境界的躍遷[4]64-75,這表明發展性需要不再處于從屬位置,追求“精神幸福”成為人們生活常態,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自然成為衡量人民生活美好程度的標尺之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對人民美好生活現實訴求的主動應答。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轉化為物質,精神的力量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僅停留在精神層面的暢想,更要以“改造世界”的決心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質性”呈現。何以呈現,“精神主動”至關重要,精神主動是主體在認識世界、把握規律的基礎上,在遵循規律、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展現的積極作為、能動奮進、勇毅自信的精神品質與精神狀態[5]32-45。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夠增長人們的才智、凝聚人們的價值共識,以精神主動賦能美好生活的實現。美好生活具有全民指向性,如果個體精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處于渙散無序的狀態,缺乏價值認同,就不能集中高效地發揮人民之智,就不能匯聚起全體人民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奔向美好生活的堅定信念與不息動力。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現實訴求不斷增強的時空境遇下,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塑造主動的精神狀態、統和美好的生活向往、構建良好的道德秩序、凝聚強大的奮斗合力,能夠為人們實現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柱與動力支撐,使人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偉大實踐中能夠有力可用、有勢可借,主動作為,共謀美好之策、同建美好家園、共享美好生活。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之義
中華民族的復興之所以附加“偉大”這一限定性前綴,是因為單純的物質崛起并不是真正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方位的復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復興之內涵,也是復興之偉力。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蘊含中華精神文化強盛繁榮的復興深義。“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5。民族精神與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魂”“源”,根深才能枝繁葉茂,魂固才能基業永存,源清才能長流不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方位、深層次、高質量的復興,不僅是物質的強盛,更是文化的繁榮與精神的富足。中華精神與文化的復興意味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根據時代與人民需要實現持續的、科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文化服務力、創造力、引領力不斷提升;意味著中國民族共同體空前堅固,中國人民的民族認同感、歸屬感、自豪感不斷增強;意味著中華民族能以嶄新的精神風貌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持續增進。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歷次磨難中成長,從歷次磨難中奮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世代中華兒女以獨特智慧培育和發展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脫貧脫困脫險、向善向上向強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鑒往知來,中華精神與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然之義與必然之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勁推力。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6]5。首先,精神共富能夠凝聚全民族強烈的精神認同,為民族復興塑造強大的精神定力。一個民族,只有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保持對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堅守認同和對其他民族精神文化的理性審視,才能堅挺精神脊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著在“兩個大局”深度演進、思想文化交鋒加劇、精神領域斗爭頻仍的歷史境況下,中國人民能夠站穩意識形態立場,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體認傳統文化精神,筑牢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居所。其次,精神共富能夠調動全民族的精神自覺,為民族復興注入不懈的精神動力。精神自覺是人的精神主動的現實體現,具有計劃性、目的性、創造性等表現特征[5]32-45。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著人們能夠普遍預見民族復興的樣態,并發揮自身聰明才智,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新方案、新策略與新方法。最后,精神共富能夠增強全民族的精神自信,為民族復興提供堅韌的精神耐力。“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需要能力,也考驗耐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著人們對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二者力量的確信,確保以團結奮斗的良久姿態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持續推向更深處。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優勢表征
精神生活的貧富是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正如法國學者基佐所言:“文明主要包括兩點:社會狀態的進展與精神狀態的進展;人的外部條件和一般條件的進展,以及人的內部性質和個人性質的進展;總而言之,是社會和人類的完善。”[7]8-9
精神缺失是資本邏輯宰制下的文明舊形態之桎梏,反映人的單向性和社會的極權性。赫伯特·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認為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新型極權主義社會,所謂新型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暴力型極權”,其通過科學技術提高生產力,創造大量的物質財富,滿足人們各種虛假需求,使人們身處一種看似舒適,實則不自由的生活模式,表現為政治領域的封閉、文化領域的同化與俗化,以及話語領域的封閉等,人們的生活被“極權主義”框定在特定范圍之內,導致人的思想和行為逐漸趨于單一化和同質化,只有對現存秩序的“慣性認同”,人成為“單向度的人”,即喪失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正如馬爾庫塞所言,“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剝奪”[8]3。除此之外,文化消費主義也侵蝕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在資本邏輯下,精神生產漠視對人的精神需求的滿足,單以精神產品的快速流通獲利為目的,結果就是缺乏“靈魂”的精神產品充斥精神市場,“占有主義”主導精神消費,精神經濟看似一片繁榮,實則是人的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虛假統一”[9]5-11。馬克思把人類文明歷程總體上分為三個階段: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關系—自由個性,造成“精神缺失”這一可悲現狀的現實原因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無法掙脫對物的依賴。
精神共富是人本邏輯主導下的文明新形態之表征,指向人的全面性和社會的有序性。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這五大文明的相育相生、同頻共振、協調發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秩序與顯性特征。中國所創造的文明形態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畸形文明形態,而是兼顧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促進社會和人類更加完善的新型文明形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何以新”之問的特定回答,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超越性指向和獨特優勢體現。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終極追求。比較視域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態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超越之一就是,在“人本邏輯”主導下,人的精神生活實現了異化的揚棄,不僅以“人”為目的,而且以“精神增值”“精神共富”為導向,旨在于精神產品的優質多樣供給與良性消化吸收的互動中跳脫“物”的束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是脈脈相通、協調有序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支撐,貫通于其他文明領域之中[10]10-1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高級樣態,能夠統一人們對經濟富強、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生態美麗的價值共識,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23-24構建精神秩序、注入精神動力,推動整個社會在有序運轉中前進。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邏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源起于馬克思主義關于精神生活的科學理論,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神富裕思想,生成于中國共產黨精神文明建設的百年實踐,以深刻的理論底蘊、文化底蘊和歷史底蘊展現出強有力的邏輯必然性。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精神生活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表達
中國當前的蓬勃發展和取得的現實成就以及未來的持續強盛無不展現和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真理性同樣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中窺見。
首先,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探討中確證精神生活的派生性與重要性。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是經典的哲學命題,討論精神不能脫離物質,黑格爾曾犯了“唯精神論”的錯誤,以“絕對精神”賦予精神以獨立的外觀,遮蔽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相反,馬克思以物質為源頭和基點,探尋精神與物質二者關系,指出“‘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11]161。“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2]2這為精神生活尋到源頭,強調了精神生活的派生性。在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人與動物的角度做了對比,認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11]56,而動物只能本能地、被動式地生產,這體現出精神生活之于人所以為人的不可或缺性。同時,精神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正所謂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11]9。
其次,在對未來社會的構想中展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場景。資本主義社會的“拜物教”思想在積聚財富的同時造成“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3]665,使人成為物的奴隸,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尋求“人的解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無情批判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進行了顛覆式構想。第一,物的極大豐富為人的精神世界的發展提供可能。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按需分配引發階級、國家、戰爭和“三大差別”的消亡,為人們追求精神滿足創造了先決條件。第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呈現樣態。在共產主義社會,人擺脫了對人和物的依賴性,“利益式分工”也隨之消亡,自由時間的充裕為人們更加積極地謀求精神生活的富足提供了條件。第三,必然王國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現實產物。精神的富足是為了現實的美好,人從異己力量中解放出來,轉而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這都需要社會成員精神的普遍獨立與富足。
最后,在精神生產和交往理論的闡發中呈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作用范式。精神生活的貧富程度是衡量人發展程度與潛力的重要因素,而精神生產是精神生活的關鍵環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11]151-152這里有兩層含義,其一,精神生產是物質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且它的產品具有物的外殼,所以同物質生產一樣,精神生產的流程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環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這四個環節的有序銜接與循環。其二,交往是精神生產、發展、富裕的重要方式,人們總是通過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式使自己處于交往的境地,物質交往能夠攜帶精神的交流,精神的交往能夠實現個體靈魂碰撞與修養的提升。正如馬克思所言,“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豐富性”[11]169。
(二)文化邏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精神富裕思想的傳承弘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其獨特的創造性、包容性、本土性和連續性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偉大智慧和美好追求理應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探尋源流。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描繪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沒有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生產力和文明水平都得到極大發展的今天才出現的“新愿景”,中華民族的先人們以其理性智慧對大同世界的暢想早已包含了對精神境界的規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大同社會描繪了一個全體成員安居樂業、講信重善、人人為公、各盡其力的理想世界,這樣美好的社會既是精神世界富足的體現,也是精神生活極大豐富的結果。其中蘊含的道德理念、文明狀態和共建共治共享思想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社會層面的應然呈現。不僅如此,先哲們在個人層面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作了設想和要求。不論是“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 ,都體現了個人精神世界的豐富與道德情操的高雅。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優秀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得以“立”、得以“興”、得以“久”的根基與靈魂,其孕育的優秀基因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描繪了底色,注入了智慧。第一,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不論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的規誡,還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勸勉,都詮釋了自強不息之于人的重要,之于人的精神的重要。第二,先人后己的集體觀念。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每一次大事都有“集體主義”的色彩,比如大禹的治水為民、岳飛的抗金衛國、司馬遷的著書立學等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典范,肩負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與使命。這些優秀基因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論構想和實現樣態繪制了亮麗底色。
最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實踐的民族”[14]105-111,不僅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做了愿景描繪,而且進行了實踐探索。第一,以物質生活的富足為首要實現。面對弟子“既富矣,又何加焉”(《論語·子路》)之問,孔子以“教之”回應,之后董仲舒指出“先飲食而后教誨,謂治人也”(《春秋繁露》)的道理,還有管子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等,都明確了物質富足之于精神追求的基礎性。第二,以見賢思齊、和而不同的態度追求精神富裕。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關鍵是要端正態度,對于個人要以“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的態度向精神修養崇高的人看齊;對于國家,則要“和而不同”,既要傳承弘揚本民族文化,又要學習、借鑒、融和各民族優秀文化,為追求精神富裕提供充足養料。第三,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和標準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在推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時要循序漸進,遵循階段性原則。
(三)歷史邏輯:中國共產黨精神文明建設百年實踐的守正創新
精神文明建設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中之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深入、完善、凸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脈絡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精神文明建設的百年歷程中厘清。
從“被動”到“主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精神文明建設以精神上“醒過來”為主要內容。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悲慘遭遇導致中國人民精神上一度陷入“被動”。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英勇斗爭,“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15]180。究其失敗之因,核心之一就是沒有從精神上喚醒人民群眾,沒有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支持。為了喚醒人民的救亡意識,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人民有了主心骨,精神上開始由被動轉為主動,同年創立“人民出版社”,為人民出好書,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思想;抗日戰爭時期把文藝作為“革命機器”的一部分來建設,大范圍開展“冬學運動”,中國人民爭獨立、求解放的意識空前強烈。可以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人民群眾的“主動革命”下取得勝利的。
從“站立”到“站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精神文明建設以精神上“站起來”為主要內容。天安門城樓上的莊嚴宣告標志著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站立”了,但并不意味著“站穩”。為了使人民群眾在精神上不僅立住而且穩住,黨在全社會開展了精神上的社會主義改造。黨領導人民禁絕黃賭毒,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開展大規模掃盲運動,提出“五愛”公德建設新標準,破除舊社會痼疾,移風易俗。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黨領導各族人民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之中,這期間涌現出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典型人物,形成一系列偉大精神,通過對“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16]5,飽滿的精神狀態成為全民所向,相信社會主義能夠實現幸福生活已成為普遍共識,中國人民在精神上逐漸“站穩”了。
從“匱乏”到“充實”,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精神文明建設以精神上“富起來”為主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人民基本溫飽得不到保障,對物質富裕的追求成為必然,相較之下,則對精神追求的重視不足。再者,“文化大革命”時期,“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壓”[17]169,文化事業停滯不前,人民精神發展受到阻礙,種種現實因素致使人民精神十分匱乏。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隨后“兩手論”把精神文明建設置于新的高度,確定“四有新人”建設目標。進入新世紀,黨確立“以德治國”新的治國方略,部署“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新的戰略任務,這一時期,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
從“先富”到“共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以精神上“強起來”為主要內容。進入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明確了新的歷史方位。一方面,主要矛盾的轉變明示我們,精神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關系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另一方面,“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需要更加強大的精神動力。由此可知,允許一部分人精神上先富起來,即局部性、散狀式的精神富裕已經不適合人民的新需求與社會的新發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即精神上“強起來”才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正確選擇與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社會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與踐行工作,開展“四史教育”,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力求精神共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然成為中國共產黨精神文明建設的新內容、新方向、新理念。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踐樣態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強精神建設,增強精神力量,提高精神水平,需要從價值主體、內容要素和推進層次入手,探索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踐樣態,為推進精神共富提供抓手。
(一)全成員參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8]142,提綱挈領地表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富裕。
首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為了人民的富裕,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46新時代以來,凡是“共同富裕”所論之處,必能看見“人民”這一主體標識與價值指向,這是人民主體地位的體現,是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生動詮釋。眾所周知,為人民謀幸福是黨的不變初心,現如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然成為人民“幸福”之基本要義,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確立“人民至上”的工作導向是現實之必然。換言之,人民立場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本立場,是黨推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基點與價值向導,提出、推進并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與黨的初心相契合、相呼應、相貫通。
其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依靠人民的富裕,必須堅持共建共享。“團結奮斗是中國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必由之路”[2]70,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紙上談兵,其不僅要堅持黨的領導,依靠黨謀大局、把方向,更需要全體人民的切身實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樓閣,并非不可抵達的美好幻境,而是全體人民集智聚力,共建共創,進而應然也必然實現的美好愿景。正所謂“幸福是奮斗出來的”,全體人民的能動參與是精神生活得以共富的動力之源,“勤勞致富,智慧致富”的理念與方法同樣是精神建設的錦囊。沒有人民智慧與力量的加持,精神共富將寸步難行,只有全體社會成員躬身入局、銜石填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如期如質實現。
最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造福人民的富裕,必須堅持普惠共享。“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2]46,在結果導向的視角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質就是人民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極大提升[19]11-16。安全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現樣態的基本表現,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獲得感與幸福感的基點,主要表現為物質的充盈消除了精神追求的后顧之憂,使人們自發自覺地追求精神富足成為可能;獲得感是人們在獲取精神產品與享受精神服務之后的充實感,需要精神文化供給真正用之于民;幸福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高級呈現,意指人民在創造、享受精神文化資源,進行精神領悟、交往之后擁有的滿足愉悅之感,即優質的情緒體驗。
(二)全方位聯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8]11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推進這一偉大工程需要實現“精神需求—精神生產—精神消費”三個環節的有序銜接與互動。
第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需求多樣的富裕。“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6]14,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上,人民精神需求的多樣性益發突顯。具言之,包括知識性需求、思想性需求、審美性需求在內的多樣性的人民精神需求,代表著人們對真理與技藝的需要、對善良與正義的追求、對文明與和諧的向往。其中,知識性需求是個人提升自身素養的基本需要,思想性需求與審美性需求則是個體成長需要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有機統一,是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滿足全體人民對多種類、高品質精神生活的旺盛需求,是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環節,能夠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原生動力。
第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生產豐富的富裕。“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20]34,精神生產豐富是對精神需求多樣的現實回應。精神生產豐富首先體現在精神生產力的極大增加,物質資料的豐富、精神生產時間的增多、高新科技的涌現使精神產品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而精神文化產品的充盈是精神生產豐富的直觀體現,展現中國精神、彰顯文化魅力、符合人民審美的各類優質創作不斷產出更新,供人民選擇;同時,多元主體的參與是精神生產持續豐富的有力保證,國家和社會、文藝工作者、廣大人民群眾分別擔任領導者、先鋒隊、主力軍的角色,合力保障精神產品的有序、高效供給,真正做到“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21]200。
第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消費升級的富裕。“精神消費是人們吸收各種精神產品來滿足自身生存發展需要的精神性活動”[4]64-75,隨著人們對情緒體驗、審美期待、感官愉悅要求的不斷提高,精神消費的升級成為必然。初級的精神消費,顧名思義,就是人們獲得低層次精神享受的消費,具有一次性、消遣性等特點,是“非綠色”的精神消費。而高級的精神消費以眼界、品味和修養的提升為目標,具有長遠性、可發展性等特點,是可以洞明世事、啟迪智慧的精神消費。另外,精神消費升級還意味著人們不再局限于對精神產品“量”的占有,而是更加注重對精神產品“質”的獲取,是從“虛假消費”到“真實消費”的跳脫與躍升。
(三)全時空推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在動態中向前發展的過程”[18]14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實現這一偉大目標,既要打破時空界限,全面推進,也要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認識。
其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統一的富裕。“堅持理論創新”作為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之一,不僅要求我們用新的理論回應新的問題,更要求我們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進而解決問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黨對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作的理論回應,而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這就意味著精神生活不能止步于口中的共同富裕,而是要專注于腳下的共同富裕。同時,在推進實現精神共富的過程中,又會出現新樣態、深層次的問題,阻礙“共”的范圍與“富”的程度,彼時,又需要新的理論來解決困難,指導實踐。概言之,推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部署“過河”的任務,又要解決“橋與船”的問題,更要奮力“抵岸”,知行統一,常進常新。
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長期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富裕。“欲速則不達,驟進祗取亡。”“促進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高度統一的”[18]146,物質生活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人的精神發展也需要循序漸進。現階段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處于目標提出向實踐自覺的轉換時期,精神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精神生產關系的調整與優化、精神生產方式的轉型與升級,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分配、監管等制度的創立完善都需要長期求索。但是,不能因為過程之漫長、道路之艱難就秉持“精神共富虛無論”。道阻且長,但行則將至。推進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場“持久戰”,只有解決好“等不得”與“急不得”的關系,保持歷史耐心,逐步實現黨制定的各階段目標,才能循序漸進,穩中取勝。
其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整體性與差異性相統一的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個總體概念,“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18]142,推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注重整體,也應尊重差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共同”內蘊著破除時空限制的“整體性”智慧,包括人民全體參與、區域整體推進、評價指標統一等多重實踐指向。但是,“整體”不是“整齊”,由于個人內在精神水平與追求不同,外在政策支持、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差異,同時同等同質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具有現實性,而應對之策是要在整體維度達到一定富裕水準后,在合理范圍內允許客觀差距的存在,從而實現差異可控、層次豐富、整體向好的精神生活富裕的理想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