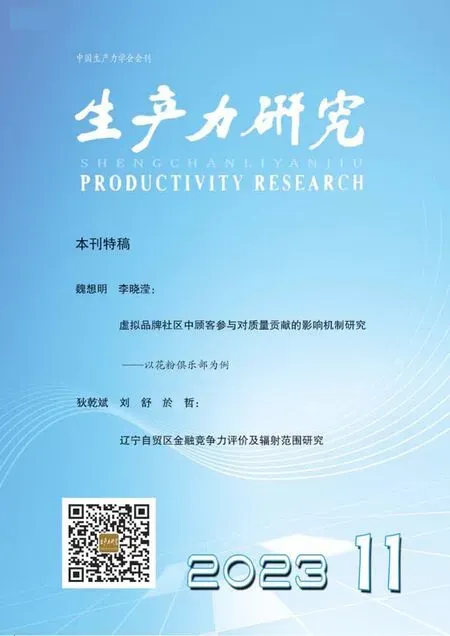社會經(jīng)濟地位、公平感知對城鄉(xiāng)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
——基于CGSS 的數(shù)據(jù)分析
周恩毅,辛敏捷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2.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
一、引言
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得到不斷改善,生活質(zhì)量得到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重視自身的幸福感。心理學家塔爾賓·夏哈爾教授曾經(jīng)說過:幸福是一種感覺,我們是跟著感覺走的,“幸福感”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同時,黨的二十大強調(diào),我們必須堅持在發(fā)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滿足人民群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不斷實現(xiàn)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如何提高居民幸福感已經(jīng)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近年來,學術界就“幸福感”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從影響因素上看,制度層面的政府的行政效率[1]、政策的不確定性[2]、宏觀層面的經(jīng)濟增長[3]、微觀層面的身心健康[4]、社會交往[5]與收入差距[6]等都影響著居民的幸福感。從研究對象上看,陳紅艷(2022)[7]學者發(fā)現(xiàn)老年人的幸福感容易受到社會參與的影響;還有學者發(fā)現(xiàn)教師的幸福感還受到外部環(huán)境以及觀念與情緒的影響[8];此外,針對新時代下的農(nóng)民群體,有人指出住房[9]、人口結(jié)構與家庭資本[10]都影響著他們的幸福感。根據(jù)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研究強調(diào)收入、住房等社會經(jīng)濟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滿足物質(zhì)生活,對社會公平與社會經(jīng)濟地位感知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也逐漸突出。同時,對于城鄉(xiāng)居民來說,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環(huán)境容易造成他們在精神需求認知上的差異,影響他們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與公平感知的程度,進而影響城鄉(xiāng)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換句話說,在社會經(jīng)濟地位與公平感知的影響下,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shù)不一定高于農(nóng)村居民的幸福指數(shù)。因此,本文立足全體居民,利用2021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CGSS2021)的調(diào)查問卷及數(shù)據(jù),采用有序Logistic 回歸模型,從社會經(jīng)濟地位和公平感知兩個維度出發(fā)研究居民的幸福感,并基于城鄉(xiāng)視角分析城鎮(zhèn)居民與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的差異,期望為縮小城鄉(xiāng)差異、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提供重要的理論價值。
二、相關概念及研究假設
(一)社會經(jīng)濟地位與居民幸福感
社會經(jīng)濟地位是人們的收入、教育以及職業(yè)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大多數(shù)學者以收入狀況來衡量人們的經(jīng)濟地位。關于收入與幸福感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經(jīng)濟學家Easterlin 提出的“幸福悖論”理論,即收入增加,但幸福不一定增加。近年來,朱春奎等(2022)[11]通過構建“收入-幸福”模型,研究公共服務獲得感如何影響居民的幸福感,建立了公共服務與居民幸福感之間的連接。張體委(2021)[12]通過對六個省份的調(diào)查分析,發(fā)現(xiàn)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地區(qū)的富裕程度能夠直接影響居民的幸福感,但收入差距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并不明顯。此外,除了收入這一經(jīng)濟指標,社會階層地位也是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另一重要指標。許海平等(2020)[13]基于社會階層認同視角,提出社會階層認同在絕對收入與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之間具有中介作用。趙玉芳等(2019)[14]研究發(fā)現(xiàn)主觀社會階層通過安全感與社會支持影響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基于以上發(fā)現(xiàn),收入水平大概率能夠反映居民的職業(yè)狀況與經(jīng)濟狀況,收入高的人或許有更好的居住條件、更好的物質(zhì)滿足,從而影響他們的幸福感。因此本研究利用收入水平衡量居民的客觀社會經(jīng)濟地位。同時,主觀階層認同也能直接影響居民的幸福感,當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生活的階層高于其他人時,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他們的獲得感,從而提高幸福感。因此,本文利用主觀階層認同來衡量主觀社會經(jīng)濟地位。此外,由于城鄉(xiāng)居民的成長和發(fā)展環(huán)境不一致,收入水平與主觀階層認同也不盡相同,城鄉(xiāng)居民的幸福感大概率是存在差異。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客觀收入對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響,并且客觀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在城鄉(xiāng)居民間可能存在差異。
假設2:主觀階層認同對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響,并且主觀階層認同對幸福感的影響在城鄉(xiāng)居民間可能存在差異。
(二)公平感知與居民幸福感
公平正義,是一種比物質(zhì)成果更高層次的精神追求。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公平正義也就越重要。社會公平感知是人們以自身在社會中所獲得的收入、地位等與他人比較而獲得的一種主觀評價。隨著社會的快速發(fā)展與共同富裕的推進,居民對于社會公平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強。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環(huán)境可以減少居民的思想壓力,促進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與合作,并為社會成員的發(fā)展提供保障。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社會公平對幸福感的影響。徐淑一和陳平(2017)[15]從公平感知視角出發(fā)研究收入與社會地位對幸福感的影響,發(fā)現(xiàn)公平感知對幸福感的影響在日益增長。孫一平(2019)[16]發(fā)現(xiàn)公平感知能夠通過影響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的幸福感從而促進市民化的提高。楊賜然等(2022)[17]發(fā)現(xiàn)醫(yī)療保障水平通過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能夠提高民生滿意度。此外,還有學者聚集于創(chuàng)業(yè)者的幸福感,發(fā)現(xiàn)公平感知能夠通過增強創(chuàng)業(yè)者的外在需求進而促進幸福感的提高[18]。因此,本文從社會公平感知這一重要維度探究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社會公平的感知程度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會從更加積極或消極地參與社會互動中體現(xiàn)出來。當居民感知到的社會公平水平較高時,他們會以積極的態(tài)度參與社會活動,從而可能增強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當居民感知到的社會公平水平較低時,他們可能對社會抱有消極態(tài)度,從而降低他們的主觀幸福感。然而,由于城鄉(xiāng)居民對生活的滿足程度不一致,對社會公平感知程度也就不一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公平感知對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并且公平感知對幸福感的影響在城鄉(xiāng)居民間可能存在差異。
三、數(shù)據(jù)及研究設計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研究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2021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CGSS)的數(shù)據(jù),CGSS 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diào)查與數(shù)據(jù)中心負責執(zhí)行的一項連續(xù)性學術調(diào)查項目,具有權威性與代表性。因此本文采取最新的2021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共有樣本量8 148 份,剔除“不知道”“拒絕回答”與缺失值等樣本后,得到有效樣本3 708 個。
(二)變量說明
1.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是居民主觀幸福感,由于幸福感是一種總體感受,因此將CGSS(2021)調(diào)查問卷的a36 的題目作為研究的因變量,對應的問題是“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共有五個選項: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較幸福以及非常幸福,分別賦值1~5 分,分數(shù)越高代表越幸福。從表1 的樣本分布情況來看,大部分居民認為生活比較幸福,占比為57.96%,認為“非常不幸福”與“比較不幸福”的人群占比比較少,分別為1.02%、4.02%。其中,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明顯高于農(nóng)村居民,城鎮(zhèn)居民認為生活幸福的占比為85.41%,農(nóng)村居民認為生活幸福的占比為80.03%。

表1 居民幸福感、主觀階層認同與公平感知的樣本分布
2.自變量。本文的自變量包括社會經(jīng)濟地位和公平感知。
根據(jù)相關文獻,大多數(shù)研究將社會經(jīng)濟地位維度分為客觀收入評價與主觀階層認同評價,本文也沿用此依據(jù)。具體來說,將調(diào)查問卷中的個人總收入取自然對數(shù)后作為客觀收入的衡量依據(jù);將CGSS(2021)調(diào)查問卷中a43 的題項作為主觀評價的依據(jù),對應的題目是“綜合看來,在目前這個社會上,您本人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屬于”,選項共有5 個層級,分別為下層、中下層、中層、中上層與上層,分別賦值1~5 分,得分越高,層級越高。從表1 的主觀階層認同分布情況來看,有大多數(shù)人認為自己處于中等階層,占比人數(shù)為39.27%。其中,城鎮(zhèn)居民認為自身處于中等階層的人數(shù)占比為45.60%,農(nóng)村居民認為自身處于中等階層的人數(shù)占比為33.87%,并且農(nóng)村居民認為自己身處下層的人數(shù)明顯高于城鎮(zhèn)居民。可見城鄉(xiāng)居民的主觀社會經(jīng)濟地位存在差異。
公平感知變量采用CGSS(2021)調(diào)查問卷中a35的題目,即“總的來說,您認為當今的社會公不公平?”共有五個選項:完全不公平、比較不公平、說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說不公平、比較不公平以及完全公平,分別賦值1~5 分,分數(shù)越高代表越公平。從表1的樣本分布情況來看,認為社會“比較公平”的人數(shù)占比最大,為53.16%。認為社會“完全公平”的人數(shù)占比為8.47%,認為社會“完全不公平”的人數(shù)占比為4.13%。其中,城鎮(zhèn)居民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占比為16.53%,農(nóng)村地區(qū)居民認為社會不公平的占比為18.69%,農(nóng)村居民認為社會不公平的人數(shù)明顯高于城鎮(zhèn)居民,可見城鄉(xiāng)居民在公平感知方面也是存在差異的。
3.控制變量。根據(jù)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年齡、婚姻等人口學特征顯著影響著居民的幸福感,因此,本文選取性別、年齡、戶籍、教育、婚姻狀況、健康狀況與政治面貌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三)描述性分析
在參與調(diào)查的3 708 個居民樣本中,城市居民有1 706 個,農(nóng)村居民有2 002 個。從表2 可以看出,我國居民的幸福感處于中等偏上位置,說明大多數(shù)人能夠從生活中感受到幸福感。此外,身體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也都處于中等水平。從社會經(jīng)濟地位來看,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并且對自身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評價也處于較低階層,說明目前有可能存在社會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等現(xiàn)象。同時,我國居民的公平感知也處于中等位置,這說明社會還有可能存在不公平現(xiàn)象。

表2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tǒng)計
從表3 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幸福感明顯高于農(nóng)村居民,城鎮(zhèn)居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與受教育程度也高于農(nóng)村地區(qū)。從社會經(jīng)濟地位層面來看,城鎮(zhèn)居民的客觀收入水平和主觀階層評價都高于農(nóng)村地區(qū)。從公平感知情況來看,農(nóng)村居民的公平感知略高于城鎮(zhèn)居民。詳細的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tǒng)計如表2、表3 所示。
(四)模型構建
本文的因變量是居民主觀幸福感,屬于有序離散變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t 模型。有序Logit 模型廣泛應用于生物學、經(jīng)濟學以及心理學等領域。本文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hapiness 是被解釋變量即居民幸福感;social-econmic 為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指標,fairness 為公平感知的指標,這兩者都為解釋變量;x1為其他控制變量;εi為隨機擾動項。運用Stata 軟件對五個模型進行分析,結(jié)果如下。
四、實證結(jié)果分析
居民主觀幸福感與控制變量之間的回歸結(jié)果如模型(1)所示。從表4 可以看出,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政治面貌、身體健康狀況以及受教育程度對居民幸福感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但民族與戶籍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

表4 居民幸福感的實證回歸結(jié)果
社會經(jīng)濟地位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回歸結(jié)果如模型(2)所示,在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加入社會經(jīng)濟地位變量。由表4 可以看出,當社會經(jīng)濟地位變量加入時,性別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逐漸降低。同時,個人收入水平對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主觀階層認同對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作用。這說明居民自身的主觀階層認同已經(jīng)超過了收入帶給他們的幸福感,人們已經(jīng)從單純的收入轉(zhuǎn)變?yōu)楦邔哟蔚男睦硇枨髞頋M足自身的幸福感。
公平感知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回歸結(jié)果如模型(3)所示,在控制變量和社會經(jīng)濟地位變量的基礎上加入公平感知變量。由表4 可以看出,在加入公平感知變量后,居民的收入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但主觀階層認同對幸福感的影響仍是積極的,并且公平感知顯著正向影響著居民的幸福感。這說明居民對社會的公平感知越高,他們的幸福感越強。
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戶籍進行控制,研究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與社會經(jīng)濟地位、公平感知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控制變量中的年齡、身體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況均正向影響著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同時,居民的收入水平對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主觀階層認同與社會公平感知對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顯著積極影響。
模型(5)同樣是在模型(3)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戶籍進行控制,研究城鎮(zhèn)居民幸福感與社會經(jīng)濟地位、公平感知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控制變量中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政治面貌與身體健康狀況對城鎮(zhèn)居民幸福感具有積極影響,但是受教育程度對居民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此外,社會經(jīng)濟地位中的收入水平不能顯著影響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而主觀階層認同對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具有顯著影響,同時,公平感知對城鎮(zhèn)居民的影響也是顯著的。這說明隨著社會的進步,城鎮(zhèn)居民更加傾向于自身的階層與社會公平帶給他們的幸福感,單一的收入指標對他們幸福感的影響已經(jīng)大大降低。
從社會經(jīng)濟地位方面來說,客觀收入水平正向影響著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并且從模型(4)和模型(5)發(fā)現(xiàn)城鄉(xiāng)居民間存在著顯著差異。農(nóng)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他們的幸福感越高,但是城鎮(zhèn)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能影響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假設1 成立。同時,主觀階層認同也顯著影響著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并且主觀階層認同對農(nóng)村居民的影響顯著高于城鎮(zhèn)地區(qū),假設2 成立。對農(nóng)村居民來說,主觀階層認同帶給他們的幸福感明顯優(yōu)于收入帶給他們的幸福感,這可能是隨著國家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實施,許多農(nóng)村人口已經(jīng)脫貧,并逐步實現(xiàn)小康的轉(zhuǎn)變,相比絕對收入,他們對階層認同的需求大大提高,大部分居民如果發(fā)現(xiàn)自己的生活相較于同齡人更好的話,他們的幸福感會逐漸上升。此外,農(nóng)村居民與城鎮(zhèn)居民的生活與發(fā)展環(huán)境不一致,可能導致農(nóng)村居民的幸福感受階層認同的程度高于城鎮(zhèn)居民,從而城鄉(xiāng)居民的幸福感在社會經(jīng)濟地位方面產(chǎn)生了差異。
從社會公平感知方面來說,公平感知對居民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居民對社會的公平感知越高,他們的幸福感越強。根據(jù)模型(4)和模型(5)發(fā)現(xiàn),公平感知對農(nóng)村居民與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也存在顯著差異。假設3 成立。城鎮(zhèn)居民的公平感知對幸福感的影響高于農(nóng)村居民,這可能是因為城鎮(zhèn)地區(qū)比農(nóng)村地區(qū)擁有更完善的生產(chǎn)條件,他們受到的社會公平感知的影響程度更強。同時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社會對城鎮(zhèn)戶籍的居民包容度更高,從而使城鄉(xiāng)居民的幸福感在公平感知方面產(chǎn)生差異。
五、結(jié)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jié)論
通過2021 年CGSS 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并運用多元有序Logit 模型來分析社會經(jīng)濟地位、社會公平感知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以及城鄉(xiāng)居民之間的差異,研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
一是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均值為4.010,幸福感整體處于中上水平,說明居民對生活水平普遍滿意。其中,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均數(shù)為4.074,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均數(shù)為3.955,城鎮(zhèn)地區(qū)居民的幸福感略高于農(nóng)村地區(qū),說明城鄉(xiāng)居民對于幸福感的差異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在逐步縮小。
二是社會經(jīng)濟地位維度方面的客觀收入水平與主觀階層認同都顯著影響著居民的幸福感,其中,農(nóng)村居民的收入正向影響著他們的幸福感,而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對幸福感沒有積極影響,同時,農(nóng)村居民的主觀階層認同對幸福感的影響明顯高于城鎮(zhèn)居民,這說明農(nóng)村居民更在意自己在同齡人中的地位以及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從而影響著他們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三是公平感知正向顯著影響著居民的幸福感。這說明公平公正的社會環(huán)境能夠有效增強居民的安全感與歸屬感。社會公平不僅可以為居民創(chuàng)造更多的機會,還能夠調(diào)動居民的生活積極性,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因而居民對社會公平感知程度越高,他們的幸福感越高。同時,城鎮(zhèn)居民的幸福感受公平感知的影響高于農(nóng)村居民,說明公平公正對于農(nóng)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程度已經(jīng)低于城鎮(zhèn)居民。這可能由于城鄉(xiāng)差異的逐步縮小,農(nóng)村居民感受到了比之前更多的社會公平。
(二)政策建議
1.提高社會經(jīng)濟地位,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異。從上文分析發(fā)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地位是影響城鄉(xiāng)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絕對收入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已經(jīng)大大降低,收入的增加不能顯著提升他們的幸福感。因此,在穩(wěn)步推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擴大農(nóng)村人口的收入,為實現(xiàn)他們追求更高層次的需求奠定物質(zhì)基礎。此外,由于主觀階層認同顯著影響著城鄉(xiāng)居民的幸福感,與他人相比自己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越高時,獲得的幸福感就越高。因此,要逐步縮小城鄉(xiāng)的收入差距,完善農(nóng)村居民的社會保障與民生建設,以促進居民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提高。
2.完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營造公正的社會環(huán)境。居民對社會的公平感知是影響幸福感的另一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強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建設,從法律、制度與政策上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huán)境。從上文分析發(fā)現(xiàn),公平感知正向影響著城鄉(xiāng)居民的幸福感,當居民感知到的社會公平程度越高時,他們在經(jīng)濟上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和資源,在政治上能夠獲得更多的民主參與,在社會交往上能夠獲得更多的信任與尊重,因此,為了保障居民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各部門要更新觀念,持續(xù)推動城鄉(xiāng)經(jīng)濟的良性發(fā)展,尤其要立足于農(nóng)村居民、女性群體等相對弱勢人群,努力消除社會中的不公平因素,不斷縮小城鄉(xiāng)差異。同時,相關部門要以人民看得見的方式,重點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為弱勢群體居民創(chuàng)造正義的社會環(huán)境。此外,還要不斷完善農(nóng)村地區(qū)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公共服務資源的投入,使得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的好處能夠普及更多的居民,從而保證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
3.推進民生建設,提高居民整體幸福感。在推進民生建設的同時提升鄉(xiāng)村建設水平,促進醫(yī)療、教育的整體發(fā)展,不斷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數(shù)。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與受教育程度能夠顯著增強居民的幸福感,因此,要加大教育基礎設施的建設,提高居民整體的平均文化程度,幫助農(nóng)村地區(qū)居民提高精神文明生活,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同時,居民要樹立正確的婚姻觀念,倡導婚姻自由,并增強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提高居民婚姻所帶來的幸福感。此外,保持健康的身體狀態(tài)與心理狀態(tài),減輕自身的工作和社會壓力,都能夠提升居民整體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