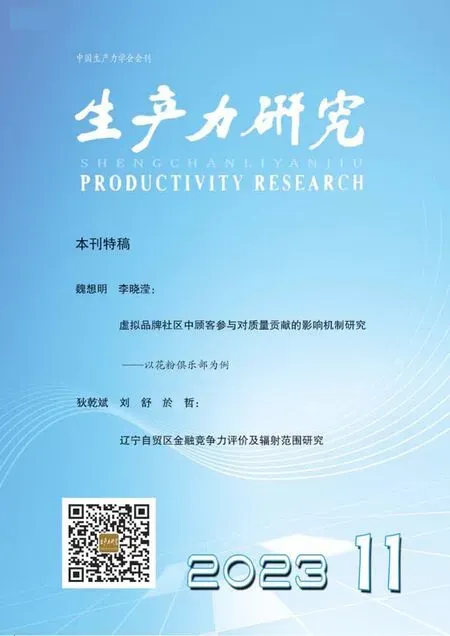數字金融素養對居民金融行為影響機制研究
——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實證分析
潘靜波,吳金旺
(1.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電子商務與新消費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金融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世界經濟數字化轉型大勢所趨,數字金融進程加快,全方位數字化社會經濟形態逐漸形成,并且衍生出相適應的數字金融服務生態,也離不開處于生態中心的居民群體。數字經濟成果逐步顯現,生產者、融資者、投資者、消費者在數字經濟助推下,給產業轉型、企業紓困、信心提振等注入“強心劑”,數字金融及場景應用加速融入經濟生活。在數字化金融生態加速進程中,數字素養和金融素養的共生共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體系、金融體系、科技體系復雜關聯下的實際應用。
數字金融進程加速過程中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其中機構與個人參與者的技術使用水平較低、數字金融場景解決方案不足,引發潛在的發展困境,導致金融服務效率不高、引起金融誠信失范、致使金融共享受限、造成金融倫理失序,繼而使得數字金融發展可持續性受阻。因此,數字經濟的背后需要數字素養和金融素養的共生共融,需要培養提升機構與個人的數字金融素養,以實現數字融合規范化、持續化、健康化發展。數字金融素養是扎根于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發展新需求的一種批判性金融應用素養,包含數字基礎設施、數字金融風險意識、數字金融風險管理能力,以及包括數字金融消費者權責等方面。
基于上述,本文的貢獻在于,嘗試從家庭中的數字金融行為切入,以結構方程探討數字金融素養中不同維度和不同類型的分指標,采用微觀調研數據分析數字金融素養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以探索建立數字金融素養理論框架,以助力金融機構提供高質量供給、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風險決策。
二、文獻綜述
數字金融素養與金融行為影響機制研究來自三條文獻脈絡,并逐步交匯:第一方面是來自經濟學研究,以個人及家庭的金融投資素養為主,這一脈絡發端較早,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不斷取得進展;第二方面是來自心理學研究,主要在財經價值觀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論上有所貢獻,如為經濟心理學在20 世紀80 年代初建立提供了交叉研究的邏輯基礎;第三方面來自教育學研究,關注于“數字素養”概念流變及影響、國外數字經濟政策發展、“數字化”貧困等研究。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數字素養、數字金融概念發展,數字素養指標體系以及金融素養對家庭金融行為的影響研究。
(一)概念演變
以色列學者Yoram Eshet-Alkalai(1994)提出認可度“數字素養”概念框架,隨后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對數字素養都有界定,雖然有不同側重,但是包括了從基礎到高級技術技能,在批判中注重實用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數字素養定義為以就業為導向,能安全使用數字技術且合適手段獲取、運用和評價的綜合能力。隨著數字金融對家庭社會的深入影響,數字素養和金融素養逐漸匯合,以適應經濟體系、金融體系、科技體系復雜關聯下的實際應用,徐玲玲(2020)[1]提出了數字金融素養概念(Digital Financial Literary),并強調了概念中“數字背景”和“數字工具”的重要性。
(二)應用研究
數字素養的應用研究以數字素養指標建立,并且在教育技術學領域推廣為主。各國都非常重視數字素養框架開發及評估應用,較為權威的框架體系涉及《歐盟數字素養框架DigComp2.0》(2017,歐盟)、《2017 數字素養影響研究報告》(2017,美國新媒體聯盟)、《全球數字素養框架》(2018,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盟數字素養框架包括概念映射、案例分析、專家咨詢、研討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框架是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應用映射、在線咨詢,美國新媒體聯盟提供的數字素養框架采用了案例分析、專家訪談和受眾研究調查等步驟,與前兩者不同的是,創新過程中建立了模型和分析,運用于教育政策制定和個人教育賦權,兼顧了應用性、可操作性(任友群等,2014)[2]。因此,數字素養指標構建技術較為成熟,但是應用研究與金融語境存在著一定割裂,缺乏與數字化實際應用場景結合,并且采用的背景和方法在指標及框架制定方面應該考慮到不同發展水平地域及國家。
(三)素養與金融行為研究
數字素養對家庭金融行為影響研究圍繞著金融素養展開,數字因素作為金融素養的技術因素。國內學者尹志超等(2014)[3]關注金融素養對家庭資產配置行為的影響,曾志耕等(2015)[4]認為金融素養可以促使居民投資組合分散化,吳衛星等(2018)[5]指出金融素養會影響居民家庭理財需求。周雨晴和何廣文(2020)[6]實證研究發現當農戶金融素養或智能化素養更高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市場參與度和金融資產配置行為影響更為強烈。對于金融行為應用研究的關注廣泛運用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主要來自金融社會工作者或者是關注家庭金融實踐問題的學者,在后續研究中還要對傳統理論“理性人”假設進行修正,在應用研究需要更多地完善以人的心理、行為視角的學科研究方法。
綜上,從文獻上來看:一是從三個學科發展脈絡分散,形成各自相對獨立的研究,研究多停留在數字素養或是金融素養框架體系和教育模式;二是對數字金融素養外延和內在的認識沒有突破,缺乏適應我國具體國情的理論建構,沒有充分重視實證分析以及框架構建后的評價研究;三是缺乏使用家庭微觀數據研究數字素養在各類場景中的運用,例如居民普遍金融投資的行為、產業鏈深化中金融服務、城市數字金融生態的影響研究。因此,本文通過理論分析研究探討數字金融素養中不同維度和不同類型的分指標,以及通過微觀調研數據分析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
三、模型構建與研究假設
(一)模型構建
數字金融素養是扎根于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發展新需求的一種批判性金融應用素養。因此分析居民金融行為,不僅僅包括對數字科技、數字產業、數字經濟的認知、理解和應用,更包括金融場景深入、金融行為及決策的影響改變。
鑒于多維評價指標和相關關聯,本研究選取結構方程模型,實現因子分析和路徑分析,測量各因素內部結構及相關之間的關系情況,也可以發現隱形關聯的概念關系。
本文的初始模型,包括結構模型和測量模型,關鍵在于構建結構模型來發現全體潛變量。本研究從數字素養、金融行為兩個維度選擇潛變量。從數字技術角度來看,文獻顯示數字素養有兩個主要方面,即“能力”和“知識”。任友群等(2014)[2]列出歐盟數字素養框架的21 個具體素養,涉及知識、技能與態度;楊爽和周志強(2019)[7]借鑒新媒體聯盟中數字素養研究提出了數字能力;汪凡(2018)[8]在建立評價體系時,認為數字安全、數字健康、數字倫理也是數字公民構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一共設置了5個數字素養維度: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從金融行為角度來看,選取了金融投資意愿、金融消費意愿、信貸意愿3 個意愿行為方向,構成研究的8 個潛變量。因此本文構建出如圖1 所示的初始結構方程模型(SEM 模型),并且通過因子分析確立最終的SEM 模型。

圖1 初始SEM 模型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1.數字素養對金融投資意愿假設。H1:數字意識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2:數字知識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3:數字行為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4:數字能力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5:數字價值觀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2.數字素養對金融消費意愿假設。H6:數字意識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7:數字知識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8:數字行為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9:數字能力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10:數字價值觀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3.數字素養對金融信貸意愿假設。H11:數字意識對金融信貸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12:數字知識對金融信貸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13:數字行為對金融信貸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14:數字能力對金融信貸意愿具有正向影響;H15:數字價值觀對金融信貸意愿具有正向影響。
四、實證模型構建
(一)量表設計與調查
本文對金融行為的測量,在測量方法的設置上,使用5 點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測量被試行為出現的可能性,本質上是用行為意愿預測行為的一種測量方法。
本文自2022 年8 月~12 月期間,通過問卷調研形式共收集浙江地區有效樣本307 份,分別從職業、受教育程度、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已有負債、婚姻狀況等方面對被調查者基本情況進行分析。
(二)信度和效度分析
首先進行自變量信度分析、因變量信度分析、自變量因子分析、因變量因子分析。采用克朗巴哈信度系數來檢查一致性。本研究因素包含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測量結果顯示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的系數大于0.7,分別為0.873、0.887、0.851、0.849、0.814,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因變量金融投資意愿、金融消費意愿、信貸意愿的克朗巴哈系數均大于0.7 的標準,同樣具有一致性信度(見表1、表2)。

表1 自變量信度分析

表2 因變量信度分析
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進行效度檢驗,其中自變量因子分析顯示結果顯著,KMO 大于0.7,Bartlett's球形檢驗值顯著(見表3),表明問卷數據符合因子分析要求,可以采用主成分法進行分析。數據及因素分析顯示,總解釋能力達到了66.977%,大于50%,檢驗結果良好效度下,遴選出5 個具有代表的因子。并且在表4 自變量因子分析中觀察加粗數字組,可以看到每個因子中不同潛變量的重要程度。

表3 自變量檢驗

表4 自變量因子分析結果

表5 因變量KMO and Bartlett's 檢驗

表6 因變量因子分析結果
因變量因子分析可得到檢驗值顯著,同上述,因子提取時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因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進行因素分析。
(三)自變量驗證,性因子分析
自變量驗證性因素分析分別為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23 道測量題,因素分析后得到表7,從數據顯示模型具備較好的配適度。

表7 自變量驗證性因素模型擬合度
由表8 可知,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的各個測量指標從標準化因素負荷、組成信度(CR)、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來看各個變量收斂效度良好。

表8 自變量因子分析結果
(四)因變量驗證性因素分析
因變量驗證性因素分析共有3 個維度,分別為金融投資意愿、金融消費意愿、信貸意愿,共包含17個測量題目,驗證性因素分析后,得到表9。

表9 因變量驗證性因素模型擬合度
由表9 可知CMIN/DF 為1.118,小于3 以下標準,AGFI、GFI、TLI、IFI、CFI 均達到0.9 以上的標準,RMR為0.041,小于0.08,RMSEA 為0.02 小于0.08,選擇的模型較為合適。
由表10 可知,從金融投資意愿、金融消費意愿、信貸意愿的各個測量指標標準化因素負荷衡、組成信度(CR)、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來看,收斂效度較為理想。

表10 因變量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五)區別效度
本文采用AVE 法對區別效度評估,結果均大于對角線外的標準化相關系數,如表11 所示。

表11 區別效度
五、數據分析與結果
利用AMOS 23.0 執行計算,使用最大似然法進行估計,結果如圖2 所示。

圖2 SEM 模型圖
(一)模型擬合度檢驗
從表12 可知CMIN/DF 為1.07,小于3 以下標準,GFI、AGFI 統計值分別為0.893、0.878,大于0.8,在可接受范圍內,TLI、IFI、CFI 均達到0.9 以上的標準,RMR 為0.051,小于0.08,RMSEA 為0.015,小于0.08,達到較好的配適度。

表12 模型擬合度檢驗結果
(二)假設檢驗
由表13 可見,數字意識對金融投資意愿不具顯著正向影響,假設不成立;數字知識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行為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能力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價值觀對金融投資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

表13 路徑系數
數字意識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知識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行為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能力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價值觀對金融消費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
數字意識對信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知識對信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行為對信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能力對信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數字價值觀對信貸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成立。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數字素養對金融行為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將數字素養分成5 個維度進行,包括數字意識、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數字價值觀,皆對金融行為有顯著影響。數字意識維度,培養居民對數字保持好奇心、重視信息檢索、具有風險防范意識;數字知識維度,從普及信息產生管理、金融科技原理、數字信息工具、平臺網站及軟件等角度展開科普活動或者投資者教育;數字行為維度,可通過數字信息案例展示、組織團隊活動、開展項目合作等方式提高金融行為意愿;數字能力維度,可通過建立數字金融信息評價指標、金融機構組織專項投資者教育活動來改善和促進;數字價值觀維度,政府建立數字治理生態,形成數字安全法則保障金融行為意愿有效持續。
2.數字意識及價值觀對金融行為分化顯著。數字意識對金融投資不具備顯著影響,假設不成立,相較金融消費、信貸行為,數字價值觀及意識則呈現非常顯著影響。數字意識屬于數字素養中較為初級階段,金融投資行為相較消費、信貸,專業知識、能力技巧更強,因此從數字意識到金融投資行為意愿改善上還需要創設場景、行為推動,在數字知識、數字行為、數字能力、價值觀上進行發力。對于不同的金融行為,需要從不同維度進行推進和引導實現。
3.數字素養對金融消費、信貸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數字素養對金融消費、信貸行為皆有顯著正向影響,我們認為,居民金融消費、信貸需求較大,同時數字素養的結合和運用基礎較好。因此在激發、引導居民的高質量消費、高質量發展中,可結合數字素養五個維度進行推進。
4.數字素養與金融行為具有指標構建可行性。數字素養與金融行為之間關系緊密,本文建立的指標體系為數字素養、金融素養融合提供了指標體系融合嘗試,通過結構方程建立了擬合度、信度、效度較高的指標模型,為后期開展數字金融素養研究做好了基礎鋪墊。
居民的數字素養水平會直接關系到享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同時影響金融素養水平。一方面,借助數字渠道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觸到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并且在實踐中促進自身金融素養的提升;另一方面,消費者基礎金融知識與數字技能和信心不足會成為普惠金融發展的約束。
(二)建議
1.促使數字金融素養共識形成。推動數字金融素養理論研究,改善金融體系信息挖掘和應用,消除數字對家庭金融行為、產業數字融合、數字金融服務的排斥(潘靜波和郭福春,2022)[9]。數字技術與金融場景數字,金融素養概念興起于技術背景,發展于金融場景。隨著數字金融對家庭社會的深入影響,數字素養和金融素養逐漸匯合,以適應經濟體系、金融體系、科技體系復雜關聯下的實際應用,數字金融素養概念提出適應了時代背景(鄒靜和鄧曉軍,2022)[10]。因此,我們需要在數字素養、金融素養基礎上豐富內涵,可進一步提出居民的數字金融素養概念。促進金融機構科技化、互聯網化,助力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風險決策,支持和完善數字金融運行機制,促使中國經濟中“存量”的數字化轉型步伐,尤其是在激發家庭金融消費、優化投資和信貸行為方面(陳瑾瑜和羅荷花,2022)[11],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2.構建金融行為中數字素養指標體系。加強數字金融素養實務應用研究,借鑒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歐盟、美國新媒體聯盟指標體系,結合地區金融場景和發展實際加快推進數字金融素養核心指標要素等,關注數字技術對金融素養的影響,以及探索金融教育數字化創新等實踐性研究。
3.培養多元包容的數字金融教育觀。數字化時代到來體現金融素養的新維度、新領域(李東榮,2020)[12],國家推進投資者教育,可以通過產學研聯動,在金融機構、高教等投教機構等組織數字金融素養的普惠金融活動、金融知識普及,促使居民金融消費、投資、信貸活動中的數字金融素養提升,完善數字金融治理,維護數字金融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