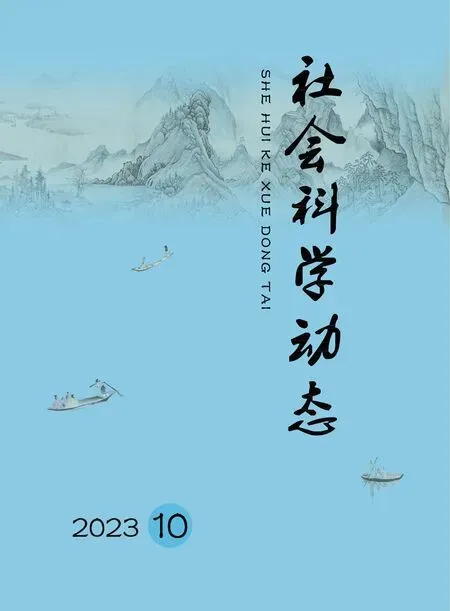荒政史的研究方法與思路
——以《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研究》為中心
李 軍 張晏齊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安是最大的責任。“防災減災救災事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是衡量執政黨領導力、檢驗政府執行力、評判國家動員力、體現民族凝聚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在與自然災害艱苦卓絕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形成了獨特的荒政體系,保障了農耕文明的綿延不絕。
20 世紀初,現代意義上對災荒的研究專著開始出現,其中具有開創之功的就是鄧拓先生的《中國救荒史》,該書的研究深刻影響了后來學者的研究思路。進入21 世紀以來,學術界對災害史的研究進一步深化,以李文海、夏明方為代表的荒政史研究者編撰成《中國荒政書集成》收錄了187 種歷史上的荒政文獻,反映了中國歷史上的救荒思想與實踐。同時,這一階段災荒史原有的學科界限也被打破,自然科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充分交叉聯合,大大推進了災害史研究的新局面。
賑貸制度是中國救災體系中一項極為特殊的救荒措施。它具有顯著的金融色彩,即國家并非無償提供恩惠性的施舍,而是存在“借貸—償還”的約束關系;此外,它又顯示了國家承擔的道義責任,以國家與農民道義關系下的信用做支撐,這種“借貸—償還”關系往往是有彈性的,甚至虛化的,不能簡單地將農村金融中的市場定價、借貸利息、違約追責等邏輯套用在賑貸制度中。以往諸多關于救災制度的研究都有不少內容涉及賑貸制度,這其中既有利用歷史文本資料對賑貸制度實施細節的還原,也有從經濟視角對賑貸制度運行邏輯開展的分析,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指向了不同的研究視野,但聚焦于賑貸制度本身的研究直至21 世紀初才出現,相關研究仍存在眾多有待完善之處。202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楊乙丹教授的新著《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研究》,是做到還原實然狀態與闡釋理論維度有機結合的典型著作,系統闡述了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的早期實踐、歷史演進、道義邏輯、多元實踐、制度創新和運行悖論,相當程度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若干空白。
一、嚴謹細致的史學考證
被譽為近代歷史學之父的利奧波德·馮·蘭克認為:“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些事實或許是偶然的和枯燥無味的——無疑地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則。”①歷史學的首要任務就是通過史料重構歷史事實,經濟史自不例外。吳承明在評價經濟史研究方法時指出:“史料考證是治史之本,實證主義不可須臾或離。”②該著做到了言之有據,通過豐富的史料、嚴謹詳實的考證推動了古代賑貸制度的研究,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用豐富的史料還原歷史本原。該著對先秦文獻、歷代官修正史、會要和典章、皇家編年資料、歷朝荒政書籍均有涉獵,還關注到類書、文人札記、地方志等文獻。此外,還使用了王國維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將發掘的出土文物和傳世文獻的記載相互驗證,所使用的出土文獻包括睡虎地秦墓竹簡、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居延漢簡等一系列重要史料,涉及的考古遺址和文物包括河南偃師商城遺址出土的20 余座國家糧倉、四川德陽黃滸鎮蔣家坪出土的漢代乞貸畫像磚等。這種對于歷史資料和歷史場域的扎實使用,為還原古代賑貸制度的面貌提供了可信的依據。
二是重新梳理了賑貸制度的早期源流。該著通過對先秦文獻的嚴謹考證,將災荒賑貸制度的誕生界定為商末周初周文王推行的“農假貸”和“散利”政策,這不同于之前“中國農貸制度肇始于周代泉府”的觀點③,使學術界對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或農貸制度的源流有了重新認識。
三是明確了賑貸制度的制度內涵。該著區分了古代荒政體系中的賑給、賑糶與賑貸,對三者的救助對象、運行機制、設計初衷和各自優勢進行了詳細介紹,在比較視角中討論了中國古代賑貸制度的內涵。書中總結了賑貸制度“資東作”的生產功能、“裕生機”的維生功能、“抑倍息”的經濟功能和“弭盜賊”的社會功能,并對賑貸制度的救助對象、時限要求、數量限制、非營利性和債務關系軟約束等內在規定進行了介紹。
四是展示了賑貸制度的演進歷程。該著詳細分析了周代賑貸制度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進程,分區域整理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賑貸行動,通過對賑貸制度源流的梳理,為我們更好理解后世災荒賑貸制度的運行奠定了基礎。同時緊緊抓住備荒倉儲和官倉相剝離這條主線,對中國荒政史中賑貸制度的變遷開展研究。作者認為,在專門的備荒倉儲出現之前,救荒主要依賴于諸色官倉,隨著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隋唐以后逐步形成了太倉、轉運倉、正倉、軍倉、常平倉和義倉“六位一體”的倉儲體系。其中常平倉和義倉專門用于災荒賑濟,承擔了主要的救災職能,成為賑貸所需糧食的主要來源。備荒倉儲的誕生標志著我國賑貸制度的專業化,也更具備科學分布的空間優勢和迅速反應的時間優勢。
二、“社會科學化”的經濟分析
吳承明認為:“經濟史學是經濟學與歷史學兩者的邊緣學科,研究者要有歷史學修養,又要有經濟學根柢。”④當前,不少研究者將視野定格在運用經濟邏輯解釋歷史事件,并以歷史事件闡釋經濟理論,眾多成果得到國際主流經濟學期刊的認可。比如陳碩教授與曹一鳴博士發表于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的論文《運河上的叛亂:1650—1911 年中國貿易通道中斷與社會沖突》⑤以及Maria Waldinger 發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的《長期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來自小冰河期的證據》⑥。這些學術成果的出現標志著對經濟史的考察越來越需要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和更廣闊的學術視野。
《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研究》一書,在對我國古代的賑貸制度進行嚴肅分析的過程中同樣使用了多學科視角融合方法。在我國傳統的荒政中,比較典型的救災行動包括賑給、賑貸和賑糶三類,三者各有獨特的作用。相比于賑濟和賑糶,賑貸代表著以國家為主體的社會救災力量對農民提供“貸款”服務,這無疑是一種經濟行為,需要運用經濟學中關于信貸關系的諸多理論對其進行解釋。該著采用大量的經濟理論以推演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運行結構和演變機制,并多角度地解讀了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的運行悖論。在對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的具體運行結構進行分析時,通過放貸政策、放貸利息、支撐機制等觀察視角,做到了將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歷史時期災荒賑貸的豐富史實相結合,融二者研究之長,避各自研究之短。在分析古代賑貸制度的社會價值時,作者不局限于“活民”這個命題,而是敏銳捕捉到賑貸同臨災賑給的不同之處——“資東作”,也即賑貸的對象是有一定生產能力的貧民,核心目的是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從而實現社會總財富的增加。此外,還提出國家的賑貸可以對民間高利貸進行打擊。著名經濟學家理查德·托尼認為,中國小農家庭負債甚至破產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廉價的信用借款渠道。⑦而賑貸顯然可以起到救助貧困小農、維護小農家庭農業的延續、推動鄉村社會經濟秩序穩定發展的作用。
在分析古代賑貸制度的制度創新和運行悖論時,該著保持了一個宏大的視野,并未簡單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我國的賑貸舉措,而是選取了新莽時期國營普惠金融擠壓民間高利貸、隋唐義倉對巨災導向型賑貸模式的矯正、北宋青苗法以“半市場、半道義”的信用機制對傳統災荒賑貸制度的改造、南宋社倉“官倡民營”的底層賑貸實踐、明代周忱通過賦役制度改革實踐將稅基培育和災荒賑貸有機結合等典型案例進行分析。作者認為:上述事例“均可看作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的典型創新”⑧。在肯定這些舉措意義的同時也指出,盡管賑貸制度具有很強的功能面向,但同樣受經濟規律的束縛,頻繁出現了“最需要錢的人最貸不到錢”“名義上是救助性的放貸,實際上卻是高利貸”“需要得到借貸的時候卻得不到”等悖論和周期性的興衰循環。此外,該著還詳細考察了國家、地方和農民等不同主體的利益結構,對制度鏈條拉長、精細化管理陷阱、國家災荒賑貸責任轉嫁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觀點。通過解釋古代賑貸制度中所反映出來的管理成本上升、尋租困境等問題,為當前經濟學理論找出了相關的實證依據。
三、從道義關系出發的另類解釋
從20 世紀初開始,歷史學開始受到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挑戰和洗禮,經歷了一個“社會科學化”的過程⑨,史學界推陳出新,產生了不少新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越來越重視對整個社會作綜合描述,如德國的卡爾·蘭普雷希特、美國的“新史學”學派、法國的“年鑒學派”等,都是這一趨勢的重要代表。歷史學不再滿足單純地核實史料、敘述事實,而是希望對歷史的演變及其背后的邏輯做出綜合解釋,因此學科融合、多重視野成為史學發展重要的新趨勢。
在歷史學“社會科學化”的潮流中,經濟史研究也更需要多學科、多視野的大歷史格局,才能從紛繁的歷史細節和高深的經濟理論中撥開迷霧。吳承明在《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一書中介紹了經濟學理論、社會學理論、計量分析和區域分析對于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可見對經濟史的研究不僅需要經濟學和歷史學的融合,還需要注意非經濟因素,認識到“經濟發展——制度改革——社會變遷,在最高層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⑩。
以往有關古代災荒賑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災荒史領域,理論的使用相對不足。實際上,賑貸不是純粹的經濟活動,而是兼具社會收益、文化傳統和政治目標的制度設計,不能用單純的經濟行為和經濟規律簡單視之,其中道德作為一種外部因素就深刻影響了賑貸制度設計。英國學者E·湯普森是道義經濟學的先驅,他在解釋18 世紀英國社會爆發的食物騷動現象時就認為:社會規范、義務和傳統觀念都是貧民發動食物騷動的直接行動契機。?詹姆斯·C·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中也探討了東南亞農民的生存倫理對于其經濟活動具有重要意義。?而楊乙丹教授吸取了上述學者對道義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以傳統農業社會國家與農民的獨特道義關系和仁義價值理念來統攝災荒賑貸制度的分析,綜合運用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等視角,不僅將賑貸置于農村金融或政策性農貸的視角下解讀,視其為一般的經濟活動,分析其經濟關系、經濟規律,更是從道義關系出發對其運行實踐、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等社會制度層面展開全面考察,理論上沖破了“經濟決定論”的束縛,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觀察賑貸制度的全貌。該著認為,道義制度對賑貸制度有以下影響:
第一,道義制度對賑貸制度的設計產生了深刻影響。“資東作”“裕生機”等功能設計,“有田無力耕者”的放貸對象,不以取息盈利為目標和“非責以必償”的價值約束,均受制于道義制度。該著解釋了“父愛主義”的主流倫理價值觀、儒家“仁政”執政理念、“重農”發展理念、“民貴君輕”觀、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和平息“天怒”等道德束縛在賑貸制度產生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在中國歷史上災荒賑貸屬于典型的道義制度安排,因此才形成了以貧困民戶為放貸對象、不以取息盈利為目的、“非責以必償”等內在規定,以及經常性地實施勸借、倚閣和蠲貸政策。
第二,道義關系不僅影響了賑貸的制度設計,同時也是賑貸制度最終背離設計初衷的重要原因。作者剖析了“賑債蠲緩的道義虛化”和“道義自覺的個體化危機”兩個賑貸制度運行過程中的重要傾向,將此與“災賑制度發展的精細化陷阱”“國家災荒賑貸責任轉嫁”一同視為古代災荒賑貸制度運行悖論原因的四個層次。這些倫理困境導致了災荒賑貸制度應該遵循的內在約束在運行中屢屢遭到突破。
四、結論
吳承明先生關于經濟學與經濟史的“源流之說”清楚詮釋了兩者的辯證關系,即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頭,而不只是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分支?,對經濟史的研究極具指導意義。作為經濟學之源,一部良好的經濟史作品無疑起到了思想實驗的重要作用。楊乙丹教授從賑貸這一特殊的救災制度出發,對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的起源、發展與社會功效,及其悖論、陷阱、道義虛化、個體化危機等弊端進行了梳理、考辨,不僅可以填補學界對賑貸制度的研究空白,也對當前的許多理論起到了補充說明的作用,并對推進當代建立完善的災害治理體系有極大地資鑒價值。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災荒賑貸制度研究》一書是建立在作者長期對賑貸制度長時段觀察的基礎上的。早在2010 年,作者就發表《組織結構演進、利益分化與傳統國家農貸的目標偏離》一文,探討農貸政策在地方官員的尋租行為下出現的目標偏離。?此后,其關注點逐步從農貸聚焦于賑貸,探討了宋代、明代等朝的賑貸制度,并關注到賑貸制度背后的道義色彩。?正是10 余年對賑貸制度持之以恒的關注,才最終形成這樣一本條理清楚、觀點明確、邏輯性強、具有理論思辨能力的研究成果。
當然,從來沒有盡善盡美的作品,人類的認識從來都是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學術界對賑貸制度的認識也依然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例如,歷史時期災荒賑貸制度總是因時因地而變,所謂道義色彩在不同的地區往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對于這些可能出現的區域差異,仍有待學界進行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