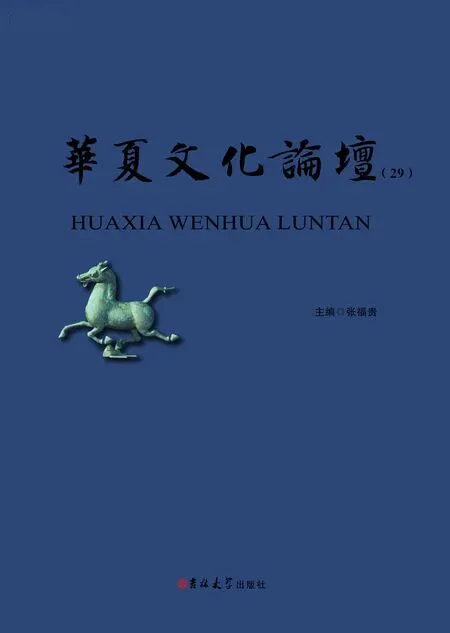《汗簡》古文札記四則
薄路萍
【內容提要】北宋初年郭忠恕所作《汗簡》,是集錄當時所見篆體古文的書籍。這類篆體古文來源龐雜,時代上以戰國文字為主,但又夾雜著部分中古俗字。其中“華”字古文作,是“華”字省艸俗寫,與“幸”同形,篆文據“幸”回改而成。“遵”字古文作,當是“尊”古文字形體的訛變,“尊”“遵”音近借用。“列”字古文,是利用篆文構件拼合而成,為中古時期“列”“(刟)”二字形混不別而導致的誤用。“遐”字古文,疑是據中古時期“嘏”的省變形體“ ”回改而成的篆文。
以上諸說似都有未妥之處。查《華山碑》釋文共有五處作“華”者,四明本有一處殘,額篆作,隸作、(《北圖》1/125-126)等形,與山和地名有關,皆從山。故鄭珍認為屮部“華”字改艸從屮,不可信。其又于山部曰:“漢《華山碑》書‘華’作‘’,知隸變‘艸’為‘山’。”③[清]鄭珍:《汗簡箋正》,王瑛、袁本良點校:《鄭珍集·小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13-814頁。可見鄭氏僅依部首說解,不明其形。李春桃先生據《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認為“”是漢代從屮之“華”古文字形體的異體訛變。但從馬王堆帛書原圖看,《字形表》的摹寫有些失真④參看[德]陶安、陳劍:《〈奏讞書〉校讀札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09頁。“華”上從三個“屮”,其中三個“屮”形作“品”字形配置和作兩個在上一個在下的都有。,且帛書古文字形體與古文形體差別較大,此說亦不可從。
諸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太帝之上。……而孟康、服虔注本皆云“望幸”下有“華”字,而摯虞《流別集》則唯云“望幸”,當是也,于義易通。直以后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似“華”字,因疑惑,遂定“華”字,使之誤也。⑤[漢]司馬遷:《史記》(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693頁。
虞世南《北堂書鈔》所見本作“梁父設壇場望華蓋號以況榮”,并案云:
《史記·司馬相如傳》“華”誤“幸”,“祝”作“況”。《索隱》云: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此則與舊鈔吻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與《史記》同。⑥(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第342頁。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
《司馬相如傳》曰:“泰山梁父設壇場望華蓋。”劉歆《遂初賦》:“奉華蓋于地側。”《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曰:“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⑦[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40頁。
“幸”“華”異文相出,其原因正是司馬貞《索隱》所言“‘幸’似‘華’字”。同時古文系統內部也可提供更為直接的證據,如“斁”在《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古文形體分別作:
兩古文來源相同,當為一字。其中《汗簡》古文右下“幸”已與“樺”字古文“”(四4/33·籀韻)右下“”①關于“”字,詳參李桂森、劉洪濤:《釋“華”及相關諸字》,《出土文獻》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第163-169頁。訛同。
俗字中也有“幸”“華”相訛的現象。唐時敦煌手寫文獻中“華”出現俗寫省艸形,如:
底卷中的手書皆為“華”字的俗寫形式,諸形與“幸”字的俗寫(《維摩詰經講經文》斯3872)、(《佛說阿彌陀佛經講經文》伯2931)、(《佛說阿彌陀佛經講經文》斯6511)、(《葉凈能詩》斯6836)、(報字所從,《雙恩記》俄96)等基本不別。其中例(1)“色”在《敦煌變文校注》中寫作“幸色”②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827頁。,曾良先生指出:“‘幸色’無解,顯然當作‘色’,即華色,言大圣呵呵而笑,面色如花。今猶語‘如花的笑臉’,即此指。”③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59-160頁。例(2)(3)在《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校注》中皆寫作“幸”,用作“華”。④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47頁;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79頁。例(4),《敦煌變文校注》曰:“原卷‘’,即‘華’俗字‘’的省旁字。白錄、潘錄皆作‘幸’,不確。”⑤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944頁。可見唐時“華”“幸”俗寫相訛的情況非常普遍,要辨識其為何字,需借助所在辭例與語境。另,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朝鮮活字本六臣注《文選·封禪文》作“望”,“”既與“華”俗寫“”(省艸)形相近,又與司馬貞所言“幸”似“華”字情況一致。
至郭忠恕作《汗簡》時,應是見到了“華”字省艸俗變作“幸”形者,因郭氏已不明其形體結構和來源,誤將其當成古文。以其上“十”為“屮”,歸入屮部。屮下部形體因與“辛”“辟”“?”等古文所從極為相似,便采用類化的方式來變換古文形體⑥參看李春桃:《古文異體關系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6頁。,作“”形。古文中像“華”字這樣據隸楷俗書回改篆文的情況并不少見。①參看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魏宜輝:《傳抄古文研究(五題)》,《漢語言文字研究》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7-89頁;孫超杰:《隸定古文相關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2022年,第63-73頁。如下文“遐”字據“ ”回改篆文的情況;再如《古文四聲韻》中“被”古文“(四3/4)”“(四4/4)”,其左旁所從“示”是“衣”旁的形近寫訛,古文寫成從示作,顯然是據已誤的楷書形體回改而成的篆文。②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23頁。
《汗簡》中“遵”字古文作:
故古文應為“尊”字。此處借“尊”表“遵”,傳世文獻中常見。如《論語·堯曰》:“尊五美屏四惡。”《隸釋》卷三《蔣君碑》作:“遵五迸四。”《后漢書·光武紀上》:“擊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李注:“遵或作尊。”②更多相通例證參看王海根:《古代漢語通假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0頁。
《汗簡》中“列”字古文作:
《汗簡》中“遐”字古文作:
“叚”字古文又有從“攴”者,如:
《玉篇·言部》:“諧,胡階反。”
《篆隸萬象名義·言部》:“諧,朝階反。”
殘本《玉篇·言部》:“話,胡快反。”
《篆隸萬象名義·言部》:“話,朝快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