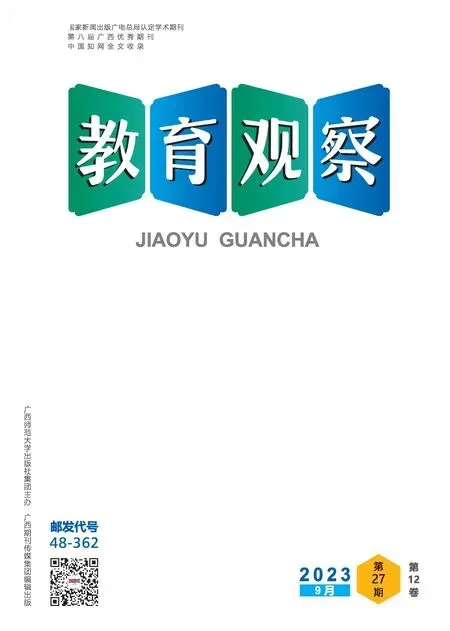國內原創繪本的圖文關系及閱讀指導建議
——基于會話含義理論視角
趙小彤,襲祥榮
(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山東濟南,250014)
一、引言
繪本,也稱圖畫書,英文稱為“Picture Book”,是以豐富的圖像語言來傳達思想的書籍藝術形式。[1]日本繪本之父松居直將圖畫書定義為“圖畫書=文×圖”。[2]兒童文學作家彭懿在《圖畫書:閱讀與經典》一書中指出:“圖畫書是用圖畫與文字共同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是圖文合奏。”[3]由此觀之,圖畫并不是文字的附屬品,自身也具備傳遞信息的作用。繪本中簡單易懂的文字與色彩明快的圖畫相互呼應,形成完美的合奏,契合兒童認知水平和直觀形象的思維特點,能夠有效激發其閱讀興趣,推動其全面和諧發展。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到繪本對兒童語言發展、社會性發展、認知發展等方面的重要價值,但繪本閱讀過程中存在的幼兒處于被動狀態、成人閱讀指導水平不高等問題也不容忽視。[4-5]兒童單純“看”繪本或單純“聽”繪本的現象,都難以讓兒童同時把握文字信息和圖像信息,進而實現繪本高質量閱讀。基于此,本文基于語用學中的會話含義理論,通過對國內優秀原創繪本會話含義進行語用推導,分析國內優秀原創繪本中的圖文關系,以期為繪本的高質量閱讀指導提供建議。
二、會話含義理論概述
會話含義理論是語用學的三大奠基理論之一,由格萊斯提出。他認為,在所有的語言交際活動中,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存在一種約定俗成的默契。[6]換句話說,雙方都應該遵守一套基本原則,再結合語言的使用,從而達到交際的目的。之后,列文森將其與阿特拉斯共同提出的信息原則和荷恩提出的兩原則結合起來,建構了會話含義的三原則推導機制和中介;三原則分別為數量原則、信息原則和方式原則,每個原則都包括說話人準則和聽話人推論兩部分。[7-8]
(一)數量原則
在數量原則方面,說話人準則是指不要讓說話人的陳述在信息上弱于說話人知道的程度,除非說話人的陳述與信息原則相抵觸;聽話人推論是指相信說話人提供的已經是對方所知道的最強的信息。[6]例如,朋友問小明幾點了,小明看了看手表后回答:“快七點了。”這樣的回答雖然是小明通過看手表而說出的真實的信息,但卻違背了數量原則,因為小明并沒有將已知信息充分說出。因此,遵循數量原則要求說話人最大限度地表述自己已知的真實信息。
(二)信息原則
信息原則中的說話人準則強調極小量準則,即只提供實現交際目的所需的最少的語言信息(注意數量原則);聽話人推論則關注擴展規則,即擴展說話人話語信息的內容,直到認定說話人的真正意圖為止。[6]例如,朋友問小明的媽媽:“小明在家嗎?”因為語境中的兩人都熟知如果小明在家便不會出去玩的事實,那么小明的媽媽就可以遵循信息原則,直接回答:“小明出去玩了。”由此可見,遵循信息原則是在對話雙方均理解的常規語境下,說話人向聽話人提供簡潔明了、清楚達意的語言信息。
(三)方式原則
方式原則中的說話人準則指不要無故用冗長、隱晦或有標記的表達形式;聽話人推論指如果說話人用了一個冗長的或有標記的表達形式,就要用無標記的表達形式表達不同的意思。[6]通俗來講,就是要求說話人說得清楚、明白、有條理,避免晦澀、歧義、啰唆、混亂,否則便是違背了方式原則。例如,每周一,李老師都會去清華大學上課。這里的“上課”可以指聽課,也可以指給學生上課,因此這句話并沒有表達清楚李老師究竟是去聽課還是去給學生上課,已造成歧義,是違背方式原則的典型表現。簡而言之,遵循方式原則強調說話人表達時不存在語病問題,能夠正確表達語言信息。
本文借鑒會話含義理論中的列文森三原則,對國內優秀原創繪本的語用含義進行推導。在推導應用時,本文將繪本創作者和讀者分別看作三原則中的說話人和聽話人,繪本中的文和圖均可作為作者說的話或說話的語境。語用含義的推導也因此變得多樣化,從而產生出“只是文章或只是圖畫都難以表達的內容”。[9]
三、國內原創繪本的圖文關系
基于會話含義理論,本文對國內優秀原創繪本的圖文關系語用推導實例進行分析,揭示國內原創繪本實現語用含義表達的主要路徑。
(一)文以圖為語境
相對文字而言,圖畫占據了繪本的主要空間,甚至可以完全沒有文字。在圖構成的語境基礎上實現同一交際目的,需要的“最小信息量”顯然比僅用文字要少得多。[9]因此,文以圖為語境就是文字遵循信息原則,只提供所需的最少的語言信息。而在圖中需要添加大量細節,讓讀者能夠基于圖構造的語境和圖中隱含的細節推導圖文想表達的深層次語用含義。國內原創繪本中文以圖為語境的表達方式主要有以小見大、暗藏信息等。
《荷花鎮的早市》是以小見大的典型例子。繪本中的文字除客觀描述情境外,皆是姑姑與陽陽、早市朋友的對話。單讀文字,可以使兒童把握人物形象特點,了解到陽陽對集市的好奇以及姑姑的好人緣。再看圖畫,整個繪本的圖畫采用遠景手法,將陽陽與姑姑置于早市的大環境,在個別圖畫中甚至需要仔細尋找他們的身影。通過刻畫主人公在人群中的普通,讓兒童感受到文字中打招呼、聊家常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此,為兒童打開了一扇認識人與人之間濃濃情誼的窗口,推動兒童的社會性發展。
暗藏信息的表達方式在原創繪本中使用頗多,如《安的種子》。該作品第三對開頁文字交代的是本、靜、安三人拿到種子后的做法:本打算種在土里、靜打算種在花盆里、安不打算種下種子。單看文字,兒童基于已有經驗可能認為種下種子才會發芽開花,由此判斷出本和靜可以種出蓮花。但是仔細觀察畫面可以發現,畫中是漫天的雪花,這無疑是向兒童傳遞隱含的時間信息——此時是寒冷的冬季。通過圖文的默契互動,激起兒童的閱讀興趣,好奇冬天蓮花是否可以發芽開花,激勵兒童在繪本中自主尋找答案。
(二)圖以文為語境
基于會話含義理論,圖以文為語境包含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文遵循了數量原則,文字本身能夠把內涵表達清楚,此時的圖不是作為文的配圖出現,而是增添大量細節以最大限度地使讀者身臨其境并解讀信息。國內原創繪本圖畫中所使用的細節刻畫、環境烘托是這種情況的常見表達形式。
方衛平指出,圖畫有著自己特殊的細節語言,它們能夠傳達微妙的故事氛圍或角色細小的情感體驗。[10]《洛神賦》是細節刻畫的典型代表,原作描述的是詩人與仙女洛神相遇、相戀,卻又因“人神道殊”而無法結合,最后含恨分離的悲劇。作者所畫洛神身披輕盈的魚鱗魚尾華服,水波化作耳環,婉如一條美人魚,盡顯辭賦所云的“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之美。作者用華麗的畫面表達較為抽象的文字,契合了兒童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依靠具體表象的特點,使人物角色躍然紙上,給兒童帶來了美的感受和體驗。同時,畫面的主色調也細致地根據人物情感的轉化而發生變化:初遇洛神時,由整體淡淡的灰調變得多彩明亮;與洛神分離時,金黃色的暖光消失,整個色調又開始變灰,盡顯凄涼。通過色調變化,幫助兒童理解人物情感的波折。
《阿詩有塊大花布》是環境烘托手法的代表。該主人公阿詩個子小、羽毛少,鳥兒們因此有時不和她玩。為了表現出阿詩的孤單,繪本巧妙地在畫中增添了兩處細節豐富的內容:陰雨天氣、被當作傘的大荷葉。陰雨天氣常被用于烘托主人公的悲傷情緒。阿詩避雨舉起的大荷葉更加反襯出其小小的個子,使得整個畫面盡顯阿詩的難過與無助。由于兒童本身對形象的視覺信息比較敏感,環境的烘托使兒童更易代入角色,讓兒童聯想到自己日常生活中與朋友的交往,從而為向兒童傳遞人際交往的智慧做好鋪墊。
第二種情況是繪本呈現的不是連貫的故事情節,文字十分簡約,且圖與圖之間缺乏因果等序列聯系。此時,需要先以圖理解大致情境,再以文為語境推導出圖中語用含義。以科普繪本《白鶴日記》為例,其第一對開頁的圖是兩只美麗的白鶴中間有一只通體呈黃色的小生命。這可能會讓兒童猜測是兩只白鶴和一只小雞。但配文為圖畫提供了語境:“媽媽說我是一只白鶴,因為爸爸媽媽都是白鶴。可是我長得跟他們一點也不像,我一點也不白。”這時,兒童便可以推出圖中的語用含義:黃色的小生命就是小時候的白鶴。這一語用含義僅看文字或僅看圖畫都是無法歸納出來的,只有充分結合兩者才能順利解讀出來。結合圖文推導出語用含義的方式不僅增長了兒童的知識,而且促進了兒童思維能力的發展。
(三)圖文呼應同一語用含義
圖文呼應同一語用含義是指文字和圖畫均作為列文森三原則中說話人所說的話。其中,文字表述意義是間接的,圖畫表達意義是直接的。當兩種表達方式同時表達同一種語用含義時,能夠收到文字有意、畫中也有意的效果,最大限度地遵守數量原則,向聽話人呈現最大信息量。這一表達路徑在國內原創繪本中的常見表達方式為圖文互證與圖文互補。
《團圓》多處運用了圖文互證的表達方式。繪本的封面書名是“團圓”,“團圓”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詞語,指一家人在一起;配圖為一家三口相擁而睡的溫馨畫面,直接呈現了一家人團聚之意。留心觀察不難注意到,“團圓”二字所采用的是剪紙元素,像是過年時貼在門框上的掛門簽。這種巧妙的圖文互證,為以形象思維為主的兒童提供了便于理解的基礎,使兒童可以推導出繪本講述的是一家人團聚的故事,以及團聚的時間是過年時。團圓的元素以圓形等中國傳統符號的形式在正文中多處體現,如包湯圓、放硬幣等,既增添了畫面性,又使兒童理解文字“團圓”的抽象意義,感受家人團圓時的幸福快樂,增進情感體驗。
《爸爸去上班》中的圖文關系則更偏向于互補。第二對開頁描述下雨時的文字為“爸爸從云上走”,第三對開頁描述遇到大河時的文字為“爸爸從水底穿過”,第四對開頁遇到堵車時的文字為“爸爸從車頂飛快地走過”。在成年人看來,這種對父親的描述好似天馬行空,但是創作者卻切切實實地將爸爸的做法畫了出來,好像這一系列看起來空想的事情就在現實中發生了。這正體現出兒童對爸爸出門上班路程的無限幻想,因為在兒童眼中爸爸的確就是蓋世英雄。圖與文的相互補充尊重了兒童的想象力,使兒童抽象的想法得以具象化,既激發兒童的閱讀興趣,又豐富兒童對父親角色的認知。
(四)圖文相悖同一語用含義
圖文相悖同一語用含義,看起來是言行相悖,是對方式原則的違背,但表面上違反原則并不意味著語義層面上的違反,更類似于“正話反說”——原本肯定的句子用否定表達,以及“反話正說”——原本否定的句子用肯定表達。例如,當自己凌晨三點鐘還不睡覺時,母親說:“你別睡覺了!”母親的話是真的讓我們別睡覺了嗎?并不是。相反,母親話語的實際意思是讓我們趕緊睡覺。
《不要和青蛙跳繩》的封面便采用了圖文相悖的手法,繪本封面的文字是“不要和青蛙跳繩”,圖畫卻是小男孩正在跟青蛙跳繩。在閱讀封面時,不免產生疑惑。但是,封面的一處細節解答了這一疑惑:鴕鳥、鱷魚、烏龜正在圍觀跳繩比賽,地上映出了很多動物的影子……這暗示許多動物來圍觀這場比賽,能夠吸引眾多動物前來圍觀的,想必這場比賽“曠日持久”。這種圖文相悖的語用表達可以充分拓展兒童的想象力,發展兒童的游戲思維。
四、國內原創繪本的閱讀指導建議
分析國內原創繪本的圖文關系后發現,在閱讀指導過程中,要充分關注圖畫和文字的獨特價值。
(一)采用多元形式幫助兒童理解繪本的文字意蘊
兒童受識字量及理解能力的限制,在自主閱讀時無法完全明白和理解繪本內容,且注意力放在畫面,對繪本中的文字缺乏敏感性,使得繪本僅僅扮演“圖書”的角色。因此,在家庭閱讀中,家長要積極開展親子共讀,陪伴兒童閱讀文本,并及時為兒童解釋文本內涵。在幼兒園閱讀中,教師要提高敏感性,及時覺察兒童的認知狀況,采用師生共讀、討論等方式幫助兒童理解繪本內容。值得注意的是,成人陪伴閱讀并不等同于全盤由成人講讀,成人可以依據兒童的識字量選擇難度適宜的繪本,先讓兒童讀容易理解的或感興趣的部分,然后對個別詞語進行簡單解釋,幫助兒童理解文字意蘊。
(二)引領兒童參與挖掘圖畫中的深層信息
家長讀書一般側重于文字,對繪本中的圖畫并不敏感,往往是從正文開始,讀到最后一頁就算結束,忽視繪本畫面尤其封面、封底傳遞的信息。在幼兒園閱讀中,由于繪本數量有限,難以實現每名兒童人手一本。于是,個別教師采取“讀”繪本的方式,讓兒童僅僅作為繪本的聽眾,這導致兒童無法了解畫面內含的豐富的精彩的信息。考慮到兒童對畫面內容的獨特敏感性,在開展繪本閱讀時,家長要關注兒童的興趣和需要,有意識地引導兒童觀察畫面,挖掘圖畫隱藏的秘密。幼兒園教師可以通過多媒體投屏等方式,幫助兒童看到繪本畫面,為后面的講解補充圖畫信息,有效實現師生共讀。
(三)重視閱讀中成人與兒童的協同互動
繪本的高質量閱讀既不是兒童的獨角戲,也不是簡單的一個讀、一個聽的表面互動,而應該是成人與兒童共同閱讀,實現雙向協同互動。成人利用自身經驗和文學素養幫助兒童理解文字意蘊,兒童發揮自身對圖畫的敏感性挖掘圖畫中的信息,兩者合力探索繪本中文和圖傳遞的信息。成人應從圖文的關系中把握繪本欲表達的深層含義,發揮繪本的教育價值,促進兒童認知、情感和社會性的發展。
五、結語
繪本像是一串珍珠項鏈,圖畫是珍珠,文字是串起珍珠的細線,細線沒有珍珠不能美麗,項鏈沒有細線也不能存在。基于語用學中的會話含義理論,對國內優秀原創繪本進行語用推導發現,圖畫和文字均是原創繪本敘事必不可少的要素,對原創繪本的閱讀指導建議提供了借鑒。本文僅選取了部分原創作品,主要從理論層面進行作品賞析,無法代表所有原創繪本的敘事路徑。原創需要結合實證數據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