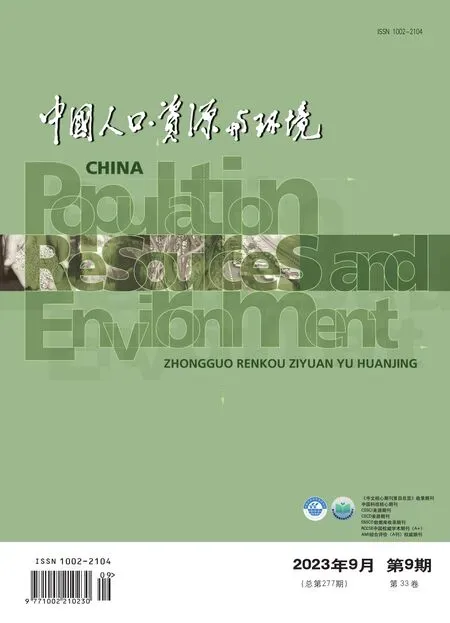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驅動機制
江永紅 劉夢媛 楊春












摘要 數字時代的到來,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提供了新動能和新契機。該研究運用2011—202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在構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綜合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運用固定效應模型、空間杜賓模型及門限回歸模型,多維度實證考察數字化對二者協調發展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①考察期內,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時間上呈平穩上升態勢,空間上呈現東高、中西低的格局。②數字化能夠有效推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在考慮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就內在機制而言,產業轉型升級、創新水平提升和能源效率增強在數字化賦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傳導作用。③分區域檢驗表明,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相較于西部,數字化對東、中部地區的賦能效應更為顯著,且該作用在東北地區并不顯著。④從空間維度來看,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具有顯著空間溢出效應,即數字化有助于提高鄰近地區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⑤門限檢驗表明,在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約束下,數字化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推動作用表現為非線性影響,在通過固定的門檻值后該影響會發生改變,具有顯著的門檻特征。基于此,該研究從夯實數字基建,加快數字技術在生態領域的應用;深化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研發水平提升,助力能源效率增強;結合區域發展特點,制定差異化發展策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 數字化;經濟增長;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
中圖分類號 F062. 5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9-0171-11 DOI:10. 12062/cpre. 20230717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持續的高速增長,然而,以往粗放式發展和大規模資源開發模式在促進經濟規模增長的同時卻未能實現發展質量的突破,同時還引發了一系列資源與環境難題。面對日益趨緊的資源和環境約束,深入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必然趨勢。協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被視為加快綠色經濟轉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黨和政府多次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無論是從宏觀層面的優化經濟結構、綠色轉型發展來看,還是就微觀層面的改善民生、提高人們生活福祉而言,探索出一條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之路都是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與此同時,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蓬勃發展,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多環節表現出強大的推動力[1],深刻影響經濟社會運作方式,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新動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國積極推進數字化進程,以數字要素為突破口,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那么,數字化能否成為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同共贏的新契機,數字化通過何種路徑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數字化對二者的協調發展是否存在空間效應及非線性效應?對于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可以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新思路。
1 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受到諸多學者關注。較為經典的有Grossman等[2]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其利用二氧化硫、微塵和懸浮顆粒3種指標探究環境質量與收入之間的關系,發現環境質量和經濟增長是一種此消彼長和相互促進的關系。國內也有學者提出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不等同于“平等發展”,經濟發展狀態決定了環境質量的高低,同時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又會作用于經濟活動本身,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應是相互促進、耦合協同的發展[3-4]。針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評價,有學者認為,相較于單一指標,構建綜合評價體系更能充分地反映經濟與環境整體系統的發展水平。如利用物理學中的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水平,多數研究得出中國經濟與環境的耦合協調程度整體呈上升趨勢,但仍處于較低水平,且存在空間分布不平衡特征的結論[5-10]。此外,有學者試圖探究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的關系。如利用系統動力學模型揭示城市經濟子系統與環境子系統的非線性結構和動態特征[11],或借助生態足跡法刻畫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非線性機制[12]。在經濟與環境協調關系的影響因素方面,已有文獻表明人口規模、技術創新[6]、人力資本[8]、產業結構[9-10]、外資進入[13]、能源效率[14]等因素會對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產生促進作用。然而,作為新時期重塑發展格局的重要驅動力,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產生的影響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探討。
從現有文獻來看,數字化的經濟效應是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點。例如,Choi等[15]、Czernich等[16]研究發現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楊慧梅等[17]基于中國省域面板數據證實了數字化對生產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及區域異質性。更進一步地,有學者指出加速產業結構調整[18-19]、促進技術創新[20]、激發大眾創新創業[21]是數字化發揮經濟效應的重要傳導路徑。隨著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部分學者探討了數字化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的積極作用,認為數字、信息等新興技術具有高滲透性、快捷性和可持續性等特征,有助于傳統產業擺脫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打破產業鏈分割,為促進經濟綠色發展提供了可能[3,22]。Ulucak等[23]以金磚國家為研究對象,發現信息技術的加持能夠促進各經濟部門的技術進步,進而助力金磚國家加速脫碳過程。李廣昊等[24]借助“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證實數字化轉型能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程文先等[25]從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角度出發,發現數字經濟可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對理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和數字化的影響效應具有重要作用,但多單一聚焦于數字化的經濟效應或環境效應,鮮有文獻將數字化和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納入統一研究框架,且缺乏二者理論機制關系的探討。基于此,該研究通過耦合協調度將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有機結合起來,就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及內在機制展開討論,在此基礎上考察區域異質性及數字化對二者協調發展的空間效應和非線性效應,以期為政府制定和調整政策提供相關的依據和建議。該研究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創新性地將數字化和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納入統一研究框架,剖析數字化影響二者協調發展的內在機理,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現有研究的空白,為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提供新思路。第二,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分析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并給出合理闡釋。第三,借助空間杜賓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探究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空間效應及非線性效應,拓展復雜情境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同共贏實現路徑的研究。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2. 1 數字化對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直接影響
數字化發展浪潮中,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創新技術廣泛應用于各領域,在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其一,從生產角度來看,采用大數據、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有助于企業實現智能化生產[26]。通過采用網絡化生產流程和數字化生產設備,企業能夠有效控制能源損耗和污染排放,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形成良性循環。此外,企業還可以借助算法的支持精確、實時地了解消費者需求,減少買賣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交易效率,從而降低資源投入和能耗。其二,從生活方式角度來看,數字化技術的普及豐富了綠色消費場景。數字化技術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開拓新的消費增長點,更加精準和高效地推動綠色消費的發展。例如,“無紙化”工作、智能打車綠色出行、廢舊產品在線回收等。其三,從環境管理角度來看,數字化能夠通過加強環境治理助推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政府利用數字化手段,可以更加有效地監測和管理環境問題,實現資源的有效管理和循環利用[27],從而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
假說1:數字化能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2. 2 數字化對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間接影響
2. 2. 1 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助推作用已得到普遍驗證。馬麗等[9]指出不同的產業結構對經濟-環境耦合協調關系的影響也有所不同,高端裝備制造產業為主的地區經濟環境耦合度較高,經濟-環境耦合協調度較差的區域產業結構多以污染性行業、初級產品加工業為主。王建康等[10]基于城市面板數據證明了不同協調類型城市主導產業差距較大。數字化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是指通過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促使經濟增長對能源的依賴轉向對信息技術的依賴,減少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污染排放,進而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具體而言,數字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助推作用主要體現在改造傳統產業和催生新產業、新業態等方面。一方面,數字化優化了傳統產業的生產方式,推動了以勞動密集型、重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向以技術密集型、環境友好型為主的產業結構躍遷[28],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在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中,以化石能源消耗為主的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逐步淘汰或轉型升級[29],降低產業發展對高碳資源的依賴,進而以低投入、低污染獲得高產出,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出以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型商業模式,促成新一輪的產業變革[19]。電子商務、智慧物流等新興產業以知識、信息、數字為核心生產要素,精準識別消費者需求,高效整合、配置生產資源,降低無效供給,在減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同時實現更高效益,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帶來新的產業動能。
假說2:數字化能夠通過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
2. 2. 2 創新激勵效應
技術創新,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被視作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洪雪飛等[6]、張國俊等[8]均證實了科技創新能有效推動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實現耦合協調發展。數字化以數據作為主要生產要素,同時兼具技術和綠色屬性,能夠通過推動綠色技術進步,為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提供不竭動力。一方面,數字技術具有信息跨時空傳播優勢,重新定義了創新邊界。依托開放式的數字信息平臺,技術創新活動由傳統的線下封閉式創新轉變為基于線上的開放整合創新,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使得各類創新主體在不同時間地點均可參與到創新過程當中[30],高效聚合創新知識資源[31-32],加快信息交互與知識傳播,極大提高了企業創新效率。Nambisan[33]研究發現,數字技術的運用為構建創新網絡、打破創新主體間的區位限制提供了有力支撐,從而強化組織創新效應。另一方面,數字信息技術與生產制造、產品研發和市場運營等環節的融合為創新活動提供了低成本優勢,進而影響企業的創新意愿。例如,市場運營環節的數字化能夠實現市場信息的及時反饋,有利于研發者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和針對性創新[34],從而降低創新成本和風險,激發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和創新效率。
假說3:數字化能夠通過促進技術創新驅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2. 2. 3 能源效率提升效應
提高能源效率是實現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8,14]。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推動能源效率的提升。隨著數字化進程的加快,云計算、人工智能及其他智能終端系統在能源行業得到廣泛的運用,促進生產、傳輸、交易和消費等環節的數據化、精細化[35],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例如,借助數字技術和5G通信技術,能夠實現煤炭勘探、開采等過程的無人化、可視化及智能化,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盡可能地降低能源損耗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36],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數字化催生能源新技術、新模式,促進能源效率的提升。近年來,數字化催生出一系列與能源生產、消費相關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如電池儲能技術、新能源汽車、智慧供應鏈、能源互聯網等,通過促進清潔能源的使用和能源效率的提升,為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提供了新契機。華為2020年發布的可持續發展報告顯示,華為數字能源在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入使用,在國內使用的可再生能源電力已達2. 2億kW·h,相當于減少約18. 8萬t二氧化碳排放。綜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可再生新能源的使用能夠有效降低環境污染,增加單位能源投入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帶動企業生產率[37],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污染減排的協調發展。據此,該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說。假說4:能源效率提升效應是數字化推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傳導路徑。
3 研究設計
3. 1 模型設定與選擇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為考察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構建如下基準模型:
Dit = α0 + α1 Digiit + αc Xit + ui + vt + εit (1)
其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被解釋變量Dit 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Digiit 表示各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Xit 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即反映省級層面可能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其他特征變量,包括人口密度、科技支持力度、經濟開放程度、城鎮化水平、金融相關率、市場化程度、政府行為。回歸系數 α1 反映出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作用效果。同時,引入了年份固定效應νt 和省份固定效應μi 來剔除其他隨地區、時間變化因素的影響。εit 為隨機誤差項。
3. 2 變量選擇
3. 2. 1 被解釋變量
(1)指標選取。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參考江永紅等[38]、張國俊等[8]的研究,遵循指標體系構建原則,結合指標數據的可獲取性,通過提取部分最具代表的指標最終形成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指標體系,見表1。從經濟實力、經濟結構、經濟活力三個維度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從環境壓力、環境質量和環境治理三個維度評價生態環境。
(2)指標測算。耦合協調度在反映各系統或要素發展水平的同時,也能反映系統間和諧一致、彼此作用的關系,被廣泛應用于資源環境、經濟管理等領域。因此,借助耦合協調度模型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i 和t 分別表示地區和時間,Cit 為耦合度,A 和B分別為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Dit 為耦合協調度,Tit 為經濟與環境的綜合協調指數,α 和β 分別表示經濟發展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對二者協調發展的貢獻率,借鑒任保平等[3]的系數選取方法,選取α = β = 0. 5。
3. 2. 2 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化發展水平。該研究參考《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對數字經濟的定義,基于數字化的內涵與特征,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27,39],擬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發展以及產業數字化發展三個維度測度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具體地,數字基礎設施水平擬用長途光纜密度、移動電話普及率以及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三個指標來衡量;數字產業發展水平擬選取軟件業務收入、電信業務總量、數字產業從業人員和數字產業工業總產值四個指標來反映,其中數字產業從業人員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行業年末平均從業人員數量來替代,數字產業工業總產值用電子信息制造業工業總產值來反映。產業數字化水平則用電子商務銷售額、快遞業務量、單位企業擁有網站數以及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四個指標來刻畫。在此基礎上,采用熵值法對各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3. 2. 3 中介變量與門檻變量
一是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選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的比值來度量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程度。這是因為污染物主要來自第二產業,當經濟由第二產業逐漸向第三產業轉移時,經濟行為對環境狀況的作用力度會減小,環境質量得到改善。二是創新激勵效應。相對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授權而言,發明專利授權更能體現一個地區的創新產出能力,故該研究選取每萬人發明專利授權量作為技術創新水平的衡量指標。三是能源效率提升效應,參照邵帥等[40]的做法,采取單位能源消耗的實際GDP產出予以度量。該值越大,說明同樣產出水平所消耗能源就越少,能源效率越高。人力資本水平采用地區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數字基礎設施變量用每百人中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表示。
3. 2. 4 控制變量
為盡量減少遺漏變量可能帶來的結果偏差問題,參考已有文獻[3,6-8,12],引入以下幾個可能影響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的因素:人口密度,用每平方公里人口數的對數來表示;科技支持力度,用財政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并取對數;經濟開放程度,采用地區進出口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并取對數;城鎮化水平,用年末常住人口中城鎮常住人口所占比重來衡量;金融相關率,用地區年末存貸款余額之和占GDP 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市場化程度,市場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影響經濟與環境的協同發展,因此參考王小魯等[41]編制的2011—2019 年市場化指數,并借鑒俞紅海等[42]的做法,根據歷年市場化指數平均增長幅度推算2020年省級市場化指數;政府支出,利用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并取對數。
3. 3 數據來源
該研究以2011—2020年中國省域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由于數據可得性等原因,研究未涉及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數據主要來自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統計年鑒等,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各省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CSMAR數據庫等進行補充。個別省份2020年工業廢水排放量數據仍有缺失,故采用線性插補法予以補齊。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 1 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時空分析
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狀況具有差異性,圖1展示了2011—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水平變化情況。結果表明:從時序變化來看,研究期間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總體上呈現平穩上升趨勢,其均值從2011年的0. 61上升到2019年的0. 71,波動幅度較小,反映出二者耦合協調度具備一定的穩定性。2020年二者耦合協調度與以往相比出現了小幅回落,為0. 703,原因可能是宏觀經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出現下滑,表面上會促進污染物的減排,但實際上經濟下滑可能會造成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的下降,打破經濟與環境系統間的平衡。例如,美國政府為應對經濟下滑加速出臺“美國優先”的制造業回歸政策,同時大幅調低汽車能耗和排放標準,不僅違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準則,也將加劇經濟與環境系統間的矛盾。
由圖2可以看出,2020年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位于前5的分別為廣東、北京、江蘇、上海和浙江,位于后5位的為吉林、山西、內蒙古、寧夏以及青海;除青海外,其余地區均達到初級協調水平(0. 6,0. 7]及以上;過半數地區未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僅有廣東、北京、江蘇等地的耦合協調度達到良好協調水平(0. 8,0. 9]。進一步分東、中、西三大區域進行空間特征考察,不難看出,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普遍較高(2020年均值達0. 75),而中西部地區大多數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均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由于東部地區具備沿海優勢和良好的區位條件,且其產業結構多以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耗能的高新技術產業、高級生產服務業為主,同時經濟實力較強,具備相對較強的環境修復與保護能力,使得經濟與環境系統間得以良好互動。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由于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其產業結構主要以高耗能企業為主,經濟發展受到生態環境約束,且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經濟實力較弱,在污染治理與環境改善方面的投資相對較少,經濟與環境系統間的協調具有一定難度。
4. 2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為控制宏觀經濟環境以及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之間的差異,該研究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2報告了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回歸(1)結果顯示,在未添加控制變量并控制時間固定效應與省份固定效應時,數字化發展水平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在回歸(2)中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數字化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由0. 357下降為0. 227,但仍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回歸結果相對穩健,數字化水平的提高的確有助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此外,回歸(2)中控制變量的結果顯示,人口密度、經濟開放程度的估計系數為負,這表明人口的過度集聚、進出口貿易不利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而城鎮化水平、市場化程度、政府財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
4. 3 作用機制檢驗
以上內容通過實證檢驗回答了數字化水平的提升能否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和假設,推動產業轉型、提高創新水平和增強能源效率可能是數字化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潛在渠道。為進一步檢驗數字化是否通過以上途徑影響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參照陳登科[13]、謝紅軍等[43]的做法,將機制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加入基準回歸方程,構建如下模型:
Mit = β0 + β1 Digiit + βc Xit + ui + vt + εit (5)
其中,Mit 表示機制變量,包括產業結構、技術創新和能源效率,其他符號解釋與基準回歸部分相同。表3匯報了機制檢驗結果。
列(1)、列(2)回歸結果表明,當機制變量為產業結構時,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其系數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數字化能夠通過發揮產業結構升級效應促進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理論上來說,數字化能夠助推傳統產業轉型并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產業由依賴傳統化石燃料向依靠綠色低碳能源轉變,為經濟增長注入新活力的同時能夠緩解環境壓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基于此,假說2得到驗證。列(4)匯報了技術創新渠道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在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過程中,數字化所帶來的創新激勵效應發揮了重要的傳導作用。數字化有助于破除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時空限制,為信息傳遞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從而激發了地區的創新活力。理論上,技術水平的提高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手段,數字化轉型依賴于綠色要素、技術要素和數據要素構成的核心生產要素,其帶來的技術創新也更偏向于綠色低碳和節能減排,有助于促進經濟綠色低碳轉型,推動地區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
列(6)回歸結果證實了地區能源效率的提升是數字化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機制。隨著數字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數字技術在能源與環境等領域不斷融合,優化能源的生產、傳輸、儲存和消費模式,推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促進整個能源行業效率的提升。例如,攀鋼集團引入阿里云工業大腦對煉鋼流程進行工藝優化,實現噸鋼生產節省原料約1. 28 kg,帶來高達2. 4倍的效率。可見,數字技術在提升清潔能源占比、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正發揮重要作用。基于此,假說4得到驗證。
4. 4 區域異質性分析
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表明,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在總體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然而,中國國土遼闊,各地區的數字化水平存在差異,在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地區不平衡現象。多項跨地區的研究表明,數字化對不同發展程度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的影響呈現異質性,需進一步對比研究。
表4展示了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度影響的檢驗結果。結果顯示,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數字化水平的系數呈現顯著正向關系,這表明數字化水平的提升對于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該作用在東部和中部地區的表現優于西部地區。對于東北地區而言,數字化系數并不顯著,這說明在該地區數字化對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東、中部地區城市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產業發展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且大量數字創新人才及創新資本的集聚優勢使得東、中部城市能夠更好地發揮數字化的賦能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發展相對滯后,數字化水平仍處于初級階段,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數字化發展初期產生的資源消耗增加可能會抵消部分賦能作用。此外這一結果還表明東北地區長期以來傳統重工業產能過剩、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等問題在數字化時代仍未得到有效緩解,這導致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不顯著。
4. 5 穩健性及內生性討論
4. 5. 1 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數字化對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提升效應是否穩健,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第一,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利用財新智庫公布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代替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回歸。該指數包括數字產業指數、融合指數、溢出指數和基礎指數等4個部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區數字化發展水平。回歸結果見表5中的列(1)、列(2)。不難看出,在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后,數字化仍在1%水平上顯著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初步證明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第二,對樣本進行1%雙向縮尾處理。考慮到研究結論對潛在極端值存在敏感性,該研究對模型數據進行1%的雙向縮尾處理,回歸結果依舊穩健。
4. 5. 2 內生性討論
此外,為緩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對數字化的反向因果以及引致的內生性問題,該研究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檢驗。參照黃群慧等[44]和Nunn等[45]的研究,引入1984年每百萬人郵局數與上一年全國互聯網端口數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采用2SLS方法進行內生性檢驗。表6詳細匯報了全樣本及分區域樣本工具變量回歸結果。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數字化系數仍顯著為正,再次證實了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度的促進作用。
5 進一步分析
5. 1 空間效應分析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化對鄰近地區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在模型1中引入數字化、經濟環境協調發展及控制變量的空間交互項,建立空間杜賓模型(SDM)。
其中,ρ 為空間自回歸系數,W 為空間權重矩陣,?1 和?c 分別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空間交互項系數,其他變量的含義和模型(1)保持一致。采用鄰接矩陣、經濟距離權重矩陣等不同矩陣反映省份之間的差距,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全局莫蘭指數Moran’I 檢驗2011—2020年數字化與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自相關性。結果顯示,鄰接矩陣和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數字化和經濟—環境協調發展均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二者在空間分布上存在集聚效應。同時,對空間杜賓模型(SDM)進行Wald和LR檢驗,結果表明,SDM模型并未退化為SEM或SAR模型,因此,該研究選擇SDM模型進行空間效應分析。此外,為比較估計結果的穩健性,在表6中列出了基于空間滯后模型(SAR)的估計結果。
表7顯示,在四種不同的模型設定下,數字化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在克服因空間相關性而產生的誤差后,數字化仍會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的穩健性。同時,空間自回歸系數ρ 也顯著為正,這表明各地區之間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存在內生的交互效應;數字化的空間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本地數字化對鄰近地區經濟-環境協調發展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進一步,將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總效應分解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代表數字化對本地區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間接效應代表數字化對鄰近地區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即空間溢出效應。從空間分解結果來看,數字化對空間關聯地區的經濟-環境協調發展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5. 2 門檻效應分析
數字化效應的發揮依賴于健全的數字化生態和產業布局,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的關鍵。考慮到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可能會隨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特征,故參照Hansen[46]的做法構建面板門檻模型,進一步探究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是否存在基于人力資本和數字基礎設施的門檻效應:
其中:q 為門限變量,指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水平,γ 為特定門限值,I (?)為根據不同門檻值進行分段的指示函數,其余變量與基準回歸部分一致。
首先檢驗門檻效應是否存在,并確定門檻個數。結果表明,人力資本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水平變量均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根據表8回歸結果可知,當人力資本水平越過門檻值后,數字化的影響系數由0. 224上升為0. 278,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人力資本水平越高,數字化越能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目前,絕大多數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低于門檻值,僅有浙江、江蘇等部分數字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越過。因而,加大專業人才培養力度與規模、進一步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是充分發揮數字化積極效應的重要途徑。由表8列(2)可知,數字基礎設施水平具有顯著的單一門檻效應。當互聯網接入寬帶用戶數未達到門檻值時,數字化的系數為0. 422,顯示出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當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邁過門檻值后,數字化的影響系數下降至0. 325,說明隨著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的進一步增加,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減弱。可能的解釋在于,較高的互聯網用戶數往往伴隨更高的能源需求,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伴隨著大量的能源消耗,產生一定的能源回彈效應[47],不利于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當前絕大多數地區寬帶接入用戶數低于門檻值,因此,為充分發揮數字化的促進作用,應加大相關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直至接近于門檻值。
6 結論與建議
在中國經濟轉型調整的進程中,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同共贏至關重要[48]。該研究從理論層面分析了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和傳導機制,并基于2011—2020年中國省域面板數據,結合耦合協調度模型衡量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構建面板固定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及門限效應模型實證檢驗數字化水平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影響,得到如下結論:第一,研究期內,各省份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時間上呈現平穩上升趨勢,2020年出現小幅回落;空間上呈東高、中西低的分布格局。第二,數字化水平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的協同共贏,通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該結果依然成立。第三,機制分析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創新激勵效應、能源效率提升效應是數字化推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第四,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驅動效應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具體而言,相較于西部地區,數字化在東部和中部地區的賦能效果最佳,在東北地區則不顯著,該結果可能是地區經濟與數字化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所致。第五,考慮空間效應后發現,數字化影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化促進了本地及鄰近地區的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第六,門限效應模型顯示,數字化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會隨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隨數字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夯實數字基礎設施,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生態保護中的“助推器”作用。通過研究發現,推動數字化發展不僅能夠提升經濟效率,還能促進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這為新時期推動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提供了新的支撐。因此,應持續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化發展提供堅實的信息基礎設施支撐。同時,各級政府可采取與數字經濟企業合作等方式,加快數字技術在生態環境領域的應用,提高數字技術在生態經濟體系中的貢獻率,充分發揮數字化的賦能效應。
第二,立足產業結構升級、強化科技創新、提升能源效率等作用機制,探索數字技術促進經濟環境協同共贏的多維路徑。政府應積極鼓勵綠色技術創新,高度重視以數字技術創新促進創新體系變革,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創新成果轉化與流動。加大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推動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進一步融合,大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在綠色低碳、共享經濟、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數字經濟在綠色低碳軌道上運行,推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第三,立足區域發展差異,制定差別化發展策略。針對區域差異性,各地政府應因地制宜,統籌考慮自身發展現狀及優勢產業特征,出臺相適宜的數字化發展政策。如東部地區,應重點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建設數字人才高地,為自主創新及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人才保障;中部應憑借自身區位優勢,積極保持與東部地區發展聯動性,推動數字化與地區傳統產業融合發展;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和信息化發展水平相對滯后,要立足資源稟賦優勢和低成本優勢,重點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導企業建立數據中心,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將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轉化為經濟發展福利;東北地區作為老工業基地和重要的農業基地,可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破地緣因素,形成數字化發展合力,開拓全新商業模式。
參考文獻
[1]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 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 經濟研究,2019,54(8):71-86.
[2] 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3] 任保平,杜宇翔. 黃河流域經濟增長-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的耦合協同關系[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1,31(2):119-129.
[4] LI Q A,GUO Q A,ZHOU M,et al.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and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environment in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J]. Sustainability,2022,14(5):2929.
[5] 崔盼盼,趙媛,夏四友,等.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與高質量發展測度及時空耦合特征[J]. 經濟地理,2020,40(5):49-57,80.
[6] 洪雪飛,李力,王俊. 創新驅動對經濟、能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基于省域面板數據與空間杜賓模型的研究[J].管理評論,2021,33(4):113-123.
[7] 李建新,梁曼,鐘業喜. 長江經濟帶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時空格局及問題區域識別[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0,29(12):2584-2596.
[8] 張國俊,王玨晗,吳坤津,等. 中國三大城市群經濟與環境協調度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J]. 地理研究,2020,39(2):272-288.
[9] 馬麗,金鳳君,劉毅. 中國經濟與環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業結構解析[J]. 地理學報,2012,67(10):1299-1307.
[10] 王建康,韓倩. 中國城市經濟-社會-環境耦合協調的時空格局[J]. 經濟地理,2021,41(5):193-203.
[11] DROUET L,EDWARDS N R,HAURIE A. Coupling climate andeconomic models in a cost‐benefit framework:a convex optimisationapproach[J]. Environmental modeling & assessment,2006,11(2):101-114.
[12] 隋建利,陳豪. 生態足跡視域下環境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路徑研究[J]. 財貿經濟,2021,42(6):54-70.
[13] 陳登科. 貿易壁壘下降與環境污染改善:來自中國企業污染數據的新證據[J]. 經濟研究,2020,55(12):98-114.
[14] 宋德勇,陳梅,朱文博. 用能權交易制度是否實現了環境和經濟的雙贏?[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32(11):134-145.
[15] CHOI C,YI M H.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panel data[J]. Economics letters,2009, 105(1):39-41.
[16] CZERNICH N,FALCK O,KRETSCHMER T,et al.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1,121(552):505-532.
[17] 楊慧梅,江璐. 數字經濟、空間效應與全要素生產率[J]. 統計研究,2021,38(4):3-15.
[18] SU J Q,SU K,WANG S B. Does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industrialstructural upgrading:a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s based onheterogene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Sustainability,2021,13(18):10105.
[19] 陳曉東,楊曉霞. 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基于灰關聯熵與耗散結構理論的研究[J]. 改革,2021(3):26-39.
[20] 溫湖煒,王圣云. 數字技術應用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J]. 科研管理,2022,43(4):66-74.
[21] 趙濤,張智,梁上坤. 數字經濟、創業活躍度與高質量發展:來自中國城市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22] VIDAS‐BUBANJA M.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ICT for sustainableeconomic development[C]//2014 37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Electronics and Microelectronics(MIPRO). Opatija,Croatia. 2014:1592-1597.
[23] ULUCAK R,DANISH,KHAN S U D. Doe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 affect CO2 mitigation under the pathway 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ode of globalization[J]. Sustainabledevelopment,2020,28(4):857-867.
[24] 李廣昊,周小亮. 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能否改善中國的環境污染:基于“寬帶中國”戰略的準自然實驗[J]. 宏觀經濟研究,2021(7):146-160.
[25] 程文先,錢學鋒. 數字經濟與中國工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J]. 經濟問題探索,2021(8):124-140.
[26] ACEMOGLU D,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factor shares,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6):1488-1542.
[27] 龐瑞芝,張帥,王群勇. 數字化能提升環境治理績效嗎:來自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1(5):1-10.
[28] 李曉華. 數字經濟新特征與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機制[J].改革,2019(11):40-51.
[29] 徐維祥,周建平,劉程軍. 數字經濟發展對城市碳排放影響的空間效應[J]. 地理研究,2022,41(1):111-129.
[30] 韓璐,陳松,梁玲玲. 數字經濟、創新環境與城市創新能力[J].科___"`研管理,2021,42(4):35-45.
[31] 韓兆安,吳海珍,趙景峰. 數字經濟驅動創新發展:知識流動的中介作用[J]. 科學學研究,2022,40(11):2055-2064,2101.
[32] KELLER W. 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y[J]. Journalof economic growth,2002,7(1):5-24.
[33] NAMBISAN 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and practice,2017,41(6):1029-1055.
[34]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enablingtechnologies,standards,and licensing models in the wirelessworld[J]. Research policy,2018,47(8):1367-1387.
[35] 陳曉紅,胡東濱,曹文治,等. 數字技術助推我國能源行業碳中和目標實現的路徑探析[J]. 中國科學院院刊,2021,36(9):1019-1029.
[36] WANG J H,HUANG Z H. The rec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ining in China[J]. Engineering,2017,3(4):439-444.
[37] SHAPIRO J S,WALKER R. Why is pollution from US manufacturingdeclining:the rol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roductivity,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12):3814-3854.
[38] 江永紅,劉冬萍. 安徽省資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綜合評價[J]. 農業技術經濟,2012(7):94-102.
[39] 潘為華,賀正楚,潘紅玉.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時空演化和分布動態[J]. 中國軟科學,2021(10):137-147.
[40] 邵帥,李欣,曹建華,等. 中國霧霾污染治理的經濟政策選擇:基于空間溢出效應的視角[J]. 經濟研究,2016,51(9):73-88.
[41] 王小魯,胡李鵬,樊綱. 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21[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42] 俞紅海,徐龍炳,陳百助. 終極控股股東控制權與自由現金流過度投資[J]. 經濟研究,2010,45(8):103-114.
[43] 謝紅軍,呂雪. 負責任的國際投資:ESG與中國OFDI[J]. 經濟研究,2022,57(3):83-99.
[44] 黃群慧,余泳澤,張松林. 互聯網發展與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內在機制與中國經驗[J]. 中國工業經濟,2019(8):5-23.
[45] NUNN N,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economic review,2014,104(6):1630-1666.
[46] 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47] 樊軼俠,徐昊.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能帶來經濟綠色化嗎:來自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經濟問題探索,2021(9):15-29.
[48] 劉陽,秦曼. 中國東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綠色效率的綜合測度與比較[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3):11-20.
(責任編輯:劉照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