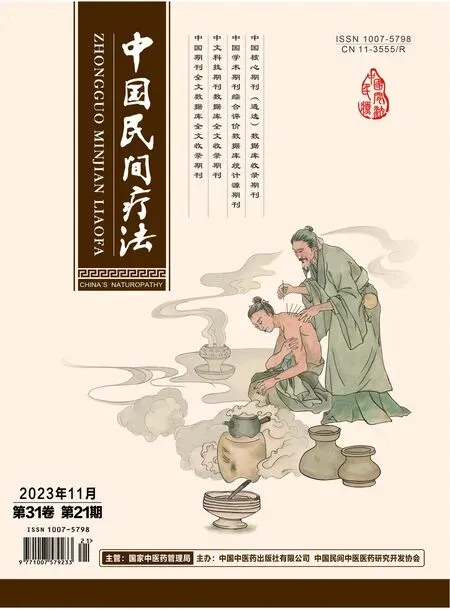敦煌神妙補心湯配合養心安神針法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的臨床觀察※
盛雪燕,顧崇禛,王明行,楊柳軍,陳文家,陳寶軍,張澤國
(甘肅省酒泉市中醫院,甘肅 酒泉 735000)
失眠,又稱為不眠、不寐,常以長期難以入眠或頻繁眠后易醒,醒后難再眠或持續似睡非睡等主觀癥狀為主,進而影響患者日間工作及生活,對患者不僅造成困擾、影響,嚴重者可繼發焦慮、抑郁等情志、精神的一類疾患[1]。隨著社會競爭或人們生活壓力增加、生活節奏加快,失眠患者逐年增加,并趨于年輕化。研究顯示,中青年失眠人群中以心脾兩虛型失眠位居首位[2-3];消化系統疾患的13.6%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失眠[4]。目前,治療失眠包括非藥物療法和藥物療法,非藥物療法雖療效確切,但因醫療費用昂貴,患者承受經濟壓力不能長期堅持治療;藥物治療可改善失眠癥狀,但不能根治,且易產生成癮性、依賴性等弊端[5]。傳統中醫藥方法包括中藥、針灸治療失眠效果好,且風險較小,在目前諸多研究中均證實中醫藥治療失眠的顯著性、優越性[6]。本研究以形神兼調、固護脾胃為核心思想,以補益心脾、養血安神為治則,采用敦煌神妙補心湯配合養心安神針法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收效良好,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甘肅省酒泉市中醫院針灸科、腦病科收治的84例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對照1組、對照2組,每組28例。治療組平均年齡(44.54±11.37)歲,病程中位數4.50(3.00,7.75)年。對照1組平均年齡(44.43±12.20)歲,病程中位數5.00(3.00,9.00)年。對照2組平均年齡(43.96±12.07)歲,病程中位數5.00(3.25,7.75)年。3組患者基線資料(年齡、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相關倫理要求[7]。
1.2 診斷標準
(1)西醫診斷標準 參考《中國成人失眠診斷與治療指南》中失眠的診斷標準[8]。以失眠為首要癥狀,主要表現為難以入睡,或醒后難再入睡,難以維持睡眠狀態(易覺醒,淺睡眠),睡眠時間短,睡眠質量不高(晨醒過早、多夢);醒后狀態不佳(易疲乏、困倦);上述癥狀每周發作≥3次,持續時間≥1個月;失眠引起臨床意義上的痛苦,工作、生活等受到影響;排除精神障礙或軀體性疾病繼發的失眠。
(2)中醫診斷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不寐的診斷標準,主要癥狀為睡眠障礙,難以入眠,多夢易醒,或睡間易醒,醒后難再眠,日間困倦,睡眠時間<5 h,具有反復發作特點[9]。參考《中醫內科學》中心脾兩虛型失眠的診斷標準[10]。主癥:不寐,多夢易醒,或睡間易醒,醒后難再眠。次癥:體質瘦弱,面色無華,倦怠懶言,心悸,健忘,眩暈,納少,腹脹,便溏。舌脈象:舌淡,苔薄,脈細弱無力。
1.3 納入標準 符合上述診斷標準;18~70歲,性別不限;患者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評分<50 分(排除精神障礙繼發的失眠),且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量表評分≥10分。
1.4 排除標準 妊娠期、哺乳期女性;不愿配合研究的患者;近1個月內參加其他臨床試驗的患者;過敏體質及多種藥物過敏者。
2 治療方法
2.1 治療組 采用敦煌神妙補心湯配合養心安神針法治療。敦煌神妙補心湯方藥組成:黨參片30 g,茯神20 g,山藥15 g,白術15 g,丹參15 g,柏子仁20 g,石菖蒲15 g,川貝母10 g,熟地黃20 g,百部5 g,炙甘草10 g,防風15 g,五味子10 g,茯苓10 g,遠志10 g,杜仲10 g,飴糖5 g。水煎,每劑3袋,每袋約200 m L,每日餐后30 min溫服。養心安神針法取穴:百會、上星、中脘、關元、巨闕、神門(雙側)、內關(雙側)、公孫(雙側)、心俞(雙側)、脾俞(雙側)、章門(雙側)、三陰交(雙側)。操作方法:患者取仰臥位,醫者運用0.30 mm×40 mm一次性針灸針(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逆督脈平刺百會、上星13 mm,行平瀉平補法;直刺神門、內關、巨闕、中脘、關元、章門、三陰交、公孫30 mm,行捻轉補法。患者取俯臥位,醫者用針灸針斜刺心俞、脾俞25 mm,行捻轉補法。留針30 min,每隔10 min行針1次。14 d為1個療程,共治療兩個療程。
2.2 對照1組 采用歸脾湯配合養心安神針法治療。歸脾湯組方:黃芪30 g,麩炒白術15 g,當歸15 g,酸棗仁15 g,木香6 g,遠志12 g,黨參片15 g,茯苓15 g,龍眼肉10 g,炙甘草6 g,大棗5 g,生姜3片。煎服方法同治療組補心湯。養心安神針組方、操作同治療組。
2.3 對照2組 采用敦煌神妙補心湯配合常規針刺治療。敦煌神妙補心湯組方、煎服方法同治療組。常規針刺治療參考《針灸學》中治療不寐的組穴原則,主穴取雙側照海、申脈、安眠、三陰交、神門及四神聰,配穴取雙側心俞、脾俞[11]。操作方法:醫者運用0.30 mm×40 mm 一次性針灸針(蘇州醫療用品廠有限公司)直刺照海、申脈、安眠、三陰交、神門30 mm;逆督脈平刺四神聰13 mm;斜刺心俞、脾俞25 mm。補瀉手法:神門、四神聰、三陰交、安眠用平補平瀉法,心俞、脾俞、照海用捻轉補法,申脈用捻轉瀉法。
3組患者每日治療1次,連續治療兩周為1個周期,休息1 d后進行下一個周期治療。共治療兩個周期。
3 療效觀察
3.1 觀察指標 ①PSQI量表評分。采用PSQI量表評估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睡眠狀態。該量表分為七大因子(主觀的睡眠質量、所需入睡時間、睡眠持續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是否借助助眠藥物、日間活動功能障礙評估),滿分為21分。評分越高,表明睡眠質量越差。②中醫證候總分。參考《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制定中醫證候評價標準[9]。失眠、心悸、神疲乏力、食納減少按無、輕度、中度、重度分別計為0、2、4、6分;健忘、多夢、面色少華、食后腹脹、便溏按無、輕度、中度、重度分別計為0、1、2、3分,舌象、脈象按輕、中、重度分別計為1、2、3分,滿分45分。根據患者所得分,總分越高,表明病情越嚴重。
3.2 療效評定標準 ①睡眠改善療效。積分改善率=(干預前PSQI量表總分-干預后PSQI量表總分)/干預前PSQI量表總分×100%。無效:積分改善率<25%;有效:25%≤積分改善率<50%;顯效:50%≤積分改善率<75%;治愈:積分改善率≥75%。②中醫證候改善療效。中醫證候改善率=(干預前中醫證候總分-干預后中醫證候總分)/干預前中醫證候總分×100%。無效:中醫證候改善率<30%;有效:30%≤中醫證候改善率<70%;顯效:70%≤中醫證候改善率<95%;治愈:中醫證候改善率≥95%。總有效率=(治愈例數+顯效例數+有效例數)/總例數×100%。
3.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時以均數± 標準差(±s)表示,組內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態分布時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M(Q1,Q3)]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組內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4 結果
(1)PSQI量表評分比較 治療前,3組患者PSQI量表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3組患者PSQI量表評分低于本組治療前(P<0.05),且治療組低于對照1組、對照2組(P<0.05);對照1組、對照2 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3組心脾兩虛型失眠患者治療前后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評分比較[分,M(Q 1,Q 3)]
(2)中醫證候總分比較 治療前,3組患者中醫證候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3組患者中醫證候總分低于本組治療前(P<0.05),且治療組低于對照1組、對照2組(P<0.05);對照1組、對照2 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3組心脾兩虛型失眠患者治療前后中醫證候總分比較[分,M(Q 1,Q 3)]
(3)睡眠改善療效比較 治療組睡眠改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1組、對照2組(P<0.05),且對照1組高于對照2組(P<0.05)。見表3。

表3 3組心脾兩虛型失眠患者睡眠改善療效比較
(4)中醫證候改善療效比較 治療組中醫證候改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1組、對照2組(P<0.05),且對照1組高于對照2組(P<0.05)。見表4。

表4 3組心脾兩虛型失眠患者中醫證候改善療效比較
4 討論
失眠屬于睡眠障礙性疾病,為臨床常見病、多發病,具有易發性、難治性特點,以夜眠困難或夜寐質量不佳為主癥[12]。該病發病因素可能與生活方式、生活環境、精神心理、軀體疾病、藥物等有關[13]。在病理機制方面,睡眠-覺醒機制與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 軸)、褪黑素水平、5-羥色胺(5-HT)中樞神經遞質密切相關[14]。當HPA 軸功能紊亂,下丘腦釋放皮質醇增加,進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CRH)含量超正常人體量,導致失眠;松果體主導睡眠、覺醒活動,其分泌的褪黑素可調節睡眠覺醒周期,促進睡眠,呈現晝低夜高規律,若人體長期夜間受強光影響則該激素水平升高,進而導致失眠;5-HT 作為神經遞質,分布于松果體和下丘腦,影響睡眠覺醒周期,當其在體內水平較高時可產生睡眠,若水平較低時則會導致失眠、抑郁等。
中醫認為,失眠多因情志不暢、飲食失節、勞倦過度、病久體虛等導致臟腑功能、營衛氣血功能失調所致,屬于“不寐”“不眠”范疇[15]。受現代生活快節奏、工作高壓力、社會環境強競爭的影響,人們易過度思慮、勞倦,生活習慣不規律,久則傷及脾胃,脾胃失和,則水谷不足以化生精微物質,久之氣血虧虛,不能上奉于心,心血不足不能濡養心神,心神不寧,故而失眠。基于此,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尤為重要。
敦煌醫學卷子《毗沙門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補心丸方》現藏英國倫敦博物院,編號為S·5598V,神妙補心湯由此卷子方藥化裁而成[16]。方中,黨參、山藥、茯苓均歸脾經,以補中益氣、健脾生血、寧心安神為主;石菖蒲歸心經,安神定志,健脾和胃,與茯苓、黨參合用,共奏健脾養心、安神之功;遠志、石菖蒲均歸心經,開心氣,寧心安神益智;熟地黃歸腎經,補血滋陰,生精補髓,合遠志補血安神;茯神歸心、脾經,柏子仁歸心經,二藥合用可健脾、養心、安神;丹參歸心經,養心活血,除煩安神;五味子歸心經,斂陰寧心安神;山藥歸脾經,補脾養陰,杜仲歸肝腎經,調肝腎,充足沖任氣血,二藥同用可健脾固腎;茯苓、茯神歸脾經,健脾寧心安神;浙貝母、百部均歸心經,養陰清心,解郁除煩,寧心安神,還可潤肺氣;防風歸脾經,為反佐藥,補中有散;飴糖入脾經,補脾氣,平補心血;甘草調和諸藥。諸藥合用,共奏補脾養心、調陰陽、和營衛、固神安眠之功。藥理研究表明,茯苓、茯神、五味子可提高入睡率,延長睡眠時間,茯苓多糖、五味子木脂素改善大鼠下丘腦組織中5-HT水平,均有鎮靜催眠作用[17-19];黨參可提高人體抗缺氧能力,增加腦組織血流[20];遠志通過調節體內的神經遞質提高睡眠質量[21];柏子仁中的皂苷成分、總萜類成分對改善小鼠睡眠效果明顯[22];石菖蒲可引藥入腦,營養神經,抗疲勞,鎮靜[23]。李應存運用敦煌神妙補心丸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收效良好[24]。張吉玲主任醫師基于上述理論及研究成果,將敦煌神妙補心丸劑改為湯劑用于心脾兩虛型失眠的治療,臨床獲益頗多。
養心安神針法為張吉玲主任醫師經驗方,逆督脈平刺百會,可理氣生血安神,上星為鬼堂,針之可健腦安神;公孫、內關為上下配穴,可健脾和胃,養心安神;公孫、神門為遠近、原絡配穴,一則養心安神,二則體現“虛者補母”理論。“上紀”中脘與“下紀”關元相配,可補脾固本,充足氣血,調和營衛、陰陽。心俞、脾俞發揮滋脾、養心、安神之效。心俞配巨闕,脾俞配章門,為前后、俞募配穴,達調養心神、強健脾氣之功。章門為脾之募穴,可疏理脾氣,生氣調血,血充則神安。三陰交為養血調陰要穴,針刺之可引陽入陰,安神助眠。養心安神針法以調心、調脾、調神為根本,按人體天、人、地部取穴,上配“天”以養腦,選用百會、上星,下象地以養足,選用公孫、三陰交,中傍人事以養五臟,選用任脈臟腑募穴巨闕、中脘、關元,體現形神同調、整體施治觀念。研究發現,針刺失眠患者頭部相關穴位(百會、上星)不僅增加大腦供血,促進神經元修復,還可減少大腦異常放電,改善失眠癥狀[25];針刺手足部穴位(公孫、三陰交、內關、神門)可興奮大腦皮層,抑制導致失眠的皮層興奮點,進而促進睡眠[26]。腦-腸軸對睡眠有一定的調節作用,針刺背俞穴(心俞、脾俞)及腹部相關穴位(中脘、關元)可促進腸道分泌促眠細胞因子如γ-氨基丁酸和谷氨酸等,這些物質通過腸神經、迷走神經上行至大腦中樞影響睡眠節律,進而調節睡眠[27]。歸脾湯為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的代表方,臨床療效明確,已經臨床研究證實[28-29]。
本研究中,對照1組與治療組比較,旨在證實敦煌神妙補心湯治療失眠臨床療效能否優于歸脾湯;對照2組與治療組比較,旨在證實養心安神針法治療失眠療效能否優于常規針刺組。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3組患者PSQI量表評分、中醫證候總分均低于本組治療前(P<0.05),且治療組均低于對照1組、對照2 組(P<0.05);治療組睡眠改善總有效率、中醫證候改善總有效率均高于對照1 組、對照2組(P<0.05)。以上結果表明,3種治療方法均能改善患者失眠癥狀,且敦煌神妙補心湯聯合養心安神針法的療效更優。
針對失眠,臨床以精神和心理療法為主,以藥物治療為輔。敦煌神妙補心湯無毒性,可長期口服。養心安神針法配穴精妙,以遠近配穴、原絡配穴、前后配穴、俞募配穴、三部取穴等方式,補脾養血調神。敦煌神妙補心湯結合養心安神針法治療心脾兩虛型失眠安全有效,從根本上調整臟腑氣血。本研究各組樣本量相對較少,隨訪時間短,在今后有條件的情況下,應當進行大樣本的臨床研究,延長隨訪時間,追蹤遠期療效,使研究結果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