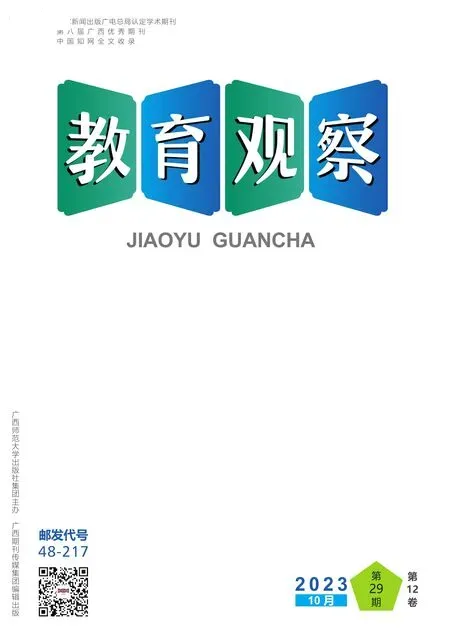高質量教育背景下中小學教師領導力提升研究
——基于成都市292所新優質學校的實證調查
馬 麗
(成都大學師范學院,四川成都,610106)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標志著我國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1]教師隊伍高質量發展是建設教育強國和教育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教師是教育引擎中的關鍵驅動者,面對新時代教育發展需求,學校組織不斷變革,教師的角色和評價標準不斷調整,如何提升教師領導力以促進學生成長和學校發展成為教育變革時代的熱點研究議題。
20世紀80年代,教師領導力伴隨美國教育改革應運而生,它以分布式領導為基礎,在領導者、跟隨者與環境的互動中產生。[2]教師領導力是促進學校改革和學生全面成長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要求。[3]在近40年的探索歷程中,學者主要結合教師領導力的內涵、教師領導力理論基礎、教師領導力的價值、教師領導力的影響因素及提升路徑等議題進行了全面探討,但我國教師領導力的實證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4-9]在高質量教育發展背景下,新優質學校教師如何在學校發展規劃、課程開發、教學變革、作業設計、家校社合作等領域充分發揮領導力亟待研究。
因此,通過一手數據探析中小學教師領導力的影響因素與提升對策具有重要價值。已有研究結合教師的人口學變量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或有研究聚焦學校具體情境與教師領導力的關系[10],為本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基礎,但仍有必要通過混合研究法在新優質學校樣本區域加以拓展,以深入探究學校組織層面及教師層面因素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進而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實踐對策。
本研究深入剖析成都市292所新優質學校的調研數據,擬對以下兩個問題進行探討:第一,從個體層面來看,教師的學歷、教齡以及個人領導意愿等因素對教師領導力有何影響;第二,從學校層面來看,所屬學段、組織文化、合作學習對教師領導力有何影響。冀望本研究能加深教育行政部門、學校領導者及教學實踐者對教師領導力的認識,并積極探尋高質量教育背景下中小學教師領導力的提升路徑。
一、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取自成都大學“新優質學校辦學活力”調研項目。2020年9月至12月,項目組面向成都市的292所新優質學校發放了2000份問卷,回收1950份,剔除明顯呈現出規律性答案的無效問卷,得到1883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為96.56%。本研究借助SPSS 22.0軟件錄入正式樣本數據,并對教師領導力量表進行信度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量表中Cronbach’s α為0.919,教師領導力問卷內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筆者對1883份有效問卷的代表性從教師人口學特征以及所在學段、地理位置、獲獎情況等方面進行了統計,從城鄉分布看,城區占40.70%,鄉鎮占59.30%;從學段來看,小學占63.90%,初中占36.10%;從學歷來看,本科及以上的占83.40%,大專及以下的占16.60%;從教師性別來看,女性教師占74.30%,男性教師占25.70%;從年齡結構來看,30歲及以下的占27.60%,31—40歲的占30.50%,41歲及以上的占41.90%;從教齡結構來看,10年及以下的占35.90%,11—20年的占25.00%,21年及其以上的占39.10%;從教師職稱結構看,初級職稱及其以下的占43.60%,中級職稱的占43.80%,高級職稱及其以上的占12.60%;從教師獲獎最高看,最高級別獎勵為校級及以下獎勵的占72.00%,縣級獎勵占16.60%,市級及以上占11.40%。
為進一步了解高質量教育背景下新優質學校教師領導力問題,研究者于2022年9月至11月在成都市成華區、金牛區、天府新區等區域的新優質學校開展了3個月的田野調研,并結合教師領導實踐對20余名新優質學校教師進行深入訪談及個案研究。田野調查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具體、形象地感知教師們在“組織領導力”“教學領導力”“同伴領導力”的態度與行為差異,并建立起量化數據與質性訪談資料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變量界定
1.因變量
教師領導力。已有研究將教師領導力分解為組織領導力、教學領導力、同伴領導力三個維度進行測量,并在實證研究中證明了三個維度之間的緊密關系。[9]結合多次調研和訪談,筆者借鑒了上述測量方式,取三個維度得分均值作為教師領導力的評價依據進行分析。
2.解釋變量
第一,領導動機。本文的領導動機分為自我效能感和領導意愿兩個維度。根據班杜拉對自我效能感的界定,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可闡釋為教師對自己所擁有的教育教學技能去影響學校改進的自信程度。[11]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感包括“我能夠對學校事務管理和決策提出有益的建議”等8個題項,通過4級量表進行測量,由“1=完全無法勝任”到“4=完全能勝任”,Cronbach’s α=為0. 91; 領導意愿包括“您參與學校事務管理與決策的意愿程度”等4個題項,采用4 級評分,由“1=非常不愿意”到“4=非常愿意”,Cronbach’s α=為0.88。本研究通過取均值的方法合成最終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和領導意愿變量。
第二,激勵文化。學校激勵文化共包括“校長邀請教師參加學校重大事情的決策”等4個調查題項。量表采用Likert 4級評分,從“1=從來沒有”到“4=經常有”,Cronbach’s α=為0.87。本研究通過取均值的方法合成了學校激勵文化變量。
第三,組織結構。文獻研究發現,教師的領導工作會受組織結構的較大影響。本文主要通過“學校相關職能部門之間溝通的順暢程度”一題來進行操作化的測量,從“1=非常不順暢”到“4=非常順暢”進行評分,本研究通過求均值的方法分析。
第四,合作學習。教師合作學習共包括“小組內存在教師相互學習的情況”等4個題項測量。“1=從來沒有”“4=經常有”,分值越高代表頻率越高。Cronbach’s α=為0.88。本研究通過取均值的方式合成了教師合作學習變量。
3.控制變量
為了更好地揭示教師領導力的影響因素,本研究對學校層面和教師層面的特征變量進行了控制。結合現有文獻研究的結果,本文引入性別(1=男;0=女)、教齡(連續變量)、職稱(類別變量)、學歷(依據中國學制折算成相應年限)、學段(1=小學;0=初中)、學校所在區域(1=城市;0=鄉鎮)6項控制變量。
具體的變量界定、測量與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界定及測量
(三)模型選擇
本研究采用OLS回歸模型進行教師領導力影響因素參數估計,多元回歸的優勢表現在控制教師人口學特征和學校基本特征后,它能提高教師自我效能、領導意愿、學校組織文化及同伴協作等變量對教師領導力的偏效應。回歸模型方程如公式1所示。其中,Ln代表第n個教師的領導力,P代表教師層面的特征,S代表學校層面的特征,J、K分別代表教師因素、學校因素的變量個數,j、k分別代表第j、k個自變量,εi為隨機誤差項。
(1)
二、結果與討論
(一)模型分析結果
通過回歸分析,從教師領導的內源和外源兩個方面呈現了中小學教師領導力的影響因素,如表2所示。其中內部因素從教師個人特征著手分析,外部因素從學校特征展開討論。模型1將教師個人特征的主要變量納入本模型,該模型的R2結果為0.52,表明自變量包含了中小學教師領導力中51.80%的變異。在控制其他因素基礎上,中小學教師領導力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p<0.05);年齡、教齡、學歷變量對教師領導力沒有顯著影響(p>0.05)。

表2 教師領導力的影響因素
從參與學校領導的個人意愿與教師領導力之間的關系來看,教師參與學校領導的意愿越強烈,越能正向影響教師領導力的發揮。結合數據,教師的領導意愿每增加1個單位,教師的領導力顯著提升0.84個單位(p<0.001);教師的自我效能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顯著,教師自我效能每增加1個單位,其領導力顯著提升0.68個單位(p<0.001)。
模型2加入學校特征變量,模型的擬合優度(R2=0.68)得到進一步提高,表明學校特征變量對教師領導力具有較大的影響。學校層面的變量與教師的個人特征共同影響著教師領導力的發揮與提升。數據顯示:當加入學校變量后,個體變量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
在控制相關變量的前提下,教師的個人意愿仍能顯著正向影響其領導力(p<0.001),但相較于模型1,個人意愿的影響效應有所降低;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依舊顯著為正(p<0.001),但與模型1的影響值相較而言有所下降;學段與學校地理位置對教師領導力不存在顯著影響(p>0.05);學校的激勵文化、組織溝通、合作學習均對教師領導力有顯著正向影響(p<0.001),而三種因素的影響程度如下:激勵文化、組織溝通、合作學習每增加1單位,教師領導力分別顯著提升0.45、0.38、0.56個單位。
(二)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增強個人特征與學校特征變量對教師領導力影響的解釋力,筆者將因變量“教師領導力”分解為“組織領導力”“教學領導力”“同伴領導力”三個維度,將學校激勵文化、組織溝通、合作學習三個核心解釋變量轉換為一個“學校環境”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個人領導意愿、學校環境對教師領導力三個子維度的影響顯著為正(p<0.001)。因變量調整之后,教師的個人特征與學校特征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依舊存在,說明自我效能感、個人領導意愿、學校環境的確會對教師領導力產生正向影響,基本驗證了前文預期結果。

表3 穩健性檢驗的估計結果
(三)結果討論
1.教師領導動機對其領導力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主要從教師的領導意愿和自我效能感兩個維度對教師領導動機進行分析。基于模型1的回歸發現,教師的領導意愿和自我效能感能顯著正向預測教師領導力。筆者在訪談中發現,提升教師的領導意愿和自我效能感將助力教師領導力的提高。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學校特征變量,個人領導意愿和自我效能感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下降0.30個百分點,但是對教師領導力的影響仍然正向顯著(p<0.001),表明個人領導意愿和自我效能感變量是教師領導力的重要影響因素。訪談資料也支持了上述觀點,J鎮M老師表示:“我是一個充滿自信又愿意帶領同伴共同進步的人,其實這往往能形成一種‘回力效應’,促使我能高效完成教育教學任務,在遇到教育教學挑戰的時候也能沉著從容應對。”
2.學校的激勵文化對其領導力有顯著正向影響
基于模型2的回歸結果,學校的激勵文化每增加1單位,教師領導力顯著提升0.45個單位(p<0.001)。結合實證調研,筆者發現學校的個性化激勵制度體系能充分調動教師們的主動性與創造性。訪談中T中學H老師說道:“T中學作為成都選課走班的窗口示范學校,1260個孩子就有1260份差異化的課表,這對教師的管理、領導能力也帶來很大挑戰。我們校長結合辦學特色,制定了一套非常科學又個性化的激勵制度,在促進年輕教師積極進取,吸收和穩定優秀骨干教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3.組織溝通對教師領導力有顯著正向影響
學校內部的溝通順暢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學校的組織結構功能。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組織溝通順暢度每提高1個單位,教師領導力顯著正向提升0.38個單位(p<0.001)。調研發現,鼓勵教師平等參與學校管理,為各部門、領導與師生雙向溝通創造平臺與條件的學校,教師的歸屬感、責任心和創造力更強。訪談資料也印證了這一觀點,Y小學的Z老師說:“作為一名平凡的小學教師,我希望自己的勞動能夠得到他人尤其是管理者的尊重和認可。如果領導和教師之間的溝通非常順暢,這不僅有利于學校領導更多更詳細地了解每位教師的個性品質及差異化發展需求,也有利于教師時刻掌握學校發展動態,并為教師營造一種支持性的組織氛圍,讓教師敢于領導、勇于領導。”
4.合作學習對教師領導力有顯著正向影響
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合作學習每提高1個單位,教師領導力顯著提升0.56個單位(p<0.001)。在新時代教育背景之下,進一步加強教師合作是加強教師專業發展、建設高質量教師隊伍的關鍵。[12]從教育領導力的層面看,建立有組織、有活力的學習與實踐共同體是助力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舉措。[13]J校W老師在訪談中說道:“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能結合彼此共同關注的話題進行交流討論、資源共享,我能了解到新的觀點及研究,這可以把我的工作推向一個新的水平。”但在一位鄉鎮中心校的S老師說道:“學校的留守兒童占65%,教師均齡50.45歲,受生源質量和教師年齡結構的影響,教師完成正常教學工作后,學校的集體備課、公開課等教師合作較為表面化,無暇顧及自身的領導力提升問題。”
三、啟示與建議
研究發現,教師領導力受制于內在因素(領導動機)和外在因素(學校環境),教師內在的領導動機與外在的學校環境相互交叉,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教師領導力。結合高質量教育發展政策賦予教師領導力時代內涵,教師領導力之提升應著力于 “賦權”與“增能”兩種路徑。一方面,從學校層面,基于“6C”制定校本教師領導力提升計劃,營造權利共享和共同決策的文化氛圍,激發教師領導潛能;另一方面,建構有組織、有活力的校內+校際學習型共同體,激勵教師自主學習和跨界閱讀;充分利用培訓提升教師領導的可行能力。
(一)賦權促發展:培養教師領導者
結合高質量教育背景,透視學校發展面臨的挑戰和要求,對人才的獲取和發展是校長的主要職責。由于傳統的“自上而下”的集權思想仍占主流,學校激勵性制度文化欠缺,組織溝通不夠順暢,致使普通教師的領導潛能無法有效釋放、遷移,[14]學校情境因素嚴重阻礙了教師領導力的提升。應賦予教師更多的領導自主權,構建具有關聯性(connected)、合作性(collaborative)、個性化(customized)、協調性(coordinated)、綜合性(comprehensive)、一致性(consistent)(簡稱“6C”)的校本化分布式領導體系。[15]作為學校的靈魂人物,校長必須有提升教師領導力的意識。積極“盤點”學校分布式領導現狀,厘清學校目前實行的分布式領導活動和政策,為教師專業發展創造的分布式領導機會,全力消除分布式領導的障礙,為教師領導力的提升制定配套的激勵體系。
近年來,各國圍繞教師領導力的提升而創造的諸多經驗值得借鑒。例如,英國《教師發展領導力框架》《行為與文化領導力框架》和《教學領導力框架》三份政策文件強調,教師領導力的培育和加強需要領導者轉變集權式領導思維,通過領導權的下放和分享,倡導學校既要關注教師的文化領導力、教學領導力,也要關注教師的協作領導力。[16]這些做法在激發中小學教師領導動機和提升領導力方面有重要參考價值。
(二)合作增能力:塑造學習型與合作型教師
教師作為教育教學知識的主動建構者,通過學習反思教育實踐中的真問題,實現自身的真改變,是其主動尋求教師專業成長的實踐路徑。通過調研發現,有的教師將學校內部的工作和校際的工作聯系起來,擴大學習網絡,實現組內和組間知識互通,推動大家進行合作學習,形成最佳實踐模式。這種協作文化有利于激發教師發展的心理動機,成為提升教師領導力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基于高質量教育背景,鼓勵教師成為主動學習者。在伙伴協作中深入理解教師自主學習的情景性、互動性、經驗性和生成性等特點,在課堂提質增效實踐中不斷反思、進步。另一方面,結合專業發展需要,拓寬個人知識面,跨界研究教育心理學、管理學、信息技術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知識,提高自身的學科整合能力,為教師領導力的提升奠定基礎。
(三)培訓促成長:提高教師領導的可行能力
阿瑪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一個人的可行能力 (capability)是指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17]可行能力是教師能夠積極主動、創新開發并有效盤活家校社資源的基礎。[18]從可行能力視角,教師領導力提升受阻本質上是因為教師的觀念轉變能力、自我規劃能力、專業成長能力、社會資本拓展能力以及參與學校領導的能力被剝奪。由此,建議教育行政部門與學校加強培養中小學教師領導的可行能力。
一方面,嚴選教師培訓機構。為了保證教師培訓質量,應嚴格遴選具有優質師資、有豐富培訓經驗、有服務能力的培訓機構,以保證教師培訓的效果。另一方面,豐富教師領導培訓內容,精準提高教師領導的認知能力和行動能力。具體而言,著力在培訓中轉變教師認知觀念是實現教師領導的重要前提;聚焦教師行動能力開發[19],通過專題講座+跟崗學習+訓后追蹤等形式為教師專業發展賦能;結合城鎮和鄉村教師專業發展不同興趣點和知識盲點,私人訂制培訓內容,為提高教師領導的社會資本搭平臺、創條件,從根本上提高教師參與學校領導的可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