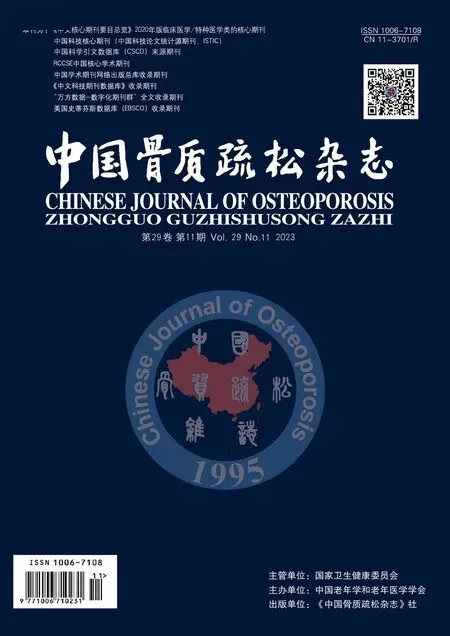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患者生存質量對心理痛楚的影響
耿貴敏 舒麗 陳靜 羅順梅 徐康蘭 王艷 劉國雄
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遵義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脊柱外科,貴州 遵義 563000
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OVCF)是最常見的脆性骨折,隨著人口老齡化,發病率顯著增加[1]。OVCF導致患者慢性背痛、失眠、活動減少、意志消沉,甚至生活難以自理,嚴重影響患者生存質量和身心健康[2-3]。心理痛楚(也稱為psychache)是精神痛苦的過程,是一種由負面情緒引起的情緒不安狀態[4]。相關研究表明,生存質量負向預測心理痛楚,生存質量水平越低越易引起悲傷、憤怒和絕望情緒,產生心理痛楚[5-6]。OVCF患者通常伴發背痛和身體功能下降,存在發生額外骨折的巨大風險,并使殘疾和死亡風險增加,容易產生“是他人負擔”的感受,即自我感受負擔[7]。自我感受負擔是心理壓力來源,且容易被忽視,從而引發心理痛楚。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自我感受負擔在OVCF患者生存質量與心理痛楚之間起中介作用。家庭成員提供更多的家庭關懷支持,利于疏導患者負面情緒(如內疚、自責、焦慮抑郁等),增強心理彈性,即家庭支持可能會調節負性生活事件與不良情緒的關系。對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家庭支持在自我感受負擔作用于生存質量和心理痛楚的過程中具有調節作用。本研究旨在以OVCF群體為研究對象,調查分析生存質量、心理痛楚、自我感受負擔與家庭支持的現狀與關系,從而為提高患者心理健康,優化患者的生存質量提供新的見解和科學證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對2021年2月至2023年1月我院收治的OVCF患者展開問卷調查。納入標準:(1)明確診斷為骨質疏松癥椎體壓縮骨折;(2)意識清晰,自主表達能力良好;(3)具備一定的理解或讀寫能力。排除標準:(1)具有與OVCF相關的神經功能缺損的患者;(2)因感染或腫瘤繼發椎體骨折的患者;(3)拒絕參與研究。本研究共發放227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25份,回收率99.11%。225例患者年齡48~93歲,中位數73(68,73.5)歲;男性49例,女性176例;109例主要照顧者為配偶,94例為子女,22例為其他。
1.2 研究工具
1.2.1簡明健康調查量表:該量表[8]包括生理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總體健康、活力、社會職能、情感職能、精神健康8個維度,共36個條目。“實際得分”為各維度所屬條目題值原始分的累加,按照(實際得分-該維度的可能最低分)/(該維度可能最高分-可能最低分)×100,轉換為0~100的標準分制。總分為各維度平均分,分數越高,生存質量越高。本研究對包括36個條目的簡明健康調查量表的信度進行了分析,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是0.603,測量條目的平均值范圍是1.209~5.151,量表的總體平均值是96.640(SD=8.894)。
1.2.2自我感受負擔量表:該量表[9]包括經濟負擔、情感負擔、身體負擔3個維度,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按5級評分,由淺至深賦值1~5分,1=從來沒有,5=總是這樣。總分范圍10~50分,分數越高,自我感受負擔程度越重。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是0.957,測量項目的平均值范圍是1.764~2.124,量表的總體平均值是19.560(SD=10.480)。
1.2.3心理痛楚量表:該量表[10]為單維度包括13個條目,每個條目按5級評分,由淺至深賦值1~5分,1=從不,5=總是。總分范圍13~65分,分數越高,心理痛楚感程度越強烈。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1,測量條目的平均值范圍是1.631~2.200,量表的總體平均值是20.053(SD=10.641)。
1.2.4家庭支持自評分量表:該量表[11]為單維度包括15個條目,每個條目只有2個選項,即“是”和“否”,分別賦值1分和0分。總分范圍0~15分,分數越高,家庭支持水平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36,測量條目的平均值范圍是0.369~0.747,量表的總體平均值是8.667(SD=4.010)。
1.3 調查方法
展開調查前,請有關專家對調查人員進行必要的培訓,包括調查態度和調查技能的培訓。在患者正式填寫調查問卷之前,首先由受過培訓的調查人員進行簡短的介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以及意義等,以獲得患者的知情和同意。由于大多數OVCF患者為老年人,可能對問卷理解有困難。因此,對這部分患者,調查人員一對一地進行問卷講解,確保患者有效理解問卷內容。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3.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分類數據以例數或構成比描述。對定量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以M(P25,P75)描述。采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應用SPSS Process插件依次選擇簡單中介模型(模型4)和包含全部調節路徑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模型59)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并對有顯著調節效應進行簡單斜率檢驗。P<0.05說明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橫斷面設計和同源數據可能存在方法偏倚問題,為減少影響,進行Harman檢驗。結果顯示,有14個大于1的特征值。第一因子解釋的方差為26.00%,小于臨界標準的40%[12]。因此,可認為本研究中不存在實質性的方法偏倚問題。
2.2 生存質量、心理痛楚、自我感受負擔及家庭支持之間的關系
225例OVCF患者生存質量得分為52(45.00,61.50)分,自我感受負擔得分為15.00(10.00,26.00)分,心理痛楚得分為26.00(16.50,31.50)分,家庭支持得分為9.00(6.00,12.00)分。Spearman秩相關結果顯示,生存質量與自我感受負擔、心理痛楚呈負相關(r=-0.547、-0.645),與家庭支持呈正相關(r=0.347);自我感受負擔與心理痛楚呈正相關(r=0.455),與家庭支持呈負相關(r=-0.423);心理痛楚與家庭支持呈負相關(r=-0.243)。
2.3 自我感受負擔的中介效應
自變量生存質量對因變量心理痛楚的負向預測作用顯著(β=-11.173,SE=0.053,t=-11.173,P<0.001),加入中介變量自我感受負擔后,預測作用依然顯著(β=-0.416,SE=0.058,t=-7.206,P<0.001)。另外,生存質量對自我感受負擔負向預測作用顯著(β=-0.557,SE=0.053,t=-10.553,P<0.001)。自我感受負擔對心理痛楚正向預測作用也顯著(β=0.317,SE=0.088,t=3.620,P<0.001)。見表1。此外,生存質量對心理痛楚的直接效應及自我感覺的中介效應的 Bootstrap 95%CI均不包含0,表明生存質量不僅能夠直接預測心理痛楚,而且能夠通過自我感覺負擔的中介作用預測心理痛楚,中介效應占29.73%。見表2。

表1 自我感受負擔在生存質量和心理痛楚的中介效應回歸分析

表2 自我感受負擔在生存質量和心理痛楚的中介效應Bootstrap檢驗
2.4 家庭支持調節的中介效應
生存質量與家庭支持的交互項對自我感受負擔的影響不顯著(β=0.012,P>0.05,95%CI:-0.013~0.036)。生存質量與家庭支持的交互項對心理痛楚的影響顯著(β=-0.036,P<0.05,95%CI:-0.064~-0.009)。自我感受負擔與家庭支持的交互項對心理痛楚的影響顯著(β=-0.029,P<0.05,95%CI:-0.057~-0.001)。見表3。家庭支持的調節作用中介模型圖見圖1。

圖1 家庭支持的調節作用中介模型

表3 家庭支持調節自我感受負擔對生存質量和心理痛楚的中介效應回歸分析
2.5 簡單斜率分析
在低、高家庭支持下,生存質量對心理痛楚的預測作用顯著(β=-0.281、-0.572,P均<0.05)。在低家庭支持下,自我感受負擔對心理痛楚的預測作用顯著(β=0.424,P<0.05),在高家庭支持下,自我感受負擔對心理痛楚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191,P>0.05),說明在低家庭支持時,OVCF患者的自我感受負擔增加會加劇心理痛楚。見圖2。

圖2 簡單斜率分析
3 討論
OVCF影響超過30%的75歲女性,其中甚至50%的85歲以上女性,在人口結構轉變和預期壽命增加的背景下,OVCF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公共健康問題[13]。OVCF與多種不良事件相關,如慢性致殘性疼痛、體力活動受限、進行性駝背、神經損傷、功能喪失和娛樂活動減少[14-15]。由于駝背或身高下降和活動受限,OVCF患者容易出現自尊心減弱、內疚、自責、焦慮、社交孤立、自我價值感降低等一系列負面情緒,長期的負面情緒轉化為心理障礙,嚴重損傷心理健康[16-17]。《“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重視國民精神和心理問題管理的重要性,特別提出要加大對重點人群的心理問題早期識別和及時干預[18]。大部分OVCF患者屬于老年群體,也是“重點人群”,不僅要關注其生理癥狀,也要重視心理健康。故本研究調查了OVCF患者心理痛楚現狀,同時分析可能存在的潛在中介作用和調節作用,為解釋OVCF患者心理痛楚的影響因素提供新的證據。
生存質量反映了個人福祉的所有方面,包括健康狀況以及環境、精神和經濟問題主觀感覺和總的滿意程度[19-20]。本研究顯示,OVCF患者心理痛楚得分為26.00(16.50,31.50)分,處于中等水平,且生存質量可以直接負向預測心理痛楚,與文獻[5-6]報道結果相符。提示OVCF患者生存質量越低,即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生理、心理、精神的主觀感覺和滿意程度下降,從而會產生精神痛苦、絕望、孤獨,甚至產生自殺意念等負性情緒體驗,心理痛楚水平提高。此外,本研究還顯示OVCF患者自我感覺負擔正向預測心理痛楚,生存質量可以通過自我感受負擔間接影響心理痛楚,即生存質量越低,自我感受負擔水平越高,心理痛楚程度越高,自我感受負擔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1的中介效應得到驗證。可能是OVCF患者通常背部肌肉無力,脊柱活動能力下降,且腰背部的劇烈疼痛,需要長時間用胸腰肢具固定或臥床休息,極易繼發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褥瘡等并發癥[21],對患者的軀體、心理、經濟和社會功能等多方面造成嚴重的影響,生存質量降低。另外,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如洗澡或穿衣困難,依賴于家庭成員的照料,同時,骨質疏松癥普遍存在病程長、較難治愈、高費用等特點,長期治療加重患者及家人的經濟負擔,產生拖累家庭而成為家人的負擔的心理感受[22],增加心理壓力,加劇心理痛楚。由此可見,家庭支持在其中存在一定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支持在生存質量→心理痛楚和自我感受負擔→心理痛楚路徑均發揮調節作用,假設2的調節效應得到驗證。簡單斜率檢驗法進一步探究家庭支持的具體調節機制,在調節生存質量→心理痛楚路徑中,隨著生存質量的增加,心理痛楚在不斷降低,高家庭支持的直線斜率>低家庭支持的直線斜率,提示隨著家庭支持的提升,生存質量對心理痛楚的影響在增強,即與低家庭支持相比,高家庭支持條件下,生存質量對心理痛楚的影響更強。在自我感受負擔→心理痛楚路徑中,隨著自我感受負擔的增加,心理痛楚在不斷增加,低家庭支持的直線斜率>高家庭支持的直線斜率,說明家庭支持反向調節自我感受負擔和心理痛楚的關系,即低家庭支持條件下,自我感受負擔增加會加劇心理痛楚。心理和社會因素可以通過影響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來緩解或加重疾病的癥狀,從而影響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和預后[23-24]。家庭為患者提供精神和物質支持,與患者有更多交流,即有效的家庭支持對改善患者生存質量和增強自信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能夠顯著提高患者的適應能力,鼓勵患者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減輕自我感受負擔和心理壓力,從而緩解心理痛楚[25]。
綜上所述,OVCF患者生存質量可以直接影響心理痛楚,也可以通過自我感受負擔間接影響心理痛楚,家庭支持對這一中介過程發揮調節作用,低家庭支持時,OVCF患者的自我感受負擔增加會加劇心理痛楚。然而,本研究存在局限性,如數據是在單個中心收集的,這限制了研究結果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并且可能存在一定偏倚。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縱向或實驗設計,結合訪談的混合方法來進一步驗證目前的研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