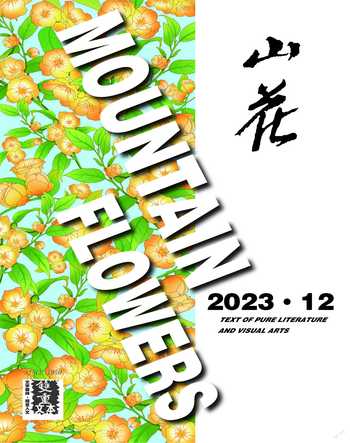修文陽明洞記
舒飛廉
今年八月底的一天,仿蘇軾《前赤壁賦》的說法,是“癸卯之秋”“七月既望”,我在貴陽市云巖區的一家酒店里醒來,早上六點鐘,天蒙蒙亮,窗外樓林間飄灑著細雨。鴻蒙初辟,混沌夢覺,我記起此行的一個籌劃,趕緊起床沐洗,襯衣長褲,運動鞋,往背包里放上礦泉水,一個人坐電梯,走出空寂的酒店大堂。站在大堂外的門廊里,風涼雨密,有七八位比我更早起來的游客,正在等前來接應的巴士,他們今日打卡的目的地是黃果樹瀑布,電視劇《西游記》里,孫悟空一受挫折,即想歸隱的“水簾洞”老家,現在已成網紅景觀。他們說,昨天的游客,摩肩接踵,前胸貼后背,好像擠北京的早高峰地鐵,花三四個小時,才走完行程。我心里想,這樣的人流,恐怕得由孫行者將全身的猴毛拔出來嚼碎,才幻化得出來。胡思亂想間,我由手機APP里叫來的出租車已經停在酒店門口的車道上,上車的時候,與師傅確定行程,往修文縣陽明洞,六十余公里,兩百元左右,走國道,大概是五十多分鐘。
師傅介紹說姓范,范偉的范,停頓片刻,又說是范仲淹的范,卻并沒有范偉的能言與范仲淹的豁達,一意操心去龍洞堡機場接下一位客人,半開著車窗,沉默地開車,一路冷雨里穿橋過隧,經過一個又一個奇崛頓挫的山丘。果然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的貴州,可以想見五百余年前王守仁得罪劉瑾,下錦衣獄,出首都,抵余杭,過江淮,入江西,走湖南,取道沅湘,而由平溪衛(今玉屏)、偏橋衛(今施秉)、鎮遠、清平衛(今凱里市清平鎮)、興隆衛(今黃平),一路西行,至修文龍場,來就驛丞之職,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沖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郁攻其中”,凡四千余公里的旅程。其中舟車勞頓,艱難險阻,九死一生,讀到他的《瘞旅文》,是可以想見的。比較起來,我們高鐵動車,機場高速,國道盤盤,朝發暮至,就好像是唐僧西游步步艱辛,悟空往還,卻只需要一陣筋斗云。
來到景區的時間是八點左右,而景區開放的時間是八點半。晨雨初歇,在門前“知行合一”的牌坊下,隔著柵欄,在持筆靜立 “致良知”石上的陽明銅像前徘徊既久,我結識了一對中年夫婦,男子清瘦、短發,戴棒球帽,女人盤發、連衣裙、微胖,我幫他們倆拍完合影后,男子介紹說姓吳,浙江余姚人,做生意的,專程來參訪“先生”。我問他夫人是何等生意,她微笑著說,是開餐飲的連鎖店,在國內也有一百多家了。景區開閘,檢票,我就是隨同這對溫和知禮的商人夫婦一起入園的,我們互相指路,此外也不多話,并沒有切磋討論的心思。我心里想,王陽明來此“居夷”有三年,哲人已去,他留在草木山石中的靈識與氣息,未必就完全泯滅了,我們在此盤桓的時間,多半也只有一兩個小時,說不定也能夠體驗到一點“未發之中”,這大概就是吳先生所說的“參訪”之“參”的誠意?
我仔細讀過《何陋軒記》與《瘞旅文》,由文本里想象出來的陽明洞大概是叢棘石穴,以陰以濕,昏黑的蜈蚣嶺,“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實際上,當下這片山林開辟成旅行的園區,已經是花樹羅列,廣場整飭,屋舍儼然,只是繞向棲霞山后山的青石路,平緩曲折,在樹木的掩映下,滯留著黎明的雨水,尚有一點陰黑之感,至于狐虺,恐怕是早已絕跡,以連鎖店老板娘的表揚,是蚊子都沒有一個。治理成這個樣子,園區的負責人還不滿意,工人們正在封閉整修君子亭、賓陽堂、陽明祠,我們能夠參觀的,大概就是何陋軒、陽明洞與新修的“王陽明紀念館”。我們在紀念館里觀看王陽明生平的展覽,同行的還有一隊穿著漢服的孩子,絳紅色的衣服,黑帽子,的確有一點像明代的書生。紀念館出口側廳的書店不錯,在陳列的種種“王學”圖書里,我看到了陳來先生的《有無之境》與鄧艾民先生的《傳習錄注疏》,我特別買了一本《傳習錄注疏》作紀念。賣書的小姑娘說,這是最后一冊,已經有破損,這也說明,來“參訪”的游客還是蠻有眼力的。我推薦給吳先生的書是《有無之境》。何陋軒也好,我們氣喘吁吁地爬上去,薄陰的天光正好由軒外映照進來,說明何陋軒的確是在東山之上,旁邊的陽明洞稱之為“東洞”是有道理的。因為光線映照在臉上,所以拍照很好,吳先生夫婦站在刻有《玩易窩記》《何陋軒記》《賓陽堂序》《銘一首》等詩文的石碑前拍照,我也請他們拍了好幾張。其中《銘一首》由清代道光年間的貴州巡撫喬用遷書錄,共六塊,嵌在軒堂正中的墻壁上,“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為學,在求放心”云云,用顏體大字刻寫出來,蒼勁古拙。喬用遷是我同鄉,據說做過咸豐皇帝的老師,湖北孝感人,家在孝南區楊店鎮,他來此山此軒,“求放心”,比我早兩百年。
陽明洞就在何陋軒的右側,有一小一大兩個前洞,加上西麓掩映在叢林中的更為狹窄的后洞,共有三個通道,分別長十余米,交會在正中的穹隆下,是為正洞,最高處三四米,周圍十余米,有人將之形容為兩室一廳,還是蠻準確的。石洞四壁曲折環繞,洞頂也高低錯落,為發育良好的鐘乳石所藻繪,千奇百怪,手捫目游,應接不暇。洞壁有清泉滴滲,匯成細流,令石筍、石幔、石柱瑩白潤澤,如膏如脂。所以“兩室一廳”一說,能象其形,恐怕還未能窮其神。我想到的比喻是鯨魚的大腦,由嘴巴里走進來,走到它寬闊的口腔里,鯨牙參差,腔壁粉白滑膩,別有狹長的通道,是往耳腔與鼻腔。東風也好,西風也好,大風起時,震動四周的林木,穿越大小連環的洞竅,嗚嗚然,啾啾然,淅瀝蕭颯,奔騰澎湃,窾坎鏜鞳,噌吰如鐘鼓,恐怕足以演繹歐陽修的《秋聲賦》,亦不亞于蘇軾蘇邁父子深夜探看過的石鐘山,也仿佛大海中的鯨歌。風如此,雨如此,天光云影莫不如此。王陽明來此穴居的時候,將之取名為“玩易窩”,“窩”字表達出來的,是對人事簡陋的釋然,對自然生機的喜悅,他研習《周易》以應世變,恐怕也會感發于此洞春夏秋冬、朝暉夕陰、風晴雨雪的萬千現象,“玩”乎,玩哉。
我們三個人在驛丞大人的“兩室一廳”里逛來逛去,想象著他在后洞里燒水煮飯,煙熏火燎,在前小洞中鋪蓋過夜,夏天蚊聚如雷,冬天寒風呼呼,在前大洞前設案讀書,一燈如豆,星月在野,大洞里會友講學,琴編圖史,講誦游適,“動心忍性,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從前來這里探訪索玩的游客估計也會有我們這樣的想象,他們中間,更有不少人有在石壁上刻寫“到此一游”的惡趣味,像安國享刻的“陽明先生遺愛處”,羅汝芳刻的“陽明別洞”,龐霖刻的“奇境”,當日抗戰將士來游,也刻有紀游壯行的文字。由明末至今,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的摩崖補丁,大概有四十余處,這些致敬的痕跡固然是真心誠意,但跑到人家的客廳里涂畫,也不能說是很講禮貌吧。“陽明先生遺愛處”七個大字刻寫在大洞的洞口,好像是刻在鯨魚的右邊臉頰上,其下有兩只鼓形石凳,我與吳先生分別坐在石凳上,我們身旁的臺階封閉,向上就是山頂上正在丁丁維修的陽明祠。吳先生不太同意我鯨魚嘴的擬像,他說:“我覺得陽明先生說‘窩,可能也想過一個‘心字。你看‘心字的三點,是三個洞口,里面斜勾,一個窩,就是廳室,陽明洞就是一個‘心字。”我覺得他說得好。《西游記》第一回,悟空到西牛賀洲拜菩提老祖為師,他們學習的地方,是在“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以“心”為情境,也蠻像這個棲霞山上的陽明洞的。吳承恩比王陽明晚出生三十余年,可能沒有像《西游記》劇組那樣來貴州“居夷”的經歷,但他多半是研習過“心學”的。唐僧師徒西游“求放心”,也是陽明之徒的“來爾同志”。孔子的學生里,有顏回、曾參一類的讀書種子,也有子貢這樣的商人,安知私淑陽明先生的徒子徒孫里,就沒有老吳這樣開連鎖店的餐飲大亨?陳來先生解釋“心即理”,心之本體,心體,將之分析成“至善者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即是天理,誠是心之本體,知是心之本體,樂是心之本體,定是心之本體,惡者失其本體”,萬物歸心,修習成就如此“主體”“個體”,官也好,士也好,商也好,都可謂街巷中的圣人吧。圣人們固然要在“心”形的山洞里冥思苦想,領悟之后,終究還是要離開山洞,往山下的道路與街巷中去,赴湯蹈火救國家也好,九九八十一難除妖魔也好,積丹于市廛也好,實踐第一。
我們動身下山。點開叫車軟件,我估計趕得上貴陽酒店中的午飯與下午的會。吳太太在山道上已經等我們有一會兒了,吳先生說以后要常來這里,今天遇到一個陰天,天晴的時候來,春天的時候來,體會都不一樣,可惜貴陽不太下雪,如果雪天里能來訪問陽明洞,雪光映照的陽明洞,是何等的光明。我跟在他身后,走在青石板上,心里想,他要是寫文章,估計也會有開一百多家連鎖店這般的成績,“修文陽明洞記”這樣的文字,他會寫得好。無論如何,我們這些游客來或不來,陽明洞總會有被朝陽、晚霞、明月、星辰、清霜映照的時刻,在這樣的時機,它都能夠沉浸在萬象森嚴的源發的宇宙之中。我也想再次訪問陽明洞,除了補上君子亭、賓陽堂的缺憾,我還特別想去觸摸一下它們周圍的那些古樹,那棵“文成柏”,據說是王陽明手植,迄今五百一十五年,高三十余米,仍根深葉茂,蒼翠如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