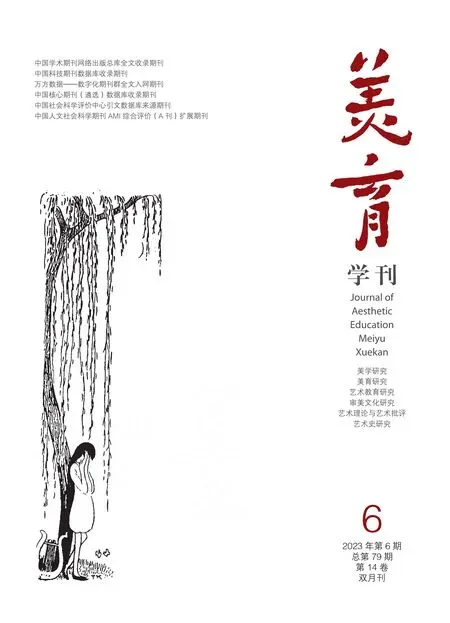溫克爾曼美學中的自由觀
孫霄宇
(洛陽師范學院 美術與藝術設計學院,河南 洛陽 471934)
溫克爾曼(J.J. Winckelmann,1717—1768)在探討希臘藝術繁榮的原因時,認為自由是核心因素,該因素不僅包含氣候環境,還具有相當明確的政治內涵。在談到政府形式時,認為從中可以強烈感受到自由民主的激勵力量,例如“民主政權、全民參與”使每個公民和國家本身的精神都得到了提升。[1]自由作為一種動力原則,是理想社會的根源,不僅利于文藝的培養,造就審美意識,也在希臘人的精神層面發展了穩固的自由心態,從而造就了民眾之間的和諧,形成沒有相互限制的自由社會關系。(1)David Bindman, Ape to Apollo: Aesthetics and the Idea of Race in the 18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p.82; Ian A.M. Nichol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John Wiley &Sons, Vol.40(3),339-41.(Summer,2004),p.341.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對于希臘的自由環境因素及其對古希臘人自由心態的影響,溫克爾曼對兩者的態度有著明顯的差異,在后者中,和諧優美的思想以及自由所孕育的鮮明精神特征盛行于古希臘人的心態[1]58,并以身形美的自由形式體現了樸素的自然主義倫理觀,而藝術的繁榮則對應了這種自由觀的理想體現。
另一方面,溫克爾曼的氣候環境論以社會學方式說明了藝術繁榮和政治自由之間的理想融合,但也在兩者之間作出了區分。[1]57政治自由往往是藝術繁榮的前奏,但兩者并不同步,或者說藝術繁榮與政治自由的錯位暗示了一個有關不同本質的自由觀的區分。作為動力原則的政治自由,與藝術繁榮構成了歷史發展的興衰模式,也為古代理想的復興提供了參考。為了探明溫克爾曼的自由觀的屬性,本文將根據其主要著述的思路結構從自由的生成條件、形式、以及對藝術的方式作用等方面展開論述。
一、環境基礎中的自由觀
關于希臘的環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就指出,希臘的溫和氣候環境造就了寬泛的自由品質,是一種包含熱情與理智的綜合秉性。[2]18世紀中葉,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Del’espritdeslois)中討論了法律和氣候的關系,其中也表述了不同地理氣候對人的體質、性格的影響,指出因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宗教。在論及理想的地理環境條件方面,溫克爾曼遵循了亞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鳩的氣候理論,首先在《思考》(GedanckenüberdieNachahmungderGriechischenWerckeinderMahlereyundBildhauer-Kunst)的開頭便以“良好的趣味產生于希臘的天空下”盛贊了希臘的良好環境。在《古代藝術史》(GeschichtederKunstdesAlterthums)的前言部分關于“阿波羅”(Apollo Belvedere)的論述中也同樣認為:“在完好的所有古代作品中,這座年輕男性裸體雕像是古代藝術的最高理想。”他斷言:“藝術家是在完好的理想基礎中制作了該作品。”據此,他將希臘在人文藝術方面的出眾和埃及、伊特魯里亞、羅馬等其他民族作比較[3]6,并極力認為環境造就的自由氛圍是希臘文化優越性的關鍵因素。
在總結環境對人的發展的影響時,溫克爾曼認為適宜的氣候條件構成了自由的寬松環境,從而造就了希臘人優美的身形和良好的品位。他在《古代藝術史》中寫道:
通過自由,整個人民的思想如同從健康的主干生出高尚的樹枝一樣。相比在低矮的室內或任何受限的地方,一個習慣于思考的人的頭腦傾向于上升到更高的廣闊領域、開闊的大道或建筑物頂上。
在后續的維也納版本中,他做了進一步闡述:
自由是希臘人的偉大事件、政權更迭和模仿之母,希臘人自誕生的那一刻起播下了高貴而崇高的思維方式的種子;正如看到無邊的海面和岸邊雄偉的懸崖上跳動的海浪,這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使心智脫離于任何卑微的想法,所以在看到如此偉大的場景時,人不可能變得無知。[1]54
寬松的環境沒有惡劣的氣候限制,古希臘人的身心才得以枝繁葉茂,尤其這種舒適清除了心理上的障礙,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在享受自然的過程中,人的身心從功利性的需求中得以釋放,從而形成穩定的自由心態。相反,溫克爾曼在論及埃及時,堅持認為不幸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埃及的君主主義和保守文化,是僵硬的威權和停滯的象征。[1]54
環境因素不僅涉及氣候,還涉及一個國家的社會氣候所帶來的養分。這其中包括憲法和政府、思維習慣等方面。[4]在論及政治環境時,溫克爾曼認為自由民主促使了“哲學家、詩人和藝術家之間相互尊重的和諧社會關系”[5],是鼓勵希臘古代藝術繁榮的另一個環境因素。而藝術作為希臘文化整體的象征,被溫克爾曼想象成希臘自由的歷史的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的崛起、繁榮和衰落。然而,在溫克爾曼的論述中,希臘藝術史卻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結構,它并不在于政治自由如何理所應當為文化藝術帶來繁榮,雅典的民主如何促進藝術家的活躍,而是在于完全實現的藝術之美與政治自由之間的脫節。希臘藝術取得的無比成就帶來的美麗與希臘自由最活躍的階段不相符,自由是藝術繁榮的前奏,它為藝術的繁榮做準備,但兩者不可能是同步的。這其中內化了理想的歷史和無法完全克服的政治約束之間的緊張關系。
溫克爾曼認為藝術史是一個從起源、繁榮、改變到衰落的動態過程,而最經典的藝術時期處于政治自由和藝術衰落兩者之間,既不是原始階段的嚴肅狀態,也不是衰落階段的過度裝飾,在理論上,該階段克服了早期埃及藝術般的僵硬樣式的外來束縛,同時也還未沉迷于文化過度精致的腐朽。[1]53在這個意義上,藝術處在它最自由的時刻。
以前者為參照,自由意味著沒有阻礙。根據早期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通常在缺失政治權力的自然狀態下出發[6],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維坦》(Leviathan)“論臣民的自由”一章中輕松地認為:“自由意味著沒有反對而已。”(2)霍布斯:《利維坦》,第二十一章“論臣民的自由”。或者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人類理解論》(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中更加自信的表達:“自由意味著有能力按照自己心理的選擇和指導思想的行為。”[7]但相比政治權力的干涉或約束,在后者中,溫克爾曼率先意識到在政治自由的寬松環境中,同時也不應否認王室贊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這里,他表明了一種反宮廷、反君主制的意識形態,并以某種方式表達了對宮廷或王室贊助的負面看法。尤其針對希臘化和羅馬時期的君主,無論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還是奧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BC.63—AD.14),或是亞歷山大,盡管他們努力以開明的意圖來培養藝術,但他們都不能使其恢復到早期希臘城邦自由統治下的水平。關于哈德良的贊助,溫克爾曼寫道:
如果能夠將藝術提升到以前的輝煌,哈德良就是這樣做的人,因為他既不缺乏知識,也不缺乏主動性。但是自由精神已經從世界上退卻了,思想和名氣的源泉已經消失……哈德良給予的援助(Hülfe)就像醫生給病人開的營養藥,不允許他們死亡,但同時又沒有給他們任何生計。[1]56
在此,溫克爾曼以藝術被動依附于君主而失去活力,批判了王室贊助對藝術的自由精神所造成的威脅。這里不同于早期自由主義者觀點之處在于,從依附的角度來思考,自由的對立面不再是限制和約束,而是奴役,將藝術家對統治者的依附等同于被奴役。[8]
作為外在因素,政治環境并不像氣候環境那樣順理成章地對藝術產生積極影響,藝術繁榮既不來自政治援助,更不受政治環境的約束,甚至表明了兩者之間的不相容。從溫克爾曼的歷史觀來看,最繁榮的藝術時期與其外在動力根源——政治自由——在時空上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政治自由是如何鼓勵藝術走向繁榮的?這里則需要將政治自由理解為一種暗示或隱喻,從自由力量背后的希臘人的心態去考量。
二、美的意識中生成的自由觀
盡管溫克爾曼肯定了外在因素為追求自由所提供的寬松環境,但這是生成自由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并不足以構成自由的本質因素。在探討藝術的繁榮基礎時,溫克爾曼通過氣候論強調了一種與優美環境相匹配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并且認為這種方式不完全依附于環境所帶來的恩惠,而是作為獨立的意識貫穿于自由理想的方方面面。這種獨立意識同樣也存在于政治環境中,并且形成藝術繁榮的基礎。這其中包括不違背人性的習俗、制度、國家社會氣候等多方面養分,而不是宮廷所提供的單方面資助。這表明了最充分發展的自由理想是從古雅典民主政治條件與孕育這種習性的自由精神的結合中產生的。[1]58
現實中的希臘人雖然以理想的天然環境和自由的社會環境為基礎,以擁有天生的美好形象來匹配理想的環境,但在溫克爾曼看來,希臘人天生的美不僅伴隨著“良好的品位”,也來自希臘人對美的后天培養。根據科爾夫(Hermann August Korff,1882—1963)的解釋:“相比氣候環境的影響,溫克爾曼對古希臘的崇拜強調了對古希臘人和生活方式的欽佩。”[3]17在飲食方面,希臘人克制食欲以保持頭腦清醒從而有利于全神貫注地思考問題;為控制身體變形,斯巴達青少年每十天對身體檢查;為避免身形受損,阿爾基比阿德(Alkibiades,BC.450—BC.404)因拒絕吹笛子以防美貌的扭曲而成為典范并在雅典的青少年中廣為流傳。在穿著方面,寬松的服飾不會阻礙身體的自然成長和發展。在生育方面,希臘人會獎勵生育貌美的孩子,因為在他們看來,肉體的美如同天賦的才能和高貴地位一樣具有卓越的價值。[9]6-7
希臘人對身體的培養不單單是平凡的生活習俗,正如西蒙尼蒂斯(Simonides,BC.556?—BC.468?)或厄庇卡爾謨(Epicharmosc,BC.540—BC.450)的詩歌中所表達的對健康和肉體美的夙愿反映了舉止行為背后的內在觀念,正是這種觀念引導著希臘人走向自由。實際上,當溫克爾曼開始解釋外部因素如何鼓勵希臘自由觀念的形成和繁榮時,已經把這一觀念的兩個不同方面分開了。作為近代德國文化復興的模范依據,他需要從希臘人的意識形態中總結出一種終極的內部誘因。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自由觀念的先決性,溫克爾曼著作中的近神觀念更表明了一種高于自然的精神意識。
基于美好的身體形象,溫克爾曼還贊揚了敏捷的印第安人,其強健的體魄展現出的旺盛的精力和堪比雄鹿的自然野性,并以此與荷馬史詩中的英雄相聯系。[9]6在古希臘的習俗中,無論是奧林匹亞賽場上的競技選手,還是戰場上的斯巴達人,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法定的訓練,在奪得第一的目標背后,他們的夙愿在于成為“如同神一般的狄亞哥拉斯(Diagoras)”[9]5。
希臘人對神崇拜的現實意義在于,他們不僅在肉體上希望接近神一般的敏捷和柔韌,在心智上,這種意識更為強烈。為了達到理想的境界,這種努力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開始,并在神的面前立下盟誓:“相比頭上戴上王冠,更希望擁有美的肉體。”這種先天與后天完美結合所造就的不凡英雄形象,更孕育了超凡的近神觀念,古希臘人的這種信仰更像是一種高貴的意識形態,而這些都指向實現真正自由的主觀愿望。[9]6
在今天看來,這些帶有畢達哥拉斯的戒律(Pythagoras’s precepts)性質的觀念和堅忍(Stoic)意識仍然具有生活指導意義。這種審美意識源于對自身肉體的完善和心智的鍛煉,并對近代歐洲人影響甚遠。溫和明朗的天空給予希臘人的兒時成長以先天的積極影響,再與后天的體育鍛煉和運動競技相結合,從而造就了他們出眾的形象。[10]從廣義上看,希臘人對美和自由的認識是等同的,溫克爾曼不把自由寄托對外在因素,也同樣不把美限于單純的外在表現。然而,在他的敘述中,美的形象仍然是自由意識形態的重要證據來源,通過對希臘人的形象舉止和思想產物這些殘留證據的形象描述,我們依然能捕捉到他所強調的主觀自由意識。如果一定要從中找一個最具形象的表達,對于溫克爾曼而言,富有活力的美好肉體即是希臘人自由精神的象征,事實上,具有男子氣概的英雄形象也正是其著作中政治自由的隱喻,尤其是青年男子。正如著作中的論述所言,美好的形象實則暗示了良好的行為意識,即美德的集中體現。對此,柏拉圖的對話篇開頭也有相同的肯定:“雅典體操青年通過外表舉止和身形姿勢展現出一種適宜的高貴和令人崇敬的靈魂。”[9]10另外,在《斐多篇》(Phaedo)中,通過對美麗肉體的熱愛想象了美的理念,即將道德的美與善和肉體的美相結合。柏拉圖對美的感知在溫克爾曼美學思想的形成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柏拉圖的著作中發現以下事實——“詩和哲學對肉體的贊美”。并且和柏拉圖一樣,“在美麗的肉體中,發現了以美德完成的精神”[11]。在某種程度上,溫克爾曼著重關注了形象背后的德行觀念,對于具有自律性或者對自由追求有著明晰思想指引的希臘人而言,意味著從政者應具備的素質,從而在“美的靈魂一般發現于美的身體”的關系中,找到了政治自由的形象依據。
三、造型美學中的自由觀

在此,無論是分析哪種情節的人物雕刻,溫克爾曼整體上都以靜穆為特征,在不同人物背景下表達著通往自由境界的狀態。在個人層面上,自由意味著自主性,這顯然繼承了希臘習俗中的自然主義傾向,這種帶有堅忍主義色彩的觀點從美學角度已經被學界多次論述,意味著在感情動蕩中保持泰然狀態,從而確保造型的平衡與統一。在溫克尓曼的自由觀念中,具有主觀意識形態的自律性和積極性是男性雕刻中自主的動力原則,從人性的拉奧孔到神性的阿波羅,面對暴力始終根據自身能力條件保持美的形象,從而引導著理性和道德觀念走向非功利性的自由狀態。在這一點上,自由和希臘青年的崇高夙愿是一致的,在宣揚個人自由不受君主或暴力壓迫或約束的同時,體現了自由的獨立性,而并非被社會性財富和特權繼承所決定。[1]55
另一方面,在公共層面上,溫克爾曼的自由觀與自治相聯系,是用來反對缺乏自我約束和放縱的消極自由觀念,這是其思想中富有政治涵義的地方。在該前提下,他對“拉奧孔”的論述在公民層面上具有實際意義。拉奧孔為了維護城邦安全而對神背叛,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換取整體的自由,使崇高之美得以升華,體現了作為城邦自由的公民美德。這符合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的解釋:公民只能在“一個具有某種規范形式的社會,包括真正的自治”中自由。[12]即,如果公民要保證個人的自由,就必須盡可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公共服務生活,從而培養最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所需的公民美德。簡言之,公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應認識到,只有某些確定的目的才是我們追求的合理目標。[13]294-295溫克爾曼對雕刻靜穆而偉大的特征分析在自治方面確實引起了當時法國藝術界政治活躍成員的強烈共鳴[1]55,并在1789年革命時期更加明確的政治化背景下起到了重要的意識形態作用。這與盧梭的激進共和傳統是一致的,即將自由視為主動自覺的積極概念。
四、自由在歷史興衰下的變遷
個人審美的積極自由觀不僅與個人修為相聯系,并且通過身心的道德方式與公共服務聯系起來,觸及了政治自由的內容——公民美德。正是在這種強烈的精神體驗中,形成了最具活力的動力來源,然而,這種體驗卻是在政治自由缺失之時形成的,后來的經典藝術則是過往對自由追求的一種象征,暗示著對自由精神的召喚。
在此,政治與藝術之間首次出現了替代關系,在戰勝波斯人之前,不僅是政治正值外來勢力的入侵,古代藝術也建立在一個嚴格的古老模式,一種為保證人體的正確形象需要而制定的安全表現框架下。此時的自由激勵精神正是最活躍的,成為希臘藝術在古代進步的驅動力,這在建立和捍衛希臘民主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戰勝波斯人之后,希臘完全擁有了啟蒙和自由,與之對應的藝術也擺脫了古老模式的限制。古典時期開始迎來繁榮之時,這也是經過一段斗爭之后的放松時刻,但激發自由精神的活力已不再活躍。[1]58由此看來,自由的愿望在精神上最強烈的時刻是在自由最缺失之時,也是外部環境限制最多的時候,當文化自由隨著政治入侵的消失而出現時,希臘人的自由相對進入一個被動的狀態。并且這種替代在藝術從繁榮走向衰落時又將再次出現,即藝術開始衰落并失去自由時,也孕育著政治自由將再次崛起。
藝術與自由之間的一個更明顯的替代發生在溫克爾曼對后來的經典時期的敘述中,這正是他用來描述古代藝術理想的雕刻作品,古老風格的最后殘余完全消失在這些作品的自由流動的優雅形式中。當藝術美進入最強烈的精致狀態,恰逢希臘人第一次受到外來統治,他們在曼蒂內亞戰役(Battle of Mantinea)被菲利普的梅塞頓(Philip of Macedon)擊敗。根據溫克爾曼的說法,這是一種過渡期,完全意義上的政治自由不復存在,但它的缺失還未形成壓迫。自由仍然被希臘人銘記,但只是以藝術的形式作為一種幻覺而存在,[1]59《軀干》正是這樣的案例。這一經典后期的作品起源于古希臘藝術經歷的最后一次復興,是希臘完全被羅馬人征服之前的產物,可以理解為馬其頓和羅馬統治之間的過渡時期僅存的獨立和自由。這似乎是希臘藝術在失去自由之前帶來的最后的完美作品之一,它的敘事性加劇了希臘藝術衰落的戲劇性,在失去政治自由的最后殘余之前,它變成了描繪希臘文化短暫余輝的形象。雕像的自然殘缺又增強了這一刻的戲劇性,反過來又重新闡明了它目前的地位,表明它如此生動地所喚起的東西:“被肢解到極致,失去頭部、手臂和腿部,但它仍然向那些能夠洞察藝術秘密的人展示它的昔日美麗光彩。”[1]61-64
《阿波羅》和《安提努斯》在溫克爾曼的歷史敘事中也占據著類似的位置。在溫克爾曼的歷史敘事中,兩者都被指定為希臘作品,但兩者已經不是希臘藝術的最佳時期的作品,并且都與古希臘政治和藝術的衰落有關,兩者在羅馬帝國早期從希臘被掠奪或進口到羅馬,僅僅是因為與當時羅馬仿制品的執行標準不同而脫穎而出。眾所周知,尼祿(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曾挪用了大量的希臘雕塑來裝飾他的宮殿,因為此時的理想已經不能再被創造,而不得不從過去掠奪。在這種情況下,安提努斯僅僅是為復興希臘藝術所做的徒勞嘗試,雖然它的美麗與哈德良時期的藝術所達到的腐朽狀態形成鮮明對比,但它仍然只是希臘理想的一部分和不完整的體現。[1]64-65在經典之后,隨著政治自由的完全喪失,藝術走向精致化的裝飾形式。在君主的盲目介入,或如前所述的王室干涉下,藝術也步入慷慨贊助條件下的依附狀態,進入文化享受的腐敗階段,自由也從積極主動走向消極被動。
因此,溫克爾曼構想中的希臘自由理想是歷史性的,也是辯證性的。如同希臘人在現實中追求自由理想一樣,當下的殘余作品同樣以美學方式勾勒出曾經的自由跡象,但個人自由的積極意識隨著歷史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非抽象的藝術形式,并隨著兩次歷史替代對應著兩種內涵:一方面是積極的審美,其動力來自政治自由的斗爭時刻;另一方面是更被動的審美自由,在這種斗爭之后以感性的方式享受自由的快樂。兩者截然不同,卻緊密相連。
五、結語
溫克爾曼以一種看似矛盾的方式說明了個人自由與整體自由的融合,以及自由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變遷關系,呈現出對自由不同維度的思考方式。他對古代雕像具有強烈情感的描述與歷史敘事語境中所具有的其他功能是分不開的,而個人自由意識也正是宏觀事物興衰的來源所在,也許正是基于這一點,溫克爾曼是以個體生物的有機生長方式來看待歷史興衰的。于他而言,希臘人對真正自由的追求并不依賴于政治影響,對約束和限制的態度更不敏感,甚至沒有形成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他對自由的認知不在于“什么是自由的障礙”,而在于“什么能引導人們自由”。希臘人對美的追求產生自主行為意識,這對于他所處的啟蒙時代具有普遍的政治意義,而藝術審美中對自由精神的體現,在他的法國同代人的寫作中更為激進和明顯,堅持將古代藝術作為共和自由的典范,強調自由在共和國的決定性特征以及對公民的良性、積極作用。[1]55
自由在法國公共層面上的作用很難說是溫克爾曼所預設的,事實上,他對自由的理解在該層面上并不多,需要澄清的是,溫克爾曼仍然是從美學的意義上來談及自由的,自由的重點仍然是個人審美體驗,而不是構成這種經驗的社會和政治形式。歸根結底,溫克爾曼強調的自由作為一種意識狀態的經驗,更多地將他與德國理想主義哲學中的自由概念聯系起來,而不是18世紀革命者想象中的激進、世俗的反宗教承諾或政治概念。在這點上,他更接近孟德斯鳩所區分的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更強調個人意志的行使。這種自由觀更為廣義,好比古典理論中美的概念比藝術美的概念更具普遍性。當一切行為皆以美為目的時,希臘人從生活習俗的自律轉化為自治,自然主義的原始欲望滲入政治自由社會,對美的追求演化成積極的自由觀,從而實現對理想的無限接近。
以上正是溫克爾曼在藝術史中探索真正內心自由的目的所在,他需要將古希臘最強烈的自由精神體驗移植入德國的貧乏處境,為希臘理想在當下真正復興做準備。但在溫克爾曼的整體思想中,首先進入他視野的是美和理想,并將美學建立在倫理道德基礎上,與人類對幸福的追求聯系在一起。只有在觀念上將美與自由等同時,行為才會從約束和限制中得以解放,也只有這種積極的自由觀才能真正為溫克爾曼在近代德國文化復興中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這對于有待復興的德國文化階層來說,是在文化自信之路的經歷中尋求自由的能力,為“內在性”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這后來被洪堡定義為教養的內涵,是公民教育的核心所在,(4)教養真正自由包括:無目的性(Zwecklosigkeit)、內在性(Innerlichkeit)、學術性(Wissenschaftlichkeit)。參見Peter Watson, The German Genius, Simon &Schuster,2010.p.110; Marchand, Down from Olympus,p.31;關于溫克爾曼對藝術與自由之間關系的傳統理解與后來德國理想主義思想中發現的傳統理解之間的區別,參見M.Podro, 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1982,p.8。也正是歌德、席勒、荷爾德林等人提倡重新面對古希臘文化的意義所在。他們認為,正是在希臘古典文化里能看到這種現實化的自由:既作為個體也作為共同體,古典時代的希臘人全面而和諧地發展出他們的自由力量。[14]在這種前提下,即便沒有主觀或客觀上的強迫或限制,人們也會真正從事那些最有利于“人類繁榮”(eudaimonia)的活動,從而實現人類最深刻的目的。[13]296對人類而言,這種恒定的欲望——對美麗事物的追求無非是植根于持久幸福的愿望。(5)Antiquarisches und die Wissenschaft der antikenKunstvor und nach Johann J. Winckelmann, Die zwei Lebensh? lften Winckelmanns in Deutschland und in Rom.https://www.cartucce.ch/topcmsimages/Ver6098265-evkgt012vp22r1lqllfb54cus83.pdf.按照這種原則,這種愿望意味著所有人共同尋求的物質滿足和幸福,也正是完全和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