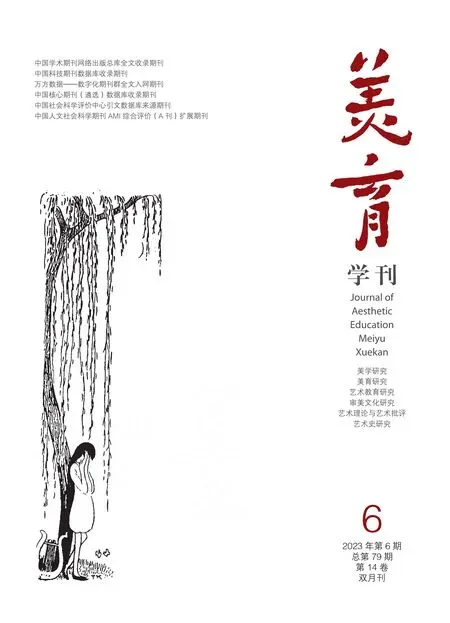可游之境與士人理想:中國山水畫的“敘事結構”
王天樂,葉思櫞
(中山大學 藝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山水畫作為中國傳統藝術文化的經典被不斷研究,不僅體現了其在藝術形式上的獨特性,也說明了其所蘊含的豐富思想與美學觀念。山水畫之所以能夠獨立藝林,引人注目,往往在于其畫面內在的視覺機制與敘事結構。(1)法國結構主義家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認為,一部敘事作品從來就只是由種種功能構成的,其中一切都表示不同程度的意義。這不是藝術問題,而是敘事的“結構問題”。詳見[法]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見張寅德:《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1頁。總結20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包括美國的一些中國藝術史學家在內,大多是從圖像風格、收藏鑒定及傳統的美學意蘊等方面對山水畫展開探討,這些探討的確推動并深入了中國山水畫的研究工作,使山水畫受到了空前的廣泛關注,但是對于山水畫的理論性探討,卻并沒有達到相應的高度與深度。其實,中國山水畫有其內在的敘事結構,這種“敘事”主要是由畫面中的點景元素的組織結構及其引發的想象情境產生的,其背后隱含了畫家特殊的審美意識與價值觀念。(2)如荷蘭歷史哲學家安克斯密特認為,歷史與審美意識有密切聯系。審美意識在歷史敘事中,不僅將歷史實在顯示于文本之中,還顯示了書寫歷史文本的意識根源。無論是歷史敘事還是圖像敘事,都必然受到作者的創作動機以及審美接受者的思想觀念與話語情境影響。因此,敘事關聯著社會結構和歷史語境。詳見[荷]安克斯密特:《歷史表現中的意義、真理和指稱》,周建漳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71頁。
對于“山水畫的敘事”問題,學者多從文本故事性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一直作為“表意”和“想象”功能的山水畫,自然和故事性的“敘事”有著較大出入,傳統的“敘事”也指一般意義上具體呈現的“故事”與“情節”,山水畫并非以展現故事情節為勝。(3)如米芾曾說“今人絕不畫故事”,米芾所說的“故事”指的就是人物畫中那般追求完整的故事事件或者某種風俗娛樂性的市井繪畫,他極力杜絕此做法,并提倡追尋意趣高古的士人之氣。詳見[宋]米芾:《畫史》,引自童強:《藝術理論基本文獻:中國古代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78頁。因此,本文并無意探討“敘事”的詞源意義,也并非從一般故事性的分析出發,而是從歷史話語和敘事建構的層面(4)美國學者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認為,敘事的模式將人類經驗放入時間中去理解,它關注的是人的意圖或目的及行為,是一種時間性的思維方式。敘事建構論認為人類主體是通過敘事及其各種方式建構而成的。在此基礎上,由人類主體的行為或活動而產生的人類文化世界,勢必普遍存在著敘事性。詳見王正中:《敘事建構論的四重關系》,載《當代文壇》,2017年第6期。對山水畫進行考察,即“敘事”在這里強調的是一種山水畫中的士人審美、群體身份等文化意識及話語建構的過程。其中,對于山水畫“敘事結構”的理解關鍵就在于山水畫中的點景元素,因為山水畫雖然描繪山水,但是畫面中非常重視與人跡有關的諸多因素,因“點景”元素的存在,畫面產生“可看性”與“可讀性”,進而構成敘事。因此,本文意在指出中國山水畫中點景元素的圖像演變與士人審美觀念之間的動態關系,說明山水畫是如何敘事,如何引發一系列的想象情節,又是怎樣一步步到達中國人理想的審美模式的。
一、想象與可游:山水畫的敘事審美特征
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說:“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1]說明繪畫是以特殊的視覺形象來實現其敘事與歌功頌詠的功能的,圖畫兼有傳記和歌賦的社會功能。而中國山水畫與西方的風景畫不同,中國的山水畫除了發展出一套完備的視覺語言外,還是一種可以引發觀者想象的圖像媒介。雖然18世紀的西方田園風景畫曾被人們當作觀看風景的旅游指南,繪畫中的風景可以影響人們對真實風景的向往與感受[2],但中國山水畫與西方的風景畫在審美欣賞模式上大有不同,西方的風景畫強調視覺的逼真性,而山水畫不僅用來觀看,最重要的可以使人心游其中。
英國的中國藝術史學家邁珂·蘇立文說:“中國山水畫比西方風景畫顯然包涵更多的內容。貫穿于中國山水畫里的理想源遠流長,在象征方面要豐富得多。詩要能吸引讀者進入由它所暗示的思想和感情的境界,山水畫家正是這樣,帶領我們來到‘象外’,飛翔于華茲華斯所說的‘無窮的象征’里。”[3]像山水畫中的一葉扁舟、一座草亭總能喚起觀者的無限想象。南朝時期的宗炳曾說,山水畫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4],中國的士人畫家想通過山水畫代替真身游歷林泉,進入畫面本身所設置的那種想象的空間中去。因此,中國繪畫的氣質并不留意畫面的視覺吸引力,筆墨韻味是觀者早已熟悉的東西,畫面仿佛只是一個示意、引導,讓觀者借著畫家的指引再次體會到那熟悉的神韻、味道。這是與西方經典畫家追求畫面逼真的視覺效果明顯不同的發展方向。[5]就如唐君毅所說那樣:“中國文學藝術之精神,其異于西洋文學藝術之精神者,即在中國文學藝術之可供人之游。”[6]這正是中國山水畫觀看模式的特別之處。
宋元時期的山水畫代表了中國繪畫史上的巔峰,這一時期的書畫講求“韻味”,士人畫家較不重視物象的形體輪廓和人物畫中復雜的故事情節,重在追求個人心性與象外之趣的表達,如蘇軾“不求形似,尚簡求韻”。日本著名美術史學家古原宏伸就曾認為:“中國的手卷繪畫相比日本的手卷畫來說,少了很大的‘敘述興趣’。”[7]如《富春山居圖》(圖1)與《鳥獸人物戲畫》(圖2)就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古原宏伸所說的“敘述”和米芾的“故事”含義一樣,也是指一種具體的故事情節。并且,他認為中國畫家更喜歡用象征的手法來表現一種可以令人想象的圖像,這在他看來就是一種“概念性”(5)這里的概念性,指的就是從一個文本出發,在繪畫中用暗示的手法交代故事的背景,不用連續表現故事的每一個情節或瞬間,從一個普遍的傳統認識中對故事情節進行概括化、觀念化的描繪。的敘事手法。[7]所以,傳統山水畫的敘事表達從不以復雜的具體“故事”為目的,而是趨向意義或觀念的“暗示性”,即通過畫中的圖像暗示達到畫家與作品、觀者之間的交流目的。這也正如邵雍所說:“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形容出造化,想象成天地。體用自此分,鬼神無敢異。詩者豈于此,史畫而已矣。”[8]因此,山水畫的“敘事結構”是一種觀念審美過程的構建與解讀過程,是內隱在畫面結構之中的,這從中國的詩畫關系中也可得到證明。

圖1 [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局部,636厘米×33厘米,現藏于浙江省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2 日本平安至鐮倉時代《鳥獸人物戲畫》局部,現藏于京都高山寺
例如,宋代盛行以詩作畫,并將此作為繪畫考試的形式。某次所試之題為“亂山藏古寺”,鄧椿《畫繼》中記載:“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9]一根“幡竿”就代替了古寺的深藏之意。正像清代吳喬在《圍爐詩話》中說:“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于聲色、故事、議論者為最上。”[10]繪畫也是如此,如毛聲山評《琵琶記》:“譬之畫家,花可畫而花之香不可畫,于是舍花而畫花傍之蝶;非畫蝶也,仍是畫花也。雪可畫而雪之寒不可畫,于是舍雪而畫雪中擁爐之人;非畫爐也,仍是畫雪也。月可畫而月之明不可畫,于是舍月而畫月下看書之人;非畫書也,仍是畫月也。”(《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因此,繪畫不必表現詩中所描述的具體事物或事件,而是以描寫某一事物和行為來進行象征、暗示。并且,畫家常會根據同一個文本作出不同的繪畫作品來,但是這些不同的作品都指向了某一個相同的主題——如山水畫敘事中的“隱逸”思想,這在宋元山水畫中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如美術藝術史學家班宗華指出:“宋代山水畫可以依據一個文本作出不同主題的作品,也因此成為一種敘事模式。雖然很豐富多元,畫家也可以用多種個性的語言來詮釋,并透過許多個性的視角來改造,但是它們終究難免是一場敘事。”[11]136班宗華所說的“敘事”的“事”,就不再僅僅指畫家對具體故事事件的敘述。他繼續解釋:“它可能是四個字的題目,也能是一篇散文或一個歷史事件,也可能只是一種心情、事件、季節、心態,如孤獨、平靜或迷醉;但是,無論如何,它都和文本一樣,雖然繪畫的特質可能會超越文本的特質,但是無論如何,繪畫都像文本一樣,告訴我們許多畫作所要表達的意義和主題。”[11]136因此,中國山水畫的“敘事”超越了具體故事情節,是一種可供觀者想象的審美敘事模式,其敘事的發生則主要是通過畫面中內在的點景元素展開的。
二、交流與可讀:山水畫中點景元素的敘事功能
從藝術本身的表達語言與敘事方式上,山水畫與文學文本不一樣,山水畫之所以能夠引起宗炳所說的“臥游”或觀者的想象并引發敘事,就是通過畫面內部各點景元素的組織與結構來展開的。山水畫中的點景元素給觀者制造了“交流”與“可讀”的敘事媒介,是引發畫面敘事的關鍵所在。
中國山水畫分為“有人之境”與“無人之境”,若將山水畫中的圖像元素按照其畫面屬性來進行劃分,可分為“自然元素”與“點景元素”兩類。“自然元素”主要指客觀世界中的山水、樹石、煙云、鳥鶴等自然物質和動植物;“點景元素”一般指具有人跡的圖像元素,如車馬、舟船、屋亭、橋梁與人物等。“點景元素”在山水畫的敘事發展中占有絕對主導的地位,這些圖像元素絕不單是一種簡單的“點景”物,它們有自身內在的敘事結構,并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它們除了可豐富畫面、構成山水畫不同審美意象等作用之外,還具有引發觀者想象、實現山水畫“可居”與“可游”的敘事功能。(圖3)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曾說道:“(山水)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出,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12]畫中的亭榭、小橋和人物,不僅起到豐富畫面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使山水畫得以展開可供觀者想象的敘事空間,也是畫家與觀者互動的中心媒介。

圖3 [宋]許道寧《漁舟唱晚圖》,48.9厘米×209.6厘米,現藏于美國納爾遜·艾金斯美術館
“點景元素”又可分為三種類型:“車馬與舟船”“屋亭與橋梁”以及“人物”。它們分別對應了山水畫“可行性”“可居性”與“可游性”的敘事功能。這三類元素不同程度地代表了士人思想觀念在山水畫敘事中的意向性投射。如“車馬”與“舟船”屬于人物出行的工具性元素,它們在畫中指示著某種空間上的可行性與可通達性。山水畫中有了車馬、舟船,就意味有道可行,有水可泛;而畫面中的“屋亭”與“橋梁”經常相連,暗示了人居的景象,屬于一種人物的棲居地或來往的空間朝向地,它們的出現為畫面增加了某種生活的“可居性”。若說車馬與舟船、屋亭與橋梁還是一種可行、可居的暗示階段,那么“人物”則是代表畫家自我形象的直接出場,也是山水畫的直接陳述,“人物”的形象與姿態關乎畫面敘事主題的走向,是一種特殊的人跡“行動素”,直接制造了山水畫的“可游”。這些圖像元素為畫面增添了一種引申到畫外的趣味性,使自然山水不再是不可進入的陌生場域,而是被人改造成一種可親近的理想自然之境。它們利用觀者的視覺結構與心理通感,以不同的形象與組成方式引發觀者對畫面的猜想與探游,共同構成了中國山水畫特殊的游觀體驗與審美模式,標示了山水畫的生命跡象以及人跡動向的細節[11]136。(圖4)所以,傳統的山水畫能夠被我們理解和解讀,就是由于這些內在的圖像元素對我們進行的“邀約”,引起我們的想象,一步步地實現與畫面的交流與對話。中國山水畫作為一種特殊的視覺圖像,當人們在對其進行欣賞時,就已經形成了一個看與被看的互動關系:山水畫內部圖像元素的結構關系則是被解讀和想象的關鍵。
因此,中國山水畫畫家通過賦予畫中的內在圖像元素特殊意義,與觀眾進行交流并引發敘事,這也是繪畫圖像與文字文本敘事的不同之處。所以,有學者認為,“在文學主題中,線性情節的語言敘事結構相對‘直白’,而藝術圖像的‘線性情節’深藏在圖式的結構中”。并且,“圖像敘事是母題、意象、題材在某個邏輯展開中表述已經發生事件的獨立結構,有了這個‘獨立結構’,主題才能被清晰地揭示出來”。[13]一般來說,山水畫的創作和一些散佚的文字和文學作品有緊密聯系,這也就涉及圖像與語言、畫與詩的關系。但是,文學敘事和繪畫敘事的方式并不一樣,文本需要有清晰的邏輯闡釋,如時間、地點以及人物的出場順序等,但繪畫并不需要,它是通過特殊的視覺語言、圖像元素來組織的。(6)關于繪畫和文本(詩歌)的研究很多,具體可參考萊辛的《拉奧孔》中關于詩與畫區別的論述。山水畫與其它繪畫一樣,是通過畫面中抽象的筆墨線條、色彩關系與復雜的空間結構并按照某種特殊的方式組合而成的,最后呈現給觀者的是一組使人產生想象的視覺形象,克萊夫·貝爾曾將其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14]。班宗華說:“文字本身為畫提供了一些可期待的元素及根據……郭熙告訴我們,如果看到畫中有一老者倚山崖而立,我們可以猜想他或許在描繪《論語》中所闡述的仁者樂山的內容。依據同樣的文本,郭熙本人可能會畫出不同的畫,但是其功能是相同的,畫的文本是相同的。”[11]136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智的,而圖像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說,文學是藝術發展道路上使人誤入歧途的向導,但在思想發展史上,它又是一個好的向導。因此,在研究山水畫的敘事層面上,我們不能再依據文本進行一比一的邏輯推導,而應該找到兩者在敘事框架中的共同元素以及這些元素在表達方式上的特殊性,比如漁父、孤舟和空亭等元素的特別意指。確切地說,就是要看山水畫中的圖像元素是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敘事的,即諸圖像元素的敘事機制。
山水畫中內在的點景元素是使山水畫展開想象與交流的重要因素,并且,山水畫不是對文學語言的二次加工,也不能將其視為一種文學故事的圖像對應,它應該是中國人一種特殊的審美觀念的集合,山水畫與文學作品有不同的敘事模式。特別是,山水故事生成的結構,對于接受者的理解與文化立場有著特殊要求,觀者接受和感受的方式,使得山水畫的敘事模式不斷發生改變并獲得新的含義。[15]山水畫之所以能夠使人進行想象與展開交流,還有賴于一定的文化語境,在山水畫的視覺形式與圖像演變之外,指向的正是畫家背后的審美意圖與行為動機。
三、身份與認同:山水畫中的士人話語理想
山水畫通過內在的點景元素引發觀者想象并構成敘事,其背后正是畫家審美觀念與文化思想的構建。一座小亭、一葉扁舟都代表了中國士人畫家群體心中的經典文化圖像。并且,山水畫的敘事也正是觀者對畫面進行解讀與理解的過程,觀者在理解過程中嘗試建立起與畫家本人的思想對話,我們也可以將其看作是對畫家思想建構的解構過程,這當然需要我們擁有一定的審美解讀與文化理解力。
日本美術史家小川裕曾將山水畫的造型手法歸結為“聯想”,并說山水畫如何構成聯想,重在觀者的參與。只有經過觀者的聯想,畫面上的線條和墨塊,才會被“看成”山水形象,甚至感到“生機”的表現。[16]其實這就是山水畫的敘事語境與交流方式。從話語建構的角度來說,任何一種繪畫樣式均可以敘事,但前提是要有一個相對的語境,也就是敘事“代碼”。不論是小說還是繪畫,藝術家在創作時都設定了一個“隱含讀者”,即特定觀眾,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觀者都可以讀懂文本和圖像的內在意義。但是,當一種觀者被圖像所吸引,并和創作者產生了共相的代碼時,圖像即可敘事。英國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也曾說,藝術的形式,也就是藝術品內部的純粹形式普通人是看不到的,難以名狀的特殊感情只有在有審美力的人的審視下才能出現。
尤其是在一些沒有具體故事情節的畫面中,要想理解畫面本身所要傳遞的意義,對圖像的敘事作出說明,就需要轉譯圖像內在元素的文化意義。此時,觀者的視覺經驗與情感想象則是影響作品敘事解讀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一些南宋的小景扇面畫中,常常有人物坐在山坡或閣樓中向遠方眺望,如朱光普的《江亭遠眺圖》(圖5)。畫面中沒有具體復雜的故事背景,而是描繪了茂盛的叢林掩映中的茅亭和亭內的士人,以及遠坡停靠的一艘小船,再遠處就是大片空白的湖面。至于畫中人在望什么,遠處的“空白”是水還是天,則需要觀者的想象與識別。觀者如若對南宋時期的文士生活與閑雅文化有所理解,就會明白這是一種文人士大夫的自我出場與生活寫照。又如在元代錢選的《歸去來辭圖》(圖6)中,錢選通過畫一位官員乘著一葉小舟回鄉的情景,參考河岸上的柳樹、在叢中掩映一角的茅舍和門前迎接的仆人等背景,觀者在讀畫的過程中,自動使情節連貫,點明了“歸隱”的主題。從畫中人物的穿著、舟船的外形、房屋的塑造中,我們能夠看出這與隋唐時期工整富麗的宮廷氛圍不同,而是一種文士之間樸素的隱逸風格,并能找出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并序》之間的圖文情境聯系。所以,只有建立好良好的溝通代碼,觀者才能明白山水畫中的特別“言說”。

圖5 [南宋]朱光普《江亭閑眺圖》局部,23.9厘米×24.4厘米,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圖6 [元]錢選《歸去來辭圖》,106.7厘米×26厘米,現藏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畫家向觀者展示畫面的同時,也隱含著畫家的思想觀念與身份意識,背后反映的更是他們的個人態度與文化立場。山水畫中圖像元素的自身演變和內在結構,其實反映的是畫家的一種文化選擇:一種士大夫的隱逸精神。例如,傳統中國的山水畫并不是單純的對景創作,在這些客觀景物進入畫面之前,畫家已經安排好了具體圖式。正如貢布里希那樣將中國山水畫視為一種文化沿襲的圖像范式,這種文化植入后的圖像范式深刻地影響到了畫家對客觀物像的選擇與敘事的方式。而且,中國山水畫并不像西方風景畫一樣為了追求某種視覺逼真的效果,也不是為了具體描述出一套完整連續的故事而達到教化人倫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種文化的選擇過程。在中國的山水畫中,畫家經常描繪深山茂林中隱現的一座小亭,或者是隨處漂泊的一葉扁舟以及坐在山坡望向遠方的高士等。這些圖像元素體現了一種敘事的引導性,并且,隨著山水畫歷史發展的演進,其自身形象也在不斷地發生改變,越來越趨向簡潔與樸素。因為山水畫要有人跡、人居的氛圍,但又要與熱鬧的世俗生活保持一定距離,畫家更傾向于營造一種清幽的“野逸之境”。而這實際指向的正是士人在圖式表達上的文化選擇問題。從山水畫敘事元素的演變中,能看出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是怎樣建構起隱逸思想的,是怎樣一步步引導觀者進入那個所設的審美境地的。
因此,山水畫的敘事結構其實就是士人的理想與話語建構過程,山水畫的“可游”也重在觀者對其的理解與解讀過程。美國芝加哥藝術史系教授詹姆斯·埃爾金斯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想要觀看一幅畫的時候而不去考慮他所隱含的歷史結構,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容易了。”[17]所以,我們就是要把這些文本中“隱含的歷史結構”找出來,考察敘事文本中的話語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荷蘭敘事學家米克·巴爾的研究視角來說,敘事其實在于一種“闡釋”的過程,并在闡釋的過程中加入了對文化研究與意識形態的分析。[18]而中國山水畫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中國山水畫不同于傳統人物畫有具體情節性的故事敘事,而主要是通過內在的圖像元素來引發觀者的記憶與想象,是一種特殊的非線性敘事。在山水畫敘事的過程中,還摻雜著抽象的筆墨語言與復雜的空間結構,以一種詩性的組織方式展現了這種不同于文字文本的視覺形象。這種組合后的圖像元素在引發觀者想象的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文人士大夫在圖像演變中的一種話語建構的過程。這些敘事元素都在以某種特殊的方式,或一葉扁舟,或一座小亭都在引導觀者,旨在傳達士人的一種特殊隱逸思想。而且,山水畫在人們觀看與被看的過程中,使得這種內在的隱逸觀念變得越來越清晰,成為士人群體在中國審美文化上的共同認同。山水畫的敘事結構實際反映的是畫家在圖像上的一種文化選擇和一套特殊的話語體系,甚至最終可以追溯到莊子“游”的思想。
從某種程度上說,山水畫是一種極其超前的藝術形態,它將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內在思想文化暗含其中,以諸圖像元素的內在組織與結構進行想象與象征。所以,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圖像學或風格學研究,而是一種敘事學研究,因為,我們需要將這些圖像元素系統地并列在一起研究,不是要看山水畫畫了什么,要看它們是被怎么畫,也就是關乎山水畫的表達方法問題,這是一種敘事結構的問題。我們需要透過這些圖像元素演變與組織,去探求那種暗含的文化思想與話語意識,尋找“誰在畫”與“誰在說”的問題的答案。
四、結語
可以說,不論是文人的閑趣自賞,還是士大夫的悟道歸隱,山水畫歷經千年發展,由兩宋成熟至明清流派迭起,構成了一套特殊的敘事結構與話語體系,深刻地影響著歷代中國人的審美經驗和價值觀念。聯系山水畫中的圖像演變與審美內涵的關系,縱觀山水畫的發展歷程,我們能夠深切地體悟到,正是這種隱形于深層結構內的話語意識建立了我們對中國哲學和民族文化的信仰與認同:一種對生命之道與自然境界的精神向往——士人在山水畫中建構了自己的理想之境與人生信念,觀者又在對山水畫的解讀中尋找到某種共同的精神慰藉。因而,山水畫不僅受到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垂青,也成為那些志在林泉者的精神圖載。對于中國山水畫敘事結構的研究,正是嘗試與經典傳統藝術的不斷對話與體會深思的過程,厘清山水畫內部圖像各元素之間的組織關系與背后的話語體系,就更能以一種清晰的視角理解中國山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