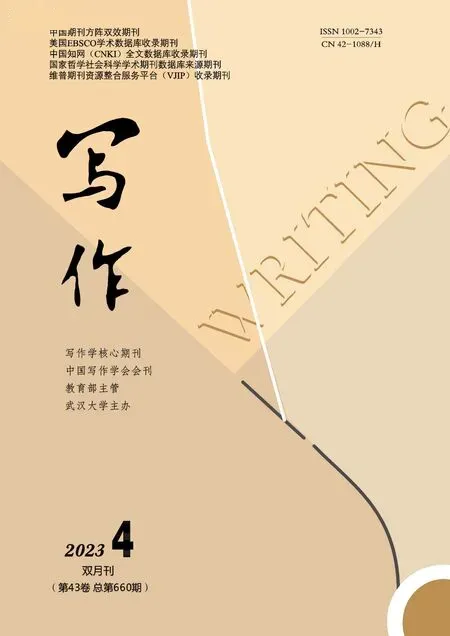寫作與講好中國故事新時代鄉土敘事研究專輯主持人語
葉立文
自新文學誕生之日起,中國作家的創作訴求就大抵不脫思想啟蒙。雖說在文學史發展過程中,這種啟蒙文學屢有消歇沉寂之勢,但時至晚近,中國文學的基本范式卻仍以發軔于晚清和“五四”,嗣后又歷經百年興衰而不墜的文學現代性模式為主。它主張“人的文學”,致力于對“人學”主題的無限張揚,雖在具體方法上形態各異,但書寫人物的存在困境,借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發掘異化根源,繼而表達人道關懷的文學理念卻薪火相傳,因此啟蒙文學的寫作倫理,迄今仍為當代作家所謹守。而這一啟蒙文學傳統最輝煌的時刻,當屬20世紀80年代。彼時風雷激蕩、云水飛揚,尤其是在1985 年前后,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橫空出世:莫言、賈平凹、余華、王安憶、韓少功等后來的文壇巨匠,無不奮發進取、發揚蹈厲,奉獻了一部又一部的當世名篇。及至90 年代,盡管文學的世俗化潮流已不可阻擋,但啟蒙文學針對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批判仍令世人警醒,因此這一彪炳史冊的文學傳統,至今依然具有蓬勃生機。
然而啟蒙文學還有另一面。我們注意到,啟蒙文學在發揮積極功用的同時,又因其對現代性義無反顧的追求而倍受詬病。基于一套文化霸權式的價值標準,啟蒙作家往往唯“現代”是舉、唯“理性”至上,通過貶抑、排斥和批判“前現代”傳統,以期實現“未完成的現代性”。這種壁壘森嚴的價值對立,無疑締造了現代性神話和啟蒙霸權等新的問題。因此可以說,如何走出新文學的啟蒙傳統,正視“老大中國”和“鄉土中國”的時代劇變,創作出符合新時代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業已成為近年來文學界所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此過程中,當代作家講述中國故事、表達中國經驗的集體訴求,無疑成了新時代文學區別于既往文學現代性模式的顯著標識。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作協近年來推行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與“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毋寧可被視為走出啟蒙文學傳統,重塑新時代文學面貌的變革之舉。
2022年7月,中國作家協會為推進新時代文學創作,在湖南湘西和益陽等地舉行了一系列文學活動。這些活動旨在號召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積極參與文學事業,努力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在這當中,如何結合新時代的現實語境,提煉混沌隱秘的中國經驗,講好深廣博大的中國故事,其實關涉的是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對民族未來的期許。因此不論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還是“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都意味著當代文學已經到了告別“老大中國”、重審“鄉土中國”的歷史時刻。鑒于此,本期專輯的三篇文章聚焦“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不僅從創作實踐層面解析新時代的鄉土小說,而且還欲借此討論新時代文學的具體內涵。
張智謙的文章,以貴州作家冉正萬的創作為研究對象,從“后鄉土”角度切入新時代文學,力圖闡明鄉土小說在新時代文學語境下的變化。在他看來,“那種將鄉土視為鄉愁寄托之所或寓言啟蒙之器的文學現代性敘事,不僅難以把握廣袤鄉村的‘后鄉土’性,更造成了文學對現實的遮蔽”。相較之下,冉正萬的小說“不是社會國家大事的寓言與民族史詩,而是對鄉土大地、鄉土生命、自我存在這三者之間割舍不斷的因緣進行敘述”。
王良博的文章,以羅偉章的非虛構作品為例,討論“真實性與文學性兼具的寫作方式”,如何“為當代中國民族史詩敘事提供經驗資源”。她認為羅偉章的非虛構寫作,“能夠有效介入真正的鄉村現場,從而緩解以虛構為主要特征的小說無力和現實建立有效連接的焦慮”。與此同時,這種寫法也讓新時代背景下的“新鄉村現狀、新農民形象因此得以建構還原”。
鄧鐘靈的文章,從分析楊志軍的《雪山大地》這部作品入手,探討鄉土小說在歷史、神話和史詩三個維度的書寫方式,認為歷史維度“補充完成了對青藏高原歷史變遷的敘述”,而神話維度則“寄寓著作者的生態理想和人格理想”。至于史詩維度,更是“以具有時代精神的史詩性作品回應著‘新時代山鄉巨變計劃’對史詩的呼喚”。三重維度“各有側重又緊密相聯,交織完成了對青藏高原山鄉巨變的多方位書寫,為此后鄉土歷史的書寫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