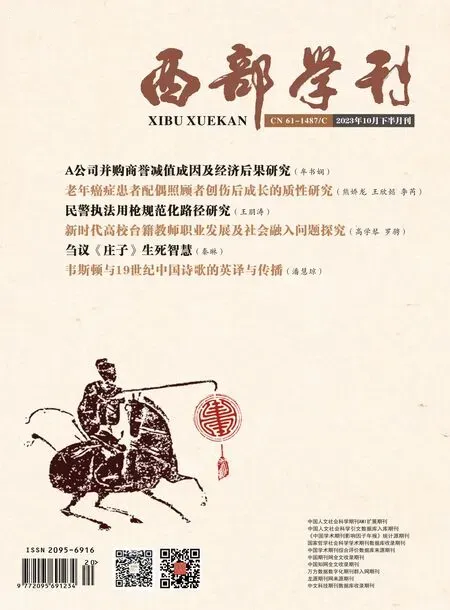“二元對立”視角下的電影《綠皮書》分析
劉蘊璇
(黑龍江大學 哲學學院,哈爾濱 150080)
電影《綠皮書》改編自《黑人旅游綠皮書》。此書是一本黑人“專用書”,書中標記旅行路線上能夠招待黑人的餐廳和旅館等。本片的劇情設定在1960年代肯尼迪執(zhí)政期間,是美國種族歧視和積極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最激烈的時候。在此期間,種族歧視在美國南方尤為嚴重。《綠皮書》講述的是一個黑人音樂家唐·雪利和他的意大利籍管家托尼·維勒歐嘉,從紐約到南方表演,一路上互相幫助,建立溫馨友誼的故事。兩人從剛開始的膚色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思維模式不同等方面互相質疑與不解,經過相處轉變?yōu)楹髞淼睦斫馀c互相陪伴。表面上看,這是一部溫暖的講述不同膚色之間友誼的故事,但其充斥著種族偏見、二元對立等后殖民主義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一、影片中二元對立結構
二元對立與后殖民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美籍巴勒斯坦裔批評家薩伊德名著《東方學》的出版,標志著后殖民主義思潮的形成。后殖民主義主要考察在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和殖民地間的文化話語權關系,其本質是對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發(fā)達國家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文化霸權主義的反抗。被殖民國家或民族意識到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讓他們有再次喪失文化主體性以及文化自信的危險,因而奮起反抗。后殖民主義更強調殖民關系的審美文化方面,又叫做“文化殖民主義”。后殖民主義致力于批判殖民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與二元對立的頑固現象。在薩伊德的體系中,《東方學》借用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話語理論體系將身份觀念和權力與地域表征聯系在一起。在“權力話語”的世界性話語中,他看到了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宗主國國家意識形態(tài)和邊緣國家政治之間明顯的二元對立。在這種悖論式的強權論述中,他國常常成為宗主國“強大神話”的軟肋,而東方國家的弱勢成為西方人力量的試金石。這一強權政治造就了所謂的“東方主義”,并以此來彰顯其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也就是“東方主義”所界定的“西方主宰東方”的政治圖景。
薩伊德將東方作為西方的他者而與西方形成了二元對立結構,體現在,西方是文明的,東方是野蠻的;西方是中心的,東方是邊緣的……。這些二元對立詞匯背后對應的是一種等級結構,一方永遠處于優(yōu)勢地位,另一方則永遠處于劣勢地位。這種二元對立結構在時間上會形成一種目的論敘述,通過設定現行的目的論的歷史敘事,得到“歷史從西方開始”這一結論。西方主體性的彰顯,預示著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區(qū)被擱置在被動地位,無法動搖。二元對立結構不僅在文學文本中顯現,也一樣存在于電影敘事中。在影片《綠皮書》中,二元對立在人物角色和權力關系中得到強有力凸顯。
(一)人物角色中的二元對立
二元對立結構在影片中,首先對應在黑人雪利與白人托尼的膚色上。種族主義者以皮膚顏色將人劃分為優(yōu)等和劣等,優(yōu)等是永遠統(tǒng)治劣等的。“白色代表著純潔、美麗和真誠,與善良、美德、智慧、勇氣等相聯系;而黑色則是墮落和邪惡的象征,具有各種嫌忌性的含義。”[1]在此結構中,盡管白人托尼家境并不富裕,但他毅然決然地扔掉了兩個黑人工人使用過的杯子。在白人托尼去應聘博士司機這個職位時,他對于雪利的牙買加裔美國人身份并不知情。當他進入應聘地點,奢華的裝飾家具讓他頗為意外。其中,關于象牙的藝術品象征著雪利與非洲的先民關系。在得知這份工作雖然高薪但不僅僅是司機這么簡單,需要為黑人提供生活服務時,托尼非常抗拒。在旅途中,托尼下車方便時拿走了自己的錢包,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雪利。在托尼眼中,盡管雪利是個有錢人,但他依舊無法改變對黑人固有的盜竊印象。這些視角都體現出黑人與白人的二元對立。
(二)權力關系中的二元對立
影片中的權力關系也通過二元對立得以凸顯。電影的開始由白人托尼引出情節(jié),雖然故事是以兩個人之間友誼溫暖故事展開,但從電影開始,就展示了這種“白人”為主的影片觀感。
影片以黑人鋼琴師與白人管家前往南方(越往南對黑人的歧視越嚴重)為白人演出為主線。每一次上臺彈鋼琴都是一種“凝視”與“被凝視”。“這種攜帶權力與欲望的看與被看或壓迫與被壓迫的權力關系既存在于男性與女性的性別關系中,也存在于白人與非裔美國人的種族關系中。”[2]白人通過聘請黑人雪利為他們演奏而獲得權力的主體性,在臺下觀看雪利的演奏使白人觀眾獲得視覺及體驗的優(yōu)越感。這種權力關系在影片中得到多方位體現。西裝店不允許雪利進行試穿;演出的場所不允許雪利在餐廳用餐;雪利只能住在《綠皮書》中的旅店內;雪利去酒吧喝酒被白人欺負……這些遭遇都解釋了黑人在社會中的被動地位。
無論是處于被動地位的東方,還是黑色皮膚的雪利博士,都充分證明,在西方眼中他們無法界定自身,在迎合西方界定的標準去定義自身后,獨特性由此喪失,文化的不自信從此貫穿始終。
二、二元對立中的身份混雜
(一)霍米·巴巴混雜理論
霍米·巴巴在混雜性批評策略中表明,文化殖民的過程就是模擬的過程,即主體對客體的模擬。認為抵抗后殖民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它,進而模仿它。模仿是“他者”逐漸向“自我”靠攏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他者”會形成自身特點,從而產生混雜。混雜隨之帶來一種新型過渡的閾限空間,既矛盾又模糊。在這種混雜中,兩種或多種文化碰撞形成“間隙閾限空間”。霍米·巴巴稱此空間為“混雜空間”或“第三空間”。“這種閾限的第三空間是一種具有臨界性質的邊緣化他者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的主體,由于閾限空間的居間性,是一種囿于本民族內的他者,亦是他民族內的他者,被雙方雙向視為異類。”[3]也就是說,在這混雜的第三空間內,如果主體本身無法達到多種屬性的平衡,就會卡在文化的間隙中,成為一種雙向的“異類”。影片中的黑人雪利博士同時具有美國精英以及黑人后裔的兩種對立身份,因此陷入雙重邊緣他者的閾限空間中,在此空間中兩種文化產生了深刻的沖突,雪利博士的“他者”身份由此顯現。
(二)唐·雪利作為白人眼中的他者
影片中雪利顛覆傳統(tǒng)黑人形象。雪利接受的精英教育,他談吐優(yōu)雅,才華橫溢。作為頂尖的鋼琴藝術家,曾被邀請到白宮演奏,影片中的南巡演出,也都是受白人邀請。他可以熟練使用多國語言,持有音樂、禮儀藝術和心理學三個博士學位。身為黑人,他甚至比許多白人都要優(yōu)秀,他的人物形象充滿了尊貴與富有,卻始終無法被白人世界真正接受。在白人眼中,雪利是名副其實的“他者”。在南巡演出中,臺上演奏的雪利是受人贊賞的鋼琴家,但在臺下他并不被允許和白人擁有同樣的權利和地位。他不被允許使用衛(wèi)生間,只好用40分鐘的時間驅車回自己的旅館;與雪利一同演出的白人同伴在舒適的餐廳享用晚餐,而他不被允許在餐廳吃晚飯,只好擠在一間狹小的“休息室”解決晚餐。雪利一直想用“黑人不是這樣的”觀點去改變一直以來對黑人的看法,可是他的忍耐卻變成白人變本加厲欺負他的籌碼。
(三)唐·雪利作為黑人眼中的他者
種族歧視在所難免,但被同族鄙夷的目光看待,才是最讓人心酸的。雪利不但被白人社會所排斥,就連他的黑人同胞也是如此。白人霸權文化的灌輸致使部分黑人喪失自我,進而開始排斥自己的同胞以及文化。雪利博士優(yōu)越的經濟條件和身份背景與底層的黑人格格不入。在黑人眼中,雪利同樣是“他者”。是與他們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人。雪利不聽爵士樂,不吃炸雞,一切有關黑人的固有印象都與雪利無關。當他和托尼看見在鄉(xiāng)間田野勞作的黑人同胞時,黑人同胞的眼神中的不屑深深刺痛了雪利的心;在黑人旅館,黑人同胞邀請他參與賭博游戲被他一口回絕,免不了讓他受到黑人同胞的奚落。雪利看起來就像一個穿著昂貴西服的“怪物”,他無法融入白人世界,同時也無法融入黑人世界。這些都是美國白人文化輸出的結果,他們讓黑人在自我認同中就產生“黑人低人一等”的意識,這種意識潛移默化地進入每一個黑人的內心,他們已經完全接受自己的膚色就是低人一等這樣的既定事實。由此引出雪利孤獨的性格特征,他經常酗酒失眠,在人際相處之間也顯得冷冰冰的,他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么,生活要這樣對待他。彌漫在空氣中的黑人“低人一等”的社會意識,深深地刺痛著雪利。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顯而易見,處于閾限空間中的雪利博士無法平衡兩種文化。當雪利試圖用不一樣的黑人方式對白人世界進行反抗時,他就已經失去了自我。他無法認同自己的黑人身份,除了膚色,雪利與其他白人無異。他試圖用“我與黑人”不同的方式獲得白人世界的認可,同時又走向了黑人同胞不認可的歧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雪利的雙重身份被撕裂,掉入間隙的尷尬境地,陷入自我孤獨之中。直到他打算開啟南巡演出,托尼的出現,雪利才在旅途中逐漸找到自我,獲得身份認同。
三、二元對立的消解與自我認同
雪利開展南巡演出,希望通過此次演出贏得白人世界的尊重。南巡演出的行動正好契合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的混雜性批評策略。在模仿的“他者”逐漸向“自我”靠攏的過程里,“他者”會形成自身特點,根據巴巴的觀點,一味模擬并不會產生身份的認同。只有在第三空間視野中,尊重不同的文化差異,建立身份協商才是消解身份認同危機的有效途徑,從而產生消解文化權力結構的方式。文化認同并非單向過程,從始至終為一種相互交融混雜的狀態(tài),直接把對方的文化給殖民同化的那種觀點根本不存在。所以身份協商尤為重要。在身份協商過程中,為了消除本質性,強調不同身份的混雜和協商,以此體現出身份的流動性,從而意義也就在不同身份之間進行流動,在此流動過程中,雪利實現了混合身份的雜糅,找到了自己恰當的位置。
影片中的身份雜糅在后續(xù)情節(jié)得以展現。雪利接受托尼嘗試炸雞的請求,兩個人大快朵頤,雪利學著托尼的樣子將骨頭拋出窗外,兩個人的旅途開始變得溫暖暢快,雪利也在這樣的舉動中逐漸獲得屬于黑人的自我認同。在阿拉巴馬演出前夜,雪利再次被拒絕在餐廳用餐,在經理提議雪利可以去附近專屬黑人用餐的“橘鳥”酒吧用餐時,雪利沒有忍耐,冒著賠付違約金的風險離開了。在“橘鳥”酒吧用餐時,雪利博士站上舞臺彈奏了他最喜愛的古典曲目,在以往的演出中,古典音樂作為白人不允許黑人彈奏的白人“專屬”曲目,雪利博士在舞臺上一次都沒有彈奏過。此時此刻,雪利博士成為了自己,這是他南巡演出以來彈奏得最開心的一次。隨后,雪利博士跟隨其他的黑人同胞開啟了爵士樂的表演,在“橘鳥”酒吧,雪利獲得了自己。演出結束,雪利博士猶豫再三決定主動前往托尼家與之一起過圣誕節(jié),孤獨的雪利博士在旅途中被兩個人的溫暖友誼所融化。
從開始“炸雞是黑人專屬”的刻板印象到開始主動嘗試,從對于“黑人的爵士樂”到后來的主動彈奏,從剛開始與親人的不主動聯系到主動去托尼家過圣誕節(jié),都展現了雪利博士的變化。“黑人如果迷失在白人主流文化中,遠離自己借以安身立命的黑色本性與民族文化底蘊,便會成為主流文化的犧牲品。”[4]此次的南巡演出以及托尼的陪伴使雪利博士打破了與黑人同胞的隔閡,他突破了自我,開始覺醒。雪利博士不再作為白人世界的他者,也從黑人同胞的他者中脫離,成為了真正的自己。此次南巡演出,托尼和雪利博士互相治愈,互相付出,進而改變了自身,收獲了跨種族、跨皮膚之間的友誼。在他們之間的二元對立得以消解,以此獲得了自我認同。
最初需要用“施坦威鋼琴”來證明自己尊嚴的雪利博士到后來主動驅車回家的雪利博士,這中間都表明了雪利博士這一路以來在自我認同的道路上砥礪前行。與托尼的相處使他意識到,能夠拯救自尊的只有自己。如果一味妥協與忍耐,并不會獲得自己想要的尊嚴和平等。只有先接受自己的皮膚,接受自己的黑人身份,站在這樣的視角下去抵抗,進行認同自我,才是有效的方式。
四、結束語
《綠皮書》作為2019年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采用了二元對立的敘事方式闡釋美國社會對于黑人的種族歧視和不公正對待。從開始的白人主體性“凝視”,到后來的雪利因為不平等待遇而拒絕為白人演出;從起初雪利不認同自己的黑人身份,拒絕一切黑人的生活方式到后來主動接納;從最初的雪利作為白人世界的他者以及黑人同胞的他者,進而達到最后的認同自我……這些都體現出在這樣的二元對立關系中,他者對于自身的審視和思考,以及做出的有效反抗。
根據霍米·巴巴的混雜性批評策略去看影片中雪利博士通過南巡演出抵抗種族歧視的意義。巴巴認為,不同文化在互相接觸的過程中是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關系,此過程中會瓦解二元對立關系,使殖民者處于一種貶低對方又好奇對方的模式中。白人對于臺下尚未進入演出狀態(tài)的雪利博士的黑人身份并沒有給予完全的尊重,依然差別對待雪利博士以及他的白人同伴。同時產生好奇,白人觀眾買票來觀賞臺上的黑人演奏鋼琴曲。雪利博士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托尼,兩個人互相改變,最后收獲了跨越種族之間的友誼,人物角色上的對立就此消解。在表演結束時,雪利借助托尼的協助,運用“反凝視”手段,向白人的不公正待遇發(fā)起了回擊,從而消解了二元對立之間的權力關系。在路途中,雪利博士開始認同自己,不再作為“他者”的存在,把自己置身于黑人之中,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出身不應該成為判斷一個人的標準。我們應該學會尊重自己,認同自己是我們用自己的力量去對抗不公最好的辦法。把自己置于尷尬境地,一定會適得其反。時間不斷前進,多元化發(fā)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流。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都迸發(fā)出耀眼的光芒。我們應該以平等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多元文化,相互交流,不斷學習,在成為更好的自己的道路上不斷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