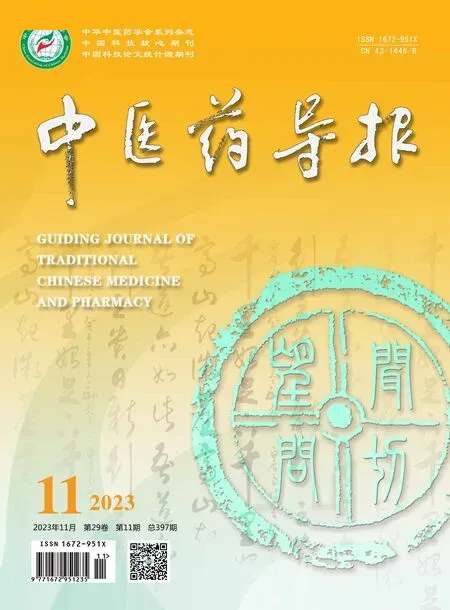網絡藥理學結合體內實驗研究藿香-龍膽草藥對治療鼻竇炎的機制*
藺 婷,熊 靜,蘭 超,田道法,,吳 婷,周振峰
(1.湖南中醫藥大學中醫藥防治眼耳鼻咽喉疾病湖南省重點實驗室,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省中醫藥防治眼耳鼻喉疾病與視功能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南 長沙 410208;2.岳陽市中醫醫院,湖南 岳陽 414000)
鼻竇炎(nasosinusitis)是發生在鼻黏膜及鼻竇黏膜的炎癥性疾病,屬于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病[1],以鼻塞、流膿涕為主要癥狀,可伴有頭面部疼痛、嗅覺減退或喪失等癥狀,臨床根據病程長短分為急性和慢性[2]。歐洲和美國鼻竇炎的發病率分別高達11%和12%[3];而我國的鼻竇炎發病率也高達8%[4-5]。以上數據表明,全球范圍內鼻竇炎的發病率日趨上升。
鼻竇炎在中醫學中屬于“鼻淵”“腦漏”范疇,中醫對鼻淵的認識歷史悠久。如《素問·氣厥論篇》就有“膽移熱于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的記載[6-7],指出鼻淵為膽移熱于腦所致。這是中醫對鼻淵病因病機最早的描述。《普濟方卷五十六》記載“夫腦為髓海……令膽移邪熱,上入于腦,則陰氣不固,而藏者泄矣,故腦液下滲于鼻,其證濁涕出不已”。隨后后世醫家在此基礎上對本病的認識有了較完善的認識。如清代醫家費伯雄所著的《醫醇賸義》記載:“腦漏者,鼻如淵泉,滑涓流涕,致病有三,曰風也、火也、寵也。”提示鼻淵的風、火、寵三因,火者多為肝膽熱盛所致。同時也指出“陽邪外爍,肝火內燔,鼻竅半通,時流黃水,此火傷之腦漏也”。上訴醫書中詳盡地論述了鼻淵與膽腑的密切關系。縱觀古今,眾多醫家治療鼻淵以“膽熱犯鼻,濕郁竅閉”立論,以清泄膽熱,利濕通竅為治法[8]。
湖南省岳陽市中醫醫院耳鼻咽喉科的自制藥藿膽鼻淵丸(湘藥制備字Z20190109000,曾用名龍膽通竅丸[9])臨床治療鼻竇炎效果顯著[10-11]。藿香-龍膽草作為藿膽鼻淵丸中的君藥,發揮了重要的治療作用。藿香,味辛、性微溫,屬升浮之品,具有辛溫通竅、祛濕化濁、除穢行氣之功效,是中醫臨床治療鼻淵的常用藥。如《外科正宗》中有關于“腦漏”的記載:“腦漏又名鼻淵……奇授藿香湯治鼻淵,黃水濁涕長流,致腦戶虛眩不已。用藿香連枝帶葉五錢,水一碗,煎七分,加公豬膽汁一枚和勻,食后通口服之,至重不過三服。如此藥苦甚不堪服用,藿香末一兩,公豬膽汁熬稠膏為丸,每服二錢食后白滾湯送下亦效。”近年來,很多醫家[12-14]在臨床治療鼻淵時都將芳香化濁之品藿香作為方中主藥。《本草綱目》中記載“相火寄在肝膽,有瀉無補,故龍膽之益肝膽之氣,正以其能瀉肝膽之邪熱也”。《本經逢原》記載“龍膽草……專瀉肝膽之火……凡屬肝經邪熱為患,用之神妙。……善清下焦濕熱”。龍膽草,味苦,性寒,歸肝、膽經,既能瀉肝膽實火,又能利肝經濕熱,瀉火除濕,兩善其功,切中鼻淵病機。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結合體內實驗探討霍膽鼻淵丸中君藥藿香-龍膽草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點,旨在揭示霍膽鼻淵丸治療慢性鼻竇炎的藥效機制。
1 材料
1.1 網絡藥理學數據庫和軟件 中草藥系統藥理學平臺TCMSP(http://lsp,nwu.edu.cn/tcmsp.php);有機小分子生物活性數據庫Pubchem(https://pubchem.ncbi.nlm.nih.gov);結構相似度預測靶點數據庫SwissTargetPrediction(http://www.swisstargetprediction.ch);全球蛋白質資源數據庫Uniprot(http://www.uniprot.org/);基因數據庫GeneCards(https://www.genecards.org/)、人類在線孟德爾遺傳數據庫OMIM(https://www.omim.org/)、人類疾病相關基因和突變數據庫DisGent(https://www.disgenet.org)平臺;繪圖軟件Venny(https://bioinfogp.cnb.csic.es/tools/venny/);檢索已知蛋白和預測蛋白互作關系平臺String(https://string-db.org/);Cytoscape3.8.2軟件;Metascape(http://metascape.org/)平臺;R語言軟件。
1.2 實驗動物 4周齡SPF級雄性SD大鼠24只,體質量(200±20)g,購于湖南斯萊克景達動物有限公司,動物質量合格證編號:202302210009;動物生產許可證號:SCXK(湘)2019-0004;實驗期間大鼠均飼養于同一環境下,保持室溫(24.0±1.0)℃,空氣濕度為55%~65%,環境安靜,大鼠自由進食進水,明、暗12 h循環飼養。動物實驗的大鼠均為麻醉后脫頸椎處死,實驗操作符合動物實驗倫理學原則,經湖南中醫藥大學實驗動物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批號:LL2023022210。
1.3 藥物與試劑 藿香(批號:221102)、龍膽草(批號:2208099)均由岳陽市中醫醫院中藥房提供,經藥劑科張禹主任藥師鑒定為藥物成分完全的道地藥材。克拉霉素片(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限公司,0.25 g/片,批號:H19990225)。脂多糖(lipopolysa ccharide,LPS)(批號:L2880)購自美國sigma公司;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ELISA試劑盒(批號:E-EL-R2856c)、白細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ELISA試劑盒(批號:E-EL-M0037c)、白細胞介素-6(IL-6)ELISA試劑盒(批號:E-EL-R0015c)均購自武漢伊萊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白介素-17(IL-17)ELISA試劑盒(批號:ml059373)購自上海酶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IL-17C一抗(批號:ER1911-25)、NF-κB p65一抗(批號:ET1603-12)、TNF-α一抗(批號:ER65189)和IL-6一抗(批號:R1412-2)均購自杭州華安生物技術有限公司;IL-1β一抗(批號:SAB5700678)購自美國Sigma Aldrich公司;二抗IRDye 680RD Goat anti-Rabbit IgG(H+L)(批號:D30110-05)購自美國Licor公司;三氯乙醛水合物(批號:C804539)購自上海麥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1.4 主要儀器 Odyssey CLX型多功能熒光成像儀(美國Licor公司);ELX800型全自動酶標分析儀(美國BioTek公司);JY-ZY5型蛋白轉印電泳槽(北京君意東方電泳設備有限公司);WD-9405B型水平搖床(北京六一儀器廠)。
2 方法
2.1 網絡藥理學預測
2.1.1 藥物化學成分與靶點搜集 通過TCMSP平臺搜尋藿香成分,設置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Availability,OB)≥30%,類藥性(Drug-likeness,DL)≥0.18,得到有效成分后通過其MOL.ID號搜尋藥物成分作用靶點。同時,將龍膽草成分名稱導入Pubchem數據庫獲得成分SMILES(Simplified Molecular Input Line Entry System)及化學結構式,將所得到的結構式導入到結構相似度預測靶點數據庫Swiss Target Prediction預測靶點。
2.1.2 “成分-靶點”網絡分析 利用Uniprot數據庫下載化合物Excel數據表格,運用“TRIM”函數優化數據,使用“VLOOKUP”函數匹配靶點基因名,并通過查閱文獻補充未匹配到的基因名稱,對得到的藥物化學成分相關靶點蛋白進行注釋。將化合物基因“Network”文件和“Type”文件導入Cytoscape3.8.2軟件進行網絡拓撲學分析,根據Degree值(基因的連接數量)調整靶點圖形、顏色、透明度和大小,構建“成分-靶點”網絡。
2.1.3 疾病靶點的預測 以鼻竇炎的英文“nasosinusitis”作為關鍵詞,在GeneCards、OMIM、DisGent平臺獲取疾病相關靶點,設置對象為“human”,使用“VLOOKUP”函數匹配靶點基因名。應用Venny軟件獲取中藥活性化合物作用靶點與疾病的交集靶點,作為藥物治療鼻竇炎的潛在靶點。
2.1.4 蛋白互作網絡(PPI)構建及網絡拓撲分析 將交集基因導入String平臺,得到蛋白互作關系。結果導入Cytoscape3.8.2軟件中進行網絡拓撲分析。隨后,把下載好的TSV文件導入Cytoscape軟件作蛋白互作網絡圖(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
2.1.5 GO和KEGG富集分析 運用R語言軟件對核心藥物作用靶點進行GO功能和KEGG信號通路富集分析。設置H. sapiens,選擇P<0.05,按P值繪制成柱狀圖,作可視化分析。同時,根據所屬通路將各靶點進行歸類,將信息導入Cytoscape 3.8.2軟件中進行可視化處理,構建“成分-靶點-通路-疾病”網絡圖。
2.2 動物實驗驗證
2.2.1 藥物制備 根據藿膽鼻淵丸[9]的處方組成,每劑處方中藿香8 g、龍膽草10 g,即人的劑量約為257 mg/kg。稱取藿香40 g、龍膽草50 g,加蒸餾水煎煮2次,將2次的煎煮液混勻,紗布過濾藥渣,放于冷凍干燥器中得到生藥質量濃度為1 g/mL的濃縮液。克拉霉素臨用時以生理鹽水溶解并配制成相應濃度。
2.2.2 動物分組與造模 將24只SPF級雄性SD大鼠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模型組、藿香-龍膽草組、陽性藥組,每組6只。對照組常規飼料和蒸餾水飼養,不作其他處理。其余各組大鼠建立鼻竇炎模型[15-16],腹腔注射10%三氯乙醛水合物(0.01 mL/kg)使大鼠麻醉,用鑷子取2.0 cm×1.0 cm×0.5 cm大小的鼻腔止血海綿塞入大鼠一側鼻腔內,隨后同側鼻腔內滴入1 mg/L的LPS 100 μL;對照組大鼠鼻腔內滴生理鹽水200 μL。
2.2.3 動物給藥與取材 根據人與動物間等效劑量[17]換算出各組給藥劑量。造模4周后,藿香-龍膽草組大鼠灌胃1 586 mg/kg藿香-龍膽草藥液2 mL;陽性藥組大鼠灌胃43 mg/kg克拉霉素片溶液2 mL;對照組和模型組大鼠灌胃2 mL生理鹽水。1次/d,連續給藥4周。末次給藥后12 h,10%三氯乙醛水合物麻醉大鼠,用血清分離管收集大鼠全血標本,并取新鮮鼻黏膜組織,備用。
2.2.4 觀察指標
2.2.4.1 ELISA法檢測血清TNF-α、IL-1β、IL-17、IL-6水平將收集的大鼠全血標本放于室溫靜置2 h,1 000×g,離心20 min,取上清液,將上清液置于-80 ℃保存,備用。按照TNF-α、IL-1β、IL-17和IL-6的ELISA試劑盒說明書分別測定大鼠血清中TNF-α、IL-1β、IL-17、IL-6的含量。本次實驗重復3次。
2.2.4.2 Western blotting法檢測TNF-α、IL-1β、IL-6、NF-κB p65和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 新鮮大鼠鼻黏膜組織研磨成粉末狀后,加組織蛋白裂解液處理30 min,獲取組織蛋白,參考胡晶等[18]的實驗方法進行蛋白定量、電泳、轉膜、顯影,檢測并分析信號值,TNF-α(抗體稀釋比例1∶1 000)、IL-1β(抗體稀釋比例1∶1 000)、NF-κB p65(抗體稀釋比例1∶1 000)和IL-17C(抗體稀釋比例1∶1 000)表達。二抗使用IRDye 680RD Goat anti-Rabbit IgG(H+L)(抗體稀釋比例1∶20 000)。本次實驗重復3次。
2.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分析軟件,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結果
3.1 中藥有效成分篩選及基因名的轉換 通過TCMSP數據庫和Swiss Target Prediction數據庫篩選,刪除未匹配到靶點的成分,得到10個中藥活性成分,其中龍膽草3個,藿香7個,最后共得到相關作用靶點258個,去除重復值后,得到163個藥物作用靶點。(見表1)

表1 中藥“成分-靶點”表
3.2 疾病和交集基因的獲取 經GeneCards、OMIM、Durgback平臺獲取鼻竇炎靶點3 852個,其中最大score評分為94.51,最小評分為0.14,最后得到2 644個疾病靶點。(見圖1)中藥靶點和疾病靶點取交集,刪除重復值,得到交集基因110個。

圖1 “中藥-疾病靶點”韋恩圖
3.3 構建“中藥成分-靶點”網絡及關鍵化合物篩選 將基因數據導入Cytoscape3.8.2軟件,得到“中藥成分-靶點”網絡圖,共421個節點(nodes),730條邊(edges)。(見圖2)根據Degree值得到排名靠前的主要成分化合物為槲皮素、龍膽堿、龍膽苦苷。(見表2)

圖2 “中藥成分-靶點”網絡圖

表2 藥物關鍵化合物
3.4 PPI網絡制作和核心蛋白的獲取 將交集基因導入String平臺,設置對象為(homo sapiens)、取最高置信度0.900,隱藏游離基因節點,得到247個節點,1 110條邊,平均節度點為9.28。下載TSV文件導入Cytoscape3.8.2后經網絡拓撲學分析,把Degree值的二倍中位數以上,介度中心值(Betweenness Centrality,BC)和緊密中心值(Closeness Centrality,CC)的中位數上靶點作為中藥藥對的核心作用靶點,排名前6靶點基因分別為AKT1、TP53、IL-6、VEGEA、TNF、IL-1β。隨著Degree值和連接分數的增高,節點的形狀越大,顏色越鮮明、線條越粗,蛋白越重要。(見圖3)

圖3 PPI 蛋白互作圖
3.5 GO與KEGG Pathway富集分析 經Metascape平臺分析,GO分析結果顯示:生物過程(biological processes,BP)4 893條,通過LogP值和基因數的百分數比重對數據進行排名,排名靠前的為對營養水平的反應、對脂多糖的反應、對細菌來源分子的反應、對藥物的反應等。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668條,主要涉及核受體活性、配體激活的轉錄因子活性、血紅素結合、DNA結合轉錄因子結合、受體配體活性、RNA聚合酶Ⅱ特異性DNA結合轉錄因子結合等。細胞成分(cellular components,CC)共379條,主要由膜筏、突觸后膜、受體復合體、細胞質核周區域、轉錄因子復合體等構成。(見圖4)

圖4 GO 富集分析圖
將交集基因導入Matescape平臺進行分析,得到279條KEGG信號通路富集結果,設置FDR<0.01篩選前20條途徑。(見圖5)根據所屬通路將各靶點進行歸類,將信息導入Cytoscape 3.8.2軟件中構建“中藥成分-靶點-通路-疾病”網絡圖。(見圖6)

圖5 KEGG 信號通路富集分析圖

圖6 “中藥成分-靶點-通路-疾病”網絡圖
KEGG通路富集分析結果表明,主要涉及的通路有脂質與動脈粥樣硬化通路、糖尿病并發癥中的AGE-RAGE信號通路、IL-17信號通路、TNF信號通路等。IL-17信號通路是介導多種炎癥疾病的發生經典信號通路,與鼻竇炎的炎癥反應過程密切相關[19]。根據PPI蛋白互作圖可知,排名前6的中藥核心靶點中有3個是IL-17信號通路中的關鍵靶點(IL-6、TNF、IL-1β)。上述結果提示,藿膽鼻淵丸中藿香-龍膽草藥對可能影響炎癥反應過程來發揮治療作用,因此后續實驗將選取IL-17信號通路相關指標進行驗證。IL-17信號通路詳細信息見圖7。

圖7 IL-17 信號通路詳解圖
3.6 各組大鼠血清中TNF-α、IL-1β、IL-6和IL-17水平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模型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IL-17水平明顯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與模型組比較,藿香-龍膽草組和陽性藥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IL-17水平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與陽性藥組比較,藿香-龍膽草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IL-17水平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8)

圖8 各組大鼠血清中TNF-α、IL-1β、IL-6 和IL-17水平比較 (,n=6)
3.7 各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IL-17/NF-κB信號通路關鍵蛋白表達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模型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TNF-α、IL-1β、NF-κB p65、IL-6、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與模型組比較,藿香-龍膽草組和陽性藥物組大鼠TNF-α、IL-1β、IL-6、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與陽性藥組比較,藿香-龍膽草組大鼠TNF-α、IL-1β、IL-6、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升高,NF-κB p65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降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圖9~10)

圖9 各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IL-17/NF-κB 信號通路關鍵蛋白表達Western blotting 圖

圖10 各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IL-17/NF-κB 信號通路關鍵蛋白相對表達量比較 (,n=6)
4 討論
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對藿膽鼻淵丸中藿香-龍膽草藥對治療鼻竇炎的靶點和潛在機制進行了分析,得到10個中藥有效活性成分,其中3個核心活性成分分別為槲皮素、龍膽堿、龍膽苦苷。彭煒等[20]研究發現,槲皮素能通過調節大鼠變應性鼻炎Th1/Th2細胞因子的平衡減輕大鼠變應性鼻炎鼻部癥狀,改善鼻黏膜炎癥程度。盧志賓等[16]證實了槲皮素具有改善鼻竇炎癥狀的作用,并發現脂多糖(LPS)誘導形成的副鼻竇炎模型小鼠經過槲皮素治療后,副鼻竇炎病理形態學明顯改善,其機制是調節高爾基應激抑制TNF-α和IL-6等炎癥因子表達。此外,槲皮素還可通過負調節TLR4信號通路抑制脂多糖誘導的細胞表面分子(CD80、CD86和MHCI/II類)和促炎性細胞因子(TNF-α、IL-1β、IL-6和IL-12p70)的表達,達到抗炎作用[21]。龍膽堿和龍膽苦苷都是龍膽草的主要活性成分。龍膽苦苷屬于環烯醚萜苷類,分子式為C16H20O;龍膽堿屬于吡啶類生物堿,分子式為C10H9NO2。研究表明,龍膽堿和龍膽苦苷均具有顯著的抗炎作用[22]。KWAK W J等[23]以雄性SD大鼠為實驗對象,發現龍膽堿可以抑制LPS誘導的促炎性細胞因子TNF-α、IL-6的表達。龍膽堿還可以通過抑制IL-8、TNF-α等炎癥因子的表達調節機體免疫[24]。ZHAO L等[25]研究表明龍膽苦苷可以通過調節IL-1β信號通路中p38、ERK和JNK蛋白的表達,抑制IL-1β誘導的大鼠關節軟骨細胞的炎癥反應。龍膽苦苷可以抑制大鼠體內TNF-α、IL-1β釋放達到減輕大鼠急性胰腺炎的作用,其作用機制與抑制NF-κB p65蛋白的表達有關[26]。葛珊等[27]研究發現,龍膽苦苷、木蘭花堿可以通過降低炎癥因子TNF-ɑ、IL-1β分泌,抑制IKKβ/NF-κB/COX-2信號通路異常激活而發揮抗炎作用。龍膽苦苷也可顯著降低C57BL/6小鼠血清中IL-1β、IL-6、IL-18和TNF-α等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水平[28]。李鑫波等[29]研究發現,龍膽苦苷可通過抑制NF-κB信號通路發揮抗炎活性。槲皮素、龍膽堿、龍膽苦苷均是藿香-龍膽草治療鼻竇炎的核心成分,提示藿香-龍膽草藥對治療疾病具有多成分發揮藥效的特點。
本研究通過對藿香-龍膽草藥對治療鼻竇炎的PPI網絡分析,發現絲氨酸/蘇氨酸激酶1(AKT)、猴腫瘤蛋白p53(TP5)3、白細胞介素-6(IL-6)、血管內皮生長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TNF等靶點是主要作用靶標。這些靶點蛋白在鼻竇炎的發生發展過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AKT1是絲氨酸/蘇氨酸激酶(AKT)中的其中一個亞型,參與細胞多種生物過程。ZHOU X C等[30]通過生物信息學和qRT-PCR實驗驗證了AKT1與慢性鼻竇炎伴鼻息肉的發病機制密切相關;TP53 GOF突變體異位表達在炎癥反應中起著關鍵作用[31]。據葉帆[32]報道,MiR-155可以通過靶向TP53INP1 3’UTR抑制TP53INP1表達,從而調節變應性鼻炎中免疫細胞ILC2的功能。VEGFA作為效果突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在參與新血管的調節和生成過程中釋放多種生長因子和炎癥因子[33]。如范雋等[34]發現慢性鼻-鼻竇炎患者的炎癥因子IL-6表達水平顯著升高,且HIF-1α及VEGF在組織中同時呈高表達,其機制與p38MAPK密切相關。近年來,隨著對鼻竇炎發病機制的進一步探索,眾多研究[35-43]均表明,IL-6、TNF在急慢性鼻竇炎的發病過程中均為重要的促炎性細胞因子,其發病機制涉及到多種信號通路。
KEGG富集主要涉及的通路有脂質與動脈粥樣硬化通路、糖尿病并發癥中的AGE-RAGE信號通路、IL-17信號通路、TNF信號通路等。其中IL-17信號通路在急性和慢性鼻竇炎癥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多個研究[44-46]已證實,IL-17最顯著的作用是其參與誘導和介導促炎癥反應。IL-17通過相應受體激活下游通路,包括核轉錄因子NF-κB、MAPK、AP-1,以誘導許多細胞因子、趨化因子的表達(例如IL-6、G-CSF、GM-CSF、IL-1β、TNF-α)。本研究以大鼠鼻竇炎為模型,采用ELISA和Western blotting方法對網絡藥理學篩選結果進行實驗驗證。實驗結果表明,模型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IL-17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提示這些炎癥相關因子在鼻竇炎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經藿香-龍膽草治療后,大鼠血清TNF-α、IL-1β、IL-6、IL-17水平明顯降低,表明藿香-龍膽草可以抑制炎癥相關因子(TNF-α、IL-1β、IL-6、IL-17)的表達。Western blotting結果顯示,模型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TNF-α、IL-1β、NF-κB p65、IL-6、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高于對照組(P<0.01),藿香-龍膽草組和陽性藥物組大鼠TNF-α、IL-1β、IL-6、IL-17C蛋白相對表達量明顯低于模型組(P<0.01);同時NF-κB p65蛋白水平也發生了變化;然而,藿香-龍膽草組大鼠鼻黏膜組織中TNF-α、IL-1β、IL-6、IL-17蛋白相對表達量高于陽性藥組,而NF-κB p65蛋白相對表達量低于陽性藥組。藿香-龍膽草和陽性藥物均可能對IF-17/NF-κB信號通路有調控作用。
綜上所述,藿香-龍膽草可能是通過IL-17激活NF-κB,抑制TNF-α、IL-1β、IL-6炎癥因子的產生,從而達到治療鼻竇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