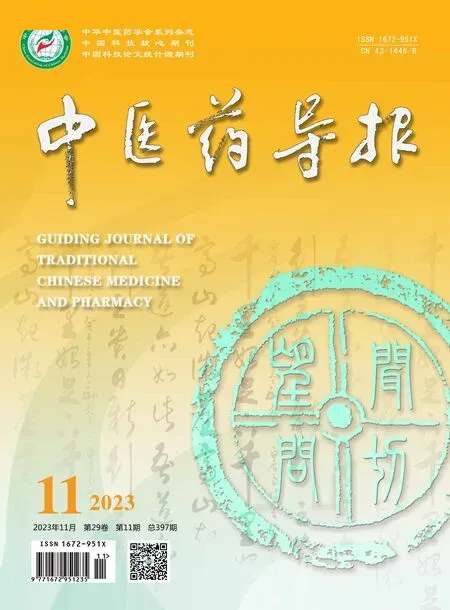國醫大師劉志明運用調氣和血攻毒法治療結腸癌經驗*
侯道瑞,楊為偉,王 瑛,李 琳
(湘潭市中醫醫院,湖南 湘潭 411100)
結腸癌是指結腸黏膜上皮在遺傳或環境等多種致癌因素作用下發生的惡性腫瘤[1]。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結腸癌新發病例數已達188萬,占全球新發癌癥的9.8%,死亡病例占全球癌癥死亡病例的9.29%[2]。目前西醫關于結腸癌的相關診療方案以手術、放療、化療等方式為主[3],而部分患者因高齡、大量腹水、腫瘤浸潤或轉移等情況,無法耐受手術或全程放療、化療的治療方式,選擇合理且有效的治療方案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4-5]。研究表明,中醫藥治療結腸癌在調節免疫功能、改善術后狀態、化療增效減毒及內科治療等方面均有獨到優勢,配合現代醫學治療可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延長生存期[6-8]。
劉志明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指導老師,國醫大師,首屆首都國醫名師,第一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科研、教學工作七十余載,學驗俱豐[9]。筆者作為傳承工作室成員及劉志明教授弟子,有幸侍診于側。現將劉志明教授運用調氣和血攻毒法治療結腸癌的經驗總結如下,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
結腸癌根據其臨床癥狀歸屬于中醫學“腸澼”“腸覃”“腸積”“臟毒”“便血”等范疇。《靈樞·水脹》云:“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系,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10]從外因角度,其指出結腸癌的產生主要是外邪侵襲,致氣血運行失常,壅滯于腸中,遷延不愈,而成有形病灶[11]。《丹溪心法·腸風臟毒二十五》曰:“人惟坐臥風濕,醉飽房勞,生冷停寒,酒面積熱,以致榮血失道,滲入大腸,此腸風藏毒之所由作也。”[12]從內因角度,指出該病與不良的生活及飲食習慣密切相關[13]。《外科正宗·臟毒論第二十九》有言:“醇酒厚味,勤勞辛苦,蘊毒流注肛門結成腫塊。”[14]其指出癌毒蘊結在結腸癌發病中的重要作用[15]。明代醫家張介賓在《景岳全書·積聚》中,從體質的角度,提出凡脾腎不足及虛弱失調之人多有積聚之病,論述了脾腎虧虛之人更易因正虛邪滯而發為腫瘤[16]。劉志明教授結合歷代先賢對腫瘤的認識及自身多年臨床經驗,認為正氣不足,陰陽失調,脾腎虧虛是結腸癌發生的根本原因,氣滯、痰凝、血瘀、毒聚是結腸癌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生理過程,氣血失和毒聚是結腸癌的重要病理基礎。
2 調氣和血攻毒法的應用
根據結腸癌的病因病機及其氣血失和毒聚的病理特點,在“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10]的理論指導下,劉志明教授提出調氣和血攻毒法治療結腸癌的基本治法。氣與血,既是構成人體的物質基礎,又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氣血相互依存,相互為用,運動不息,周流全身,共同協調機體的生命活動[17-18]。毒者,即癌毒也,一般是指貫穿惡性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異致癌性毒邪[19]。而氣血之本在脾腎,劉志明教授常以健脾補腎為扶正之基礎,通過靈活運用調氣、和血、攻毒之治法,協理氣血陰陽,糾正氣血、陰陽異常改變的病理狀態,使氣血充盈,陰陽調達,則癌毒自消,正氣自復,身安體健。
2.1 調氣 調氣,一能補已虛之氣,二可疏郁滯不暢之氣。劉志明教授認為,結腸癌的治療,首在調氣。調氣不僅僅是補氣,還要求補而不滯,疏其調達。臨床上常用四君子湯類方為補氣基本方,在四君子湯的基礎上,辨證配伍陳皮、厚樸、焦三仙等理氣醒脾之品,使補而不滯。四君子湯作為健脾益氣的代表方劑,出自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相關研究表明四君子湯能影響自然殺傷細胞活性及結腸癌細胞增殖,抑制小鼠結腸癌皮下瘤生長,抑制外周血白細胞的炎癥反應,降低細胞程序性死亡配體-1蛋白及抗體表達[20]。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歷代醫家均強調脾與腎相互滋養的關系[21]。劉志明教授也常加山藥、桑椹、制何首烏等補腎培元之品,以收脾腎同治、先后天同調之效。
2.2 和血 和血,一方面在于補已虛之血,另一方面在于清離經及瘀滯之血。劉志明教授指出,結腸癌除正氣不足,氣血虧虛之外,還多伴有腸道局部充血、潰瘍、出血等病變。治療上,不僅要補不足之氣血,還要注意清離經之血和瘀滯之血,慎用太過滋膩之品。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血液運行遲緩、凝滯,脈道壅阻不暢及血液逸于脈外而停積等,均可導致血行失度。劉志明教授在臨床上取當歸補血湯、當歸芍藥散方義,常用當歸、芍藥等養血和營,伍黃芪益氣生血,以使陽生陰長、氣旺血生,同時補而不滯,補而不留瘀。當歸補血湯出自李杲的《內外傷辨惑論·暑傷胃氣論》,為臨床上補益氣血的代表方。現代研究顯示,其還具有抑制腫瘤術后復發、轉移等作用[22]。當歸芍藥散出自張仲景《金匱要略·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其核心病機為血虛血瘀,水濕停滯。當歸芍藥散中三水藥與三血藥協調配伍,共奏養血、祛瘀、利水之功[23]。如瘀滯較重,也可佐以乳香、沒藥等以行氣活血,祛瘀生新。研究表明,“乳香-沒藥”藥對含有多種抗腫瘤的有效成分,兩者經合理配伍后其抗腫瘤作用更為顯著[24]。
2.3 攻毒 攻毒,一方面是指攻痰凝、濕濁、瘀血、熱邪諸邪積聚之毒,另一方面是指攻伐癌毒。劉志明教授基于中醫“癌毒”理論,指出惡性腫瘤的發生是由于人體正氣不足,臟腑、經絡、陰陽、氣血功能失調,引起氣滯、血瘀、痰凝、熱毒、濕濁諸邪積聚、交阻,乃致腫瘤。此外,邪毒長期作用于人體,氣血凝滯,日久成積,積久化熱,耗氣傷陰。癌毒是貫穿惡性腫瘤發生發展過程始終的一種特異致癌性毒邪,是在氣血虧虛,諸邪膠結的基礎上,多種因素作用下的內生性復合病理因素[19]。外感六淫或內傷七情等因素導致人體氣血津液代謝紊亂,形成痰濕、瘀血、熱毒等病理產物,痰濕、瘀血、熱毒等蘊結不解釀成癌毒,癌毒膠結留滯則發為癌病。同時癌毒作為有形實邪,又可進一步阻滯氣血津液,加重痰濕、瘀血、熱毒之凝滯,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結腸癌的治療中,除了要調氣和血,恢復腸道正常生理功能,還要適當佐以攻毒散結抗癌之品,如瓜蔞、川貝母、白花蛇舌草、半枝蓮、薏苡仁,甚至成藥西黃丸等,在祛除癌毒的同時清除氣血失和所產生的一系列病理積聚產物,標本同治,多法并舉,共奏扶正祛邪之功。
2.4 綜合應用 劉志明教授基于脾為后天之本的傳統中醫理論,認為脾不健運可見于結腸癌患者的多個階段。治療上應注意以扶助正氣、培補后天之本為主,佐以消散癥瘕積塊。脾胃健運,生化之源不竭,正氣旺盛,才能耐受祛邪藥物之攻伐。正氣已復,若可受攻藥,則佐以清熱解毒、軟堅散結之牛黃、麝香、乳香及沒藥等,攻補兼施,延長患者存活期,改善生存質量。治療過程中應靈活施治,或七攻三補,或三攻七補,或五攻五補,視其邪正虛實而調之,補虛而不滯實,通泄而不傷正。此外,臨床上運用調氣和血攻毒法治療結腸癌,還應根據病變過程中引發氣血失和毒聚的不同病因或病理,辨證后選用熱者清之、寒者溫之、濕者滲之、積者導之、下者舉之、滑者攝之等法,治病求本,隨證施治。
3 驗案舉隅
3.1 病案1 患者,女,42歲,2020年8月4日初診。主訴:腹脹痛近3個月。患者于2020年5月因腹脹腹痛就診于當地醫院,完善腸鏡等相關檢查,診斷為“乙狀結腸癌”。2020年5月28日在全麻下行腹腔鏡下乙狀結腸癌根治術,術后病理檢查提示中分化腺癌,闌尾底部漿膜面見癌轉移,左肝轉移性結腸癌結節。術后行4次腹腔熱灌注化療。刻下癥見:下腹部隱痛,納可寐佳,大小便正常。舌紅,苔薄黃,脈細。西醫診斷:乙狀結腸癌伴肝轉移;中分化腺癌(T4N1M1Ⅳ期)術后;腹腔灌注化療后。中醫診斷:結腸癌;辨證:氣血不足,熱毒未盡。治法:健脾益氣養血,清熱解毒散結。方用異功散、當歸補血湯、芍藥甘草湯合瓜蔞貝母飲加減,處方:黃芪24 g,當歸12 g,白芍12 g,黨參12 g,茯苓12 g,天花粉12 g,白術9 g,陳皮9 g,川貝母9 g,甘草9 g,白花蛇舌草30 g。15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另口服西黃丸(1 g/次,2次/d,)。囑清淡飲食,規律作息。
2診:2021年7月23日,患者間斷服用上方近1年。自覺精神、食納尚可,大便稀溏,一日四五行,進食涼、生冷后腹瀉次數增多,偶有胸悶,無腹痛,無惡寒發熱。月經正常。舌淡紅苔薄白,脈弦滑。辨證:脾虛濕阻,氣血不足,痰結毒聚。治法:健脾利濕,益氣養血,化痰散結。方選香砂六君子湯、當歸補血湯和瓜蔞貝母飲加減,處方:黃芪18 g,黨參15 g,天花粉15 g,當歸12 g,白芍12 g,茯苓12 g,白術12 g,川貝母12 g,黃芩12 g,陳皮9 g,砂仁9 g,甘草9 g,白花蛇舌草30 g。15劑,煎服法同前。繼服西黃丸,服法同前。
3診:2021年12月23日,訴服上方100余劑,自覺精神可,納可,時易饑,無腹脹腹痛,大便成形,一日一行,體質量增加。舌質紅,苔白,脈細。2021年12月20日復查腹部CT示:腹部情況大致同術后,未見復發征象。患者服藥后癥狀好轉,病情穩定。中醫診斷及辨證同前,繼續予以健脾利濕,化痰散結。方選六君子湯、半夏厚樸湯合瓜蔞貝母飲加減,處方:黨參12 g,茯苓12g,花粉12g,白術9g,陳皮9 g,厚樸9 g,川貝母9 g,半夏9 g,黃芩9 g,甘草6 g,白花蛇舌草30 g。15劑,煎服法同前。繼服西黃丸,服法同前。
半年后隨訪,患者一直服用3診方,配合西黃丸,未服用其他藥物和其他治療,精神飲食睡眠可,體質量稍增,大小便正常。2022年7月復查血常規、肝腎功能及腫瘤標志物均示正常。
按語:本案患者為乙狀結腸癌術后,灌注化療后,屬中醫癌病范疇。手術為有形之創傷,手術之后,氣血耗傷,腸胃失于濡養,不榮而痛,故初診以“下腹部隱痛”為主癥。考慮患者有闌尾及左肝轉移,癌毒仍留戀未盡,與正氣搏結為患。腹腔灌注化療,雖可清解有形之癌毒,但化療藥屬大毒之品,對人體機體亦有較強的毒副作用,結合患者舌脈診,考慮為氣血不足,熱毒未盡之證。劉志明教授根據“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傳統理論,主張癌腫治療當以扶正為先,以健脾益氣養血為主,輔以清熱解毒以散邪。選用異功散(即四君子湯加陳皮)以益氣健脾,行氣通滯,當歸補血湯益氣生血,伍以芍藥甘草湯緩急止痛,共奏氣血雙調、補而不滯之效。天花粉、川貝母、甘草,合為“瓜蔞貝母飲”,出自《增訂胎產心法》,原方主治“乳房結核焮腫”[25],現代常用于治療痰熱壅結之乳癰、肺癰、瘰癘等病證。劉志明教授取其清熱化痰、散結消腫之功效,配合白花蛇舌草,廣泛用于全身各處癌腫的治療,同時配合西黃丸長期口服,以加強清熱解毒、消腫散結之效。西黃丸中牛黃清熱豁痰,息風解毒;麝香活血開竅,散瘀通經。兩相合用,可走竄周身之孔竅,搜剔潛伏之癌毒,邪無所遁則癌清毒消,為劉志明教授獨特的用藥經驗之一。全方以黃芪為君藥,黃芪為補氣之圣藥。《本草備要》言其乃“溫分肉,實腠理,瀉陰火,解肌熱”[26]。《神農本草經》言其“主癰疽久敗創,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瘺”[26]。黃芪扶正之中兼有祛邪之意。當歸、白芍、茯苓、白術、黨參為臣藥,益氣養血,扶正培本,共助生化之源。佐以陳皮、砂仁理氣散結,以防補益之品壅滯腸胃,配合天花粉、貝母、黃芩、白花蛇舌草以清熱解毒散結。使藥以甘草調和諸藥,兼有健脾益氣、清熱解毒之效,契合全方扶正不助邪,祛邪不傷正之旨。全方攻補兼施,氣血同調,在益氣養血、行氣化滯的基礎上,佐以攻毒散結之品,俾氣調血順,結散毒消。2診時患者腹痛消失,但出現大便稀溏,進食涼、生冷后腹瀉,考慮為脾不升清。脾虛濕阻證明顯,故黨參、白術加量以增強益氣健脾燥濕之功,加砂仁、黃芩以加強理氣清熱燥濕之效,俾脾健、氣行、濕去。3診時患者腹痛消失,大便成形,體質量增加,體質改善,各項指標均較前好轉,故去黃芪、當歸、白芍等益氣生血之品以免助邪復生,加用半夏、厚樸以增強理氣燥濕、化痰散結之效。在后續的治療過程中,根據患者虛實變化及耐受情況,靈活調節扶正、祛邪之強弱,俾藥證相符,方與人合。2022年7月患者復查情況良好,體質量增加,療效滿意。劉志明教授治療內傷雜病,尤其是惡性腫瘤,以“調理為要”“扶正為先”,留人治病,徐徐圖之,故常藥性平和且藥量不大,顧護胃氣,有方有守,循序漸進,終獲良效。
3.2 驗案2 患者,女,50歲,2021年2月4日初診。主訴:乙狀結腸癌術后2年余。患者于2年前在外院診斷為結腸癌,術后病理檢查提示“(乙狀結腸)高中分化腺癌”,予以輔助化療。化療期間出現閉經,并逐漸出現腰痛,站立困難,甚則出現間斷血尿。刻下癥見:腹脹,有時可捫及包塊,雙下肢乏力,稍有口干口苦,口中咸味,納食尚可,睡眠時好時差,大便干結,間斷血尿。舌質淡紅,苔薄白,脈細。西醫診斷:乙狀結腸癌;高中分化腺癌;術后輔助化療后。中醫診斷:癌病;辨證:氣血虧虛,邪毒留戀。治法:益氣養血,解毒散結。方用八珍湯、玉屏風散、桂枝湯合瓜蔞貝母飲加減,處方:太子參15 g,茯苓12 g,白術12 g,當歸9 g,黃芪18 g,防風12 g,白芍9 g,桂枝9 g,甘草6 g,天花粉15 g,浙貝母12 g,白花蛇舌草30 g。15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21年7月6日,患者訴間斷服用上方近半年,精神體力較前好轉,目前稍有神疲乏力,偶有腹部脹痛,進食后及夜間尤為明顯,納食可,小便黃,大便成形。舌紅,苔薄黃,脈細。辨證:肝郁脾虛,氣血失和。治法:疏肝健脾,調和氣血。方選逍遙散加減,處方:柴胡9 g,法半夏9 g,黃芩9 g,太子參12 g,當歸9 g,白芍9 g,瓜蔞12 g,厚樸9 g,山楂9 g,神曲9 g,麥芽9 g,枳殼9 g,甘草6 g,浙貝母12 g,白花蛇舌草30 g。14劑,煎服法同前。
2021年7月21日隨訪,患者諸癥好轉。2022年10月隨訪,患者間斷服用2診方,精神體力可,腹脹好轉,大小便大致正常。
按語:本案患者乙狀結腸癌病理診斷明確,屬中醫“癌病”范疇。初診時以腹脹為主,時有包塊,伴乏力,口干口苦,大便干結,間斷血尿,考慮為術后及輔助化療之后,氣血耗損,榮養不足,氣虛運化,邪毒內結,氣機不暢,故腹脹、乏力。血虛失卻濡養、腑氣不通,故大便干結。氣血虧虛,統攝無權,故間斷血尿。結合舌脈,四診合參,中醫辨證為氣血虧虛,邪毒留戀。劉志明教授緊扣“氣-血-毒”之病機,治療上以益氣養血,解毒散結為法,方用八珍湯健脾益氣,養血和血,妙用桂枝疏肝理氣溫經,助四君子湯疏肝健脾,合白芍酸甘養血和營。玉屏風散益氣顧衛防外感,內則加浙貝母、白花蛇舌草、天花粉解毒散結以清留戀之癌毒。方中生黃芪補氣健脾,托毒生肌,為君藥;太子參、茯苓、白術健脾益氣,當歸、白芍養血調血,五藥共為臣藥;佐以桂枝疏肝溫經通絡,防風祛風勝濕,天花粉、浙貝母、白花蛇舌草解毒散結;甘草為使藥,調和諸藥。全方補調同施、標本兼治,共奏調氣和血攻毒之功。2診時患者精神體力好轉,尿血消失,大便成形,病情好轉,但仍食后腹脹,稍有神疲,考慮為久病之后,雖癌毒稍清,但仍氣血失和,肝脾不調。選用逍遙散加減以疏肝健脾,調和氣血。方中柴胡為君藥,疏肝解郁,開樞機之不利;太子參、當歸、白芍健脾益氣養血,枳實、厚樸調理氣機,加山楂、神曲、麥芽健脾助運化,共為臣藥;佐以瓜蔞、浙貝母、黃芩、白花蛇舌草清熱解毒散結,補攻兼施,顧護脾胃,調和氣血;甘草為使藥,調和諸藥。劉志明教授治療惡性腫瘤,尤重調理,根據患者氣血、陰陽、正邪之不同,靈活予以扶正、祛邪、調氣、和血之品,正勝邪退,陰陽氣血協諧。
4 結語
《素問·調經論篇》云:“五臟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27]陰陽失調、氣血失和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癌毒為惡性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異致癌性毒邪。劉志明教授以“氣、血、毒”為著眼點,指出結腸癌是在正氣不足,陰陽失調,脾腎虧虛的基礎上,氣滯、痰凝、血瘀、癌毒,相互影響,膠結為患,氣血失和毒聚發為本病。臨床上主張在調氣和血攻毒法的基礎上,辨證配合多種治法以治病求本、隨證施治,臨床療效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