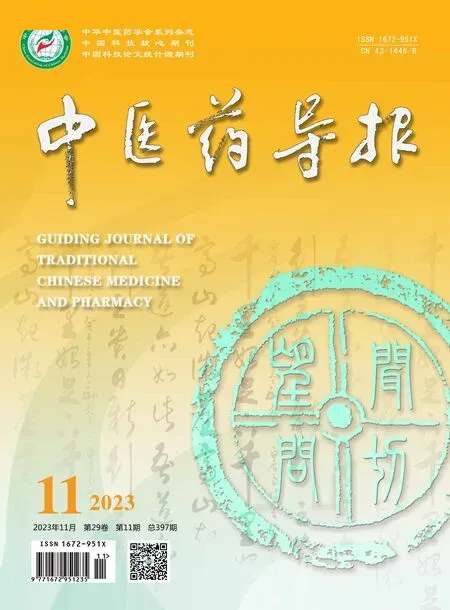潘月麗運用升陽通絡疏肝法治療小兒疳氣型疳證經驗*
崔正九,王欣欣,賈廣媛,刁娟娟,潘月麗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014;2.日照市中醫醫院,山東 日照 276800;3.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山東 濟南 250013)
小兒疳證是中醫兒科的一種常見疾病。古代醫家將疳證列為兒科四大要證之一,是因喂養不當或病后失調,以致脾胃虛損、運化失健而形成的一種慢性病證。本病是以形體消瘦、面黃發枯、飲食異常、大便不調、精神萎靡或煩躁等為主癥的一類慢性脾胃系疾病[1]。疳的含義,古代醫學有兩種解釋,一說是“疳”者“甘”也,另一說是“疳”者“干”也。本病與西醫學的“微量元素缺乏”“蛋白質-能量營養不良”“維生素營養障礙”等疾病相關。現代醫學主要依靠營養治療結合病因治療進行干預,存在治療周期長、花費較高等局限性[2]。中醫藥治療疳證歷史悠久,歷代醫家對該病分類方法認識不一。目前臨床常依據疳證各階段的嚴重程度和主癥表現,將其分為疳氣、疳積、干疳三大常證和眼疳、口疳、疳腫脹3種兼證[3]。當代醫家治療本病多以健脾益氣為基本治法,考慮水濕、氣滯為主要病理因素[4]。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生活、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該病的整體發病率顯著降低,但因飲食不節、養護失宜所致的疳氣型疳證患兒日漸增多[5]。前期預防和及時治療疳氣型疳證成為當前兒科醫生面臨的主要問題。中醫的未病先防與辨證論治理論在治療本病方面優勢突出,療效顯著,復發率低且無明顯不良反應[6]。
潘月麗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中醫藥管理局第五批師承指導老師,從事中醫兒科臨床、教學、科研三十余年,對兒童腎臟疾病、消化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等疾病研究頗有研究,尤其擅長對兒童脾胃系疾病的診治。筆者有幸侍診左右,忝列門墻以聆聽教誨,跟診學習中感悟頗多。現將其運用“升陽通絡疏肝法”治療小兒疳氣型疳證的臨床經驗梳理和總結如下,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
1.1 飲食所傷,脾陽不升,精微不布 陽氣具有溫煦臟腑、化清養神之功。小兒飲食不知自調,若過服生冷或宿食停聚,日久傷及脾陽,則致脾的運化功能失常,充養后天的精微物質難以產生。《血證論·男女異同論篇》[7]云:“脾陽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陽宜動宜升,可將水谷精微運輸至五臟六腑和皮毛孔竅,濡養肌肉四肢。小兒體為純陽,機體發育所需水谷精微比任何時期都更為迫切,源頭匱乏或布散不及使陽氣萌動、激發之性湮滅,故在外可見形體消瘦、面色少華、毛發稀疏、乏力等形神不足的虛象。脾升胃降是全身氣機升降的樞紐。脾陽不升,清氣無力升舉而留于下焦,濁氣失其本位而暫居于上,終致清濁倒置。《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8]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嗔脹。”又因土虛木乘,肝氣上逆,可兼有急躁易怒、腹脹、大便干稀不調等癥。
1.2 久病損耗,胃絡不通,積滯內停 《黃帝內經·靈樞》[9]載:“谷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說明氣血津液通過經絡脈道這一途徑運行全身,從而濡養和聯絡臟腑和體表,維持生命活動。《臨證指南醫案·積聚》[10]指出:“初則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人體正氣有賴于宗氣的充養,中焦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氣是宗氣的重要組成部分[11]。土居中央,中控四方,五臟六腑之病日久均可傷及脾胃,使正氣漸減,邪氣乘虛入于中焦血絡。胃絡瘀滯不通或失于濡養,受納和腐熟之力不足,積滯停聚于胃腑,故見食欲不振,腹部脹滿。經絡脈通道受阻,水谷精微不得布散全身濡養機體,則見形瘦少華,毛發稀疏,納眠差等。《素問·平人氣象論篇》[8]云:“胃之大絡,名曰虛里。”測虛里搏動可知宗氣盛衰,反映脾胃功能的正常與否,由此推測胃絡不通可影響心的正常功能,故疳證患兒在臨床上常伴有心悸、煩躁不安、嗜睡等兼癥。
1.3 宿食不化,肝失條達,血氣受阻 水谷久積胃中不化,生為濁氣糟粕,順勢下流。肝氣升發之性不得施展,以致木氣遏郁,阻礙正常生理功能發揮。肝以血為體,以氣為用,若疏泄、藏血功能失常,氣血化生和運行不暢,機體不得濡養,則見體瘦、面色暗淡、毛發無澤。肝調暢氣機失司亦可影響情志的變化,不及者可見精神萎靡,太過者表現為急躁亢奮[12]。《難經·七十七難》[13]記載:“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于脾,故先實其脾氣。”條文雖指出肝病易傳至脾,臨床發現兩者常互為傳變。脾統血與肝藏血共同維持了血液的量與用,脾主運化和肝主疏泄使全身氣機通而不滯,氣血在肝與脾胃失調的情況下可表現為血/氣虛、血瘀、血熱、氣滯的狀態。《景岳全書·血證》[14]云:“陽主氣,故氣全則神旺;陰主血,故血盛則形強。”氣血不調使形神失養,是導致疳證的重要原因之一。謝晶日認為少陽樞機不利影響脾胃有2個途徑:一是肝膽氣機受阻導致木盛乘土,脾胃失運而漸生濕邪;二是三焦氣機失調使水濕停聚,加重脾胃損傷[15]。
2 診治思路
2.1 治本以升陽,助清氣四布,五臟皆安 疳氣型疳證是疳證的初期階段。潘月麗教授指出氣虛之象可存在于疾病全過程,初期見臟腑不足時不可妄用補劑,否則易壅塞清氣,化熱傷津,加重“疳者干也”的病理環境。脾之陽氣是后天生命活動的原動力,小兒如日中朝陽,機體陽氣更需“顧護”與“引領”,使其充盛且循道而行[16]。脾陽不振是病機的本質,潘月麗教授在遣方用藥時遵循升重于補的原則,常選用柴胡、黃芪、升麻、葛根之類,取其升舉之性,使陽氣回歸本位,帶動水谷精微布散全身,激發各臟腑的生理機能。潘月麗教授認為調治本病也不可偏執于升法,升中有降才能將清濁分離,互不相干,可酌選理氣、降逆之品(厚樸、木香、枳殼、砂仁等)以助升清降濁。脾虛易生濕邪,與宿食相合日久化熱,濕熱熏蒸中焦,煎灼陰津,留滯清陽,導致病情遷延甚至加重。臨床中若見患兒舌苔黃膩、口中異味、大便干結,潘月麗教授常佐清利濕熱之品除升清之礙。
2.2 治標以通絡,使邪氣祛散,三焦得通 絡脈位置表淺,率先受邪,且經脈和絡脈氣血互通,久病會引起絡脈及全身血行異常[17]。外邪、瘀血、痰飲滯于胃絡,是疳證發病的主要誘因,表現出一派邪實之象。潘月麗教授認為邪氣存絡為實,絡脈不榮為虛,病位在表,治療應通、補共施。運用通絡之法不可長期應用活血祛瘀,應辨證施用祛邪而不傷正、補虛而不滋膩之品以暢通胃絡,諸如辛溫通絡、消積通絡、益氣通絡、行氣通絡等治法。疳者甘也,無積不成疳,恣食肥甘厚味是傷及胃絡的重要原因之一。潘月麗教授運用通絡法時善加用焦三仙(焦山楂、焦麥芽、焦神曲),取焦制之溫性充養絡氣。焦山楂可活血祛瘀;焦麥芽助肝木疏泄以行氣;焦神曲和胃止嘔。三藥合用以活血、行氣、和胃,共奏通絡之用。胃絡從足陽明胃經和足太陰脾經上支橫別出,走勢分支錯雜,迂回狹窄,細小甚微處呈網格狀分布于胃腑,藥物難以到達[18]。潘月麗教授運用葛根、升麻、白芷、石膏等胃經引經藥使絡脈盡通,三焦順接。
2.3 佐治以疏肝,為土木共達,氣血充盛 木土相克關系失常在五臟中可表現為肝乘脾和脾侮肝。在治療疳氣型疳證時,輔以疏肝是為防止土木互傳。若肝氣升無太過,可助脾氣升而不降,使胃氣降中蘊升,以此保持臟腑氣機協調平衡,氣行則瘀血自祛[19]。潘月麗教授常從內治、外治和情緒管理三方面靈活運用疏肝法:一是用藥時常配伍疏肝理氣之類(柴胡、郁金、枳殼、香附、延胡索、白芍等),強調藥物用量不可過大,以免升陽之勢渙散。二是運用小兒推拿中按弦走搓摩、推腹陰陽、推抹肋緣下、分運內八卦等疏肝手法。同時配合揉板門、揉足三里等健脾揉法,使熱力下滲,刺激穴位更充分,調和氣血。三是對4歲以上患兒進行健康宣教,鼓勵其在主動配合治療的同時正確對待疾病,養成良好的生活飲食習慣。告知其監護人在患兒出現急躁、精神不振時給予適當安撫。疏肝之法雖重要,但必須在早期運用升陽通絡法調治脾胃的前提下兼顧,單用此法效果欠佳。方法雖看似雜糅,但在“辨證精準”的基礎上緊扣病機,靈活運用,可達到祛病痊形的目的[20]。
2.4 辨病緩急,隨癥加減,標本同治“病有標本,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是指病情穩定(慢性病或急性病恢復期)時期應以治本為要,病情危急時則采取治標之法[21]。就病機而言,疳證為慢性疾病,其發病本質為脾陽不升。但邪實和體虛共同作用可表現出一系列急癥,如嘔吐、水腫、出血等,以絡氣不榮不通,肝氣郁結為標。潘月麗教授診治時先辨患兒主癥緩急歸屬,定治標治本之主次,再依據兼癥加減用藥。潘月麗教授強調治標治本是相對而言,切不可孤立任何一方,在標本同治的基礎上側重用藥才是運用之道。疳氣型疳證患兒臨床癥狀復雜多樣,虛實側重不同,故潘月麗教授認為不可止于一方一藥,應依據患兒體質、疾病主癥和機體氣血陰陽盛衰酌而選之,方獲良效。治本雖在于升陽,但不可過用補陽升陽之藥,以免造成胃氣上逆,火升熱盛。消食誘導胃氣恢復,滋陰填補元陰耗傷,在治療后期應加以考慮。大部分疳氣型疳證患兒有嗜食零食、過食冷飲、添加高能量食品、饑飽不定的習慣[22]。《素問·痹論篇》[8]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潘月麗教授主張對患兒家長進行科學的飲食指導和保健培訓是藥物治療的前提,準確合理的飲食與推拿手法可避免疳證發生,有助于疾病康復,體現了未病先防與既病防變的要義。
3 驗案舉隅
患兒,男,5歲,2021年8月12日初診。主訴:食欲不振伴體質量、身高增長緩慢1年余。現病史:患兒1年前因“積食”出現嘔吐、腹脹、晨起口中異味、大便干稀不調,當地中醫院診斷為“小兒積滯”,予中西醫結合治療(具體不詳),后癥狀逐漸向愈,但食量較前減少,偶有干嘔,未予關注。刻下癥見:身高103.6 cm,體質量12.1 kg,不思飲食,面色萎黃,形體偏瘦,毛發稀疏,飯后常有腹痛、腹脹,夜間易醒,頭面多汗,怕冷,性格急躁,晨起口臭,手足心熱,偶有乏力,大便干結,如棗核狀,1周1次,小便數。舌紅,苔厚膩,脈細澀。查體:輕度漏斗胸,腹部皮下脂肪0.4 cm。既往病史:患兒足月順產,混合喂養,既往有多次“積滯”“呼吸道感染”病史。血常規檢查示:WBC 8.42×109/L,RBC 4.5×1012/L,Hb 122 g/L。西醫診斷:輕度營養不良。中醫診斷:疳氣型疳證(陽郁絡阻證)。治法:升補脾陽,通絡和胃,疏肝理氣。方選升陽益胃湯合柴胡疏肝散加減,處方:黃芪12 g,姜半夏6 g,黨參12 g,炙甘草6 g,獨活6 g,白芍9 g,羌活6 g,茯苓12 g,柴胡9 g,白術9 g,黃連3 g,當歸6 g,焦山楂9 g,焦麥芽9 g,焦神曲9 g,川芎6 g,香附6 g,麩炒枳殼6 g。7劑,1劑/d,水煎取汁100 mL,分早晚溫服。另囑患兒及家長三餐飲食葷素(1∶3)搭配,適當增加戶外運動,睡前1 h不再進食,配合日常捏脊、摩腹、揉足三里、分運內八卦。
2診:2021年8月19日,家屬代訴患兒食欲略增,腹痛、腹脹次數減少,寐欠安,自汗,盜汗,四肢微涼,急躁易怒,晨起偶有口臭,手足心熱,大便略干,兩日一行,小便調。舌紅,苔薄膩,脈細澀。予上方去香附、川芎,加焦梔子3 g。7劑,煎服法同前。
3診:2021年8月26日,家屬代訴患兒飯量增多,主動索食,餐后無腹痛,偶有腹脹,夜間不易再醒,汗量減少,四肢溫暖,晨起口中無異味,仍有急躁,手足心熱,大便成形,色黃質軟,1次/d,小便調。舌淡紅,苔薄白,脈細數。予2診方去柴胡,加熟地黃10 g,牡丹皮6 g。7劑,煎服法同前。
4診:2021年9月2日,家屬代訴患兒體質量13.2 kg,主動進餐,餐后無異常不適,汗出較前明顯減輕,頭發可見濃密小絨毛,肢體溫,未見手足心熱,情緒穩定,眠安,二便調。舌淡紅,苔薄白,脈細。效不更方,續服3診方。7劑服10 d。另囑停藥后改單味鮮荷葉15 g,煮水代茶飲,1次/d。
3個月后隨訪,家長代訴患兒諸癥消失,狀況平穩,體質量增至17.2 kg,身高增至105.7 cm。
按語:本案患兒因飲食停滯中焦而發病,嘔吐傷津,病久耗氣,脾胃失于運化與轉輸,機體供需平衡失調,故身高、體質量低于正常,面黃發疏。既往病史表明病本為虛,易受邪犯,脾陽受遏無力升發水谷精微,腦絡及軀干四肢失于溫養,見夜寐不安、頭面多汗、怕冷、乏力。脾陽不升則胃氣不降,氣聚而化熱,氣滯、熱邪入于胃絡,凝血為瘀,加重傷陰,見腹痛、腹脹、急躁、口臭、手足心熱、便干。舌紅苔厚膩、脈細澀佐證了虛、熱、瘀為此階段的病理特點。患兒未見急癥,故重在升補脾陽以治本,化瘀和胃與疏肝理氣輔之。潘月麗教授四診合參,辨其為陽郁絡阻證,方選升陽益胃湯合柴胡疏肝散。方中黃芪益氣升陽,入脾經,為君藥。黨參、炙甘草補中益氣,姜半夏和胃降逆。三者調達氣機樞紐,助清升濁降,共為臣藥。佐以獨活、羌活祛風除濕;茯苓、白術健脾滲濕,協發清陽;川芎、當歸化瘀而不傷正;焦三仙消積和胃;麩炒枳殼理氣消積;少佐黃連內清瘀久化生之熱,共用通絡;白芍、柴胡、香附疏肝行氣和胃[23-24]。研究[25]指出捏脊產生的皮膚刺激經傳入神經到達大腦皮層中樞及腸神經系統后,可通過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調節相應神經肽類物質的濃度調整胃腸功能。故本案運用內外合治后起效顯著。2診時患兒癥狀改善,潘月麗教授認為患兒脾土素虛,陽氣氤氳于中,長期服用行氣、活血之品可擾亂助陽升清與統攝血液的功能,故去香附、川芎,加焦梔子清三焦血熱以免加重傷陰耗液。3診時患兒癥狀僅存急躁和手足心熱,故去柴胡防劫肝陰,加熟地黃滋陰補血,牡丹皮除煩熱、破結蓄。有研究[26]指出熟地黃中梓醇、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等成分具有抗抑郁的作用,亦是疏肝法的應用。4診時患兒基本恢復,潘月麗教授認為慢病應緩治,不可猝然停藥,以免因飲食勞倦而復發,故守3診方以祛邪扶正,后以單味荷葉升發脾陽、化濕和胃、入肝涼血,徐徐調治,收效滿意。
4 結語
疳氣型疳證是兒童脾胃系疾病的常見病,但因其癥狀輕、病程長、并發癥少的特點容易被患兒家長忽視,延誤病情。潘月麗教授從臟腑關系出發,提出脾、胃、肝與疳氣型疳證發病相關;從病理角度分析了陽氣、絡氣、郁氣在特定臟腑中共同致病的機制;從標本關系探討了升脾陽、通胃絡、疏肝氣的治法在病情緩急時的應用原則。潘月麗教授倡導“雜合以治”的治療思想,運用藥物、推拿、飲食調護、情緒管理等方法共同施治,促使疾病盡快向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