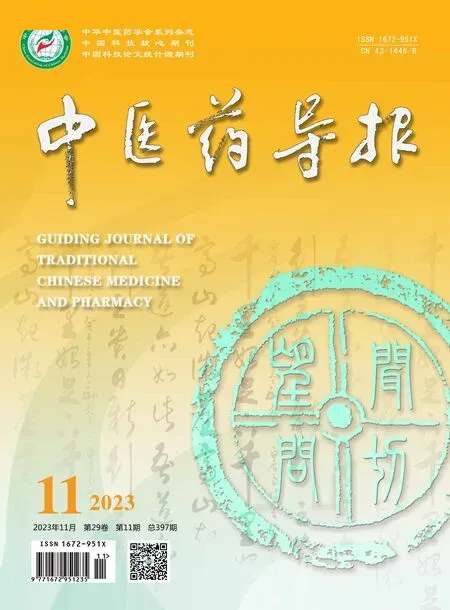金實從絡論治白塞病經驗*
鄭焙珠,韓善夯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省中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白塞病一般指貝赫切特綜合征,屬于一種全身性免疫系統疾病,是具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在感染等因素作用下,引起固有和適應性免疫異常應答,最終導致的系統性血管炎[1]。本病可侵害人體多個器官,包括口腔、皮膚、關節肌肉、眼睛、血管、心臟、肺和神經系統等,主要表現為反復口腔和會陰部潰瘍、皮疹、下肢結節紅斑、眼部虹膜炎、食管潰瘍、小腸或結腸潰瘍及關節腫痛等。病理改變可累及大、中、小血管,出現血管壁完整性的破壞、血管閉塞和血栓形成[2]。白塞病在我國發病率為14/10萬[2]。目前還沒有針對白塞病的大規模流行病學資料,可能實際患病率更高。白塞病需要規律的藥物治療,包括各種調節免疫的藥物,不治療則預后不好,嚴重則危及生命。西醫治療一般采用糖皮質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等藥物[3-4],可有效緩解臨床癥狀,但存在停藥后病情反復、長期服用則不良反應明顯等問題。中醫學根據該病臨床癥狀將其歸屬于“狐惑病”范疇。中醫藥治療本病具有獨特優勢,可在認識本病的基礎上通過中醫辨證施治和辨病相結合,做到因病而異、因人而異、因證而異。
金實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全國第五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江蘇省名老中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從事中醫臨床五十余載,擅用絡病學理論治療多種血管炎性疾病,尤其對于白塞病的治療具有獨到見解。金實教授認為白塞病病位在絡脈,以病邪襲絡為始因,提出“絡氣有余、絡血瘀滯”的病機關鍵,強調該病發展過程中存在瘀毒阻絡、絡道受損的病理改變。治療上金實教授主張和絡之氣血、通絡之瘀毒,臨床療效頗豐。筆者有幸跟師學習,受益匪淺,現將其從絡論治白塞病經驗總結如下,以供參考借鑒。
1 病在絡脈,濕熱毒邪襲絡為因
絡脈為機體交通氣血最小的單位,具有自身獨特的生理結構和病變特點。《靈樞·本臟》曰:“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靈樞·脈度》言:“經脈為里,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5]絡脈從經脈橫支別出,網絡全身,承擔著運行輸布水谷所化氣血、溝通經脈、濡養周身的生理功能[6]。《醫門法律·絡脈論》謂:“十二經生十二絡,十二絡生一百八十系絡,系絡分支為一百八十纏絡,纏絡分支連系三萬四千孫絡,孫絡之間有纏絆。”[7]孫絡絡體細小,處于末端孫絡約160多億根,其“孫絡之間有纏絆”相連之說與現代醫學認為血液與組織細胞間物質交換在直徑<10 μm毛細血管處實現相吻合。同時,這種細小迂曲的結構基礎也導致邪氣入絡時出現“易入難出、易滯易瘀”的病變特點。
金實教授認為白塞病病在絡脈。白塞病以“瘍”為主要表現,臨床病變多端,病情纏綿難愈。這種發病特點與絡脈的生理功能、結構基礎和病變特點息息相關。朱丹溪云:“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8]正常情況下,絡氣與絡血如并行的兩條“河流”,之間有億萬“溝渠”互相交通、循環流動、陰陽順接,共同維系臟腑正常的生理機能。若邪氣襲絡,絡之“溝渠”不暢,致氣血陰陽失調,氣盛血瘀,久而損傷絡體,絡脈失去其正常的結構,則可外生瘍變。若腦絡受損則發為神經型白塞病,若腸絡受損則發為腸型白塞病,絡脈分布廣泛的特點與白塞病累及多系統的臨床表現相契合。白塞病病程以年計,且臨床病情常反復,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故金實教授認為沉疴痼疾當究絡脈治法。《臨證指南醫案》載“經年宿病,病必在絡”[9]。邪氣入絡,難出易滯的病變特點是疾病纏綿不愈的內在邏輯。
中醫藥治療本病歷史悠久。《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第三》指出狐惑的臨床表現:“狐惑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于喉為惑,蝕于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10]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指出本病病因:“此皆由濕毒氣所為也。”[11]《備急千金要方·傷寒不發汗變成狐惑》有言:“因火為邪,血散脈中,傷脈尚可,傷臟則劇……火力雖微,內功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12]孫思邈亦指出此為火傷血脈。金實教授依據古代醫家臨證思想及經驗,認為白塞病多由濕熱毒邪所致,濕熱毒邪侵襲絡脈,擾亂絡脈“行血氣而營陰陽”的功能,致絡道受損而發病。
2 絡氣有余、絡血瘀滯為病機關鍵
《素問·調經論篇》言:“風雨之傷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脈,孫脈滿則傳入于絡脈,絡脈滿則輸于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于分腠之間。”指出外邪傷人,由皮膚傳至絡脈,致“絡脈滿”。《靈樞·百病始生》提及:“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里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指出內傷飲食、情志不暢,皆可致“絡積”[5]。金實教授認為,絡脈滿或絡積,本質為絡氣病。絡氣與營衛之氣、宗氣、元氣、經氣同宗,是機體實現氣的功能的基本單位。根據白塞病濕熱毒蘊的特點,金實教授提出絡氣有余的概念,強調邪盛的病理狀態。
絡氣有余,一指氣盛絡滿。葉天士言“夫熱邪、濕邪,皆氣也”[9]。或先天稟賦不足,外感濕熱邪氣;或飲食不節,嗜食辛辣,濕熱內生;或七情不暢,郁而生熱,諸濕熱邪氣侵襲絡脈,致絡氣亢盛。《素問·皮部論篇》載:“邪客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于絡脈,絡脈滿則注于經脈”[5]。絡滿則返,濕熱邪氣由絡脈傳于肝經,則見目赤灼痛、外陰潮濕潰瘍;傳于心脾,則見口潰色紅、四肢紅斑隱隱。現代研究[13]表明,白塞病患者活動期IL-6、IL-8、IL-12、TNF-α、VEGF和丙二醛水平升高,Th1、Th2、Th17應答可能同時在白塞病中發揮作用。根據現代“氣絡-NEI網絡”的理論[14],絡氣功能涵蓋了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等,絡氣有余則可出現促炎因子升高、免疫調節紊亂。二指絡陰不足。絡陰不足是氣盛的前提,也是氣盛的繼發改變。《儒門事親》云:“榮虛衛實,皮膚不仁,痹而不知癢痛。”[15]氣血相互為用,若陰血不足,則陽獨亢。氣有余可化火傷陰,氣盛的狀態亦加重陰虛。臨床中,白塞病患者常伴有口干、眼干、視物模糊等陰虛之象[16]。相關研究通過對現有記載的關于白塞病的方藥進行分析,發現頻數位于前五的中藥依次為:甘草、黃芩、黃連、生地黃、當歸[17]。這與白塞病“濕熱毒蘊”的特點相符合,注重清熱燥濕、瀉火解毒,而氣盛絡滿的同時易耗傷陰液,故常配伍滋陰涼血之品。
《砭經》言“氣無形,主功能,血有形,主形質。百病皆生于氣,氣之在人,和則為正氣,不和則為邪氣”[18]。《臨證指南醫案》提及“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綿不去”[9]。金實教授認為白塞病患者病起于絡氣有余,濕熱毒邪擾亂絡脈正常的生理功能,日久及血,絡血運行失常,而成瘀滯狀態,絡脈失養,不能維持其正常的結構形態。絡氣有余,為病之始;絡血瘀滯,為病之漸。反過來,絡血瘀滯可進一步阻礙絡氣的循環流動,兩者互為因果。現代研究[19]表明,白塞病可累及動脈、靜脈,其中以深靜脈血栓最為多見,內皮功能損傷可能是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在疾病發展過程中金實教授強調“毒”或者“瘀毒”的存在。《金匱要略心典》曰:“毒,邪氣蘊結不解之謂。”[20]絡脈細小迂曲的結構導致邪氣易入難出,血易滯易瘀。隨著病情進展,諸濕熱邪氣稽留成毒,毒與血結,一方面煎灼津液,致血凝而不流,邪毒愈盛則血瘀更重,血流不暢則邪毒無出路可祛;另一方面阻礙氣血再生。《黃帝內經》亦言:“血與之氣者,異名同類爾”[5]。血為氣之母,瘀毒凝滯則新血不生,久而氣難獨存,形成“瘀、毒、虛”膠結、絡體受損的復雜局面,病根深伏,致疾病纏綿難愈,頻發久發。
3 治當以和絡氣血、通絡解毒為要
《難經》謂“是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21]。《素問·調經論篇》曰:“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王冰注:經隧者,五藏之大絡,以行血氣者也。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調治之道,亦守其經隧焉。絡脈以通為用。正如《素問·三部九候論篇》所言:“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其出血,以見通之。”[5]金實教授認為治療當恢復絡脈“行氣血”的生理功能,修復絡道的正常結構,提出和絡氣血、通絡解毒的治法。
3.1 以虛實為經、氣血為緯,辨證施治 白塞病起病隱匿,診時病已久深,臨床表現往往虛實錯雜,故金實教授強調以虛實為度,辨證施治。氣有余,則瀉其經髓。承制調平是氣絡學說的核心理論,只有平亢抑絡,抵御這種亢盛之氣,才能打破“絡滿”或“絡積”的局面[22-23]。臨床以口腔、前陰、后陰潰瘍,雙目紅赤,關節肌肉腫痛,心煩易怒,舌苔黃膩或兼有齒痕等濕熱邪盛為主要表現。金實教授常以黃芩、黃柏、黃連、石膏、知母、白鮮皮等清熱祛濕,瀉氣暢絡;生地黃、丹參、赤芍、牡丹皮等涼血活血,化瘀通絡。臨床若兼見虛煩多汗,五心煩熱,寐差,舌紅苔薄黃少津等陰虛內熱之象,金實教授喜加減麥冬、枸杞子、山茱萸、女貞子等味甘之品緩氣和絡。氣不足,則補其經髓。臨床中亦有少數病人,病情纏綿難愈,以潰瘍發白、久不收口,畏寒肢冷、乏力納呆、寐差,舌淡等氣血不足為主要表現。金實教授常用白術、茯苓、黃芪、黨參等益氣和絡;白芍、當歸、雞血藤、熟地黃等養血通絡。
3.2 祛邪外出,通絡解毒 金實教授認為瘀毒阻絡貫穿白塞病全程,調和氣血時,常需配伍解毒通絡之品。毒之出路不外乎發表從汗而解、瀉下從里而解和嘔噦從上而解。根據絡脈的生理、病理特點以及疾病的病變特點,白塞病之瘀毒區別于一般治法。絡病的產生往往由淺入深,由氣及血,致使絡脈損傷或不通,而絡病向愈亦是祛邪外出的過程。金實教授喜配伍金銀花、連翹溝通氣血、解毒和絡。金銀花和連翹均有清熱解毒、疏散風熱之功,透營轉氣,使病邪由血分透轉氣分、由深層出淺層,從而達到絡道修復、絡脈通暢的效果[24]。
4 驗案舉隅
4.1 病案1 患者,女,43歲,2022年1月11日初診。主訴:口腔潰瘍反復20年余,眼紅3個月。患者既往反復口潰,平均每年超過3次,外院確診為白塞病,長期口服中藥治療,期間口腔潰瘍反復。近3個月,患者嗜食辛辣后出現左眼紅赤脹痛。刻下癥見:口潰,左眼紅赤脹痛,心煩易急,納寐可,二便調。舌紅,苔薄白,邊有齒印,脈細。查體:下唇內側見2個橢圓形白色的潰瘍面,邊緣色紅,左眼結膜充血,無分泌物,面有痘疹。西醫診斷:白塞病。中醫診斷:狐惑病;辨證:絡氣有余,瘀毒阻絡。治法:清氣化瘀,解毒和絡。方選玉女煎和四妙勇安湯加減,處方:生地黃30 g,生石膏15 g,知母10 g,麥冬15 g,川牛膝10 g,連翹30 g,金銀花15 g,玄參12 g,當歸10 g,甘草6 g,牡丹皮10 g,夏枯草15 g,炒蒺藜15 g,酒萸肉10 g,谷精草15 g。14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22年2月18日,患者訴春節停藥至今,口腔潰瘍1個月未發作,期間眼紅脹痛好轉。昨日下午自覺左眼脹痛,可見血絲,納寐可,二便調。舌紅苔薄白有齒印,脈細。予上方生石膏增至30 g。14劑,煎服法同前。
3診:2022年3月6日,患者訴左眼脹痛好轉,無口腔潰瘍,余無特殊不適。繼服2診方以鞏固療效。14劑,煎服法同前。
后電話隨訪,患者訴繼服2診方30劑,口腔潰瘍、眼紅未再復發。
按語:玉女煎出自《景岳全書》,是清胃熱、滋腎陰的要方,為張景岳治療虛火上攻、灼傷血絡而出現牙痛、牙齦出血、口渴煩熱等癥狀的一首著名方劑。方中以生石膏清瀉陽明有余之火,熟地黃、麥冬治療少陰之不足。金實教授以方藥測證,拓展玉女煎適應證,常用玉女煎治療白塞病絡氣滿而陰不足證。本案患者為中年女性,平素飲食不節,嗜食辛辣,內生濕熱,濕熱邪氣侵襲絡脈,絡氣疾行,癥見痘疹、口潰。濕熱久郁化毒,伏于血絡,致絡脈不通,甚則絡體受損,故病情反復,纏綿難愈。患者今因飲食不忌,濕熱更重,邪氣攪動絡脈瘀毒而新發目赤。治宜清氣化瘀,解毒和絡。金實教授宗于玉女煎之意,并加用四妙勇安湯,加強清熱解毒之攻。方中重用生地黃、生石膏,配伍玄參、知母,苦寒以瀉氣涼血;當歸、牡丹皮活血化瘀;金銀花、連翹祛邪外出,解毒通絡;又少佐麥冬、甘草顧護脾胃,防陰傷之變。《靈樞·經脈》言:“肝足厥陰之脈……過陰氣……連目系……其支者,從目系,下頰里,環唇內。”[5]患者以眼炎為急,絡氣為實邪所壅,究其根本,為肝經熱盛,上犯于目絡,目絡“行氣血”功能失司而發病。故金實教授于方中加谷精草既疏肝明目,又引諸藥入肝經;夏枯草、炒蒺藜,清瀉肝經之火,肅本澄源;配伍酒萸肉酸澀補肝體;牛膝引火下行,制肝陽上亢之勢。2診時患者眼炎復作,考慮濕熱為重,此時當以清氣為要,故增生石膏的用量。3診時患者訴諸癥顯減,然伏毒未清,當需守方。本案治絡兼顧調經,治氣與治血共進,諸藥同行,疾病乃愈。
4.2 病案2 患者,女,44歲,2021年9月10日初診。主訴:口腔潰瘍、會陰部潰瘍間斷發作8年余,加重1個月。患者8年來間斷出現口腔潰瘍、會陰部潰瘍,平均每年超過3次,患者近1年規律口服沙利度胺,1片/d,期間潰瘍未發。1個月前,患者自行停沙利度胺,潰瘍復作3次,7~10 d好轉。刻下癥見:口腔、會陰部潰瘍各發1枚,潰瘍處灼熱疼痛,納寐可,小便色黃,大便溏結不調。舌紅苔薄黃膩,脈細。西醫診斷:白塞病。中醫診斷:狐惑病;辨證:絡氣有余,火毒阻絡。治法:以清氣瀉火,解毒暢絡。方選玉女煎和黃連解毒湯加減,處方:生地黃30 g,生石膏30 g,知母10 g,麥冬15 g,川牛膝10 g,黃柏10 g,黃連6 g,熟大黃6 g,牡丹皮10 g,焦梔子6 g,山豆根6 g,豆蔻仁5 g,酒萸肉10 g,甘草5 g。28劑,1劑/d,水煎服,分早晚溫服。
2診:2021年11月5日,訴口腔、會陰部均無潰瘍,近2 d胃脘隱痛,納寐可,二便調。舌紅苔薄稍膩,脈細。予上方加陳皮8 g,14劑,煎服法同前。
后電話隨訪,患者訴間斷服藥,期間口腔、會陰部潰瘍發作1次,3 d好轉,現潰瘍未復發,胃無不適。
按語:本案患者為中年女性,患者病程日久,病根頑固,瘀毒深伏于內。此次病情以潰瘍新起,頻繁發作為特點,癥見口腔、會陰部潰瘍,潰瘍處灼熱疼痛,小便色黃,舌紅苔薄黃膩,一派濕熱內盛、氣盛絡滿之象。“氣有余便是火”,實火生于亢害。一方面充斥上下,病變累及口腔、會陰;另一方面攪動瘀毒,使毒從火化,助長火勢,潰瘍不止。金實教授抓住病機關鍵,靈活辨證,以絡氣有余為引,火毒阻絡為變,故治療宜清氣瀉火,解毒暢絡。初診時金實教授重用生石膏、生地黃,苦寒之品,清氣暢絡;黃柏、黃連、熟大黃、焦梔子,取黃連解毒湯之意,清瀉火毒;配伍山豆根,增加解毒之功;配伍牛膝下行直折火勢;牡丹皮活血化瘀,使火無所附庸;知母、酒萸肉、麥冬,酸甘柔潤,以保陰液;豆蔻仁,辛溫歸脾,防苦寒之弊;佐以甘草,調和諸藥。2診時患者訴潰瘍好轉,胃痛隱隱,藥達病所,故效不更方,乘勝追擊,慮其脾胃不耐藥力,故加用陳皮健脾理氣。
5 結語
白塞病臨床表現復雜,變化繁多。金實教授辨病與辨證相結合,抓住白塞病血管炎的本質,以病位在絡脈,絡氣有余,絡血瘀滯為不變。其主張從絡論治白塞病,治以和絡氣血,解毒通絡;以邪為變,邪有千變萬化,有來源之變,有隨機生化之變,故癥狀各不相同,治療上各有側重,臨證思路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