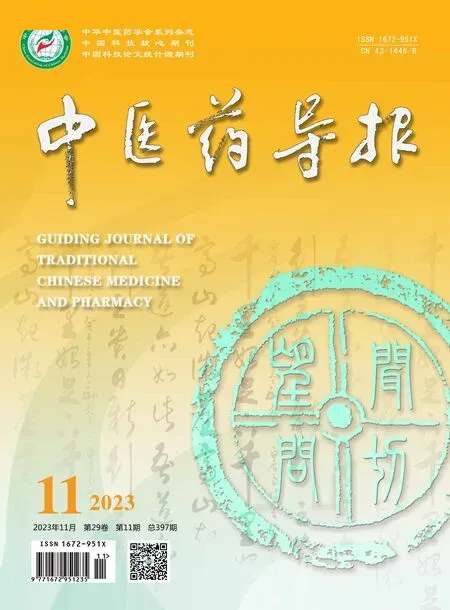喻昌辨治肺癆學術觀點*
王 翔,王 鵬,呂栢慶
(安徽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安微 合肥 230038)
肺癆是具有傳染性的慢性虛弱性疾患,以咳嗽、咯血、潮熱、盜汗及身體逐漸消瘦為主要臨床特征。本病稱謂眾多,如虛勞、癆瘵、傳尸、鬼疰,近現代,才統一命名為肺癆、肺結核病[1]。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的流行,全球結核控制形勢變得嚴峻,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2022年全球結核病報告》[2]顯示,終止結核病方面取得的進展出現倒退,去年全球新增結核病患者1060萬,我國新發患者78萬,在30個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中排第3位。結核病已成為全球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之后單一感染源引起的第二大死因[2]。現代醫學的治療手段主要包括抗結核藥物治療、免疫治療、外科治療等,但對于耐藥性肺結核治療,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4]。同時有研究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肺癆具有一定優勢,在提高痰菌陰轉率、調節機體免疫功能、緩解藥物不良反應等方面療效顯著[5]。
《醫門法律》系我國醫學史上主倡醫學規范的著作,其中設“虛勞”門,對肺癆的病因病機、治則治法和處方用藥進行系統闡述,以四大經典為主,旁及朱丹溪、李東垣等各家觀點,并融入其臨床實踐,使得論述有理有據,頗具特色。同時喻昌在前人的臨證醫案中發現大量失治、誤治情況,進而列“律十條”,對治療禁例作專門闡述,希冀后世醫家引以為戒,盡量減少臨床中的醫源性錯誤。筆者現將其治療肺癆的學術觀點作如下淺析,以饗同道。
1 病因病機
1.1 內傷元氣,精血虧虛 肺癆的正氣虛弱理論,在先賢的著作中已有論述,喻昌受前人啟發,認為內傷元氣,精血虧虛為肺癆發病的根源。虛勞門開篇即言:“虛勞之證,《金匱》敘于血痹之下,可見勞則必勞其精血也。”[6]314喻昌點明其病因為“始因脫血、血虛血少”[6]314。首先其繼承《黃帝內經》對虛勞病的觀點,“凡言虛病不及于勞,然以大肉枯槁,大骨陷下,胸中氣高,五臟各見危證,則固已言之”[6]315,后又通過秦越人的虛損論,推理出其獨重脾胃的觀點。其次參看金元各家著作,繼承朱丹溪的癆瘵主乎陰虛論和李東垣的內傷元氣論。如《丹溪心法》言:“勞瘵之證,非止一端。其始也,未有不因氣體虛弱,勞傷心腎而得之,以心主血,腎主精,精竭血燥,則勞生焉。”[7]《脾胃論》在“胃虛元氣不足諸病所生論”中言及“必先中虛邪,然后賊邪得入矣”[8]。最后喻昌從先天不足和后天失養兩個角度,分析男子、小兒患肺癆的病因,男子多因縱欲勞精,而致陰精日損,轉勞轉虛,轉虛轉勞。童子則因臟腑脆嫩,素體虛弱而轉為癆。正如《中藏經》在“傳尸論篇”所言:“傳尸者,非為一門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氣衰弱,臟腑羸虛,中于鬼氣,因感其邪,遂成其疾。”[9]正氣強弱是肺癆發病的關鍵,也是其傳變轉歸的重要因素。若正氣較強,則能抵御癆蟲,病變局限于肺,趨于好轉;正氣虛弱,則易病情加重,發展成多臟虛損。
1.2 氣滯不行,瘀血阻絡 喻昌認為肺癆通常會由精血虧虛進展至血瘀階段,進而形成虛實錯雜之候。血虛血少,艱于流布,發熱致痹。血蓄于內,氣滯蒸血為熱,熱蒸不已,瘵病成焉[6]314。其提出血虛導致血瘀發熱而成瘵的觀點。隨后論及男子精血兩虛,血不化精,則成血痹。血痹則新血不生,并素有之血,亦瘀積不行。血瘀則榮虛,榮虛則發熱,熱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為蟲,遂成傳尸瘵證[6]315,即血瘀導致榮虛發熱,蒸血化蟲而成瘵。最后提及女子血干經閉,發熱不止,癆瘵之候更多[6]316,即女子常于血瘀的體質狀態之下,發熱成瘵。兒童則因臟腑脆嫩,寒熱積滯,易于結癖成疳,血痹不行,氣蒸發熱。其后亦有多位醫家秉承血瘀致癆的思想,李梴主張“扶正祛邪蟲亦亡”,并在《醫學入門》的癆瘵篇中指出:“蟲亦氣血凝滯,痰與瘀血化成。但平補氣血為主,加以烏梅、青蒿、朱砂之類,而蟲自亡矣。”[10]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上卷“男子勞病”中,提出“查外無表癥,內無里癥,所見之癥皆是血瘀之癥”的見解,其血府逐瘀湯歌訣亦有“血化下行不作癆”的闡述,明確提出肺癆與瘀血的關系[11]。
1.3 外感淫邪,癆蟲內侵 喻昌繼承前人觀點,認為虛勞之人由于正氣虧虛更易受到外邪侵襲,感染癆蟲而致肺癆。他在書中指出醫和視晉平公疾的案例:“是近女室,晦而生內熱蠱惑之疾,非鬼非食,不可為也。”[6]316其次提及紫庭方,主治傳尸、伏尸皆有蟲[6]324。最后引唐代醫家蘇游之言,傳尸之候,先從腎起,依次傳及心肺肝脾,脾初受氣,兩脅虛脹,食不消化,又時瀉利,水谷生蟲[6]324。在此基礎上提出“血瘀則榮虛,榮虛則發熱,熱久則蒸其所瘀之血,化而為蟲,遂成傳尸瘵證,肺癆窮兇極厲,竭人之神氣而養蟲之神氣,人死則蟲亦死”[6]315的見解。恰如唐宗海所言:“人身亦必先有瘀血,虛熱郁蒸,乃生癆蟲。”[12]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臨床經驗的積累,醫家對肺癆病因的認識逐漸加深,對同一病機的理解也不斷深入。從以《金匱要略》為代表的虛勞論,至《千金要方》的肺蟲致病說,再到《醫門法律》的瘀血日久致癆論,皆為后世醫家探析其病因病機提供多重思路。但在現行“十三五”規劃教材《中醫內科學》[13]中,對于肺癆病因病機演變的描述均以虛證為主,未提及虛實錯雜的轉化,氣滯血瘀僅在最后的醫案中略提,其論述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聶廣等[14]臨床觀察100例化療前肺癆患者,結果顯示疾病初期多有火熱之象,存在正邪交爭,虛實轉化的演變過程,而這與教材觀點不同。
2 治法方藥
2.1 健脾補腎,清金潤肺 肺癆的病因大多始于虛勞,由于“勞則氣耗”,過勞后未能及時調整休息,而令機體長時間處于免疫低下的狀態。喻昌遵循李東垣、朱丹溪之理,主張健脾補腎,清金潤肺,選用補中益氣湯、大補陰丸等方,進行加減用藥,從而培補正氣,提高免疫。喻昌非常重視補虛之法,提出治療當立足于患者體質的氣血陰陽狀態,因人制宜進行辨治。首先對于內傷元氣,真陽下陷,而生虛熱者,喻昌提出遵《黃帝內經》之法,以脾腎為要,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強調宜升宜補,選用東垣補中益氣湯、益胃升陽湯二方,用甘溫之藥,大補其氣,提其下陷[6]327。其次對于房勞過度,亡血失精者,注重養血填精、補腎固脫,通過健脾增強其運化功能,令氣血生化有源,正氣盛壯,祛邪外出。他認為陰虛者十有八九,陽虛者十之一二而已。對于陰虛偏重者,選用丹溪大補陰丸、四物加黃柏知母湯二方;陽虛偏重者,選嚴用和芪附湯、參附湯二方[6]330。最后對于陰虛火旺者,主張滋陰降火,潤肺止咳,通過保肺金而滋生化之源。喻昌認為補肺腎即是補陰,臨床多用辛甘淡平寒涼之品,例如薏苡仁、天冬、麥冬、百合、枇杷葉、五味子、桑白皮、地骨皮、牡丹皮等,再佐以生地黃汁、藕汁、人乳汁、童便等藥進行治療。薏苡仁之屬,治肺虛;參地黃膏子之類(以人參、黃芪、熟地黃、天冬、麥冬、枸杞子、五味子之屬煎膏[6]321),治腎虛。若是病久陰損及陽,出現肺脾腎三臟皆虧之證,則通常氣血陰陽各有側重,喻昌叮嚀后世醫者用昔人之法,應如持衡在手,較量于輕重之間,細心推辨“陽常有余,陰常不足”,領悟法中之奧。
2.2 行氣通滯,活血化瘀 喻昌認為肺癆病的發展常由氣血虧虛,進展到氣滯血瘀的病理階段,繼承張仲景亟驅其舊生其新的觀點,主張氣血同調,選用大黃?蟲丸、四物湯等方,行氣通滯,活血化瘀,血道暢通則熱隨瘀去。喻昌言:“虛勞發熱,未有不由瘀血者。”[6]32《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云:“五勞虛極羸瘦……內有干血。”[15]張仲景稱肺癆為干血勞,并指出其病因為飲食起居不節之內傷,而后氣阻血瘀,治以緩中補虛,選用大黃?蟲丸,以潤劑潤其血之干,以蠕動啖血之物行死血。喻昌細參其證,認為此法能夠活血去瘀,調和營衛。許州陳大夫傳張仲景百勞丸方云:“治一切癆瘵積滯,不經藥壞證者宜服。方中選用當歸、乳香、沒藥、虻蟲、大黃、水蛭、桃仁等活血化瘀類藥,將其研成細末,煉蜜為丸,服之以取惡物為度。”[6]328即在患病初期素體未虛之際運用活血之法。
喻昌認為婦人與男子體質不同,氣滯血瘀者居多,在治療上應注重行氣活血,處方用藥上亦當有所區別[6]316。其提出:“婦女癆瘵,十中二三,沖為血海,瘀積不行,乃至血干經斷,骨蒸潮熱,夜夢鬼交,宜急導其血,加人參以行之。”[6]332其強調在肺癆初起之時,以峻劑加人參,扶正祛邪,活血化瘀,退熱除蒸;若是遭夫離絕,菀結不解,后月事不以時下者,則先用理氣之藥調暢情志,后用活血之藥疏通經絡。正如朱丹溪所言:“始健,可用子和法,后若羸瘦,四物湯加減,送消積丸,不致陽虛。蒸蒸發熱,積病最多,勞病,四物湯加炒柏、竹瀝、人尿姜汁,大補為上。”[7]運用八綱辨證對疾病所處階段做出準確判斷,再結合兼證加減用藥,從而使得治療取得良好效果。
2.3 祛邪外出,抗癆殺蟲 喻昌博覽各家之言,已經認識到在肺癆形成過程中的癆蟲病因,但并不主張單獨殺蟲,其認為若是一味去蟲,則蟲去人亦去,強調以補虛為主,兼顧活血化瘀從而驅蟲外出。如論及《金匱要略》附《肘后備急方》獺肝散,歷代醫家運用獺肝殺蟲治癆獲得良效,而他發現張仲景主張行血逐瘀而非攻毒殺蟲,所以制緩中補虛大黃?蟲丸一方。后世醫家唐宗海秉承其辨治思想,認為“殺蟲是治其標,去瘀是治其本也”[12],提出“不治其虛,但殺其蟲,病終不能愈也”[12]的觀點。
在肺癆的治療上,喻昌非常重視時機的選取,強調治未病,在肺癆將成未成之際進行治療便可事半功倍,其言:“儻能服膺仲景幾先之哲,吃力于男子、童子、女子,瘵病將成未成之界,其活人之功,皆是起白骨而予以生全,為彼蒼所眷注矣。”[6]317
3 用藥特色
3.1 喜用人參顧護正氣 《醫門法律·虛勞門諸方》所載方劑中,建中類方居多,用藥甘緩為主,且人參出現頻率頗高,所載30首方中用人參者高達15首。在肺癆初成之際加強祛邪外出之功,在虛損階段則以無形之氣助生人體有形之血。歷代對于人參的運用存在爭議,王節齋認為:“人參入手太陰,能補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陰消,惟宜苦甘寒之藥,生血降火。世人不識,往往服參、芪為補而死者多矣。”[16]喻昌認為王節齋之說失之偏頗,他在《寓意草》中對人參的應用進行詳細闡述。首先表明“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如表藥中,少助元氣,以祛邪為主,使邪氣得藥,一涌而去,全非補養虛弱之意也。即和解藥中,有人參之大力者居間,外邪遇正,自不爭而退舍”[17]101。《神農本草經》記載人參能夠補五臟,定魂魄,除邪氣;薛己《薛氏醫案》謂其但入肺經,助肺氣而通經活血,乃氣中之血藥。由此可見人參乃扶正祛邪之良藥。
喻昌對部分醫者畏用人參的現象進行剖析,其云:“蓋不當用參而用之殺人者,皆是與黃芪、白術、當歸、干姜、肉桂、大附子等藥,同行溫補之誤所致。不與羌、獨、柴、前、芎、芷、芩、姜、半等藥,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17]102他強調在臨床治療中不可一味溫補,而要運用汗法或和法,令邪有出路,與此同時加用人參,通過培補正氣而祛邪外出。喻昌在“律十條”中提及“凡治癆瘵發熱,乘其初成,胃氣尚可勝藥,急以峻劑加入人參,導血開囊,退熱行瘀,全生保命,所關甚大”[6]332,論及婦人癆瘵時,亦強調“急導其血,加人參行之,則成功旦夕可也”[6]332。
3.2 慎用苦寒及輕揚之品 喻氏在處方用藥方面,始終注重顧護脾胃,慎用苦寒以及輕揚之品,他強調以脾、腎二臟為要,溫之以氣,補之以味,謹守精氣,調其陰陽。其言:“服寒涼藥,證雖大減,脈反加數者,陽郁也。宜升宜補,大忌寒涼,犯之必死。”[6]323即使是真臟虛損復受邪熱者,亦大忌黃芩、黃連、黃柏,強調驟用苦寒,反瀉其陽。“律十條”中亦對后世醫者進行告誡,如第二條:“若通套退熱之藥,與病即不相當,是謂誅伐無過,邪反不服,乃至熱久血干津竭。”[6]332又如第四條:“凡虛勞病最防脾氣下溜,若過用寒涼,致其人清谷者,醫之罪也。”[6]332其同時指出一切輕揚之品,禁不可用,用之反引熱勢外出而增其熾,灼干津液,肌肉枯槁四出,更不可認為陽實而責其汗,否則必動其血,下厥上竭,醫之罪也。
4 驗案賞析
《古今醫案按》的癆瘵篇收錄喻昌醫案二則,清代醫家余震認為前案箋方釋證,直造軒岐之堂,后案酌古斟今,足分和緩之坐[18]。兩案均出自《寓意草》“辨治楊季登二女奇癥奇驗”篇,胡卣臣認為其辨證用藥,通于神明,究莫測其涯涘[17]86。故研究兩案蘊含的診治經驗對于臨床具有重要價值,現對其作如下分析。
4.1 楊季登次女案“季登次女,亦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余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于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投十余劑,全不對病。余為徘徊治法,因自訐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癥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漸似喪敗之余,此曷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為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診間見其面色時赤時黃。余曰:此癥確有邪祟,附人臟腑;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才曰:此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栗而絕,以姜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婿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早言?吾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芪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斤,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余蓋以祟附于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膻,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大便而出,仿上古遺精變氣祝由遺事充其義耳。”[17]85
按語:本案患者汗多食少,倦怠消瘦,筋掣肉顫,喻昌認為此乃大驚大虛之候,遂以溫補劑加安神藥治之,然服數劑,病無增減。復診查其神情喪敗,面色時赤時黃,尚有口流白沫,戰栗而絕之癥,喻昌將其歸因于“邪祟”。“邪祟”一詞首見于《格致余論》的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言其病因為氣血兩虧,神衰邪入。余震據案斷其癆瘵,筆者認為該患者尚處于此病將成未成之際,證屬氣陰兩虛。氣虛固攝無力,遂現多汗、口流白沫之象;陰血不足,虛風內動,遂致筋掣肉顫、戰栗而絕之癥。喻昌用犀角、羚羊角、虎威骨、龍齒除邪惡氣,殺鬼疰毒;鹿角霜、人參、黃芪補中益氣,安神定驚,治疾病之本;牡蠣粉收斂固澀,止汗止咳,治疾病之標;再加以半斤羊肉,其性大熱,中和介石與靈骨之寒,溫肝暖脾而補虛養血。全方共奏益氣養陰、除熱息風之效。但喻昌從上古移精變氣,將“邪祟”轉附骨角的祝由角度進行解釋,筆者認為此論述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難以科學指導當今臨床用藥。
4.2 熊仲紓先生幼男案“吾鄉熊仲紓先生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癥,食飲如常,但脈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殗碟,《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即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17]86
按語:本案患者脈細神呆,氣奪色夭,一派氣血兩虛、精氣衰憊之象。喻昌診其“殗殜”,在中醫學的古籍文獻中虛勞、結核類疾病常被稱為“殗殜”[19]。《左傳·昭公元年》載醫和診晉平公,言其病“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喻昌酌古斟今,認為本案患者雖有殗殜內熱之表現,但未曾近女,且食飲如常,故斷其非純虛無實之證,遂行補氣養血、活血通經之法,令患者以案1湯劑送服牛黃丸。喻昌在著作中未提及牛黃丸的組成,筆者通過查閱《中醫方劑大辭典》,發現同名異方者甚多,主治多為驚癇與疳證,其中有3首方劑主治癆瘵,且均含牛黃、麝香、人參3味藥。筆者推測牛黃丸應以牛黃為主藥,行清心開竅、豁痰定驚之功;麝香則活血通經,除邪辟惡,《本草經集注》記載其能“辟惡夢及尸疰鬼氣”[20];人參補脾益肺,祛邪外出。喻昌辨證準確,處方精當,兩方合用共奏健脾益氣、養血活血之效。患者服藥旬日而安。
5 小結
我國每年有將近80萬的肺癆新發患者[2]。隨著結核耐藥性的不斷增強,患者的生存狀況及國家的公共健康管理均面臨一定的挑戰。目前西藥在抗癆殺蟲方面起著關鍵作用,但長時間使用化療藥物,容易引起過敏及胃腸反應,患者常因難以耐受而中斷治療[21]。因此中醫藥防治肺癆的重點應為培補正氣祛邪外出,以及減輕不良反應,保證西藥治療的全程性。
喻昌在儒、佛、醫等領域均有涉及,最終以醫學名世,他不僅博覽醫書繼承前人學術精華,還能提出獨到見解[22]。在肺癆病機方面,其強調正氣虧虛,瘀血阻絡,癆蟲侵襲,認為三者相互為因、相互遞進;在治療方面,其主張以補虛為主,兼顧活血化瘀,同時注重審時度勢,治肺癆于將成未成之際;在用藥方面,其則喜用人參顧護正氣,慎用苦寒及輕揚之品。
當前學者對于肺癆的文獻研究尚未全面,喻昌論病析治嚴謹,針砭時弊,因此整理其辨治肺癆的臨證經驗與學術特色,以期為現代中醫臨床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