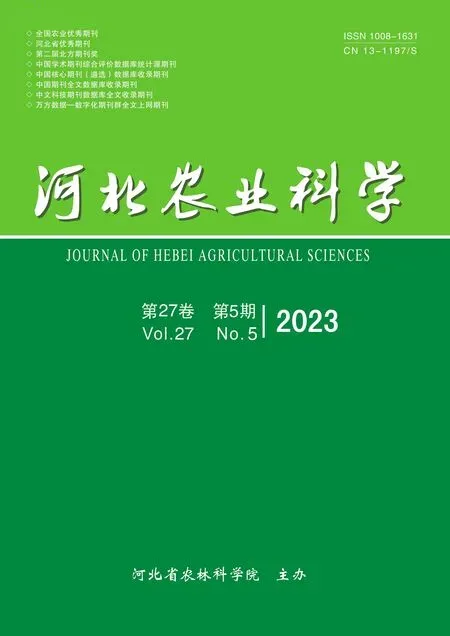河北省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和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與分析
苗海民
(燕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近年來,隨著城鄉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相關制度環境的不斷改善,對農村人地關系的跟蹤與分析引發了學者們的關注[1]。一些學者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地流轉有積極作用,姚洋[2]認為非農就業市場結構對農地制度和流轉市場的發育密切相關,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必然會影響農地的流轉,James[3]、賀振華[4]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促進了農地流轉市場的發育,帶動了農地流轉[5,6];張務偉等[7]、Baozhong 等[8]認為非農就業轉移和農地流轉之間存在協同關系,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的相關性會提高[9]。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勞動力轉移未必會促進農地流轉,葉劍平等[10]認為我國土地流轉的發生率嚴重滯后于農村勞動轉移率,一方面是因為土地的生存性依賴是抑制土地流轉的重要根源[11,12],另一方面是因為勞動力轉移與農地的流轉不存在因果關系[13];廖洪樂[14]認為勞動力流動對農戶土地流轉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只有當農戶勞動力流動達到閥值時才能有效促進土地流轉。Klaus 等[15]、Mullan 等[16]認為當農村勞動力真正從農業生產中轉出時,才能促進土地流轉市場發育。綜上所述,現有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農村家庭勞動力流動與土地流轉的關系,而對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和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入的影響研究甚少。基于此,利用河北省的面源數據,分析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進而為改善城鄉要素市場制度建設提供政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選取2017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河北省的數據,剔除空缺值和異常值,最終獲得觀測樣本值共計5 978個。涉及的指標主要有流動人口及家庭成員人口基本信息、流動范圍和趨向、就業和社會保障、收支和居住等。
1.2 研究方法
1.2.1 理論分析與假設 隨著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加之農二代的代際革命與市民化追求[16],使得農民工從外出務工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標,開始逐步向成為城市市民并融合到城市中目標轉變。這種轉變是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規律,但是在城鄉二元制度路徑依賴下,現有相關制度不利于農民工非農就業和市民化目標的實現,也不利于城鄉融合發展。因此,外出務工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與土地經營的小規模化,是農民工家庭在既有制度下的自我選擇,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城市融合與土地流轉具有內在關聯。
1.2.1.1 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對農地流轉的影響機理分析。我國農民工就業多為非正規就業,就業穩定性較差和相關福利均不太理想[17]。在這種制度環境下,大多農民工通過農村鄉土社會網絡建立起了自己穩定的非農就業渠道,農民工主要依靠傳統的血緣、地緣人際關系,以點帶面地不斷擴大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規模。由于缺乏正規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加之城市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當前農民工就業多是基于傳統農村鄉土社會網絡發展而來。從而,農民工的這種非農就業及其穩定性加大了對農村社會的依賴,不利于其脫離鄉土農村社會。而農民工對農村依賴的增強,會映射到對農業生產和土地流轉上,使得農民工家庭更加傾向于經營土地,從而不利于農村土地的流轉。因此提出假設1: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不利于農村土地流轉。
1.2.1.2 農民工城市融合對農地流轉的機理分析。盡管大多數農民工非農就業局限在農村鄉土社會網絡中,但是隨著農民工非農就業時間的積累,以及當前城市人口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戶籍制度的改革,農民工城市融合度在不斷提高[18]。當城市的拉力大于農村的拉力時,農民工逐漸脫離農村鄉土社會網絡,逐步融入到城市社會中,降低對農村社會的依賴。因此,城市社會融合降低了農民工對農村鄉土社會網絡的依賴,從而使得農民工對農村土地的粘度下降,更加傾向于土地的流轉。所以,農民工城市融合的提升,會促進農村土地的流轉。因此提出假設2: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融合有利于農村土地流轉。
1.2.2 Mprobit 回歸模型構建
1.2.2.1 指標體系構建。根據研究內容與數據的可獲得性,構建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評價指標體系(表1)。
被解釋變量為土地流轉(Y)。從農民工家庭實際情況看,隨著農二代的代際革命發展,農民工對土地依賴作用逐漸減弱。但是鑒于城市非農就業不穩定性增強和市民化成本約束,農民工對農地依然具有一定的粘性,不同粘性使得農民工對土地流轉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土地流轉存在以人情租形式的零貨幣化租金流轉方式,也存在貨幣租金形式的流轉方式,兩者是土地市場發展不同階段的土地流轉方式,故被解釋變量存在土地未流轉、零租金流轉、非零租金流轉3 種形式。
核心解釋變量是指農民工的非農就業穩定性和城市社會融合2 個方面。非農就業穩定性是較低層次的市民化,并進一步影響到高層次的城市社會融合。
控制變量主要是指農民工的個人特征變量及其家庭特征變量,農民工的個人特征變量具體包括非農就業者的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和健康狀況等;農民工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特征、土地特征和家庭收入等。
1.2.2.2 MProbit 模型構建。根據研究內容,構建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MProbit 模型,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Y為土地流轉形式;β1為截距項,Xi為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βi為回歸系數,ε 為殘差項。
2 結果與分析
2.1 核心解釋變量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
2.1.1 非農就業穩定性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分析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分別在0.01、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零租金、非零租金土流轉行為,即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越強,越抑制其土地流轉,說明固定雇主身份抑制了農民工的土地流轉。這可能是因為當前大多數農民工對土地有較強的依賴性,非農就業穩定性是在傳統鄉土農村社會網絡下形成的,并非直接從非農勞動力市場中獲取,抑制了土地流轉行為的發生。假設1 得到了驗證。
2.1.2 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分析 城市社會融合在0.05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零租金、非零租金土流轉行為,即農民工的城市社會融合度越高,越能促進其土地流轉。因此隨著城市流動時間的積累,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意味著其從傳統農村鄉土社會網絡向城市鄉土社會網絡的發展,降低了農民工對農村社會和農業的依賴,從而使得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促進了土地流轉。假設2 得到了驗證。
2.2 控制變量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
2.2.1 控制變量對零租金流轉行為的影響 在非農就業穩定性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1)中,年齡(X3)、受教育程度(X4)、有效證件(X14)、家庭總收入(X17)、土地面積(X18)、家庭總數人數(X20)和家庭撫養壓力(X21)正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3、X14、X17、X20和X21顯著正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他變量負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6、X8、X9、X15和X16顯著負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表2)。
在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2)中,年齡(X3)、有效證件(X14)、家庭總收入(X17)、土地面積(X18)、家庭總數人數(X20)和家庭撫養壓力(X21)顯著正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他變量負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6、X8、X9、X14、X15、X16顯著負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
2.2.2 控制變量對非零租金流轉行為的影響 在非農就業穩定性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1)中,受教育年限(X4)、喪偶或離異(X7)、健康狀況(X8)、從事住宿餐飲業(X13)、省內跨市(X15)、市內跨縣(X16)、土地面積(X18)和家庭總人口(X20)負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4、X15和X20顯著負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他變量正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3顯著正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
在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2) 中,受教育年限(X4)、喪偶或離異(X7)、健康狀況(X8)、從事住宿餐飲業(X13)、省內跨市(X15)、市內跨縣(X16)、土地面積(X18)和家庭總人口(X20)負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4、X15和X20顯著負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他變量正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其中X3顯著正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表2)。
2.3 核心解釋變量對土地流轉行為的邊際效應
2.3.1 非農就業穩定性對土地流轉行為的邊際效應分析 有固定雇主的農民工土地不流轉的邊際效應大于其他農民工,零租金流轉、非零租金流轉的邊際效應小于其他農民工(表3)。說明有固定雇主會抑制農民工土地流轉行為。

表3 非農就業穩定性、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的邊際效應Table 3 Marginal effects of no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2.3.2 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的邊際效應分析認為自己是本地人的農民工土地不流轉的邊際效應小于其他農民工,零租金流轉、非零租金流轉的邊際效應大于其他農民工,說明城市社會融合可以促進農民工土地流轉行為。
3 主要結論與建議
3.1 主要結論
基于河北省的面源數據,構建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評價指標體系,利用Mprobit 模型分析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對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以及邊際效應,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農民工非農就業穩定性分別在0.01、0.05 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零租金、非零租金土流轉行為;城市社會融合在0.05 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零租金、非零租金土流轉行為。
(2)在非農就業穩定性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1)、城市社會融合對土地流轉行為影響的方程(2) 中,年齡(X3)、有效證件(X14)、家庭總收入(X17)、土地面積(X18)、家庭總數人數(X20)和家庭撫養壓力(X21) 正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婚姻(X6)、健康狀況(X8)、制造業(X9)、省內跨市(X15)和市內跨縣(X16)顯著負向影響零租金流轉行為;受教育年限(X4)、省內跨市(X15)和家庭總人口(X20) 顯著負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年齡(X3)顯著正向影響非零租金流轉行為。
(3)有固定雇主的農民工土地不流轉的邊際效應大于其他農民工,零租金流轉、非零租金流轉的邊際效應小于其他農民工。認為自己是本地人的農民工土地不流轉的邊際效應小于其他農民工,零租金流轉、非零租金流轉的邊際效應大于其他農民工。
3.2 建議
3.2.1 拓寬農民工非農就業渠道 政府應轉變職能,建立并完善農民工就業網絡平臺和人才服務網,及時更新各種招聘和求職信息,拓寬企業信息來源,了解農民工供給渠道[19,20]。
3.2.2 深化城市人口制度改革 轉變城市人口管理理念,堅持以“淡化戶籍意識,強化居民意識”理念,以居住證為載體,逐步讓進城農民工享有戶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可靠、有效、優質的農民工就業信息服務系統,充分利用和整合資源,推進農民工信息網絡建設,為加強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