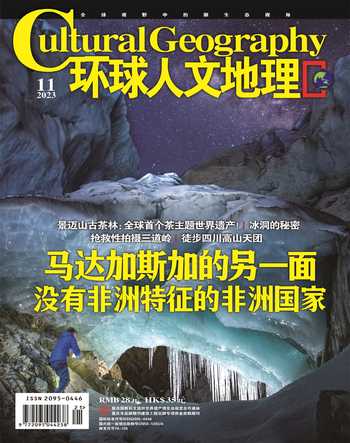石堰塘的春秋
李俊蝶
1.
重慶多以山水特征取作地名。比如:沱,單義為可以停船的水灣。用于地名,則李家沱、唐家沱;凼:水坑,田地里漚肥的小坑。常見有,白馬凼、斑鳩凼;還有著名的長江三峽、巫峽、瞿塘峽中的峽,指的是兩坡陡峭、中間狹而深的谷地。
在重慶,與石相關(guān)的地名有13259處,與堰塘相關(guān)的,8346處。連起來的石堰塘有多少我不清楚,只聽說,合川就有三處。父親祖輩生活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
石堰塘。石頭,水塘。
石堰塘,確實有兩口石頭修建的簡易水塘。大點的叫大堰塘,小點的叫小堰塘。做飯洗衣農(nóng)用灌溉,塘里也種荷花,養(yǎng)魚。夏季,堰塘的水只到坡坎的一半,等冬季逐漸盈滿。
石堰塘,忙碌的時節(jié)是春天和秋天。春天插秧,秋天收割。
2.
母親說,她把我放進水桶。然后是老井田,她在前面插秧,我在身后漂浮,繩子的一頭連著她的腰,一頭連著裝我的水桶。
這個充滿詩意的描述,遮掩住她當時的窘境。農(nóng)忙時節(jié),還未歸家的丈夫,無人看顧的尚在學步的孩子。
她不擅長農(nóng)活。挑水施肥鋤地,完全不會。她在家做姑娘的時候,做活前頭有三個哥哥頂著,又因為排行老幺,體弱,更是被照顧得多。她和父親經(jīng)二伯母介紹就確定了關(guān)系,婚后第一次到石堰塘,才知道這里與她從小生活的地方有多么不一樣。
這里沒有寬闊的河,沒有水碼頭,沒有石板路,只有山一座連著一座。這里分一、四、七,去鎮(zhèn)上趕集添置肉食、日常用品,可以坐一元的班車或者相近的人家結(jié)伴走路。這里竹林茂盛,家家戶戶的男人都慣用竹條編制背簍、簸箕、掃帚之類。
母親努力地融入這里的生活。山路走到腳起泡,挑水吃力就半桶半桶地挑,鋤頭第二天還要做活就直接丟在田里。辦法總歸是人想出來的,日子慢慢就過得順絡。
當養(yǎng)殖的風兒吹到石堰塘。母親背著背簍,上坡下坎地收割著蒲公英、拉拉秧、牛筋草。石堰塘生長出的青草芬芳。她總在露珠凝結(jié)的清晨出門或借一些霞光歸家,她總能比別人找到好地方。她的兔子在石堰塘養(yǎng)得最好,一窩窩的活潑肥美,一窩窩的聽話乖巧。村上的隊上的婦人,也常來向她討教。
而后談起那段時光,母親說,“我這個外鄉(xiāng)嫁來的女人,沒有歸屬感。起初是常被多事的笑話不會農(nóng)活,你父親又常不在身邊,我在人后暗自較勁。后來得虧這些雞呀兔的,在我手上都很靈很乖,讓我有了些生活的底氣。也真感謝石堰塘這片土地對我這個蠢笨的人照顧了許多。”
3.
一只麻雀跳進水洼洗澡,石堰塘的春天就來了。
關(guān)于春天。關(guān)于石堰塘。麥穗飽滿,我匍匐在一片麥地,等著呼喊著我名字的母親走過。麥苗桿細長,葉子也細長,我緊張地低下頭貼近土地,麥穗高昂著。母親是穿著什么樣式的衣服呢?手里拿著竹條嗎?只還憶得起泥土顏色發(fā)黑,麥苗是扎眼的綠。
這是我逃學的第三天。我在上學時間到處游蕩的信息終是傳進了母親的耳朵里。當我發(fā)現(xiàn)遠遠走來的母親,慌張著躲避,周遭都是低矮的菜苗,只有那一片麥地。
母親走后,我躲進了一間未完工的紅磚房。這里離家很近,我靜靜地坐在一堆紅磚之上,仿佛一只蝴蝶等著宿命降臨。陽光落進沒有門窗的房,安靜。我小聲哼起不知名的調(diào)子。衣兜里還剩有一個紅桔。我拿著它走到陽光下,看著它發(fā)亮。它逐漸發(fā)燙。那時的我為接下來的結(jié)局恐慌,也沒有想到過會離開石堰塘。
這個小村莊,溫暖。可以包容錯誤,彷徨。也允許著夸大時光。把思想放下,就看見了大地和天空寬廣。
這里,竹林很綠,言語很深。空氣中漂浮砂仁花的奇思妙想。在這里,我撫摸過桃樹的眼淚,收藏野雞的尾巴毛,旁觀九月是一場眾生的喧鬧。
我喜愛村莊上方懸停的云,在黃昏的黃,或者清晨的純白、微藍。我的家沒有羊群,但抬頭看到它,就感覺自己躺在綠油油的山坡上放羊。我說開個花吧,呼啦啦地身邊就無數(shù)多小野花冒出了頭,五顏六色的漂亮。云朵是一種不知名的白,我把它放進指甲,與鳳仙花一起慵懶。也留下部分,送給堰塘里的白荷問安。當云朵變成雨落下,屋壩就濕了,母雞飛著跑著臥進竹林的沙坑避雨。而我在竹林之外,仰頭張著嘴在雨里走走停停。那時有一個神奇的夢里有一個神奇的人告訴我,有一滴神奇的雨吃掉就能幻化成云,守護莊子里的生靈。
4.
像月亮是星星的依傍,我經(jīng)常想起石堰塘。追著野兔滿山跑,支起竹簍逮雀鳥,青蛙跳進水塘,爬上桃樹被八角釘刺咬,放聲大哭又大笑。某些被壓抑的野性在腦海叫囂。
回到石堰塘。年輕的一輩大多離開了這里去城市定居,只剩下年邁的人跟著石堰塘一起年邁。所以,她,愈發(fā)寂靜,泥土也失去生機。
穿過小堰塘的竹林,老屋就近了。他灰蒙著,角落飄搖著斷斷續(xù)續(xù)的風干的蜘蛛網(wǎng)。堂屋很暗,二樓轉(zhuǎn)角的燈不亮了,谷倉沒再裝過稻米。陰雨從閣樓縫隙流下,白墻便有了烏黑的淚痕。青苔干涸,我摩挲著水泥石的露臺,在這里的,我臆想不夠一把沙灘椅的童年,藍白條紋的帆布,我曾躺在上面見過一整個繁星璀璨的夜晚。
在睜眼夢就失溫的惆悵里,白云溫順,黃昏掉落只言片語。桑葚熟了,有些晚荷在霞光里生長蓮子,螃蟹悄悄地紅起來。離鄉(xiāng)的年月,石堰塘逐漸成為拗口的生詞。成為筆記里干癟的情深。成為后院雨后被鳥啄爛的桃子。成為許多風過花落的憾事。
我試著沿著父親的足跡去觸摸,在一個傍晚,太陽落坡,父親與大伯扛著拌桶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撿拾掉落的稻谷走了好遠好遠。在那個傍晚,我彎下的腰,骨頭磋磨的那刻成為若干年后身體的疼痛,時刻提醒著。
這片生養(yǎng)的土地,是一位圣者,她隱身于我的歡樂,出現(xiàn)在落寞。
她讓我有一地安息,讓我踏實的遠去和隨意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