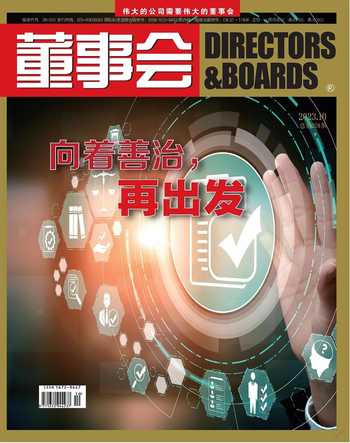對并購標的業績造假必須“零容忍”
熊錦秋

一旦交易對手對并購標的業績造假,上市公司則需要對公司層面的財務報告進行差錯更正,上市公司是否由此產生對投資者的民事責任?這需要視情況而定
10月9日聯創股份發布公告稱,被告人孔剛等共謀包裝上海鏊投被聯創股份高價并購,山東省高院終審判決維持原判,五名被告人均被判犯有合同詐騙罪,分別被判處三年至無期徒刑不等的刑期。筆者認為,應依法嚴懲并購標的業績造假行為。
2017年9月和2018年8月,孔剛等人與聯創股份簽訂協議,約定聯創股份分兩次收購上海鏊投全部股權。在孔剛策劃下,上海鏊投通過借用體外資金、購買虛假業績等手段虛增公司業績,提升上海鏊投估值,以達到被上市公司并購的目的;在不具備合同履行能力的情況下,許諾很高的業績承諾,最終誘騙上市公司與其簽訂協議。根據判決結果的司法鑒定數據,上海鏊投2017年至2019年期間累計虛增凈利潤約3.44億元。
高估值、高商譽、高業績承諾的“三高”并購重組,在A股市場可謂屢見不鮮、前赴后繼。有些上市公司的并購案例中,交易對手對標的高業績承諾純屬吹牛,目的是獲得高對價。但業績吹牛容易兌現卻難,有些并購完成后交易對手繼續對標的業績實施造假,以規避或減少可能存在的業績補償責任,同時確保其所獲上市公司股票可按時解鎖減持。
并購種交易對手業績造假、騙取上市公司股票或現金等違法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的特征,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此類行為情節特別嚴重的甚至可處無期徒刑。對此,從刑事角度追責,可強力懲治并購市場的欺詐等違法行為,形成高壓震懾。尤其本案中,法院還判決被告人向上市公司返還違法所得現金及股票,這有利于減少上市公司損失,讓違法者在金錢方面也難以得到絲毫好處。
上市公司并購完成后,如果向標的公司派駐管理人員并取得實際管理權,交易對手或以此作為擺脫業績補償責任的借口。由此,上市公司對標的公司原主要負責人任職一般不會輕易作出變動安排,這也導致標的公司財務造假存有一定操作空間。上市公司在聘請中介機構進行審計時,相關人員對并購標的業績真實性應多加留意。
事實上,對于交易對手支撐溢價幾倍甚至十幾倍收購的極高業績承諾,上市公司董監高理應抱著高度懷疑而非輕信的態度。假若標的公司凈資產1億元,承諾年凈利潤1億元,這么高的收益率堪比畝產稻谷上萬斤一樣不切實際。如果當初輕易相信實施并購,標的公司業績在納入上市公司合并報表范圍幾年之后才察覺被騙,此時上市公司再向交易對手起訴追責或為時已晚。標的公司財務數據不實將導致上市公司財報不實,甚至構成虛假陳述,會對投資者利益產生影響。
一旦交易對手對并購標的業績造假,上市公司則需要對公司層面的財務報告進行差錯更正,上市公司是否由此產生對投資者的民事責任?筆者認為,這需要視情況而定。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侵權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條規定:“被告能夠證明虛假陳述不具有重大性,并以此抗辯不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只有證明虛假陳述行為具有重大性,虛假陳述行為和投資者的損失之間才具有因果關系。當然,對于不具有重大性的舉證責任,由被告來承擔。
就本案而言,由于聯創股份2018年、2019年凈利潤分別為-19.54億元、-14.74億元,在此期間并購標的業績造假規模對于上市公司整體業績的影響貌似不大,是否構成重大性標準有待推敲。當然對重大性的認定,還需結合標的業績造假實施、揭露及上市公司更正行為綜合判斷,要考察相應時期股價和交易量變化等情況。
如果并購標的業績造假,導致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被法院認定達到重大性標準,那么相關主體自然就應承擔對投資者的民事賠償責任。要追究這個責任,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向直接策劃實施并購標的業績造假者(主要是交易對手)追究賠償責任,其次是向輕信標的畸高業績、在上市公司年報等簽字的董監高追究民事責任,若其存在與交易對手共謀造假的行為,也可作為首要追責主體進行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