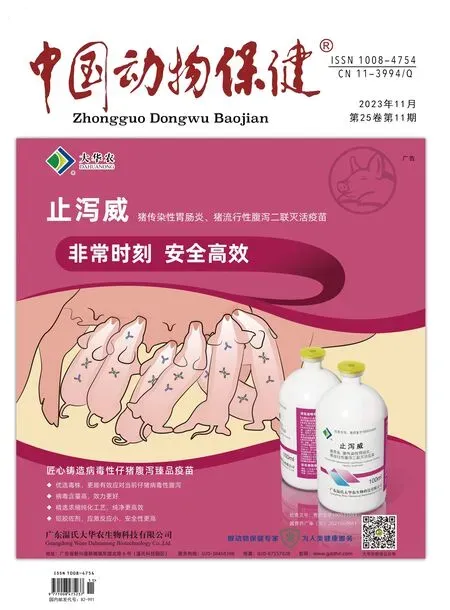布魯氏菌病在我國流行現狀及防控措施
洛桑江白
(西藏自治區獸醫生物藥品制造廠 拉薩 850000)
布魯氏菌病是由革蘭氏陰性球菌布魯氏菌經過多途徑侵入機體,引起人畜共患變態反應性傳染病。最早關于布魯氏菌病的記錄在公元前4 世紀,隨后在公元79 年結合考古研究,在古老的山羊標本里發現布魯氏菌病,直到1859 年,英國陸軍醫生Jeffery Marston 從醫學角度分析了該病,1887 年由英國軍醫Bruce 首次分離到本病病原體[1],將其命名為“布魯氏菌”。之后隨著研究的深入,布魯氏菌病在全世界廣泛流行,且尼日利亞、印度、巴西、巴基斯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多見,我國將其列為乙類法定傳染病。布魯氏菌病可引起牲畜中晚期流產、宮內胎兒死亡或早產,后代生育能力弱等對哺乳動物造成很大影響[2]。患者可出現反復高熱、肌痛、發冷、關節痛、體重減輕等癥狀。該病幾乎會影響人體的每一個器官和系統,且流行率一直在波動,該病已成為流行最廣泛的人畜共患病,目前尚未有下降的趨勢。因此,綜合防控研究對人群及牲畜健康發展非常重要。
1 國內流行現狀
牛羊布魯氏菌病的危害主要是流產,繁殖受到影響等,對農業生產影響較大。我國西北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牛羊布魯氏菌病發病率較高,特別是甘肅河西地區。張輝[3]在2013—2017 年對河西5 市的19 個縣的1 456 357 只羊進行血清分析,結果顯示陽性率每年依次為0.17%、0.87%、1.87%、1.25%、0.33% 。整體呈先升后降趨勢,分析原因可能是牛羊布魯氏菌病防控經費不足、養殖環節缺乏科學飼養管理及各部門的協調不到位等因素有關。近年來我國對布魯氏菌病的防治方面,設立省級監測點、相關機構做好了病例發現及通報工作、加強了流行病學監控等加大防控措施,故情況有所好轉。陳永亮等[4]對北京密云區布魯氏菌病發病率進行調查發現,2013—2017年顯示感染動物以羊為主,占總感染動物的81.25%,且導致人間傳播感染布魯氏菌病的來源主要是羊,屠宰場工作人員、飼養員、運輸員等高危職業人群感染率較高。
布魯氏菌病分散世界各地,在我國首次報告于1905 年,重慶有2 例,至1949 年,北京有29 例[5]。當時我國醫療資源匱乏且公民意識淡薄等多種復雜因素,使1960 年左右布魯氏菌病在我國人間流行情況較為嚴重,盡管在20 世紀70、80 年代逐年下降,但是90年代布魯氏菌病的疫情有上升趨勢,就國內而言,90 年代隨著病原菌的變異及人員流動范圍的擴大,每年實際新發布魯氏菌病例數可能達到10 萬人左右[5],且屠宰場工作人員、飼養員、畜牧人員等為主要發病人群。2010 年底東北農業大學動物試驗中,28 名師生感染布魯氏菌病。浙江省鎮海區疾控中心在2011 年抽取1 個屠宰場和2 個奶牛場的血樣時,發現2 名屠宰場工作人員感染布魯氏菌病。2019 年12 月7 日,蘭州獸醫研究所96 人感染布魯氏菌病,均未出現明顯的感染癥狀,為隱性感染。飛鶴乳業也曾有數百頭奶牛和數十名工作人員被感染。近年來我國人間布病感染的情況日益嚴重,2019 年我國人間布病病例數達44 036 例(同比增長16.05%),2020 年人間新發病例數上漲至47 245 例[6]。主要分布在北方省份,南方增長比例高于北方。
2 布魯氏菌病的發病機制及臨床表現
布魯氏菌病的發病機制在人群中大致如下:布魯氏菌侵入人體后可隨淋巴液沿著淋巴管轉移,轉移至相應的淋巴后被巨噬細胞吞噬。細菌進入巨噬細胞后,在巨噬細胞中可引發免疫反應,受到一系列化學殺菌物質和自由基的攻擊,繼而形成布魯氏菌的原發病灶。潛伏在機體內的布魯氏菌,在人體免疫力減弱時,通過在細胞內質網進行增殖復制,在原發病灶處大量繁殖,并利用多種毒力因子在巨噬細胞內得以持續存活,可導致巨噬細胞破裂并進入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中,當大量病原菌侵入人體時,吞噬反應能力被激發。當血液循環中的病原菌含量激增到超出機體的吞噬能力時,進入富含巨噬細胞的組織,如骨髓、肝臟、脾臟等器官導致機體器質性病變,同時擴散到如孕婦胎盤滋養細胞、胎兒肺和生殖道等目標器官。受累的臟器中,病原菌可繼續繁殖生長,采取一種兼性和隱蔽的細胞內生活方式,同時又不斷進入血流并分泌毒素,反反復復形成慢性感染。隨著病情反復發作,避開先天性和適應性免疫反應及抗生素的作用,有些肉芽組織發展為纖維化硬化性病變,并持續損害宿主機體健康[7]。
人感染后潛伏期一般為7~60 d,平均潛伏期為14~21 d(短者1 d 即可發病,長者6 個月到1 年才發病)。臨床表現:布魯氏菌病屬于多系統多臟器損傷性疾病,以乏力、發熱、食欲差、多汗以及肝脾及淋巴結腫大、骨關節炎、肌肉疼痛、體重下降等器質性病變等為主要癥狀[7],臨床表現比較復雜,其中關節疼痛和發熱最為常見。布魯氏菌病與傷寒、副傷寒、淋巴結核、風濕熱、肺結核、瘧疾和風濕性關節炎等疾病容易誤診,必須依據臨床特征、流行病學史和實驗室檢查等綜合給予診斷[7-9]。
3 防控技術
3.1 診斷技術
有些布魯氏菌患者早期臨床表現無明顯特異性,因此實驗室診斷尤為重要[10]。常規的診斷技術有虎紅平板凝集試驗、熒光偏振檢測法、ELISA 試驗、半抗原-瓊脂擴散試驗和病原學檢測:①虎紅平板凝集試驗(RBT),適合早期診斷,敏感性高、特異性低,價格便宜,操作簡便。對疫苗產生的抗體敏感性高,適合篩選試驗。目前有市面上有高通量全自動智能布病檢測儀器,適用批量篩查;②熒光偏振檢測法(FPA),方便快捷,15 s 至2 min 分鐘能出結果。敏感性高、特異性高。結合疫苗免疫時間,能一定程度上區分疫苗與野毒感染。儀器便攜,能夠在野檢測樣品,但是需要特定的FPA 儀,比起傳統方法,試劑較貴;③ELISA 試驗,敏感性高,適合篩選試驗。試驗通量高并對疫苗產生的抗體敏感性高,但是試劑不同,敏感性和特異性差異大;④半抗原-瓊脂擴散試驗(NK-GD),NK 抗原作為鑒別野毒感染與疫苗免疫的重要靶標,S2 和Rev.1 免疫背景下,能區分感染抗體和疫苗抗體,有效鑒別假陽性。操作技術和儀器設備簡單、結果肉眼直觀、成本低但敏感性低,與布魯氏菌產生的抗原刺激強弱有關;⑤病原學檢測針對流產物、生殖道分泌物、淋巴結、脾臟、乳等進行明確的診斷,但是耗時長、費用貴,需在BSL-3 實驗室分離鑒定,要做好生物防護。
3.2 免疫技術
控制布魯氏菌病最經濟的方法之一就是對高危人群和牲畜進行疫苗免疫。目前常規的牲畜免疫疫苗有:①A19 株和S2 株疫苗是最常見的預防布魯氏菌病的疫苗,屬于弱毒活疫苗。S2 疫苗應用于牛時,難以控制劑量,提供的保護力不如A19 疫苗,但是S2 疫苗提供的保護力對于非疫區的布病防控工作仍然可觀[6];②布魯氏菌滅活疫苗:綿羊布魯氏菌病的滅活疫苗是滅活198 的5 種抗原與高分子L-121 和細胞壁酰基二肽結合[11],可作為綿羊布魯氏菌的有效疫苗;③布魯氏菌亞單位疫苗,是一種重要的DNA 疫苗,通過分析布魯氏菌的免疫活性,優選布魯氏菌的免疫片段制成的疫苗。最近獲得新獸藥證書的布魯氏菌基因缺失標記活疫苗(M5-90),配套鑒別診斷技術,可以實現對自然感染和免疫動物的有效區別;④布魯氏菌合成肽疫苗:是預防布魯氏菌最安全的疫苗,通過人工合成具有免疫作用的保護性短肽與載體連接,添加佐劑合成。某些特定肽可能具有細胞免疫系統優先識別的特性,進而激活T 細胞發揮作用[12]。
4 防控措施
近年來布魯氏菌病感染率上升的趨勢,2022 年我國農業農村部制定畜間布病五年行動方案,以“系統治理、源頭防控、維護三個安全”的指導思想,到2026 年,實現總體流行率有效降低,個體陽性率控制在0.4%以下,群體陽性率控制在7%以下的總體目標。對重點種牛、種羊、奶山羊和肉牛采取疫苗免疫、定期檢疫等源頭防控措施。加強傳播途徑中相關主要因素的管理,加強對屠宰場的檢疫和監督管理,病畜與健康牲畜分群放牧,病畜屠宰淘汰以及糞便要經無害化處理;流產物應深埋,污染場地嚴格消毒;加強對乳、肉、皮、毛等的監督管理;保護水源,防止被患者及病畜的排泄物污染。高危人群做好個人防護,實施菌苗免疫。接觸病畜時,戴好口罩、應著防護工作服、圍裙、帽子、手套等做好綜合控制措施[13]。
面對這種危險性與挑戰性并存的疾病,應將構建綜合防控協調機制,明確和強化監管職責,加大布病的科研投入,研發高效的診斷方法以及疫苗、藥物;完善疫情報告制度,密切監測布病疫情;疫情防控工作進行督導,提高群眾對布病的危害意識,從動物源頭阻斷向人群的傳播等措施,保障人類、動物和環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