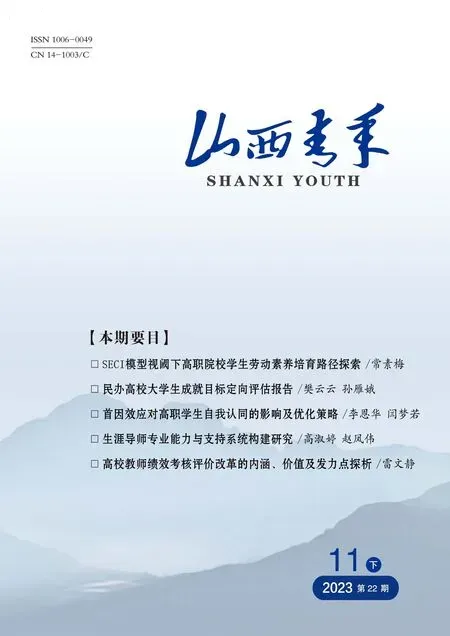高職醫學生心理社會失調干預及康復措施研究
劉 芳 黨亞玲 孔艷蓉 王思云
云南工程職業學院,云南 昆明 650304
由于個體在心理方面存在某些問題,當其融入群體時,極易產生社會適應不良即社會失調,在心理、生理和行為特征上出現異常表現,例如失眠、煩躁、注意力不集中、緊張、難以融入新環境、迷茫、自卑、抑郁等,這種社會失調往往由多重因素引起,例如原生家庭、環境改變、遺傳和疾病、教育、文化、社會重大事件等。
本研究面向某高職院校一千余名受訪者,采用SSS(軀體化癥狀自評量表)、PHQ-9(抑郁癥篩查量表)、GAD-7(廣泛性焦慮量表)、應激感受量表對在校醫學生的身心健康情況進行調查,篩查出心理方面存在社會失調狀況的典型案例并確定干預對象,著重關注其在心理社會失調方面存在的問題,探索其產生的原因和表現,以CBT 團隊聯動方式,通過認知行為干預,使干預對象的社會適應不良狀況得到改善。
一、高職醫學生在成人初顯期出現心理社會失調的原因分析
所謂成人初顯期是由青春期向成人期過渡的階段,通常為18 ~25 歲。這一發展階段具有不穩定性,個體的抑郁呈現上升趨勢,進入成年期后,隨著生活和心理狀態的穩定,抑郁狀況逐漸下降(Galambos&Krahn,2006;Meadows,Brown,&Elder,2006)[1]。抑郁狀況會使個體產生一定程度的錯誤認知,焦慮情緒亦會外化為軀體癥狀。研究發現,對于部分個體而言,抑郁和焦慮同時存在、共同作用,使個體產生社會失調。因此,多角度關注被研究者在成人初顯期的心理發展狀況,對于了解其社會失調成因具有重要意義。
(一)原生家庭給個體帶來的焦慮
成人初顯期是個體與原生家庭逐漸分離的時期。研究發現,對于部分親子關系依賴性較強的個體,分離會帶來高水平的焦慮,個體焦慮水平最高峰值出現在大一上學期,在大二獲得改善,父母的焦慮情緒容易對個體產生消極影響,使個體出現不適應環境、孤獨感體驗和輕度抑郁表現。
絕大部分受訪者家庭在基礎教育階段呈現穩態平衡,這一家庭結構會隨著高考目標達成而重構,三位一體變成“2+1”結構,地域空間的阻隔,子女自我獨立發展的需求,家庭成員的變化(例如父母生二孩、離婚,家庭成員遭遇疾病或意外)等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個體心理狀況的穩定性,使個體在變化中失衡繼而出現疾病癥狀。個體在成人初顯期受到家庭風險因素的影響,進入成年期后抑郁水平仍然較高[1]。
在關于生活費一項的調查中,有4.6%的受訪者少于500 元/月,2.4%每月多于2000 元,總體來看每月1200 元以內的受訪者總占比為61.2%,大部分學生的日常開支都來源于家庭提供的經濟支持。雖然這個階段的個體可以完全支配生活費,但個體在成人初顯期不斷增長的物質欲望與有限的經濟來源極易形成矛盾,少數個體會因貧困產生反哺家庭的渴望,甚至產生自責、負疚、自卑等負性情緒,這些因素都會使個體產生焦慮。
(二)個體在成人初顯期突顯的學習和生存壓力
大一新生從被安排被照顧的單一環境來到以自我管理為主的大學,往往適應不良,因此這個時期普遍被視為高校心理問題高發階段[2]。相對其他專業,醫學生課業負擔重、成績要求高、學習壓力大,但高職醫學生與本科醫學生相比,存在學習基礎薄弱、學習能力較弱、無法高效投入學習、自律性較差的問題,這種矛盾的對立使部分高職醫學生產生強烈的內心沖突和自我否定,并以消極態度逃避沖突,盡管對現狀(學習和生活狀態、學校環境、人際關系等)不滿卻無法自我矯正。
高職醫學生的就業焦慮甚于本科學生,其學歷層次與社會用人需求極度不匹配,高學歷化是城市大中型醫療衛生機構聘用人員的必然選擇,招聘多為本科起步,碩博優先,專科層次需求量極少,但高職學生受基層醫療機構設施落后或簡陋、現代醫療技術難開展、個人發展空間受限等因素影響,多不愿選擇在醫療衛生人才短缺的社區和農村就業,學歷尷尬和就業困難等因素傳導給個體更大的心理壓力,直接影響到個體的心理穩定性,伴隨產生迷茫、逃避或者躺平的心態。
(三)社會發展問題投射到個體身上所帶來的負性情緒
時代的焦慮投射到個體身上,在經濟增長遲緩、就業崗位緊張的大背景下,有限的社會資源和個體發展動力之間形成矛盾,海量碎片化信息沖擊使個體價值觀產生動搖,部分個體面對格局變化會產生諸如焦慮、受挫等情緒,擔心個人價值得不到彰顯,或者因競爭失利而產生懊惱,或者害怕未知選擇逃避,這些負面情緒都會使個體出現社會失調表現。
二、高職醫學生心理社會失調的主要表現
為了解本項目研究對象心理社會失調現狀、表現及影響因素,研究小組以問卷星形式面向在校高職醫學生采集樣本,調查前所有受訪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發出并收回問卷1033 份,合格問卷973 份,有效率為94.19%,涉及專業為護理、醫學影像技術、口腔醫學技術、康復治療技術等。在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中(如表1 所示),連續資料用M(IQR)表示,分類變量用例數(%)表示,其中生活質量受訪者自評為7(3)分、疲勞程度受訪者自評為6(2)分,學習狀態較差率為1.5%(15/973),學習狀態一般率為96.3%(937/973),學習狀態較好率為2.2%(21/973)。中位受訪者處于無抑郁、無焦慮、無嗜睡、學習狀態一般的狀況。而抑郁情緒與不同程度的各類軀體癥狀(例如頭暈頭痛、心血管癥狀、胃腸道癥狀、肌肉酸痛、身體部位發麻、視物模糊等)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

表1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三、認知行為干預措施
心理社會失調的預防,國際提法見于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第七十七屆會議議程項目16.1(1986 年1 月14 日)。項目研究以《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 年)》為指導,以美國認知療法之父Dr.Aaron T.Beck 的認知療法為主要理論基礎,結合國內外研究經驗和啟示,組成包括高校教師、臨床醫生和高年級醫學生在內的CBT 團隊,主要采取團體輔導、個別會談及朋輩輔導進行干預。
(一)團體輔導
團體輔導定位于異質性成長團體,由通過篩查存在失調狀況的個體組成,干預方式為心理咨詢師協助個體進行自尊提升訓練,提高自信心,改善個體身處群體時的不適感。干預在私密舒適的空間進行,1 次/月,100 分鐘/次,團體活動總輔導時長為4 個月,分為初始、過渡、改變和結束階段。在初始階段,讓成員了解團體輔導的內容和形式,此時個體初識需要建立團隊間相互信任,確立團隊契約;過渡階段,讓團隊成員了解認知模式、核心信念與中間信念,識別自動思維;改變階段,通過訓練,讓個體能識別自動思維逐步矯正核心信念,學會欣賞他人和無條件接納自己,乃至改變個體的一些不良行為;結束階段,讓個體將在團隊中收獲的善意和接納應用于日常場景,成員告別。活動形式以認識自我、評價他人、情景劇、小組討論和角色扮演等方式為主。
(二)個別會談
個別會談以Judith S.Beck 所著的《認知療法基礎與應用》[3]為指導開展,2 次/月,30 ~60分鐘/次,由心理咨詢師與個體在私密舒適的空間進行。采用初次評估、典型的一天、活動圖表、阻礙發展報告、會談報告、思維記錄表、認知概念化圖表等認知行為干預技術,重點在于幫助個體進行自我認知調整,建立正向的核心信念,矯正中間信念,促進自我接納,使個體獲得在群體生活中的解決問題能力提升,最終將習得自我認知的技能應用于真實場景,改善社會失調狀況。
(三)朋輩輔導
朋輩心理輔導者來源于本科和專科學校的高年級醫學生。對于輔導者的選拔遵循保密原則,要求其具備一定的醫學素養和交際素養,掌握基本的心理輔導技能,態度真誠,善于傾聽,有同理心和較為明晰的自我認知,主要任務是以同齡人視角支持和帶動被干預者積極面對自身存在問題,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焦慮、抑郁狀況,在心理督導和心理咨詢師的指導下,參與認知行為的矯正。
四、對于高職醫學生社會失調者的康復模式思考
常規而言,對于社會失調者的康復,其目的在于使其在軀體、心理和社會能力等方面具備正常的日常生活和學習活動的能力,鞏固樹立正向的核心信念,在生活、學習和工作等方面,對其進行行為強化訓練,使其具備正常學習工作的能力和人際交往技能,能夠解決問題和應付應激[4]。基于本研究的干預模式探索,康復方案可繼續采用CBT 模式,由學校的心理咨詢師進行團體輔導和個別會談,康復治療師進行作業治療,朋輩輔導者進行社交技能訓練,有必要者由精神科醫生介入診療,階段性考查、評估該方案在臨床癥狀、社交技能及學業成就方面的干預效果[5]。后續根據評估效果決定是否調整方案。
基于對高職醫學生心理社會失調干預及康復措施研究項目,著力于探索對心理社會失調者的干預和康復措施及其有效運行機制,對因心理障礙和伴隨軀體不適、社會失調的高職醫學生做到早發現、早干預,矯正其負性核心信念,幫助其發展新的正性核心信念,通過實踐檢驗正性核心信念對其思維方式、情緒反應和行為的有力改善,最終提高個體應對當前問題的能力,改善社會失調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