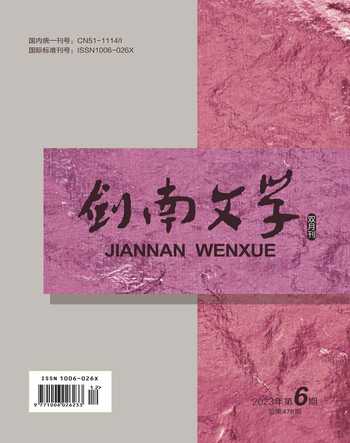九月(外六首)
月亮一旦下落,九月便會抵達跟前
李白、蘇軾、我,同時抬頭
歷史的針跳動了三下
三朵桂花在緊致的幕后繡出
我們足夠孤獨了
愈發被歷史的受挫補充
我們沐浴著這段垂憐的過程
比如,銀色的月光正侵入每一根發絲
比如微風飲盡我們額頭滲出的酒液
超級月亮
劇烈的滿月,這是我第一次,用劇烈
形容,那寒冷的宮殿。
蒼生居于大地,大地居于蒼生的影子
然后才有A居于B,夜晚
賦予了這一切,我失眠劇烈
月在試圖暴露,我一直以來的缺口
她想折服我于這種劇烈的感知
我并不認輸,為了較勁,狠狠指向月亮
她卻在我的耳后溫柔地吻下一條血痕
蟲鳴驟歇,四周的靜讓這些事物并
不真實
也許不真實的是我,我的靈魂
在千年前,可能是獨酌的李白
在萬年前應該是一塊與月亮相伴
卻沒有方向、丑陋無比的隕石,但現在
一定是附著于這片土地的菩提
用稀疏的影子普渡眾生
秋色
刻舟求劍,故地重游
一旦完成閉合,堅固的大廈
會瞬間崩塌,此時,桂花正挑動眉毛
秋天的實感掛滿枝頭
月光冷冷淌過,生銹的鐵門
我的影子布滿缺口,遺失的日子點
綴其中
模糊的愛人應該學會了自行車
劉海像一道明亮的秋風皺起
太窄了,說的是時間,也是我
能夠反應的余地,愛情的刀刃上
斗膽行走,比憐憫自己更為令人著迷
悔恨的事無需重提,要走的人早就
關上窗戶
說什么挽留之辭,不過是黃昏后仍
然噪人的蟬鳴
時間之樹
兒時,我為橡子橢圓的身材而歌
與竹木結合,構建自然的陀螺
旋轉式,跳躍式,如一場天鵝舞表演
季節輪換,樹洞里的住客,來了又走
橡樹,挺著筆直的腰板,迎接歲月
父親坐在樹下,抽旱煙
腳背裸露著青筋,這條是漢水
那條是楚河,父親的鋤頭才從沙場
回來
滿臉都是濕潤的紅土
頭頂的橡子在稀疏中墜落
摩擦出鋼鐵的聲音,所有的風都往
這里吹
這是一塊不容易缺水的地方
故人說
瞳孔中漂浮的面具太多了
褶皺的,光滑的,白嫩的,黝黑的
這些面具共同構建了一個詞語
——故人,故人曾將一只不穿鞋的腳
伸進流淌的江水中,學著孔夫子頭
疼的樣子
感嘆,“這就是被時間撞擊的感覺
啊”
我將另一只不穿鞋的腳
踩進水中,試圖將時間逼停
但故人,還是走了——從紅綠燈路
口走的
斑馬的頭部迎來一只陌生的戒指
帶著桂花香氣,這香,硬得像金剛石
或許她來自江水,我成功逼停的
某一個部位,直到閃爍的綠燈讓一
切幻想
柔軟下來,原來時間已經磨得那么
銳利
回憶已無江水著色后的那般干凈
像植物的人
我從來沒有告訴你,關于泥土的一切
它們在揚起的鋤頭下,屈服
久而久之,留下一個滲著地下水的
深坑
不停地向外界吐露見不到光的孤獨
等到梨樹彎下腰的季節
我那瘸腿的爺爺,猶如堅硬的青岡樹
直挺挺躺下去,回到記憶的初始點
任由時間之外的人,往往復復
這一次,我明白人的生命永遠離不
開土壤
像植物出生時,裹著碳灰
活著時,吃著觀音土,死了埋在土里
它們驗證著一個字——根
但我不一樣。老墳山所有的梨樹枯
萎了
一座座草房子也隨之坍塌,我們走了
我們也該走了,哥哥轉身說
爺爺的墳好像長大了
秋天
鐵質板凳的心是木頭做的,木樨封
住窗口
不斷有花香飛濺進來,門被撞上
命運之槍已經打響,子彈穿心,也不
過如此
我又不是一定要懷念,在陌生校門
口塑造一個夜晚
頂上金碧輝煌的大字,被方圓十里
的空虛叩拜
你不也如此高傲?那是半年前的事了
齒狀的時間仍無法割開你隱藏的秘密
那鮮紅的嘴唇咀嚼著詞語的銹跡
果真是那么冰冷,你也滲透進來吧
你也是極具穿透力的事物
關于你那修剪萬遍的面孔
滲透進來吧,合同漸漸無力的雨水
它們像一頭疲憊的水牛,開墾了世
間所有的土地
接下來,飽滿的江水漸漸退卻
雪下滿后山,把我們走過多次的梧
桐大道
染得雪白,這是另一個
值得感動的季節,那些生機勃勃的
夢境
不正是因果的反芻耶
【作者簡介】
肖柴胡,2001年生,重慶人,四川農業大學中文系在讀。作品見于《詩刊》《星星》《飛天》《詩歌月刊》《散文詩》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