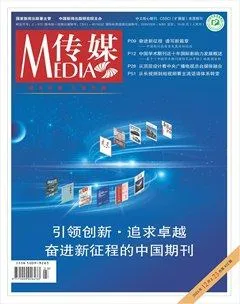新媒介與新接受:電子游戲玩家的“虛體”與“代理”
張東一

摘要:在新媒體語境下,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電子游戲的日漸流行與成熟,使其在新媒介意義上成為一種開創性的藝術形式,進而使這種技術化娛樂行為的傳播與接受機制可以在游戲美學的視域里得到關注與揭示。數字化背景下的電子游戲也是一種特殊的美的存在與傳播形式,其核心機制在于游戲主體即玩家是以虛體來感受游戲世界的規則與秩序的,并通過“代理”進程延伸了玩家的“本體感知”進而傳達出電子游戲語境中的“美”。
關鍵詞:電子游戲 新媒介 美學接受 虛體代理
從1947年1月25日世界上第一個《陰極射線管娛樂裝置》電子游戲專利申請算起,電子游戲至今已經走過了近八十年的發展歷程。這期間,不論是以文字為載體開創了文字游戲先河的Star Trek(1971),還是以數字技術為3D游戲奠基的Space Roger(1990),電子游戲作為一種開創性的藝術形式早已成為當代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同時,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得電子游戲的載體不斷迭代,電子容器與設備性能愈發頻繁的更新,不僅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宏大而廣闊的創作空間,更為游戲行業的快速發展開發了廣闊的受眾群體。綜合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游戲市場規模約為人民幣11107.6億元,全球移動游戲市場規模約為人民幣5945.19億元;2022年,中國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雖較前一年下降10.33%,但仍達到人民幣2658.84億元,其中移動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占比72.61%;2022年,全球游戲玩家達到32億,較上一年增加約2億,中國游戲用戶雖比上一年略有減少,但仍達6.64億人。基于如此龐大的用戶規模與營業額數據,學界對電子游戲的探討與研究日益興起并不斷深化,從單一的游戲性到藝術性,再到具有哲學視點的思辨性,有關新媒介視野下的游戲美學的傳播與接受機制也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
一、接受美學——電子游戲的新視域
隨著媒介的不斷迭代,從文字到圖像再到影像,“美”的表達、傳達與接受方式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面對電子游戲這個充滿新生力的藝術形式,在全球數億游戲玩家感受到游戲美感的時候,在當下電子游戲承載了越來越多現實意義的時候,我們必須思考這樣的問題:游戲的美究竟是怎樣被玩家所感知的?或者說,游戲中所蘊含的美的接受機制是什么?
早在20世紀末,Gonzalo Frasca便以《當游戲遇見敘事》(Ludology meets narratology)等論述,系統性地整理出了電子游戲的游戲敘事過程,奠定了游戲敘事學的邏輯與指向,之后2001年Espen Aarseth 主持《游戲研究》(Game Studies)一刊,不僅使電子游戲的研究有了可以廣泛交流的陣地,同時也使其研究實踐有了體系化和規范性。而隨著電子游戲技術的快速進化,以及游戲市場的巨大壓迫,學界對其也逐漸重視起來。除西方電子游戲的主要研究者Jesper Juul,Markku Eskelinen,C.Thi Nguyen等人之外,國內近年來如藍江、嚴鋒、汪代明等人也將目光投注在電子游戲領域,不僅著眼于電子游戲這一特殊的新型媒介,探討電子游戲的敘事模式、電子游戲的虛擬生存等問題,還在電子游戲語境下的美學傳達與接受方式的探討中,指出美學這一概念完全可以指代審美層面上對電子游戲設計美感的解讀。他們通過游戲內部的具體設計與事物以小見大地分析游戲是由一個個細節建構起的“美”的世界,就是近似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寫的對文學文本現實效果的呈現那樣,強調游戲也會通過堆砌看似與游戲進程無關的細節來塑造現實效果。顯然,這種分析方式更容易在游戲進程中被玩家所體會和理解,但其分析的對象范圍卻往往僅局限于同一種近似風格的少部分游戲,可能缺少了宏觀層面的理論視野,所以對游戲敘事模式的研究同樣成為游戲學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如Frasca是從技術層面整理出一套相對完整的游戲敘事的整體框架,其他人也從藝術理論的角度宏觀地進行敘事學在游戲語境下的特征分析。此外,近年來學界還興起了從“本體論”等后現代理論視角分析電子游戲文化生態的研究理路,既有著探索游戲或虛擬世界中的物體存在的新鮮角度,也有著在具體文化語境下探尋不同游戲美學風格差異的討論,充分體現出了后現代語境下關于電子游戲藝術品質和功能的思考等。
不過,盡管學界已經通過敘事和文化等分析對電子游戲的美學的特殊性及其形成與傳達的模式進行了探索,但對游戲美學的接受過程即游戲中的美是如何被玩家所感知的深入討論卻仍然相對較少,目前只是剛剛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具有創新意義的見解,如Jesper Juul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可玩的論文》(Playable Essay)就是一個代表:在這篇內含一個小游戲的論文中,Juul通過電子游戲與文字論述結合的方式,直觀地分析了電子游戲中的“圖片”(Pictures)是怎樣在電子游戲中成為“物體”(Objects)并被玩家所感受到的,這就不禁讓我們更加有了向電子游戲語境中的美學感知進行探索的自覺。
二、游戲角色——電子游戲的接受設置
隨著圖像時代的到來和視覺文化的轉向,電子游戲與電影一樣,都在蓬勃發展中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一面,同時盡管電子游戲與電影二者間有著諸多不同,但實際都是通過視聽語言來表現具體內容的,因此電子游戲的美學接受模式,就與影視戲劇傳統的美學表現與感受模式有異曲同工之處。如眾所知,傳統的影視與戲劇藝術鑒賞模式往往受制于觀眾——文本的二元接受模式即有著“第四面墻(Fourth Wall)”,很難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觀眾與故事文本從始至終的全然交互。直到電子游戲的出現,才可說是填補了這種交互性不足的媒介空白,因為電子游戲在誕生之初,就被設計為“被互動”的文本形態,它的原初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類可以參與其中并進行互動。為此,電子游戲較于影視戲劇的特色與優勢就在于它增添了一個新的設置:游戲角色(Game Characters)。
這個游戲角色特指各種游戲中被設計可以讓玩家進行游戲內交互活動的單位或設定,它的存在讓電子游戲和影視作品之間劃開了界限,電影的交互關系是觀眾—電影,而游戲的交互關系則是玩家—游戲角色—游戲。也就是說,影視戲劇中的故事文本是獨立于觀眾的,它們本身就是完整、獨立的藝術成品,而電子游戲的世界架構和玩家的個體參與則是水乳交融的,玩家的存在是游戲故事文本行進的必要條件,游戲中的故事文本也會因為玩家的參與和活動而作出相應的改變和調整。這種特殊的“美”的接受方式在游戲美學語境下需要玩家的交互,需要游戲角色的身份代入,也就需要玩家在游戲中的“虛體代理”。
對于玩家進入游戲文本的方式和定義,美國學者Nguyen指出,游戲中的美學內容實際是以“代理姿態(Agential Posture)”所呈現出的美感,即游戲的美學問題其實是玩家以代理的形象或以“代理姿態”所經歷的美。藍江同樣指出了游戲美學與傳統美學在兩個美學系統中關于主體存在的不同理解,他將這種游戲角色的概念稱為“寧芙化的虛體”,而“虛體”作為玩家在游戲世界中的數碼化的身體,“讓電子游戲與其他的藝術和創作形式有著本質的不同,也正是這個虛體,讓電影技術始終無法打破的笛卡爾的主體—客體或者克拉里的觀察者和世界的二分,從而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他認為虛體化作為電子游戲的特征之一,可以讓玩家“創造一個或多個角色,操控其行為,通過虛體接收游戲世界龐雜數據的反饋并作出回應。”而這種具有去身性的虛體與Nguyen的代理概念具有相同的意味,即它們所指代的都是“美”在游戲美學的語境中具有顛覆性意義的新的單位——游戲角色。

游戲角色成為玩家介入游戲文本的窗口,玩家通過游戲角色實現對游戲的交互,游戲則通過游戲角色傳達給玩家電子游戲語境下的美的體驗,因此“美”的接受模式在電子游戲語境下得到進一步延伸。Nguyen和藍江在其代理姿態和游戲虛體之上,還對游戲美學的體驗模式也有著相似的論述:Nguyen認為玩家審美體驗的對象一定程度上來自于他們自己的代理感,玩家在游戲中以第一人稱或第一經歷者所感受到的美比起其他藝術形式要具有多一層的接受過程,即游戲的美首先被玩家的代理身份接收,玩家進而再從代理感中獲得美的反饋。類似地,藍江也強調游戲虛體的美學體驗在于,其所謂虛體本身對于玩家雖然是去身的,但其所帶來的體驗感卻是具身性的,而且玩家是以虛體來感受游戲世界的規則與秩序的。“我們習慣于通過工具和物體的拓展來感受我們的身體”,所以在這種間接的體驗模式中,游戲角色恰成為玩家在游戲中擴展“本體感知(Extended Proprioception)”的“工具”,玩家在電子游戲中的審美體驗也正來自于這種具有“工具性”的虛體代理。
三、“大地”和“世界”——本體延伸的感知錯位
在游戲愈發被認同為一種藝術形式時,海德格爾的觀點可以作為我們理解這一藝術的依據之一。“藝術作品的作品存在首先是建立世界”,“詩意的本性是存在的創立和真理的創立”,因此在游戲“創立”其游戲世界和游戲存在時,其作為詩意活動的“世界”便生成了。同時“‘世界和‘大地相互根本不同但又不可分離”,“大地”是“那永久的自我歸閉者及其庇護者的無所迫使的顯現”,“世界”則是“在歷史性民眾的命運中,簡單和基本決定的寬闊道路的自我顯露的敞開”,于是在“歸閉”和“敞開”的矛盾對立中,電子游戲的“世界性質”便更加清晰起來,它在現實和歷史的“大地”堅固的基礎上創立出了一個虛擬的又極度敞開的“世界”,又通過建立起這樣敞開的世界,不僅顯現了大地,也被賦予了“接納”存在者的意義,為“存在者的真理將自身設入作品”提供了前提。而且只有詩意才能使人居住,“詩意并不是超臨和脫離于大地。相反,詩意使人進入大地,從屬大地,使人居住”,所以電子游戲實際上是為眾多玩家開辟了現實生活“居住”之外的另一片屬地,一片真正具有“詩意”的屬地。因此電子游戲之所以致力于“臨場感”和“沉浸感”,就是因其所要塑造的正是一個供人“詩意居住”的地域,是在建立世界的進程中為“存在”本身提供賦予其存在意義的空間,為居住提供回歸其本體論的余地。同時也恰是在這樣一個被構建出的游戲世界中,玩家可以通過被延伸的本體感知感受到與現實世界相勾聯又相互獨立的美的傳達。
盡管在本體感知延伸的觸角中,我們可以通過現實的感知邏輯理解電子游戲語境中的美,但也會在電子游戲的世界中有著不同于現實世界的美的感受,即感覺到現實的“大地”和電子游戲的“世界”似乎有時會充滿美的矛盾。換句話說,盡管電子游戲中玩家依然可以通過代理進程中的本體感知感應游戲中的美,但這種感知在其“被延伸”“被工具化”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與玩家們的直接感知形成錯位。比如,可以設想,在游戲中的怪物意象被塑造的進程中,若設計者刻意加強其外表與視覺沖擊力,削弱其可對游戲世界和游戲角色造成的破壞與傷害,那么這一怪物意象則更多會讓玩家感受到刺激、興奮,而非恐懼、害怕,同理反之亦然,所以說電子游戲中的物體在“被塑造”的進程中會與現實世界的構建邏輯形成差異。
同時,從玩家“延伸的本體感知”角度看,玩家通過“被延伸”的本體感知來對電子游戲中的事物進行審美判斷,也是造成現實世界與游戲世界中美的表現錯位的因素之一。當玩家在《上古卷軸五》(The Elder Scrolls V)開場的陰暗洞穴中來到開闊的天際,玩家會在目睹廣闊天地時感受到美;當玩家在《輻射四》(Fall Out IV)的廢土世界中看到荒蕪原野上橫陳的尸體和廢棄物時,也會形成一種美的感受。前者是玩家延伸的本體感知所直接反映出的美的感受,即在現實和電子游戲語境下都會感知到的美,后者則是經過電子游戲“不完全真實”的塑造進程,在“不真實”感中為玩家的本體感知帶來了美的感受,即僅能在電子游戲中感知到美,在現實世界中它甚至會被厭惡、唾棄。這些都證明,目前受制于技術條件的電子游戲制作不可能完全讓電子游戲中的所有物體都成為符合現實規律和邏輯的“真實物體”,而正是在物體的“不完全真實”和玩家感知的“本體性延伸”中,這種“不真實感”才會更加明顯,美的錯位才會愈加可感,因此越來越多的電子游戲也才會更加注重對細節真實的把握以及對臨場感和沉浸感的塑造。這還意味著,從代理的角度分析游戲角色及其接受審美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玩家的電子游戲審美感知邏輯,還可以幫助我們通過對現實世界和電子游戲兩種不同語境中美的差異性體會,進一步明晰電子游戲中美的生成與存在的特殊性。
作者單位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參考文獻
[1]TAVINOR G.The art of videogames[M].New York:WileyBlackwell,2009.
[2]THI NGUYEN C.Games:agency as art[M].Oxford:0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3][德]M·海德格爾.詩·語言·思[M].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4]藍江.文本、影像與虛體——走向數字時代的游戲化生存[J].電影藝術,2021(09).
[5]藍江,馬文佳.從“逍遙游”到數字主體:當代數字游戲哲學的主體批判[J].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2).
[6]汪代明.論電子游戲藝術的特征[J].文藝爭鳴,2006(03).
[7]吳冠軍.元宇宙到多重宇宙——透過銀幕重思電子游戲本體論[J].文藝研究,2022(09).
【編輯: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