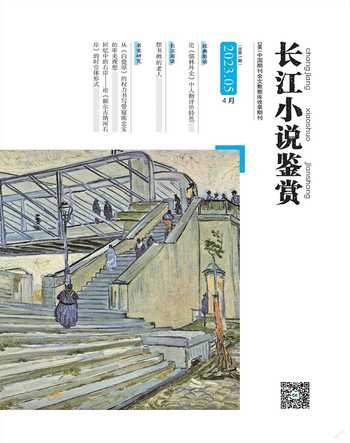淺析遲子建長篇小說《煙火漫卷》中多重審美意蘊
[摘? 要] 《煙火漫卷》是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遲子建以主人公劉建國為中心人物,以其尋找銅錘為主要線索,以哈爾濱這座城市為時空背景,書寫與之相關的上下三代人的故事。遲子建秉持著生態美學理念,細描哈爾濱在百年變遷的歷史中的城市景象和市井生活,與書中人物命運聯結,賦予人、城市、自然更深層次的意義。
[關鍵詞] 《煙火漫卷》? 哈爾濱書寫? 自然生態? 生存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一、動態、平衡與復調敘事
《煙火漫卷》以自然時間“春”“夏”“秋”“冬”為敘述順序,書寫隨時間變革的自然、城市景觀和縱橫交錯的人生命運。并且上下兩部除了以季節為時間線,各自更有側重的次時間線,上部著重將故事設置在清晨之中,下部則是夜晚。不僅如此,遲子建在《煙火漫卷》中的鋪陳十分宏大,現實中的故事隨著自然時間進行刻畫,同時在文中運用“回溯”的手法對舊時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進行描繪,現實與歷史形成對話和映照,歷史是現實的因,現實是歷史的果,以此方式聯結上下三代人的人物命運,刻畫歲月長河之中城市與人的關系,以及城市、人性變遷。而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對比刻畫,遠不止于此,遲子建還精心刻畫現實中的舊物,如榆櫻院中的彩繪玻璃、劉鼎初多年前的譯著、舊貨市場,試圖將哈爾濱這座城市中更深層次的底蘊呈現出來,因此可以從《煙火漫卷》之中洞見哈爾濱這座城市的特殊性、時代性,人性的高光與低處。遲子建在這本小說中并沒有選擇限制性視角進行敘事,而是利用非聚焦式手段對城市、人物、自然進行刻畫,這有助于遲子建構建宏大的城市人物版圖,加之可以自由出入不同人物的思想,代入豐富的視角,以一個女性作家的讀者身份對城市、自然進行審美觀照,對人物關系與作品思想二次解讀。小說中籠罩的寧靜氛圍,是作者以女性溫柔的視角,以特有詩情畫意式的書寫方式,對景觀進行架構,對城市予以女性或母性的比擬,在寧靜的畫面之中,暗含著現實與歷史的“波濤洶涌”,但遲子建都盡量將其詩意化,控制在“平衡”的范圍之內,如同書寫人物的善與惡一般,永遠存在動態的關系之內,對“惡”的呈現是非極端化的,同時對“善”的刻畫也非菩薩式的,人性的復雜得以深刻呈現,即在寧靜平衡的畫面中娓娓道來不穩定的、意外的、動態的因素。
在上部中,遲子建將時間背景置于春夏兩季,開篇第一章即寫了哈爾濱在晨曦之中的城市橫截面與人物眾生相,人物出場或者情節發展的時間背景都設置在早晨,統一在了第一部分的其他章節,如第二章主人公黃娥與劉建國相約在日出時分捕魚、第三章于大衛約劉建國一起去祭奠謝普蓮娜、第四章劉光復與劉驕華在日出時分談話等。由此可見,上部以劉建國為線索,串聯劉建國故事的同時,以傳統零聚焦寫作方式,形成以劉建國為中心,黃娥、于大衛、劉驕華等上下三代人在內的龐大的關系網,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關系網中的人物關系更加復雜,不再以劉建國為中心點發生故事,而是支線與支線進行勾連,如黃娥和翁子安、于大衛和翁子安、謝楚薇與黃娥等,給予了此類角色不同的身份,以此窺探社會與人物的關系,以及人在命運長河之中的種種選擇與結果。
在下部中,時間背景為秋冬兩季,而這兩季作為一年中的結尾,自然預示著小說情節發展走向了結尾。在這一部中,故事大多發展在夜晚或傍晚,正式將情節推向高潮。如果說上部呈現的大部分是過去的故事,而下部中的矛盾與沖突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交雜,將過去的矛盾放置在現實表面,并由舊矛盾生發出新的故事情節,投射城市中普通人物的命運,豐富小說人物的多層性,繼而彰顯哈爾濱這座城市強大的包容性。
二、歷史、城市與人物群像
1.尋找與丟失的主題意蘊
《煙火漫卷》以丟失與尋找為故事主線,追溯舊時的“錯誤”或“意外”,使得現實生活承受生命痛感。在小說中,每一個人物都在丟失,都在尋找,丟失或尋找的事物卻有所不同。劉建國與于大衛、謝楚薇夫婦是在尋找銅錘,但更多的是尋找能夠釋放自己愛子之情、思念之情的閘口。劉光復丟失的是夫妻之愛,尋找的卻是舊時哈爾濱城市的記憶,因為這些舊物確證著劉光復的身份,通過重回歷史,讓自己從現實生活中的傷感里回撤。劉驕華丟失的是丈夫的忠誠與責任,卻無法尋找到這份感情的替代物。謝普蓮娜,在她一生漫長的經歷當中,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兩任丈夫,隨后又遺失了自己的孫子銅錘,父親留給謝普蓮娜的房子和遺產,也在戰亂中丟失,加之在現代城市中早已難見猶太后裔的身影,因此謝普蓮娜一生都在丟失與尋找的路上,直到謝世。除此之外,書中榆櫻院中的次要人物也同樣經歷著丟失與尋找過程之中的傷痛。
丟失與尋找的主題并不單單投射在人物之中,哈爾濱這座城市也面臨著歷史的打磨與變遷,遲子建將故事放置于現代都市背景之中,但用大量的篇幅書寫最平凡最普通的市井生活,與新感覺派式的都市生活大相徑庭,大部分批評將這種寫作方式看作是對都市生活、異化生活的反叛。從另一角度看,作者也是在已丟失了純粹的鄉土精神風貌的都市之中書寫牧歌式的鄉土情懷。就哈爾濱這座城市的主體性來看,哈爾濱充當的更像是糅雜大量歷史、政治、現實元素的命運之境,對應著人物的身世與心酸,由于20世紀的戰亂、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各國人口遷徙而來,又離去,國家歷史的傷痕與新時代的快速發展,使得哈爾濱不得不適應每一個歷史時期,又不斷地在不同的時期被一次次剝奪已獲得的主體性,但每一時期的特質都存留在了歷史的夾縫之中,投射到人物身上,如劉建國是一名日本遺孤、謝普蓮娜是猶太人,黃娥身上更有與都市相對的鄉土氣息,在建筑上,舊時哈爾濱的街市上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等宗教寺廟、巴洛克建筑群、半中半西的榆櫻院。種種象征,確證著哈爾濱百年以來的丟失與尋找歷程,人物與城市形成互觀,在鏡像中相互印證彼此的歷史與成長。
2.完美的理想式人物形象被打破
從整體來看,不論是劉建國還是書中任何一位人物,都有博大的胸懷與堅韌的生命力,作者從開篇即給我們塑造了近乎完美的理想式人物形象,但筆者認為所謂的“理想性人格”在書寫的過程中卻在被慢慢打破。
在前六章中,讀者僅知劉建國丟失了銅錘,其中緣由和細節并未加以呈現,劉建國在文中的形象一直帶有強烈的普世光環,直到上部第七章,其近乎完美的人物角色才隨著文本的敘事逐漸被打破,但仍然有批評認為,劉建國將銅錘丟失更多應該歸結于外界的因素,而非劉建國自身的原因。到下部第四章中,劉建國意圖猥褻小男孩武鳴,這一行為卻無法輕易為劉建國開脫,如果說銅錘丟失又找回,于大衛等人從青年到中年近半個世紀的傷痛逐漸彌合,而劉建國給武鳴帶去的傷痛卻是長達一生的。同時,劉建國卻無法真正從內心承認自己的過錯并懺悔,面對武鳴的叔叔時,謊稱是替朋友來問候,將自己的罪責移給了自己虛構出的人物,在此意義上,劉建國非但不是理想主義人格,還有虛偽與懦弱。
黃娥形象并非如劉建國一般,從敘事開始就是完美的,黃娥的閃光點更多體現在細微之處,如劉光復逝世時,黃娥特地取松花江水為劉光復凈身、收養劉建國的雁子、為雜拌兒制作城市地圖等,但黃娥與外來男子保持著不正當關系,又借著劉建國“好人”角色,不由分說地試圖將雜拌兒硬塞給劉建國做兒子,盡管黃娥身上有眾多純潔樸實一般的鄉土情懷和亮點,但在這一層面上,卻是社會意義上的“道德綁架”,不顧他人想法,強加自我意愿于旁者身上。文中與黃娥相似的人物仍有許多,如劉驕華為黃娥母子提供住處,主要目的是讓黃娥與劉建國成為伴侶,照顧劉建國的后半生;謝楚薇對雜拌兒巨細無遺的照顧,是為了填補其丟失兒子的遺憾,并且想要與雜拌兒的親生母親黃娥爭奪雜拌兒的撫養權;于大衛也猜忌謝楚薇與其他男子有不正當關系,并懷疑銅錘并非自己的親生兒子,以此減輕自己失去兒子的疼痛感;翁子安早就得知自己的身世,即自己是銅錘,并祭拜了謝普蓮娜,但他卻仍向劉建國隱瞞,使劉建國繼續處于深深愧疚之中。
因此遲子建書寫的更多是現實生活中最為普通的人物,而他們并非理想人格,是優點與缺陷的集合畫像,鮮活的且現實的,文本中的人物在歷史的長河、現實的變遷之中,承受著遺失、迷茫、懷疑,種種傾倒而來的裂痕,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深深的憂郁癥候,并為此不斷尋找解脫的方式——救贖。作者無法去判定選取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是否恰當,只能在故事之外重回現場,繪制煙火漫卷式的人物群像。
3.自然、城市與歷史
作者為表明哈爾濱是座有包容性的城市,在小說中大量鋪陳關于哈爾濱的自然、城市景觀,并繪制其在一年四季中不斷變化的生態畫像,作者盡管在后記中表明自己書寫的是城市文學,但筆墨的篇幅占比卻無限傾向了在哈爾濱城市之中的自然生態書寫,顯而易見,自然與人性是作者寫作的審美宗旨。然而,《煙火漫卷》與歌頌鄉村、批判城市等主題小說(如《邊城》)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書中作者始終以溫情的筆墨對待哈爾濱、對待城市、對待人物,面對城市主體也并非極端的批判態度,如劉驕華兒子的許多行為方式已被現代社會異化了,擁有著一身陋習,與書中其他人物相比,顯得其更加平庸與不堪,但書中仍不忘展現他好的一面,作者更傾向于將自己放置于中立的位置,并沒有敘述其行為形成的緣由,也沒有講述城市中的惡,僅展現其作為一名普通人的多面性,敘事意圖更加單純。如此一來,正如于小植所說,《煙火漫卷》中的哈爾濱書寫并非城市書寫,而是一部將哈爾濱作為故事發生背景,書寫在這座城市中所發生的人與事的小說。
當然,書中有關哈爾濱的敘述也并非如此簡單,動物意象及江水意象頻繁地出現在文中各處,作者也在上部第二章中寫到“一座城市有一條江,等于擁有了一冊大自然饋贈的日歷”,點明江水意象在文中承擔的角色,即作為一年四季的日歷,如春天河流開江,伴隨著碎冰;夏季雨水豪邁,與江水一起容易形成災澇;秋天松花江瘦身;冬季冰封的松花江,被切割成冰塊,雕成冰雕。然而作者在文中對江水的處理遠不止于此,江水有著更加溫情擬人化的深層內蘊,它的變動承載著哈爾濱人生息之中的疼痛。江水承擔著黃娥與丈夫盧木頭的生計,但這也成了夫婦之間矛盾爆發的導火線,而劉光復在癌細胞擴散之時,仍然想在解凍的松花江游上一回,是劉光復作為一名城市中的老人,對江水的熱愛,是在彌留之際對哈爾濱最深刻的眷戀。盡數書中人物,劉光復無疑是最深愛哈爾濱這座城市或故鄉的人,縱然書中人物眾多,而以江水映射出的劉光復念鄉之情卻再未出現在第二人身上。同樣,在劉光復進入搶救室之后,黃娥用雙手將并不澄澈的松花江江水捂熱,為劉光復凈身,完成劉光復在松花江中游泳的心愿,江水進而也彰顯出了劉光復與黃娥清澈見底的純粹之心。
同樣,鷹有多種解讀,一為鷹作為盧木頭的化身,也是書中的隱喻。在前期敘事中,盧木頭的失蹤一直是謎題,每每鷹的出現便提示著黃娥作為盧木頭妻子的身份,留給讀者“黃娥能找回盧木頭”的閱讀期待,當謎底揭曉,這份隱喻也失去了功效,鷹最終死在了塑膠跑道上。與鷹具有相同作用的即是在上部第二章中黃娥在江邊撿到的一頂帽子,這頂帽子迫使黃娥不斷想起已去世的丈夫盧木頭,使得在哈爾濱已逐漸適應新生活的黃娥被重新喚醒了對丈夫的虧欠與內疚,帽子與鷹一起不斷地催促黃娥盡快完成自己的贖罪。許多批評認為鷹是書中人物經歷的象征,如鷹的死亡是社會因素與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自然與現代社會對抗即是《煙火漫卷》的主旨,是對小說核心事件的預演。筆者則更偏向于,城市的現代化并非事件的主因,而生活中的“意外”才是故事的核心,人生有許多意外,如同意外丟失了銅錘、盧木頭的意外死亡等,面對這些意外事故,采取何種態度面對,才是遲子建思考的終點,而遲子建想要表達的即是面對人生的裂痕時,應與鷹在臨死前仍不忘掙扎展翅,不放棄重新騰飛的機會一樣,堅韌不屈。書中的各個人物也做到了這一點,劉建國、于大衛、謝普蓮娜、黃娥等,展示的是微小生命中的巨大能量,歌頌著生命中的堅持與執著。
在小說中,除自然與動物意象之外,其中所描寫的獨特的建筑群唯哈爾濱這座城市獨有,這些城市景觀往往與歷史相勾連,如榆櫻院、猶太老會堂變身的音樂廳、舊貨市場、猶太公墓、教堂等,以此重回歷史現場,重塑歷史城市畫像。在這些景觀中,毫無疑問榆櫻院是最為重要的故事背景場所,歷史的痕跡在這里鮮明生動地重現,榆櫻院更是哈爾濱這座有著多元文化城市的形象縮影,但榆櫻院同樣也是屬于過去的,通過榆櫻院使歷史與現實交織,與哈爾濱的歷史對照的同時,映射著人物命運的羈絆。而在小說結尾,謎底已然解開,身份終于歸位,處于歷史事件中心的人物卻已遲暮,歲月、時間、救贖、痛苦似乎畫上句號。如若進一步追問,幾十年的生活不會歸來,裂痕不會抹去,歲月也不會重來。哈爾濱這座城市過于厚重的歷史如同榆櫻院中這兩塊易碎的玻璃,以城市之軀承擔百年來的戰爭、歷史、政治紛擾,也如同書中的人物,平凡的軀體卻承受百斤之重的疼痛。
通過彩繪玻璃觸摸破碎的歷史的同時,現實也在一層層剝離人的心智,人也如同一座城,《煙火漫卷》即是寫的城中之人,人中之城,人與城在歲月的長河中相互襯托、依賴,以此形成哀痛卻向上的社會文化景象,壓抑與沉悶附著在人與城的無限光陰之中。
因此,作者不僅眷戀自然生態,對現代生活中的市井煙火進行描繪,也更執著于歷史景觀與建筑,而非現代生活中城市的燈火,《煙火漫卷》即是以懷舊敘事方式書寫現代城市中的人物故事和反思人性。
參考文獻
[1]? ? 遲子建.煙火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2]? ?崔慶蕾.煙火中的城市抒情、反思與批判——讀遲子建長篇新作《煙火漫卷》[J].小說評論,2021(3).
[3]? ?于小植.“城市主體”建構及其限度——論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J].文學評論,2021(6).
[4]? ?楊姿.何以成東北?——以《煙火漫卷》為例談城市文學的區域感[J].當代文壇,2021(6).
[5]? ?韓明明,劉川鄂.尋岸之美的締造者——論遲子建生態女性主義文學觀及其創作[J].文藝評論,2021(6).
(責任編輯 李亞云)
作者簡介:于洋,西南交通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