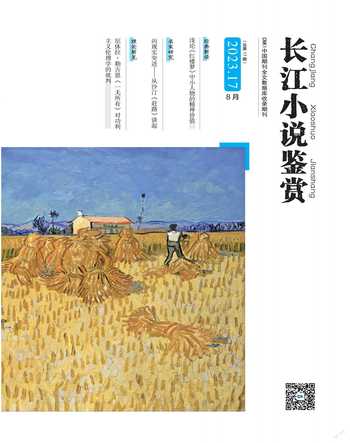永恒的原鄉想象 ——論潘雨桐小說中的哲性鄉愁
蔣 婷
[摘? 要] 潘雨桐在馬華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直被低估,其作品大多是步入生命之秋時對人如何棲居于非“家”土地的思考。流寓許久的潘雨桐渴望精神還鄉,創作沖動隱喻為哲性鄉愁。在辨認原鄉時,雙重的故鄉帶來了雙重的創傷記憶,文化中國的原鄉形象因此無法被清晰勾勒。與潘雨桐共同持有哲性鄉愁的是第三世界的同胞,身份的迷思和無所歸附的尷尬使得他們淪為赤裸生命,他們以隱匿的方式建筑命運共同體。一眾馬華作家雖然暫時安頓了肉體,在精神向度上依舊處于內在流離的不安狀態,渴望找到原鄉卻不得,只能永恒地尋找,哲性鄉愁則成為解讀他們作品的永恒密鑰。
[關鍵詞] 潘雨桐? 原鄉想象? 鄉愁? 哲性鄉愁? 馬華文學
[中圖分類號] I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7-0049-05
潘雨桐在馬華文學史上地位一直被低估,其人生經歷如下:出生于馬來西亞的他,祖籍廣東梅縣,1954年于大馬芙蓉中華中學初中畢業,1957年于新加坡中正中學高中畢業。作為最早一批旅臺的馬華作家,潘雨桐1958年入中國臺灣,取得臺灣中興大學農學士學位后又赴美攻讀遺傳育種學博士。獲得博士學位后潘雨桐在臺灣中興大學任職三年(1972—1974年),又回到了大馬,服務于農業界。在一次又一次的遷徙之中,潘雨桐作品展露出的家園感更顯復雜。學界目前對潘雨桐的研究集中在其作品中的寫作范式和中國古典氣質,卻未見有剖析潘雨桐創作的心靈訴求,而潘雨桐作為會漢語的馬來人,在“離家-再離家-回家”的漂泊經驗中,馬來西亞的“家”和中國的“家”對其又意味著什么?潘雨桐的華文小說哀怨幽婉,似是無家可歸的泣訴。
潘雨桐的創作起步較晚,其作品面世從20世紀70年代末才開始,也因此被納入“第二代”旅臺馬華作家[1],“這種中年氣質式的追憶情結也成為他創作道路的基本特征”[2],潘雨桐著述不豐,僅有五部小說集:《因風吹過薔薇》(1976)集結四個中短篇,以在美留學生呈現人生困境,《昨夜星辰》(1978)、《靜水大雪》(1996)和《野店》(1998)三部短篇小說集各錄十一篇目,背景時空涉及中國臺灣、美國、馬來西亞,是作者對其經歷去蕪存菁的藝術加工,《河岸傳說》(2002)用八個短篇刻畫了作者本人在山野陽光作業中體認到的后殖民創傷。
由此可見,潘雨桐的小說雖不是寫自己,但“我”卻無處不在,人到中年的筆觸更具思考和整合人生的意味。步入生命之秋的潘雨桐,提筆思索的是“人”如何立身棲居于非“家”的土地,“一切有目標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層面被喻為一種鄉愁或尋求歸宿的沖動”[3]。潘雨桐歸正返本,意圖為自己的生命找到靈魂的立足點,創作內容正是還鄉的隱喻,也即哲性鄉愁,他求索于人生記憶并希冀筑建形而上的歸宿,這便是他想象原鄉的根本原因。
一、鄉關何處:含混的原鄉
任何海外華人溯源歷史都能在中國找到自己的祖先,中國的大地上寄存著他們遙遠的集體記憶,大量的華人南下馬來,馬華作家和中國之間的關系顯得更加復雜。潘雨桐的父親是中國移民的第一代,潘雨桐也因此成為第一代土生土長的大馬華裔,在馬來讀中學,后又在中國臺灣讀大學,雙重的故鄉(中國/馬來)使得其小說處于故鄉的失序結構之中,充滿哀婉的氣質。
潘雨桐的哲性鄉愁第一層便是由故土而生發的原鄉形象的自我塑造。人和故鄉的關系是文學的恒久命題,對故鄉的追憶和尋找這類感傷情緒被稱作鄉愁,安土重遷的華人執著于指認自己的故鄉,“一旦被迫遠離這個空間,人們的家園感和故土意識就被反復地激發,返歸的愿望就會噴涌而出”[4],但很多第二代馬來華人并沒有在祖居地居住,所以馬華文學中的“故鄉”更多的是虛擬想象中的故鄉,被構建出來的便是“原鄉”。在經歷了多重離散的海外華人作家筆下,抒寫原鄉便成了他們自覺的使命。嘗試塑造原鄉形象是希望找到原鄉,無論結局成功與否,尋找的過程便是哲性鄉愁。
潘雨桐在塑造原鄉形象上,和一眾馬華作家不謀而合,試圖在中國古典器具和物件中追尋原鄉記憶,有“戀物”的傾向。小說刻意運用寓言式的意象,特定的文化符號被編排進小說,器物符號早已脫離本身的能指,所指變得抽象,勾連起作者對古老“神州”的神往與迷戀。《一水天涯》中中國臺灣女子林月云嫁到馬來西亞十幾年沒有歸家,心中的鄉愁濃得化不開,洗刷從大陸走私來的茶壺會出神,由壺身上的蓮花圖樣聯想到背誦過的《愛蓮說》,在馬來政府推行馬來文的政策下,林月云還教女兒小莉背誦中國古詩文,以此抵抗母語的流失,從而記住文化的根。在器物之外,馬來華人試圖攫取符號背后的文化記憶,但小說中女兒小莉會被同學嘲笑講中文,象征著林月云華人身份的語言也將終止于她這一代,內在的中國文化并不能起到救贖的作用,“失語”的環境必將導致“失身”的身份憂思。
大馬和中國的生活經驗混合在原鄉想象中,由此,潘雨桐將“原鄉形象”投射到一對充滿張力的青年男女身上。《一水天涯》中臺灣女子與馬來華人陳凡結合,兩人的婚姻關系隱喻著潘雨桐心中的中國和馬來西亞的對話。陳凡曾說:“政府的獎學金華人更是難以獲得……我們有許多成績優良的學生,只能望大學的門興嘆了”[5]。
求學中國臺灣的客居經驗并沒有滿足想象中的中國圖像,反而更加激發了他的文化鄉愁,基于中國文化的文化鄉愁并不意味著潘雨桐的“原鄉”本體,臺灣經驗讓潘雨桐意識到二者的差距。《紫月亮》中敘述者“我”一直寄居在二舅家,性格固執的二舅幫“我”張羅相親,二舅強硬的態度象征著主導權力意志,而“我”卻因為有了心上人紫荊違背了二舅的意志,貌美的北方女子紫荊善于作畫,對極具中國古典氣質的紫荊姑娘的沉迷恰恰隱喻了“我”對文化中國的追求。“我”也試圖為當時的中國貢獻力量,小說結尾才點出紫荊姑娘只是一縷幽魂。潘雨桐本欲上溯生命源頭尋求靈魂歸處卻不得,原鄉形象構建過程滲透出作家的悲涼。
海外華文作家在異國他鄉,必然會接觸到異國的文化,文化的矛盾和沖突也在所難免,潘雨桐小說的中國古典氣質是其置身多元文化語境的抵抗方式。置身在文化差異中的潘雨桐暗索自己“唐人”的身份,小說“在真實與虛構框架之下,輾轉繁復”[6]。潘雨桐不斷解構其離散流寓的經歷,再根據個人文化心智把它重構,選擇用方塊字寫出小說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尋找原鄉的努力,承接文化中國和歷史中國的血脈,“只要是用方塊字書寫,不管身處何國何地,都難以割舍這份母體情懷”[5]。用華文寫作也只能作為調適鄉愁的抵抗,原鄉神話不斷破滅,內在中國和母體情懷也隨之松動,《鄉關》剖白似的哀嘆“已經忘了源自何處,回歸何方,只好自我認定是一個新的變種”[7]。馬來華人無所依靠,在所居地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無根的他們只能自欺欺人般倔強地持有唐人身份,卻依然掩蓋不了他們自我異化為“變種”的窘境。
回首北望,鄉關何處?在南洋的土地北望神州大地,潘雨桐嘗試尋找烏托邦化的原鄉,原鄉形象始終不能被清晰勾勒,文化中國的器具、語言都無法縫合身心具散的海外華人無以自處的創傷。潘雨桐希望找到“原鄉”,雙鄉糾葛的馬來華人實則是在非鄉的雙重失落,客觀上他們的生活被邊緣化和區別對待,主觀上他們的原鄉情結在漂泊之中漸漸消解,馬來華人也逐漸接受心靈的流浪漂泊。潘雨桐將自身離散經歷重組,在眾多馬來華人妥協于無根的狀態時,他卻倔強地用寫作抵抗內心的焦慮,文本努力即是哲性鄉愁的載體。
二、何人在地:第三世界的赤裸生命
潘雨桐的高明之處在于,意識到哲性鄉愁不僅僅屬于個體,更屬于整個第三世界的無根者,原鄉想象的生發者是共同離散的群體。“細讀潘雨桐的小說,讀者會發現,這個世界越來越小,不論天涯與海角,人類的悲苦命運是緊緊相連的。”[8]潘雨桐為第三世界的離散者構筑了命運共同體,將無根/失根的人們(包括他自己)惺惺相惜為“難兄難弟”。
潘雨桐第二層的還鄉努力是構筑了其獨有的人道主義身體詩學,尤其是對弱勢女性的關懷。如《冬谷歲月》中雜貨店老板把菲律賓女人桃樂珊“批發”后盡情享用,再如《那個從西雙版納來的女人叫蒂奴》中的張小燕被剝奪了姓名變成性商品。“身體是事件被銘寫的表面”[9],無數個女人的經歷反映了弱勢馬來人無法保全自身的悲苦,創傷事件隨時都會發生。《東谷歲月》中女兒被輪奸后“秀蘭伏臥在那里,一身的瑩白還閃了點點殷紅,無言的張了張口。”[10]女性的身體被動地經歷突發事件,無聲地承受虐辱,一眾身體大多是阿甘本所說的“赤裸生命”,身體被剝去了生命形式和價值,裸露在外,是男性或者是施暴者的發泄、管制的對象。赤裸生命飽含作家的憐憫情懷,銘刻著諸多華人受辱、沒有政治保障的“事件”。
饒有趣味的是,作者在小說落款處多加“閨閣”二字。潘雨桐曾經在龜咯眺海寫作,“閨閣”是其個人化的命名,閨閣意識不僅是潘雨桐獨特的“閨怨”抒情氣質,更是潘雨桐將自己拋擲在閨閣中,用妾位的身份去體悟這些女性的不幸遭遇。“由于公司業務的關系,潘雨桐常去東馬來西亞的沙巴,東馬還是很落后的地方,他看到了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非法移民搶劫、強奸、殺人等許多慘不忍睹的事實,也接觸到下層工人的生活,以及異常夫妻的可悲現象。”[5]潘雨桐的人道主義立場拋棄傳統的知識分子對弱勢群體高高在上的憐憫,而是將自己放在“妾位”,用同樣弱勢的姿態和同胞們同甘共苦,“對我(潘雨桐,下同)的國土我的家園我的同胞”[11]更關注一些。
潘雨桐并非熱衷于讓女性受苦,這個時候被輪暴者其實就是潘雨桐本人,對他施暴的是語言的剝奪、種族的歧視、混血之子的身份尷尬、二等公民的差別待遇等。但為了避免文字獄,不少在馬華人將異化的語言轉換成可接受的隱晦符碼,借助寓言、科幻等隱匿書寫,所以潘雨桐才以美學的悲劇來自述離散身世之苦。
除了被侵犯的女性身體,小說中還有少見的“反抗”的身體,《逆旅風情》中的露嘉西雅從菲律賓偷渡來馬,別無長處的她利用自己的身體兌換物質,周旋在眾人之間且絲毫不在意流言,一心只想擺脫貧困,身體也因此從“被侵占”的被動狀態轉變為“主動索取”的主體性建構;《熱帶雨林》中菲裔伊莉不愿被金錢操控,洞穿男人欲望,反過來主動去結交男性。這一眾女性隱喻了弱勢群體的復仇,也寄托了潘雨桐對第三世界同胞處境改善的期盼。
身體詩學是潘雨桐的微觀處理。馬來西亞的政治結構與種族結構密不可分,1957年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宣布獨立后,人種復雜,語言眾多。馬來人、印尼移民及原住民幾近半數,中國人后代的華裔約占三分之一,其他為印度裔、歐亞混血裔、阿美尼亞裔、阿拉伯裔、泰裔、越南裔等。在復雜的種族結構中,馬來政府推行馬來文,其他民族的語言被降格。“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屬于個人和力比多驅力的文本,總是以國家語言的方式來投射一種政治。”[10]馬來華人在失語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政治身份,淪為在地的族群“他者”,邊緣的“他者”們奢求政府來解救已不可能,只能自救。
《天涯路》是一部書信體小說,背景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越南排華運動,四位馬來西亞華裔Y.T、A.K、K.Y、K.N解救越南難民朋友李光宇和素未謀面的張達明等人,千方百計地和官員周旋后終于將他們成功救出難民營:“這就是難民了,他們和我們有什么不一樣?黑頭發、黑眼珠、黃皮膚……要是我們也只穿一條短褲,把頭發的油脂洗去,光著腳丫和他們站在一起,不也是難民嗎?”[10]衣著雖不同,華裔“難兄難弟”卻共有模糊的政治背景,“越南難民的流離,是大馬華人的殷鑒”[10]。據統計,1978至1989年間,大約有100萬人逃離越南,其中60%至70%為華人,他們投奔怒海,大約有10%葬身魚腹。小說末尾是第三世界難民流亡寓言,“天是祭壇,海是血淚,無言是千年萬載沉冤的一種控訴,沉冤在灘上海里張大了口,張大了千個萬個千萬年不閉的口。”[12]難民同胞面對怒號的血海也義無反顧,人微言輕的他們仍可聚沙成塔,在夾縫中惺惺相惜,共同抵抗命運的戲弄。
潘雨桐指認故鄉必然要處理故鄉人的問題,故鄉雖已成虛妄的存在,欣慰的是在地者互助相惜,身份認同的迷思和無所歸附的尷尬反而將第三世界的華裔同胞團結起來,哲性鄉愁的持有者是整個流散群體,他們以隱匿的方式建筑故鄉人的命運共同體,赤裸生命之間存在著內在張力。
三、如何存在:永恒的哲性鄉愁
馬華作家都在“尋找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坐標,沒有他人的影子,歡唱著獨一無二的高音”[13],自我生命狀態的思索和魂歸何處的鄉愁貫穿潘雨桐小說,“對生命安頓之處和本真狀態的追尋則是哲性的鄉愁,也就是為‘終極信念而生的終極鄉愁”[14],其文學創作無疑是其自我調適的救贖嘗試,也是其哲性鄉愁的注腳。
潘雨桐最終離開中國臺灣,復歸大馬,身體的一再遷移猶若“落葉歸根”,但歸向哪個根?何以為家?《冬夜》中的小儲在馬來西亞森美蘭州的芙蓉長大,在紐約謀生階段和芙蓉老鄉老高交好,時常共同回憶中學時光,小儲經老高介紹想要購買秦老大的房子,秦老大頗有古龍武俠小說里的俠肝義膽的豪情。流散的華裔割舍不下大馬回憶,另一方面又尋求文化中國的努力,秦老大的“房屋”是小儲扎根異鄉的庇護所,最終小儲在返家途中遇刺被劫,臥倒在雪地里,腦海里想的卻是異地的家人和自我的責任。還鄉努力在書中以宿命論般的悲劇流產,也是作者潘雨桐內心對哲性鄉愁之旅的自我懷疑,作家似乎并沒有自信能找到救贖的方式。
身體無法回鄉,或說“故鄉”的實體本就不存在,馬華作家展現出超然的韌勁,為靈魂鑄造家園,以求詩意的精神還鄉,這也是作家虔誠的朝圣。潘雨桐哲性鄉愁的紓解出口有兩個,一是鄉土人情,二是鄉土山水。“疲了、累了,我們相背而眠。我想我的事,我遙遠的家,母親、妹妹,我家鄉的山和水,童年時走過的路……”[15]家鄉物質實體是精神幻想需要的依憑,按圖索驥,將破碎的家園感用情感黏合,借靈性山水宣泄苦悶。潘雨桐念念不忘的是馬來本土的記憶,《煙鎖重樓》中凌浩天回歸故土大馬時卻常常想起故鄉的事,家鄉人生存的情感方式和大馬獨有的地方特產勾連了他記憶中真正的原鄉。
這也剛好解釋了潘雨桐為何辭去中國臺灣教職工作,再次回歸大馬的行為。在東馬工作期間,他目睹了家園雨林被破壞,“大河兩岸的林地砍伐過度,野生動物連藏身的地方都沒有了。”[15]自然生態變得不和諧,人類為了牟利非法盜伐,施工的重型機械在潘雨桐的筆下像一只只“變了形螃蟹,不管是大白天還是黑夜里,全都毫無忌憚地爬上了河岸,對著雨林的邊緣直沖過去,把雨林一口一口地侵吞下肚”[16],雨林本是原住民的居住地,現代化進程擠占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后期轉向自然寫作的潘雨桐內心無疑是失望的,他所紓解哲性鄉愁的密鑰被破壞,內心的平靜被打破。
生態寫作可以理解為潘雨桐的戀地情結,即人和環境的情感紐帶,情感是復雜的,“更為持久和難以表達的情感則是對某個地方的依戀,因為那個地方是他的家園和記憶儲藏之地,也是生計的來源。”[17]當潘雨桐復歸大馬,家園大地的肌理日漸裸露,此時他的雨林系列小說完全不同于以往自困于身世之苦的離散創作,而是另辟魔幻神話的路徑,用鬼魅復仇懲罰人類的惡性。《河水鯊魚》中的杜維拉因為捕捉小鯊魚而在雨林中暴斃身亡;《河岸傳說》中的阿楚破壞大河鏟光樹木,最后引來河水倒灌被淹死;《旱魃》里娃系達的男人砍伯公樹意外身亡,如此因果報應的自然復仇不再贅述,潘雨桐用詭異神秘的雨林傳說來提醒人們,對自然應抱有敬畏之心。雨林有自身的禁忌,一草一木也是生命,人的生命并不比雨林生態中任何一個物種更加高貴,作者轉型到雨林書寫階段開始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哲性鄉愁之旅不斷升華,精神返鄉的過程也不斷受阻。
巴赫金說,“怪誕魔幻現實主義的主要特點是把一切高級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表征官方)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肉體層面、大地和身體層面(表征民間)。”[18]潘雨桐轉型至自然寫作,選取他最在乎也最熟悉的雨林意象系統,賦予最高層精神和理想的隱喻,魔幻化雨林是他抵抗故土異化的敘事策略,亦是他精神返鄉過程中對記憶中故土山水風貌的捍衛。
馬華文學一度被標簽化,部分作家一度以消費異域蕉風椰雨的南洋圖像為賣點,抑或標簽化、套路化馬華文本,馬來文藝的獨特性和主體性一度被擱置。異鄉人的潘雨桐在想象與現實的邊界操作,永遠在尋覓他的主體和身份,體現在小說中就是一種不安的情緒和隱隱約約的抵抗姿態。潘雨桐一直通過寫作來尋找屬于自己的國度,在此過程中建構自我的生命主體性。
哲性鄉愁持有者是痛苦的,潘雨桐曾自困于“重復結構”之中,“那樣重復的語詞宣告卻也在對方的遺忘中喚醒他們祖輩的記憶,甚至把原屬于他們祖輩的和故鄉斷裂的創傷深化為仿佛可以經由遺傳而延續的集體創傷。”[19]自耽于漂泊之苦、失根之痛,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重復著被現實打擊又無路可走的固定程式,更甚者沉淪在不屬于自己的創傷記憶中。走不出創傷記憶的民族難以發展。尋找原鄉是潘雨桐永遠的愿望,也是其永恒的哲性鄉愁。
潘雨桐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小說走向顛覆傳統的封閉文本,更具多聲部的開放性。《純屬虛構》由三個斷裂的劇場組成,主角之一叫潘雨桐,劇場一和劇場二的劇評相互抵牾,同一個故事呈現出三種形態。許文榮從政治抵抗詩學分析,“他者已經被賦予和自我的同等的發言權,彼此在平等的層次上展開對話”[14]。真的存在各民族平等相待的世界新秩序嗎?如果有,潘雨桐也不會被哲性鄉愁羈絆了。更準確地說,多聲部文本的小說是潘雨桐與自我的深層對話,在調適心靈世界時無法找到出口,只能內證于斯:“我忽然瞥見,遠方,有人踽踽獨行。咦?那人怎么那么像潘雨桐呢?看真切些,又不太像——是他?不是他?是誰?”[20]結尾處控訴無數個“潘雨桐”找不到精神的出口。
如前所述,潘雨桐的哲性鄉愁尚未消解,如潘雨桐那樣的一眾馬華作家雖然暫時在某地安頓了肉體,在精神向度上卻是不安定的,身體不再流離,生命主體追尋尚未得到圓滿的答案,還處于內在流離的狀態。換言之,這是當下馬華文壇的規律,永恒的尋找也即永恒的哲性鄉愁。
四、結語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曾提到,“馬華文學的傳承一向頗有曲折。華人雖占馬來西亞人口的大宗,但華族文化卻并未受到官方應有的重視。然而落籍于斯的唐山子民卻化不可能為可能,徑行發展出一派文學傳統。六七十年代以來,馬華學生絡繹來臺就學或定居,在寶島又植下極有特色的文學花果。擺蕩在僑鄉亦是故鄉、彼岸猶若此岸的不確定性間,馬華文學所透露鄉關何處的慨嘆,以及靈根自植的韌性。”靈根自植毋寧說是一種結果,不如說是一種正在進行的尋找,種植自我靈根的嘗試必將遭遇種種困難,不安惶惑也在所難免,馬華文學的韌性也就在于沒有放棄哲性鄉愁。
潘雨桐的哲性鄉愁頗具代表性,作家奮力尋找原鄉形象,當故鄉實體蕩然無存,只能將各種故鄉元素糅雜于含混的想象中。唯一清晰的是哲性鄉愁的持有者,苦難敘事營造了赤裸生命的語境,無數個相似的身體在各大政治事件中流動,在地華人身處暗處,依舊向往新的人文生態。
哲性鄉愁會不會消失?在潘雨桐已出版的文本中,尚未找到其具體的靈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哲性鄉愁已經超越現象本身,成了促成作家文本的內在動機,“哲性鄉愁”甚至可以理解為馬華文學史的自律性。從潘雨桐創作中的心路歷程可以窺見,在形而上的角度探幽馬華作家的哲性鄉愁,馬華作家似乎一直在尋找什么,其核心都是意圖找到靈魂的立足點。“尋找”的主體永恒存在,那么,“哲性鄉愁”便永恒存在。
參考文獻
[1] 陳大為. 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M]. 臺南:臺灣文學館出版社,2012.
[2] 金進. 論馬華作家潘雨桐的小說創作[J].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1(2).
[3] 龔剛. 錢鐘書與文藝的西潮[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
[4] 汪民安. 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5] 潘雨桐. 昨夜星辰[M]. 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78.
[6] 張錦忠. 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M]. 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7] 黃昌明. 飄蓬無根——讀潘雨桐《因風吹過薔薇》[J]. 文訊(臺北),1988(36).
[8] Michel 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9] 潘雨桐. 靜水大雪[M]. 馬來西亞:彩虹出版社,1996.
[10] 潘雨桐.因風飛過薔薇[M]. 臺北:聯合出版社,1976.
[11] 張京媛. 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2] 陳大為. 躍入隱喻的雨林——導讀當代馬華文學[J]. 誠品好讀(臺北),2001(13).
[13] 龔剛. 從感性的思鄉到哲性的鄉愁——論臺灣離散詩人的三重鄉愁[J]. 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
[14] 潘雨桐. 野店[M].臺北:聯合出版社,1978.
[15] 潘雨桐. 河岸傳說[M].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16] 段義孚. 戀地情結[M].志丞,劉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17] 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憲 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8] 黃錦樹. 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M].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出版社,1996.
[19] 許文榮. 南方喧囂: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M].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
[20] 黎紫書. 山瘟[M].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 羅? 芳)
作者簡介:蔣婷,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世界華人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