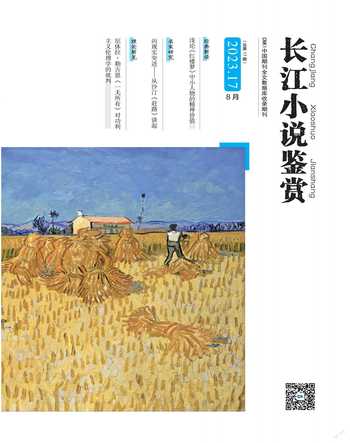向現實突進
張 萌
[摘? 要] 《趕路》講述了一個撲朔迷離的謀殺案件。讀者跟隨作者的敘述抽絲剝繭,可以發現行人的交談、意象的刻畫里處處埋藏著殺人事件的暗線,而小說所采用的內聚焦敘述視角更加重了小說的懸疑性。本文將《趕路》同沙汀兩年后創作的另一篇小說《在祠堂里》進行互文性閱讀,可補足前者未曾呈現的事件的側面,由此又可發現隱藏在文本中的精神暗線:沙汀致力于以現實主義筆法對20世紀30年代中期四川底層社會的困境進行藝術性地再現,揭露時人所受精神與身體之戕害。
[關鍵詞] 《趕路》 敘事策略? 互文性閱讀? 現實主義特色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7-0065-04
《趕路》是一個以第一人稱為敘述視角展開的故事。小說寫“我”趕車回鄉,然而途中汽車出現故障,“我”只能借宿在路邊的涼粉攤上,恰巧見證了一個計劃周密的謀殺案件。所有的信息、人物感知都是模糊零碎的,當謀殺行為發生,回顧“我”途中的所見所聞,故事鏈條才得以重新串聯:軍閥團長懷疑姨太太同她的家庭教師有染,于是派人一路跟蹤監視她,最后他的手下在半路伺機假扮土匪殺死了青年教師。這是一個乍看情節曖昧不清,仔細一看卻處處有伏筆的小故事。本文試圖分析《趕路》的敘事結構、敘述視角及版本改編等基本故事邏輯,兼引入其他關聯文本,以探究沙汀這一時期的創作理念和藝術特色。
一、草蛇灰線:《趕路》的敘事策略
小說開篇用大量篇幅鋪敘“蜀道之難”——小川北一帶的荒寒、從重慶到成都得受十天上下的活罪、隨時可能遭受土匪搶劫、歇腳旅店里的藏污納垢……“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踏上了回鄉的路。在擁擠的汽車車廂里,“我”與青年教師初次相逢。這位年輕人似乎從一出場就與眾不同:車中乘客各顯其能,艱難尋找著立身的空隙。與“我”一同趕車的同伴被軍官“像驅逐一匹瘟狗似的”從駕駛員旁邊相對寬敞的座位趕走,但這并不是為了軍官自己,而是為他身后的青年。青年給人的初印象是“不是那種慣會坐在茶樓邊等女人看的不良少年”,也不是“牛市口以上”的屠豬販酒之輩。此后,他便時時以各種方式出現在“我”的視野里。
汽車途中拋錨,“我”下車休息的間隙聽見關于他的零星議論,其中間雜著“干掉他”“栽點罪名”等話。汽車修理好再次上路后又再次拋錨,“我”決心改乘滑竿繼續路程,然而道中遇雨,一行人只得在路邊攤暫宿一夜。此處“我”同家庭教師再次相遇,這一次他身上的神秘感更重、謎團更多。一個男人到涼粉攤同過往旅客攀談,本已經離開,卻又在青年出現后再次到來,“神色中像是窺視著誰”,青年自己似乎總懷著莫名的不安和憂慮,“不很說話,不時嘆一口氣,隨即十分煩躁地走向馬路邊去”,而當“我”同他談起對這一帶匪禍的憂慮時,他只是“嘆了一口氣”便陷入沉默。隨著所聞所見所感越來越多,“我”關于青年處境的預感也愈加不祥。小說的結尾處,青年消失,遠處傳來兩聲槍響,一位青年的生命在無人的角落隕滅,一切歸于平靜。
至此,來龍去脈終于明晰:青年是軍閥姨太太的家庭教師,他與姨太太產生了不明的感情,由此得罪軍閥,引來殺身之禍。文本中的意象尤其是對青年形象的兩次聯想,似乎也暗示其命運走向的不同尋常。車出故障停在路邊,我一邊聽著旁人的八卦,一邊看青年的背影:“一只手吊著一根垂枝,俯著頭,使人想到一個縊死者的背影。”相互交談時“我”感受到了他的恐懼,他“閃著懷疑和苦惱的目光,在指揮刀下面,在那罪惡的黑掌下面,恰像一只羔羊似的”。“羔羊”一般同任人宰割、柔弱、無反抗之力等意義關聯,似乎意在暗示他已深入虎穴,唯一能做的事不過是等待鍘刀落下,而“縊死者”是小說敘事里第一次出現同死亡相關的暗示,作為一個不尋常的意象,它的出現一方面帶來了敘事節奏的變化,一方面也改變了敘事氛圍,使事件籠罩了一層陰謀恐怖的陰云。
此外,小說中“公雞”意象出現了兩次,一次是“我”和青年交流對安全的擔憂時,看見“放在靈柩下的路燈”,靈柩上還有一只咯咯咯的公雞;另一次是青年教師被殺害后,“我”看見“雄雞咯咯地小聲哼著,用翅膀拍著棺材”。古人認為雞和雞血有著超自然的神力,可以驅鬼邪、去災禍,因而其成為祭祀活動中的重要元素。一條生命消失,無知無覺的動物還繼續鳴叫著,似是祭奠,似是哀鳴,似是宣告,又似乎表明一切如常,上位者濫用私刑同踩死螞蟻般輕而易舉、不值掛心。
從敘述視角看,“我”是事件的見證人,是故事的敘述者,同時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看客。小說雖采用了信息獲取受限的內聚焦視角,隨著敘事的展開,那些在日間得來的印象和談話、青年人的不安和恐懼,“一時間在我的心里連貫起來了”,盡管“我”出于惻隱之心想勸他離開,另一方面又害怕唐突的舉動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當“我”被手電筒的光束驚醒,想到“完事了”,這一簡潔而平常的敘述更顯示出“我”的冷漠,這場風波終于以青年殞命而結束,一切塵埃落定,這似乎是大家隱隱期待的結局。自在涼粉攤重遇青年教師開始,“我”開始對事件的起因、隱情和可能出現的結果感到好奇,然而“我”也無意介入這一切,因為青年的命運走向是“我”能力之外的事。從某種程度上說,內聚焦視角是整個故事得以成立的關鍵,也是其真實感的來源,讀者和故事的敘述者共享等量的信息,隨著敘述者了解的信息增加,讀者也漸漸撥開迷霧,得以還原事件的真相。
在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的小說集《土餅》中,沙汀對《趕路》進行了部分修改,在青年被軍官“押送”著出場后,增加了這樣一段描述:
從他那不安定的神情,和對那軍官的一種欠自然的態度上,我還猜想他們當中會存在著一種神秘關系。他似乎在被那位特權者脅迫著,但他能夠做到的,卻又只有對于命運的服從。[1]
修訂版預埋了更多伏筆,使人物命運走向的敘述鋪排更加自然,青年教師甫一進入汽車車廂,行文就埋下“即將走向懸崖”這類命運暗示。《趕路》開篇用輕快的語調說著:“不錯,現在我們有汽車好坐了……雖然多出點錢,人卻可以少受十天上下的活罪。”相較于從前坐轎竿對人精力的消耗、時常遭遇土匪搶劫等風險,坐汽車趕路顯然更便捷舒適。然而,就在這個被“我”稱贊為“近代物質文明”的空間里,一場謀殺正隱秘地發生。沙汀或許是想要以此表現當時巴蜀地區底層社會的生態。盡管現代文明正緩慢地滲入鄉土,但在這里,暴力、野蠻的地方政權絲毫沒有被削弱,甚至普通民眾也對此習以為常,旅途中出現被特權者脅迫的陌生人,并不會引起任何騷動,連議論也少有。幕后的軍閥、為虎作倀的打手、以“我”為代表的無力而沉默的看客,共同建構了這個令人絕望的屠宰場。
二、《在祠堂里》:《趕路》的另一個故事
《在祠堂里》是沙汀于1936年創作的又一篇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個明目張膽的謀殺事件。出身貧賤的洗衣婆女兒鄙棄當連長太太的富裕生活,與一個青年真心相愛,連長因妻子的不忠惱羞成怒,于是強行把她訂進棺材活活悶死。小說情節集中于慘劇發生的前夜,貫穿其中的有兩條線索,一是看客們的閑談、嘲諷;二是軍閥和他太太的爭吵、咒罵。從始至終,被害的女主人公都沒有正式露面,也無血腥場面的肆意渲染,唯一的在場場景是看客聽到她同丈夫辯駁的聲音,而越軌行為的原委、二人關系破裂的來龍去脈都是通過看客們的議論推測出來的,就連她最終被丈夫毒打直至被釘死在棺材里的過程也主要通過院壩里看熱鬧人的視覺、聽覺及心理感受反映出來。
若讀者將《在祠堂里》和《趕路》進行互文解讀,便可補上《趕路》敘述留下的空白:和連長妻子產生曖昧的青年男人被暗殺,那妻子作為最直接當事人的命運又會如何?這篇小說為讀者揭曉故事的另一側面,妻子同樣會死,且可能死得更凄慘。從旁人口中,連長太太的性格得以管窺一二:她性格倔強、“驕傲又冷淡”“見了誰也不理睬,對于那個已經逃跑了的青年人是例外”,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性格,讓她不會如旁人所說,將連長的寵幸當作恩賜,反而會因為追求純粹平等的感情而招致毒手。連長太太被鄉俗審判、被作為上位者的丈夫物化、被暴力掠去生命,“祠堂”是眾人活動、眾多言談交匯所依托的空間,也是囚禁和扼殺自由靈魂的牢籠,對于這個逆流而上的孤獨者來說,死亡或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解脫。
《在祠堂里》同樣塑造了看客的形象,同《趕路》一樣,他們也充當了敘述者加見證者的雙重角色,只是這些看客比《趕路》中的“我”更冷漠、自私、虛偽。《在祠堂里》中,一邊是連長太太被釘進棺材的慘劇,一邊是同住祠堂的七公公和布客大嫂之流看笑話似的議論和打探。當聽聞連長下屬對洗衣婆女兒刻毒而猥褻的聯想時,圍觀的人紛紛嘆息,然而緊接著小說話鋒一轉:“這也不過是幾分鐘中間的事,那種容易使人變旁觀者的好奇心理,立刻就把他們的同情和不安趕跑了;重新又為一種漠然的期待所占據。”面對他人的不幸,這些人的態度竟是幸災樂禍、唯恐不亂的,本屬被侮辱、被損害的底層人物加入吃人的鏈條而成了上位者的幫兇。底層互害也是沙汀這一時期的小說著力敘述的主題。
《趕路》和《在祠堂里》兩篇小說創作時間前后相隔不到兩年,但前者展示的是軍閥混戰時期四川底層社會的亂象,后者則以20世紀30年代中期國民黨中央力量入川后為寫作背景[2]。盡管故事發生的社會環境略有不同,人物的行為邏輯、命運走向卻驚人相似,這個時期,四川地區始終被人治和暴力籠罩,現代物質文明的引入并未孕育出真正的文明根芽。沙汀直接接受過魯迅的創作指導,也在實踐中承襲著魯迅精神,被認為“是吃著魯迅的奶成長的”作家,在魯迅筆下確立標準并得到極大發展的“看-被看”模式在沙汀的創作中得到了繼承,他借描繪軍閥混戰下飽受折磨的中國西南一隅,展現底層民眾生存空間的逼仄,兼及刻畫受壓迫者的不自知和冷漠,正視農村社會的不堪,直刺地方實力派的暴行和對人命慘無人道的迫害、操縱,表達了他對苦難的下層人民的同情。
三、接續左翼文脈:向現實突進
以上文本中,沙汀所描繪的是一個并未走向現代文明的四川社會的殘酷圖景。川西北的場鎮是沙汀生長的地方,也是沙汀藝術的啟蒙地。沙汀晚年在《收獲》上發表《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一文以回顧他的寫作之路,談到創作原則,他說:“我一直在創作上按照這一條辦事:寫自己所熟悉的。”[3]青少年時期,沙汀常跟隨舅父坐茶館和四處做客,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物,他的舅父鄭慕周入袍哥幫會,沙汀也跟隨左右,幫舅父遞送消息、運送小型武器,走遍了安縣的大街小巷,因而對四川鄉鎮文化、基層政權了解甚深。在對四川鄉土深入體察中收獲的生活經驗,為沙汀日后的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也幫助他形成獨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母親去世后,沙汀從上海回到家鄉四川,加之先前在成都、上海間輾轉的經驗做鋪墊,他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故鄉。自此,沙汀在現代經驗和鄉土傳統間找到了著力點,開始系統地建筑巴蜀鄉土世界。
除呈現故事主線外,小說《趕路》開篇就講了故事發生的背景——20世紀30年代匪禍橫行、山長水遠的四川。“汽車”又是小說承擔人物行為、推進事件的最重要空間:候車的人往往需要“逗留到十日以上”,車來時眾人爭搶如“一場全武行的競技”,車上路后還沒有行駛三十公里就“花費去五六個鐘頭、停下來修理過四次”,當司機破罐破摔拒絕修車后,乘客們“有的送上煙紙有的夸獎技術”,以各種方式安撫這個掌握他們旅途命運的人。小小一個汽車里,不同境遇下的眾生相展示得淋漓盡致,信息的閉塞、交通的艱難、掌握權力者的傲慢和人在這種環境里所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都在平靜而稍帶戲謔的敘述里盡數體現。
誠如李慶信所言:“巴蜀大地因為長期的半封閉狀態,讓它始終和中原大地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而結合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特殊情況等多種因素,讓四川產生了獨特的權力分配格局和權力結構方式,讓四川鄉土社會滋生出一種膜拜權力、臣服強力人物的文化生態。”[4]20世紀30到40年代,國家積貧積弱,大小軍閥混戰不斷,底層民眾苦苦在夾縫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當時的鄉土小說和現實主義小說,都對國民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境有著深刻的觀察。都市場景里再常見不過的三角戀愛在這時竟招來殺身之禍,軍閥只手遮天的能力令人震驚。吏治不良是民國時期基層社會的痼疾,在閉塞自足、山高水遠的地域更是如此,在沙汀的川西北鄉土世界里,他描寫了一大批強權庇佑下的投機者,從棒客、袍哥一類的土匪,到士兵、司令這類軍閥,再到以保長甲長、鄉長為代表的基層官僚,他們以蠻力和霸權為膀臂成為鄉土秩序忠實的維護者。
團長處置家庭教師、連長公然將妻子殺害這類濫用私刑的故事在當時的四川并不罕見。時人曾這樣觀察記述:“川省政治軍事方面,有一種特殊現象,為他省所無者,即所謂防區制也。……四川之軍事政權悉操于軍事領袖之手,予取予求,惟心所欲。”[5]此處所提及的防區制建制于1918年,當時的四川被劃分為十一個區,各個區域都有人駐扎。這種制度的特點是每個軍閥在其管轄的防區內,不僅可以把持捐稅,還能肆意征發、截留稅款,同時他們還擁有委任官員的權力,更掌握著百姓的生殺大權,如此,軍閥在自己的管區中集財政權、行政權、司法權于一身,“每個防區就成為一個獨立王國”[6]。這就能解釋《趕路》《在祠堂里》的軍閥草菅人命、肆意妄為的底氣來自何處。這不僅是個體的作惡,更是結構性的痼疾,而沙汀所做就是將“自己所熟悉的”表現出來,作為那一段歷史事實的旁證。
四、結語
“四川作家”和“左翼作家”是沙汀身上最鮮明的兩個標簽,前者體現了他創作中的地域文化經驗,后者則成為其創作精神的暗線,鄉土的滋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使沙汀的小說體現了獨特的地域文化,閱讀沙汀的作品,讀者可以看到文學是如何與民國時期四川的歷史發生交匯的。沙汀的小說世界里,一切人物皆有原型,一切故事都有真實的歷史背景,沙汀對現實主義審美品格的遵循使他如實反映了當時四川地區吏治的失敗和普通民眾的困境,在文學創作里生發更為獨特的藝術觸角,由此展現出了更廣闊且深入的現實生活。
參考文獻
[1] 沙汀.趕路[M]//土餅.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2] 杜雪楠.沙汀小說知識分子道路選擇主題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17.
[3] 沙汀.生活是創作的源泉[J].收獲,1979(1).
[4] 李慶信.沙汀小說藝術探微[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5] 李振吾,陳慧一.川游見聞[J].生活,1931(11).
[6] 隗瀛濤, 李有明,李潤蒼,等.四川近代史[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7] 沙汀.沙汀自傳:時代沖擊圈[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
[8] 黃曼君,馬光裕.沙汀研究資料[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9] 李生露.沙汀年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0] 沙汀.沙汀文集[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
(責任編輯 陸曉璇)
作者簡介:張萌,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