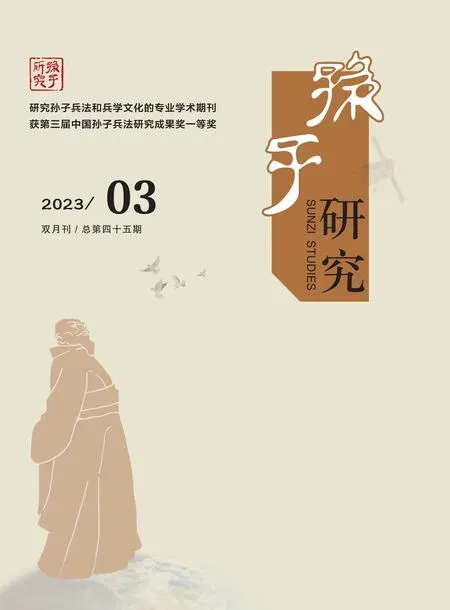《老子》兵書說再商榷
——以老子之“道”為考察
高 凱
老子生于春秋時期,與孔子同時代,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的戰亂時期。受時代影響,儒、墨、道、法等幾大學派無一不談兵,所以說春秋時期也是一個“百家言兵”的時期。〔1〕老子作為道家學派創始人,其書中蘊含著豐富的中國古代兵學思想,獨具特色。所以,不少人將《老子》一書視為兵書。如《隋書·經籍志》將《老子》列入兵家類著述;唐代王真認為《老子》一書:“原夫深衷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于兵也。”〔2〕清代魏源也持類似觀點,說:“《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見兵之 形。”〔3〕近代學者郭沫若在《中國史稿》中認為:“《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學著作,又是一部兵書。”〔4〕相反,也有學者認為《老子》不是兵書,比如華鐘彥認為《老子》八十一章中的辯證法思想雖對兵家有指導作用,但其言行涉及言兵者只有十章,其中積極言兵者只有五章,故無論從數量與質量上都無法承認《老子》是一部兵書。〔5〕李澤厚也持此觀點,他說:“雖然承認《老子》與兵家有密切關系,但是,《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講兵的書,決不能說《老子》書的全部內容或主要論點就是講軍事斗爭的。”〔6〕
通行本《老子》一書共八十一章,其中有十二章直接談及兵學思想,那么《老子》一書是否就可以被視為兵書呢?如果不是,《老子》談論兵學的目的又是什么?要想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楚“道”的基本內涵,在此基礎上審視《老子》兵學思想及其意義,就可以對《老子》一書的立論方向做出判斷。
一、“道”與兵學
(一)“道”的地位和提出
“道”是《老子》一書的核心主題。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說:“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故見素樸以絕圣智,寡私欲以棄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謂也。”〔7〕依照王弼所說,五千言的《老子》其實說的就是一個主要意思——崇本息末。本是什么?本就是“道”,即自然無為,崇本就是遵循“道”。末是什么?就是與“道”(自然無為)相對立的經驗世界中人為行為或者人為事物,比如儒家所倡導的仁義。可見,《老子》一書的主題和宗旨就是言“道”,書中也正是以對“道”的探討為邏輯起點展開其對宇宙人生等全部哲學問題的論述。那么何謂“道”呢?或者說“道”究竟是何物呢?
“道”的原始意義是路,本義是人所行走之路。《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8〕由此來看,“道”也就是人行走活動中的路,從行走活動本身即現象學所說的事情本身而言,“道”是形而上的,處于人所經驗意識之外。隨后,人們將行走之后產生的路對象化、意識化,即由動詞的“道”到名詞的“道”,從而形成抽象的觀念——“道”。朱熹講“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9〕,也有此意。“道”作為老子哲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則具有更多的哲學內涵,至少有三層含義:本體論意義上的“道”、生成論意義上的“道”和作為行為原則的“道”。下面,結合兵學具體論之。
(二)本體的“道”與兵學
“道”是老子哲學中的本體,那么其性質和作用就相當于后來程朱理學中的“理”。在先秦哲學中,并沒有“理”的哲學概念,但并非沒有“理”的內涵。“道”這一概念就包含“理”的內涵。在程朱理學中,“理”是人類理性的一個預設,在經驗世界中“與物無對”,是一種超驗的、抽象的、絕對實在。那么,作為本體的“道”(理)有哪些性質呢?
首先,“道”是“與物相對”的“無”,“道”具有不可言說性。《老子》開篇即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可見,“道”具有不可言說性,這里指的是不可“道”之“常道”,“常道”也就是本體意義上的“道”,也就是王弼所說的“無”,“無”即“道”。在王弼看來,“道”在經驗世界中并沒有具體的形象可以感知,是無法用語言來訴說和描述的。王弼認為任何語言和文字都具有確定性和指稱性,一旦對其賦予名稱,就指向了具體形體的意義,都只會偏向一極,便立刻破壞了其絕對性、無限性及圓滿性。老子將其稱之為道、玄、微、遠、大,都只是從某一方面來描述作為本體的“道”某一方面的特性。因此,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說:“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10〕由此來看,老子所言的本體之“道”,是不可以用言語文字來表述的,在經驗世界中并沒有具體事物與之相對。所以,王弼將之稱為“無名”更加合適。
其次,“道”是超越現象和具體事物的實在,“道”還具有先驗性。老子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一章》)老子的“道”是渾然不可得而知的,但并非不存在。萬事萬物因“道”而存在,道是經驗世界中各種現象和萬事萬物的始和母。或者說,“道”是萬事萬物的生存根據,我們所看到事事物物活動背后的指向就是“道”,現象只不過是“道”的呈現而已。
再次,“道”具有抽象性。老子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老子·十四章》)這是說,“道”不可感性直觀。正是因為“道”是超驗的抽象之物,因此是無形無象,不可直接經驗直觀的。亦即在經驗層面,人無法通過耳眼鼻舌身來獲取“道”的材料,即康德哲學認為感性無法直觀“道”,唯有通過人的理性才可以把握,所以老子稱為“恍惚”。
由此來看,“道”的性質完全符合“理”的性質,“道”即“理”。作為理的一面來說,“道”是經驗世界中萬事萬物存在的依據,是事物生存和活動的客觀法則,即經驗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及其行為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道”。反之,不符合“道”的,就是不合理的存在,也就喪失了存在的本體依據,必然走向滅亡。作為本體的“道”與兵學有什么關系呢?老子思想中的兵學是否符合“道”呢?
從本體之“道”來看,戰爭是非法存在的,不為“道”(理)所規范。老子直接指出戰爭是與“道”相悖之物,有道者不為。老子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兇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三十一章》)
老子認為,窮兵黷武之人是不祥的,一切事物都排斥和厭棄這種人,因而符合“道”的人是不會和這種人相處的。兵家和兵學的存在是非法的,其存在并不依據“道”(理)而存在。從現實層面來看,用兵和兵者都是與代表“道”的君子相對立的,符合“道”、代表“道”的“有道者”對兵事采取的是極其厭惡的態度,即使不得不采取用兵行動,最后也是以“喪禮”的方式來對待此事。因此,老子用“不祥”“惡之”“兇事”等大量的否定詞來描述“佳兵者”。總之,“佳兵者”站在了“道”的對立面,用兵的行為也失去了“道”(理)的規范,其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三)行為準則的“道”與兵學
對人而言,“道”是人的行為準則;對天地萬物來說,“道”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原則。這就意味著人同萬物都必然遵循“道”。那么,作為行為準則的“道”是什么呢?老子認為,“道”就是“自然無為”,“自然無為”就是人和萬物的行為準則。
對此,老子直截了當地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認為“道”是天地人的根本大法,是其生存活動必須遵循的客觀行為準則,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也就是說,人同天地一樣都要按照“自然無為”的“道”去行為去活動。王弼對此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 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于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道[ 法] 自然,天故資焉。天法于道,地故則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王]所以為主,其[主]之者[一]也。〔11〕
在王弼看來,“法”即法則,而“自然無為”就是根本大法。首先,人、地、天、道之間依次相法,這是一個邏輯遞進關系,歸根到底都要因循自然,不違背自然,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其次,所謂“法自然”,即指“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這樣方可不違背“自然”,此處的“自然”就是說人的一切生存活動(行為活動)都必須在符合“自然無為”這一大原則下進行,即人的行為準則就是“道”(自然無為),“道”是萬事萬物生存的一種必然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不違背自然,萬事萬物才能實現自己的本性。由此看來,“道”即自然,自然是對“道”的描述。此外,“無為”也是對“道”的描述,其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三十七章》)
可見,“無為”就是順應“道”,正因為“無為”,天地萬物由之以成,這也就是“無不為”。而人(侯王)所要做的就是“無為”,就是效法“道”。如此一來,自然沒有邪念惡欲,天下自定。老子賦予“道”以新的內涵,將“自然無為”視為人和萬物的本性,人的本質生存狀態就是“自然無為”的狀態,人所要做的就是抱樸歸真以至于“自然無為”。如果背“道”而行,那么將會招致嚴重的后果。“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老子·三十九章》)這些都是違背“道”的結果。
作為行為準則的“道”與兵學有什么關系呢?老子思想中的兵學是否符合“自然無為”的行為準則呢?在老子看來,顯然不符合。用兵非“無為”而是人為,兵學非自然而是造施。可見,老子言兵的目的是為其“道”服務的,只不過是從反面來論證其“道”之“自然無為”罷了。
雖然從“道”的角度看,老子兵學并不與之相符合,甚至與“道”相悖,那么是否就可以說《老子》一書中不存在兵學?其實不然,《老子》一書五千余言,其中有不少直接談及兵學的章節。不可否認,老子思想中蘊含著獨特的道家兵學思想。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老子談兵的目的還是論述其“道”之“自然無為”。
二、老子“道”的兵學
老子兵學與兵家、法家、墨家、儒家等兵學思想相比,有其獨特的思想魅力。其特點是在反戰、反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然”的用兵思想。也就是說,在迫不得已發動戰爭的情形下,老子強調要在“道”的規范下來用兵,軍事行動要符合“道”的行為準則,否則就是非法的。
首先,老子對戰爭的態度是反戰、反兵。春秋時期戰爭頻發,民眾飽受戰爭摧殘,“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得勝數”(《墨子·非攻》)。老子早就看到戰爭的極大破壞性,他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老子· 三十章》)正是基于此,老子堅決反對兵事,認為戰爭乃“不祥之器”,有道之君不會輕啟戰端,不會主動選擇“兵強天下”;“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在老子看來,戰爭和用兵不僅是一種非自然的人為干預,更是一種妄為,與“自然無為”之道背道而馳,與個體生命的自然長生截然相反,這是老子所不能允許的。
其次,老子堅持“自然無為”的用兵原則。“自然無為”(道)是老子哲學中的根本行為準則,或者說是事物的生存方式。老子談論兵學也是為了要證明任何事物都要在這一根本準則下去行為。“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認為要除暴消亂,就要因物之性、順其自然,就會達到不攻自破、不戰而勝的神奇效果。王弼在《老子道德經注》中更加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為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12〕要想避免戰亂,就要順應事物的自然本性,因勢利導,“強梁”“暴亂”自會不攻自破,“不戰屈人之兵”的神奇妙用自會實現。由此看來,老子雖然談兵,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種自然的威懾力,在遵循“自然無為”的前提下,達到兵不血刃的效果,這是一種“無兵勝有兵”的自然而然的理念,也是老子不爭而勝的兵學戰略。“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八章》)老子以水喻“道”,水是最接近于其“道”的,水的特征就是柔弱不爭。在用兵方面,老子認為將帥在領兵打仗過程中,要像水一樣“不爭而善勝”,或以退為進,或以守為攻,總之不主動用兵。“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老子·六十八章》)善于領兵作戰的統帥不主動侵犯別人,后而不先,故不會被激怒,只有不爭才會戰勝敵人。“不爭”就是老子的無為之道在領兵作戰中的具體體現,主動的爭奪就是人為、妄為,與“自然無為”之道相矛盾。
在“道”的行為原則下,老子指出兵者的特征是柔弱,柔弱是“自然無為”之道的一種具體體現。他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萬物生來就是柔弱的,這是萬物自然稟賦的本性,柔弱意味著生。生死兩個極端狀態的體現就是柔弱和堅強,柔弱代表著萬物的生存狀態,而堅強則代表著萬物的死亡狀態。老子最終追求的就是以自然的方式活著,也就是說自己的生存不受外力和人為的干預。所以,老子反復強調柔弱勝剛強的道理,體現在用兵之道上:“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老子·七十六章》)萬物之中最能體現出柔弱的莫過于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老子以水為喻,點出了水就是“道”在經驗世界的最好體現。相反,兵強士勇則是至剛至強的體現,柔弱則生則壽,剛強則死則夭,“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老子·七十三章》),用兵逞強、士卒好勇,必敗無疑。
再次,“以奇用兵”并非老子兵學。學界有些學者認為老子兵學思想的一大創新是“以奇用兵”〔13〕。其實不然,老子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是持反對態度的。在國家的治理中,老子反復強調君主要始終把持“自然無為”之道,“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三章》),不要一絲一毫的人為造施。具體來看,“正”借“政”,指的是刑名政術;奇,王弼解釋為“詭異亂群”。“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意思是君主以“道”治國則國治,以刑名法術等人為的政治行為去治理國家必然導致奇兵興起,而只有“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14〕才能取得天下。所以,老子所說的“以奇用兵”的意思是非以“道”用兵,奇與“道”相反,是一種錯誤的用兵思路。
總之,老子兵學思想為道家兵學涂上了極具特色的一筆,在先秦百家論兵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老子言兵而意不在兵,在于論“道”之自然無為。
三、老子的人生追求與兵學
“道”在老子哲學中意義非凡,既是萬事萬物的本體(理),也是萬事萬物的行為準則,落實在個體生命上,就是天長地久,與天地同壽,這也是老子在現實層面上的個人追求。或者說,人按照“道”去生存的目的就是自然長壽,即不以“生生之厚”刻意追求個人生存的自然長生。
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老子認為,天地是永恒存在的。而天地之所以能永恒存在,是因為它們的一切運作、變化都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作為,正因為“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生養萬物而獨不生自己,反而得到了長生。這其實也正是“道”之自然無為的體現。所以,老子認為圣人(道家意義上符合自然無為的圣人)也應該如此,無為,不爭,不去主動追求生命的長存,這樣方可自然長生。所以,老子又說:“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老子·七十五章》)自然長生的圣人也就是“善攝生者”。
兵者與老子的長生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老子說:“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老子·五十章》)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帶來的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主動人為地去追求“生生之厚”,反而造成短壽甚至死亡的結果;反之,不主動人為地自然而然地生存,卻成就了長生。沒有兵戎相見的危害、沒有野獸的侵害、沒有兵器的傷害,自然也就實現了個體生命的長壽長久。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和兵事明顯是與老子的人生追求背離的,用兵帶來的結果恰恰是人為地去傷害個體生命,甚至導致無數生命死亡。這是老子所不能允許的,老子言“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正是要說明這一點。
結論
老子以“道”立論,構建了一個理論體系,“道”既是萬事萬物的存在依據,更是其生存的行為準則,還是其對一切事物及其行為的評判準則。符合“道”的就是合法的,凡是與“道”相違背的就應該“棄之如敝履”。作為形而上的絕對存在,無論是王侯、圣人還是民,其存在和行為的依據都應該是“道”。老子的兵學也是“道”的反面論證。在兵學思想上,一方面,人為的兵事與老子所崇尚的自然無為的“道”之間存在著巨大矛盾;另一方面,老子的終極追求是“無以生為生”的個體生命的自然長生,破壞力極大的兵事會對人的生命造成最為致命的傷害,這與老子的終極目的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兵家之事不為老子所容。《老子》一書雖然包含獨特且豐富的兵學思想,但并不能說其是兵書,從其立論宗旨來看,它還是一部哲學著作。老子論兵在意不在兵,目的是以兵為喻,就像以水為喻一樣,其意在于強調道之自然無為,這才是《老子》一書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