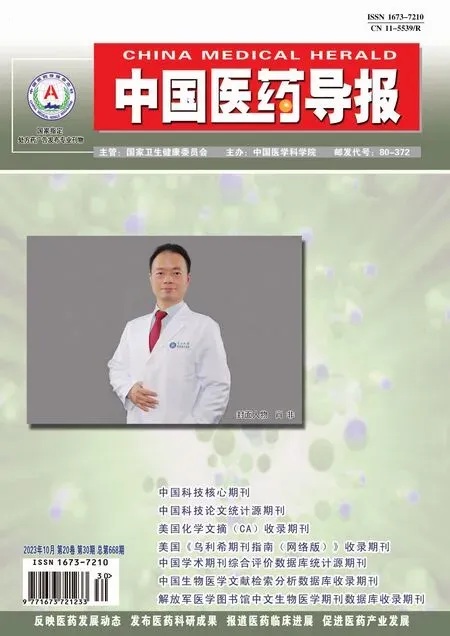曹陽教授從寒熱辨證治療惡性腫瘤相關性胃癱的臨床經驗
杜若芳 曹 陽 梁秋然 林熙明 胡凱文 衛 月
1.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北京 100029;2.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腫瘤科,北京 100078
惡性腫瘤相關性胃癱(malignancy-associated gastroparesis,MAG)是以胃排空障礙為主要征象的由非機械性梗阻因素引起的胃動力紊亂綜合征,在胃、胰腺、膽囊、食管和肺惡性腫瘤中常被報道發生。臨床表現為上腹飽脹不適、惡心、嘔吐及頑固性呃逆等癥狀,疼痛不明顯,食后吐出大量胃內容物,吐后癥狀暫時緩解[1]。西醫認為,MAG 由手術或放療后引起的迷走神經切斷綜合征所導致,治療上以對癥為主,療效不理想[2-3]。多項文獻及臨床研究表明,中醫藥可顯著改善MAG 癥狀,具有療效好、不良反應小、患者接受度高等優點[4-6]。
曹陽教授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以下簡稱“我院”)主任醫師、教授,繼承國家級名老中醫王沛教授學術思想,從醫30 余載,倡導腫瘤局部治療結合中醫全身調理的治療理念,對以內外治法治療惡性腫瘤及其術后并發癥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曹陽教授在臨床中基于寒熱辨證診治大量MAG 患者,經治療后效果滿意。
1 病因病機
中醫學中并無與MAG 相對應的病名,現代醫家根據其臨床表現,將其納入“痞滿”“嘔吐”“胃脘痛”的范疇。最新專家共識提出,MAG 的病因由腫瘤、手術、麻醉、情志等多種因素構成,病機以中焦氣機升降失常為主,兼有氣虛、氣滯、血瘀、痰凝、濕阻、癌毒,證見寒熱虛實之不同[7]。崔藝馨等[8]認為脾胃陽虛、中氣乏源、血瘀阻絡為本病根本病機。魏群等[9]認為本病總屬本虛標實,脾胃虛弱為本,血瘀、氣滯、濕阻為標,病位在胃,與脾、肝等也有緊密聯系,脾胃虛寒為其主要誘因。綜上,多數醫家將MAG 歸納為虛實夾雜,虛為脾胃虛弱,夾雜氣滯、血瘀、痰凝、濕阻等邪實,證見寒熱。
曹陽教授亦認為本病多屬本虛標實。惡性腫瘤患者常素體正氣不足,脾陽胃陰虛弱致使脾胃納運失調,局部邪實結聚。加之手術和放療等常用治療措施具有寒熱屬性,導致患者在正虛的基礎上出現體質的寒熱偏頗。因此,曹陽教授在臨證中常從寒熱角度辨治本病。
1.1 中陽不足,運化失職,寒濕內生
曹陽教授發現,MAG 寒證常見于術后的惡性腫瘤患者,多因患者素體稟賦不足或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正氣漸衰,且腫瘤生長耗傷人體陽氣,加之術中暴露沖洗導致寒邪入胃,更損其陽[10]。故而,此類患者常表現為脾胃虛寒證。MAG 寒證證似太陰病。太陰病是指外邪由表入里或寒邪直中太陰或表證失治勿治,以中陽不足,運化失職,寒濕內生,氣滯水停,升降失常為主要病機的一類病證[11]。這與MAG 寒證的成因相吻合。《傷寒論》[12]中談及:“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MAG 寒證就脾胃癥狀而言,因內外寒濕阻滯,脾胃升降失常,導致患者脘腹部脹滿明顯,畏寒喜暖,得熱則舒;寒濕困遏中焦,胃無法受納、腐熟,故飲水稍多即欲嘔吐,嘔吐物清冷,不思飲食,或伴有腹瀉。
1.2 胃陰耗傷,熱毒結聚,濕熱內盛
曹陽教授發現,MAG 熱證常發生于放療后的惡性腫瘤患者。此類患者早期多胃陰不足,失于腐熟通降,致使胃中水谷積滯,釀生濕熱,且放療毒邪侵犯陰虛體質和陽腑,易從陽化為“熱毒”,加重患者陰液耗傷、內熱熾盛的傾向[13-14]。故而此類患者以胃陰耗傷,熱毒結聚,濕熱內盛,困阻中焦為根本病機,雖有陰虛,但實熱更甚。《三因極一病證方論》[15]曰:“病者胃中夾熱,煩躁,聚結涎沫,食入即吐,名曰熱嘔。”《壽世保元》[16]曰:“有濕熱太甚,上來心下而為痞者。”嘔吐及痞滿皆有熱證,MAG 熱證的證候特點是熱嘔證和熱痞證的結合。患者胃熱熾盛則見嘔吐物酸腐;火熱之邪上炎熏蒸脾胃,致使上焦不納,中焦不化,出現食入即吐,吐多而猛;濕邪郁于中焦易阻氣機致使胸悶痞滿、腹脹納呆;熱傷津液而濕存于內,故患者口渴不欲多飲。
2 治則治法
2.1 寒者熱之,熱者寒之
經對臨床病例的隨診觀察,曹陽教授發現,多數情況下MAG 的臨床表現與寒熱本質相一致。適用于《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出的“寒者熱之,熱者寒之”的正治法。在辨證基礎上,對于寒證選擇溫補之法,對于熱證選擇清泄之法。
2.2 脾胃同治,有所偏重
曹陽教授認為MAG 的治療應遵循“脾胃同治,有所偏重”的原則。脾升胃降,居中焦斡旋氣機,生理狀態下相輔相成,病理狀態下勢必相互影響[17]。因此,MAG 疾病無論是寒證還是熱證,均為脾胃合病,治療當兼顧脾胃。《素問·太陰陽明論》提出“陽道實,陰道虛”,認為脾病多虛、寒,胃病多實、熱。故而MAG 的治療在脾胃同治的基礎上,寒證應偏重脾,熱證應偏重胃[18]。
2.3 外治為主,內治為輔
曹陽教授指出,外治法和內治法作為中醫的兩大傳統治法,均可應用于MAG 的治療。外治法是施于體表或從體外進行治療的方法,包括中藥膏摩、穴位貼敷、中藥熱庵包、艾灸、刮痧、拔罐等治療方式,具有應用范圍廣、接受度高、療效卓著、副作用少等優點,對于不肯服藥之人,不能服藥之人,不能服藥之癥,更能發揮作用。《理瀹駢文》[19]記載:“外治之理即內治之理,外治之藥亦即內治之藥,所異者法耳。”外治法同內治法一樣,講求辨證論治,其組方原則和用藥與口服劑相同[20]。內治法以中藥湯劑口服為主,由于MAG患者存在胃腸功能紊亂,且部分術后患者需禁食水并配合胃腸減壓及腸外營養治療,大量內服中藥會導致患者惡心、嘔吐、腹脹等癥狀的加重且容易引起患者心理抗拒[21]。因此,對于MAG 患者應以外治為主,在能進食后遵循“少量、漸進”的原則輔以中藥口服內治。
3 治療經驗
3.1 用藥經驗
曹陽教授指出,MAG 寒證治當溫中燥濕,行氣除滿。干姜大熱無毒,守而不走,為溫中散寒,健脾止嘔之要藥;厚樸既可除無形之濕滿,又可消有形之實滿,為消除脹滿之要藥。選用干姜、厚樸二藥為君,溫中與行氣并重,化濕與健脾并行[22]。在此基礎上,多配伍性偏辛溫且入脾胃經的藥物,如肉桂、丁香、木香、枳殼、砂仁等。肉桂可治一切里虛陰寒、寒邪克里之為病,對于脾胃虛寒導致的脘腹冷痛、嘔吐泄瀉功效明顯;丁香可溫脾胃而行氣滯,尤善降逆,用治嘔吐;木香為溫散之藥,《本草求真》[23]記載:“木香……為三焦氣分要藥,然三焦則又以中為要,故凡脾胃虛寒凝滯而見吐瀉停食……服此辛香味苦,則能下氣而寬中矣。”枳殼既能破氣除痞,又可消積導滯,長于治療脘腹脹滿疼痛;砂仁乃醒脾調胃要藥,重在溫脾。全方外用時常加小劑量全蝎以發揮其走竄作用,促使藥物內通臟腑、外透經絡。
曹陽教授指出,MAG 熱證治當清熱利濕,行氣導滯。用藥在寒證用藥的基礎上,去干姜、肉桂等溫中藥物,保留其余藥物的行氣功效,并加用連翹、黃連、大黃、薄荷、冰片等辛涼清熱藥物。連翹、薄荷輕清涼散,解熱于上,用治上焦不納;黃連有清化中焦脾胃濕熱之功,用治中焦不化;冰片辛苦微寒,《新修本草》[24]中記載:“主心腹邪氣,風濕積聚。”善下脾胃惡氣,消食散脹滿;大黃瀉火通便,滌蕩中焦燥熱內結。全方外用時亦需配伍小劑量全蝎引藥入里。
3.2 治療方式
曹陽教授以中藥膏摩作為MAG 的主要治療方式。膏摩屬于外治法之一,膏即膏劑,是由各種藥物混合熬制而成的推拿介質,摩指的是推拿按摩手法[25]。推拿按摩本身具有補虛泄實、疏通經絡、順行氣血的作用,有助于胃腸功能的恢復,與中藥合用,可以促進藥物的吸收和藥力的運行,發揮藥物的治療作用。曹陽教授對于膏摩用藥的選擇是在寒熱辨證的基礎上,參照上述用藥經驗得出。操作方法為將藥物打粉后或以顆粒制成膏劑,每日施術時將膏劑加熱后厚涂脘腹部,順時針按摩并點按中脘、天樞等脾胃病要穴。
在臨床診治中,對于MAG 癥狀較重的患者,曹陽教授往往在中藥膏摩的基礎上,加用穴位貼敷并聯合其他具有散寒或泄熱功效的外治治療手段,以達到增強療效、推進改善進程的目的。在治療MAG 寒證時可配合應用中藥熱庵包、艾灸、溫針灸等治療方法。中藥熱庵包常選用吳茱萸、小茴香、干姜3 種具有散寒止痛、溫胃止嘔功效的藥物;艾灸沿脾經循行處進行,并配合內關穴、豐隆穴、公孫穴等穴位施溫針以化濕散寒、溫胃止嘔。MAG 熱證的治療可配合應用拔罐、刮痧、針刺放血等方法。拔罐法選取背部膀胱經逆經走罐并配合大椎穴刺絡拔罐以泄熱祛濕。刮痧療法選取脾經、胃經健脾和胃,肝經治肝實脾,大小腸經通腑泄熱。合谷、金津、玉液的點刺出血及大腸井穴商陽、胃滎穴內庭的點刺放血對于緩解熱嘔療效明確,對于嘔吐癥狀明顯的患者可酌情加用。胃癱恢復后期患者能經口進食后,可參照上述用藥經驗,配合予以中藥濃煎劑每次10~20 ml,2 次/d,少量口服。
4 病案舉隅
患者,男,65 歲,2020 年12 月11 日主因“膽管癌術后1 月余,間斷腹脹惡心20 余天”于我院腫瘤科就診。患者2020 年11 月7 日因梗阻性黃疸于外院行胰十二指腸根治性手術,術后病理示:膽管中低分化腺癌,術中空腸造瘺留置空腸營養管。術后第5 日夾閉胃管,逐漸減量腸外營養,開始腸內營養,患者未訴特殊不適。術后第8 日起停止胃腸減壓及腸內營養改予流食后患者出現腹脹、惡心,嘔吐大量胃內容物,予再次留置胃腸減壓,每日平均引流胃內容物1 200 ml,此后患者間斷腹脹、惡心,無法進食,術后第11 日查上消化道造影、立位腹平片除外消化系統梗阻,明確診斷為胃癱,予持續胃腸減壓、營養支持、促胃動力治療20 余日后仍未見好轉。現癥見:腹脹明顯,時有惡心,無嘔吐,有排氣,畏寒喜熱,尤以腹部為甚,全身乏力,四肢不溫,大便溏泄,舌淡胖,苔白,脈沉弦。西醫診斷:膽管中低分化腺癌,胰十二指腸根治性手術后,胃癱。中醫診斷為痞滿,脾胃虛寒、氣滯濕阻證。治療方案:(1)西醫治療:予持續胃腸減壓,不足量營養支持治療。(2)中醫治療:①中藥膏摩治療。干姜15 g、厚樸20 g、肉桂15 g、丁香20 g、木香20 g、枳殼20 g、砂仁6 g、全蝎6 g,共4 劑。將中藥顆粒制成膏劑,每日施術時將膏劑加熱后厚涂脘腹部,順時針按摩并點按中脘、天樞穴,上述操作每組3 min 左右,重復3 組,1次/d。②穴位貼敷:予膏摩方藥劑量減半后共4 劑,由蜂蜜調成糊狀,制成敷貼,于中脘穴、神闕穴貼敷,每次4~6 h,1 次/d。(3)中醫調攝:調暢情志,適量活動。
2020 年12 月15 日二診:引流胃液減少至550 ml,腹脹、乏力、畏寒怕冷減輕,大便溏。舌淡胖,苔白,脈沉弦。西醫治療調整為間斷胃腸減壓,暫不予進食,中醫治療方案同前,繼予膏摩、穴位貼敷各3 劑。
2020 年12 月18 日三診:引流胃液減少至300 ml,乏力、腹脹減輕,大便成形。舌淡胖,苔白,脈沉弦。予腸外營養持續減量,持續夾閉胃管,嘗試進食米湯,增加運動時間。中醫治療方案繼予膏摩、穴位貼敷各3劑,用法同上,并加用膏摩組方去全蝎減半劑量濃煎劑20 ml 口服,2 次/d,共3 劑。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2020 年12 月21 日四診:患者自訴未引流胃液,無腹脹,無惡心、嘔吐,可進食溫熱半流食。舌淡,苔薄白,脈沉弦。予拔除胃管,停止靜脈營養支持,進食軟食,少食多餐,中醫治療方案在膏摩原方基礎上調整組方中厚樸至15 g、枳殼至10 g、砂仁至10 g,穴位貼敷及中藥濃煎劑隨之調整,各7 劑。7 日后隨訪,患者病情未見反復,進食量逐漸恢復,生活質量顯著改善。按語:患者老年男性,臟腑功能減退,陽氣漸衰,加之手術傷陽,釀成脾胃陽虛內寒之證。中陽不足、寒濕內生阻塞中焦氣機,影響脾胃運化功能,治療當以“溫通”為主,治以溫中燥濕,行氣除滿。患者就診時不能進食伴持續胃液引流,胃癱情況相對較重,故以西醫治療進行生命支持,以中醫治療改善病情。選擇外治法為主要治法,中藥膏摩為主要方式,配合穴位貼敷增強療效。組方以干姜、厚樸為君,治以溫中行氣,降逆止嘔;肉桂、丁香、木香、枳殼為臣,其中肉桂補火助陽,助干姜溫脾暖胃,散寒祛濕,丁香、木香、枳殼行氣寬中,助厚樸消脹除滿,通利氣機;佐以砂仁醒脾開胃,增進食欲;全蝎為使,引領諸藥直達病所。膏摩操作手法為順時針掌摩全腹,順行中焦氣機,配合中脘點按健脾和胃,天樞點按理氣止痛[26]。二診時患者胃液引流減少,腹脹減輕,治療有效,故將胃腸減壓調整為間斷性,持續同前治療方案鞏固療效。三診時患者引流胃液持續減少伴隨腹脹好轉,故減量腸外營養以增強患者“饑餓感”,促進胃腸活動,嘗試逐步進食過渡,此時予少量中藥濃煎劑口服,從內健運脾胃,與外治法相互配合。四診時患者完全恢復自主進食,無腹脹及惡心、嘔吐癥狀,可適當減少厚樸、枳殼等行氣除脹藥物的用量,并增加砂仁用量增進食欲,再行7 日鞏固治療后隨訪,可見患者病情好轉,未見反復,治療有效。
5 小結
曹陽教授認為,惡性腫瘤患者正氣不足,脾陽胃陰虛弱,加之手術、放療等常規治療變生寒熱,導致患者寒熱癥狀表現明顯,故而當從寒熱辨證論治,寒證治以溫中燥濕,行氣除滿,熱證治以清熱利濕,行氣導滯。兩證用藥時各取溫中及清熱藥,并兼顧化濕行氣。在治療中以外治法中的中藥膏摩為主要治療方式,同時根據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病勢走向和治療接受度酌情配合其他外治治療,在恢復經口進食后可加用中藥濃煎劑內服。曹陽教授指出,MAG 治療起始變化較快,應密切隨診調整治療方案,及至患者病情穩定后再延長就診時間。該辨治方法在臨床中展現出了簡便驗廉、劑型豐富、內外兼治的優點,具有臨床應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