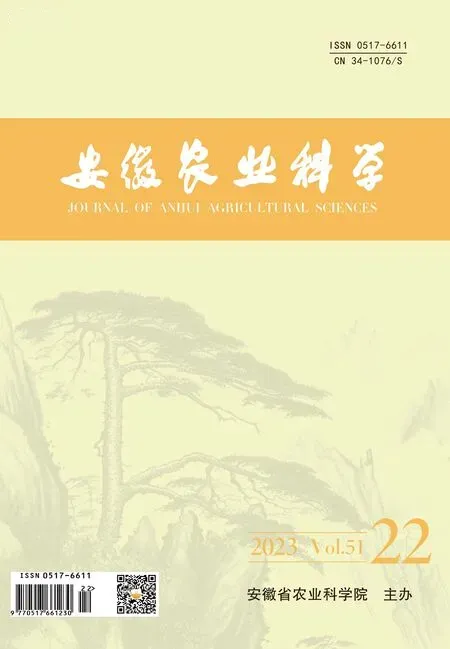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路徑分析
楊 煌,李雙元
(青海大學財經學院,青海西寧 810000)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命題后,相關學術研究與討論蓬勃興起。羅必良[1]認為小農不可能消失,并且小農能夠實現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另外,從現實來看,我國農業現代化歷史發展脈絡中,小農戶與現代農業之間的關系也是由互斥向互構方向演變[2],兩者逐步成為互為表里的有機統一體,而在國際上也不乏將兩者進行有機銜接的成功案例[3]。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應如何實現有機銜接是一個更為復雜和系統性的問題,該研究試圖以農業產業化過程中不同主體為視角梳理出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不同看法,并分析各主體在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過程中的特點。
1 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路徑
經過文獻梳理發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大致有兩條路徑,一是內涵發展的方式,即鼓勵小農戶精細化、集約化生產,激發其內在發展動力,不斷提高其自身對接市場,抵御風險的能力,從而實現現代化;二是外延發展的方式,即依靠其他經營主體和不同生產組織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難的問題[4]。依照此分類,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路徑分為內源式發展和外延式發展兩大類。
1.1 內源式發展不少學者高度重視以小農為基礎的現代農業發展理論[5-8],這些觀點都認為小農戶為主體的現代農業生產與現代農業帶動小農戶所進行的生產并無優劣之分,其一,前者的發展模式能以較低的成本把農民組織起來,并利用熟人社會的特質,實現外部風險內部化;其二,雖然后者更有利于農產品標準化和規模化的供給,但前者能夠基于小農戶與自然更為緊密的動態聯系以及其豐富的社會關系網絡更好地促進農產品差異化和特色化的供給,使得小農戶在生產技術提高、與市場聯系加強的同時保持多元的種植和養殖模式;其三,前者的發展模式能夠有效規避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小農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諸如“精英俘獲”“空殼社”等風險[2-9]。這樣的研究視角始終賦予小農戶在中國現代農業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其銜接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小農戶在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走向現代化,另一方面,打破了之前研究所認為的小農戶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弱勢和被動地位,也不再拘泥于討論何種新型經營主體更為有效,轉而關注小農戶發展的內生動力。
1.2 外延式發展學者們從農業企業[10-12]、村集體[13-15]、合作社[16-18]、鄉村經紀人[19-21]以及其他提供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主體[22-23]等角度闡述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外延式發展路徑。學界對于這些模式的作用研究已十分豐富,涉及經濟功能,如降低交易費用、優化小農戶生產經營服務、幫助農戶持續增收并保護小農戶利益、合理利益分配,以及社會功能,如增進民主與提升信任水平、提升農戶社會資本水平,這些都對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具有重大意義。
2 當前研究的不足
總體上看,近年來學界對于“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關于有機銜接的路徑,也有不少學者從銜接主體的視角出發展開了討論,其中包含的主體有小農戶、農業企業、村集體、合作社、鄉村經紀人以及其他提供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主體。通過梳理,各個主體各有優劣,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應該深入考察鄉村社會內部,充分考慮各地區的異質性,靈活運用,達到優勢互補。當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
2.1 不同經營主體發揮作用的界限劃定不夠清晰準確針對小農戶不斷分化以及不同鄉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性較大的情況應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內源式的發展路徑適用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農村地區,而對于欠發達地區,僅依靠小農戶個體從而實現短期的跨越式發展是不現實的[24],借助外部力量的扶持來實現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將更具可行性。
2.2 對鄉村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認識不夠深刻當前理論研究存在與實踐有機結合不足的問題。學界關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主體研究和路徑研究已十分豐富,學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仍然存在交易費用過大、合同契約不穩定以及外來資本融入鄉村社會困難等問題。究其根本,是沒有充分認識到中國鄉村傳統文化和社會關系對經濟行為的深刻影響。要深刻認識到,農業現代化并非簡單依靠購入機械、升級設備就能實現,而是需要深入面對整個中國鄉村社會,充分尊重并考慮村莊的社會結構和農民的觀念心態等非正式制度因素才能夠實現[25]。
費孝通[26]指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其組織形式是通過親疏有別的差序格局形成的。在熟人社會中,社會關系被像水波一樣一圈圈推出去的聯系區分成了家人、熟人和陌生人[27],并形成“內核-外圍”結構[28]。這樣的社會,其顯著特征是輿論壓人、面子有價、近乎人情、內外有別、鄉土情重、不搞特殊化等,人們所擁有的“關系”就是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各主體之間的交易往往不是短期的一次博弈,信任關系和信譽機制至關重要[29]。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強,鄉村社會也發生著變遷[30],學者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半熟人社會”[31]、“無主體熟人社會”[32]等概念,這樣的變遷究竟只是“量變”還是已經達到“質變”的程度?目前學界尚存爭議[33],但是筆者認為,目前中國的鄉村社會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熟人社會”相關機制所影響。
第一,“內外有別”的歧視原則。這從徐宗陽[25]描述的一個關于農業機械化的失敗案例中可以獲得證據,文中所寫的本地機手對于外來資本的種種邏輯行為充分體現了這一原則。周娟[34]也描述了農業企業剛剛進駐村莊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存在破壞大棚、偷盜電纜、強制收取“過路費”等現象。這2個例子都描繪了鄉村社會的內部小農戶所奉行的“內外有別”原則,即對內講究情面,凡事以和為貴,對外則奉行另一套邏輯,漠視陌生人利益,甚至用暴力或暴力威脅作為交涉手段,這也為外來資本的嵌入甚至扎根增加了難度。
第二,特殊的“公正觀”。賀雪峰[35]提出了小農戶群體里所存在的一種特殊的“公正觀”,即不在乎自己得到或失去多少,但絕不能讓其他人“搭便車”的非理性觀念。這樣非理性的觀念及行為往往導致集體行動的失敗,從而對原本就很脆弱的農業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這樣的“集體失敗”原本可以利用傳統社會中的宗族勢力通過傳統文化、禮俗約束等加以避免,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諸如地方宗族、鄉紳等的傳統力量已十分微小,因此這樣的失敗在鄉村社會中時有發生。
第三,厚重的鄉土情結。羅必良[36]根據稟賦效應提出,土地產權對于小農戶來說是一種人格化的財產,小農戶賦予自己的土地一種情感價值,這種“情感價值”使其總認為自己的土地比別人土地的價值更高,從而在產權交易過程中造成了高額的交易費用,這也是導致土地確權改革下小農戶土地流轉行為達不到預期政策目的的關鍵原因。同樣的,晉洪濤等[37]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了農戶有償退出宅基地積極性不高的問題,這源于小農戶特殊的“家”和“面子”觀念。其一,小農戶有著濃厚的鄉土情結以及“落葉歸根”的思想;其二,為了自己的“面子”,小農戶在熟人圈子里過度“婚備競賽”后導致的財富流失引發了他們對老年居所的擔憂,這進一步削弱了其退出宅基地的意愿。
面對中國鄉村“熟人社會”相關機制的影響,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可從以下兩方面著手:①針對外來資本,要積極適應鄉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推動陌生關系熟悉化;②針對原有鄉村社會,應重塑鄉村“熟人社會”,培育有序、理性、法制精神[33]。就前者而言,劉少杰[38]提出了交易市場中的陌生關系熟悉化,具體而言,是需要建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熟悉關系并產生信任關系,其能夠有效降低交易中的不確定性、風險性和交易成本,借助權威的熟人社會治理機制也將更有利于合同的簽訂與履行[39],這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孕育的思維方式,這樣類似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威廉姆森的關系合同理論,其同樣認為非正式制度有利于降低機會主義從而降低交易成本。當然,要實現外來資本的陌生關系熟悉化,就需要依靠其他諸如村集體、鄉村經紀人、產地中間商[40]等已扎根于鄉村社會的主體,并與之構建穩定長效的利益聯結機制,這將大大降低其“關系嵌入”的成本。就后者而言,加強鄉村地區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普及教育,加強培訓是關鍵舉措。特別是加強農戶農技方面的培訓至關重要,在這之中,選擇合適的培訓主體又是重中之重,要多主體取長補短,切不可流于形式,也不可僅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不注重鄉村社會五位一體,綜合發展。
3 研究展望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文化多元,各地區鄉村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較強。因此對“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一問題的探討需深入鄉村內部,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另外,費孝通關于鄉土社會的論述,其重要啟示在于,要想研究好中國農村問題,必須充分考慮不同的文化背景,必須著眼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當地的社會結構。在村莊社會,市場行為絕非簡單的“買”與“賣”的交易關系,而是卷入了更復雜的社會關系,這就使得在鄉村社會,大量的交易行為是一種感性而非理性的選擇[41]。僅從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的角度分析“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問題,將導致種種謬誤。
未來的研究還應重視社會資本在鄉村社會的運作機制,社會資本是一種與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相區別的社會資源,其中包含了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社會規范等核心內容[42],其存在可以為社會組織或個人帶來便利或經濟效益,因此,其在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