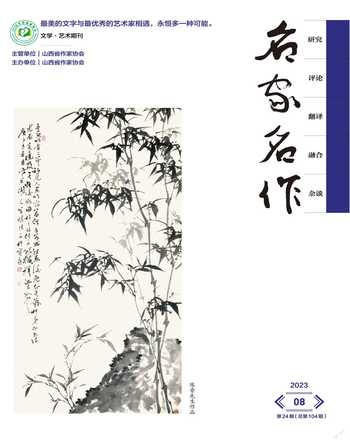人類表演學視閾下傳統藝術的角色表演研究
[摘要] 在約定俗成的認知中,“角色”常作為某一民間藝術的小戲、小場,或者秧歌隊中固定的人物,在民俗表演中起到維持表演順利進行、符號象征等作用。這里的“角色”被限定在傳統意義的表演場域中,可以被視為具有審美意義的角色表演。在人類表演學家的視角中,“表演”不僅限于傳統舞臺和鏡頭下的產物,而是用這種傳統“表演”的意義重新審視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習慣。由此,延伸至對表演活動中“角色”身份的反思,以海陽秧歌為例,試圖重新探討在民俗藝術發展過程中發揮效用的“角色”相關問題,既包括傳統意義的角色表演,也包括社會表演中的角色研究,旨在為傳統藝術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民俗性認識。
[關? 鍵? 詞] 傳統藝術;角色表演;海陽秧歌
在約定俗成的認知中,“角色”常作為某一民間藝術的小戲、小場,或者秧歌隊中固定的人物,在民俗表演起到維持表演順利進行、符號象征等作用,常常是由當地的民間藝人進行角色扮演。扮演人物時雖然具體的人物身份與表演內容是固定的,但會根據不同藝人的個性與表演能力,在共同的表演規約上體現不同的特色。由此不難發現,這里的“角色”主要是被限定在傳統意義的表演場域中,其可以被視為是具有審美意義的角色表演。換句話說,在這種表演活動中,其有著明確的表演者與觀眾,在觀與演的互動中實現表演活動的展示,從而在加深集體共同文化意識的同時,強化文化功能在族群內部的社會功用,加強人與人的聯系與融通,促進民俗文化、藝術的傳承。但除了這些在民俗藝術中發揮直接作用的表演者,還有一些發揮“隱性作用”的表演群體同樣在表演活動中扮演角色、發揮效用——而這也正是人類表演學研究的重點所在。在人類表演學家的視角中,首先對“表演”的界定進行再思考—— “表演”不僅限于傳統舞臺和鏡頭下的產物,而是用這種傳統“表演”的意義重新審視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習慣。由此,筆者延伸至對表演活動中“角色”身份的反思,以海陽秧歌為例,試圖重新探討在民俗藝術發展過程中發揮效用的“角色”相關問題,既包括傳統意義的角色表演,也包括社會表演中的角色研究,旨在為傳統藝術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民俗性認識。
一、人類表演學與角色表演
“傳統的戲劇研究一般只研究審美的藝術表演,人類表演學并不反對舞蹈音樂戲劇,只是將這種研究擴大到另外的四大類。”人類表演學家理查德·謝克納將表演的行為概括為五大門類,即審美表演、社會表演、大眾表演、儀式表演和游戲表演[1]。其中,審美表演主要是指傳統意義中的藝術表演,其有著明確的觀演身份,在演出期間建立觀演關系,并直接獲得審美體驗,其具體可分為傳統的、經典的、現代的、后現代的。而海陽秧歌在審美表演中則可以被劃分至傳統的范疇中。在謝克納的解釋中,社會表演是指日常生活的表演。在社會表演中,要求根據自身的角色設計相應的行為,從而實現表演的展示。海陽秧歌除了在秧歌隊的表演中有人物角色的扮演,還包括其他群體的角色表演以維持海陽秧歌儀式表演的穩定秩序。換句話說,在傳統的觀念認知中,“表演”常被約定俗成為傳統的“劇場”表演,但是人類表演學的學者并不局限于傳統舞臺場域中的藝術審美表演,而是擴大了“表演”的內涵,主張“一切人類活動都可以當作表演來研究”。在這個視角下,延伸至海陽秧歌中“角色”的探討,并非僅限于對具體的人物角色,即王大娘、箍漏匠、丑婆、傻小子、翠花、貨郎、花鼓、小嫚等角色的表演行為的分析,而是基于社會中的表演,同樣也是一種角色扮演。下面圍繞海陽秧歌,分別對傳統意義中的角色表演與社會表演中的角色表演進行闡釋與分析。
二、傳統意義中的角色表演
傳統意義中的角色表演,指的是秧歌隊的表演。以海陽秧歌為例,主要有王大娘、箍漏匠、丑婆、傻小子、翠花、貨郎、花鼓、小嫚、樂大夫等角色。其表演方式一方面是通過兩人為對的方式,確認人物關系與身份的同時,完成秧歌表演的敘事表達。比如在丑婆與傻小子為對進行表演時,由于二者是母子關系,因此其表演關系常表現以丑婆為主導,從而體現以母為尊的孝道思想。另一方面是通過單獨出現或者集體表演的方式,如王大娘與箍漏匠是夫妻的關系,因此其表演方式深受封建時期男女地位的影響,表現為男角主導、女角配合。在表演時,箍漏匠以扇頭作為指引,指明行動的方向,王大娘與之配合,在你進我推、你去我追、你引我攔中表現質樸的愛情故事。單獨出現角色的典型代表就是樂大父,其在秧歌隊的表演中起到統領、指揮的作用,因此常常由德高望重、技藝超群的人來擔任。而小嫚、花鼓則是以集體表演的方式出現的角色代表。不僅如此,海陽秧歌在民間還是一種儀式性的行為。“儀式通常被界定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溝通(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過渡(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性的)、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2]其一方面表現為秧歌隊的表演具有嚴格的程序,即拜進、串街、走大陣、耍小場、跑陣式、演場、拜出,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因此,具體秧歌的小場表演實際僅是整個秧歌隊表演的一部分,而其他的程序同樣是角色表演的環節之一。其顯著的區別表現在是否以傳統意義中的秧歌表演為標志。換句話說,角色在進行拜進、串街等行為時,同樣被視為角色的表演,因為其具有“展示”的意義。而這也應合了人類表演學對于表演的界定,即“有意識地展示自己的行為,那就是表演”[3]。另一方面,儀式性還表現為海陽秧歌表演一整套的行為方式。在海陽秧歌中,秧歌隊的表演僅是秧歌儀式表演的一部分。按照老祖宗的規矩,每一年的第一場秧歌必須是祭祀祖先,俗稱“悅廟”。再拜村里德高望重、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從大年初三開始,各村的秧歌隊相互走街串巷,互拜新年,寓意吉祥。鬧至正月十一,秧歌活動推向高潮,人們濟濟一堂,共同觀演秧歌,感受秧歌帶來的喜慶氛圍。正月十五,秧歌隊緊隨“燈官”走燈陣、鬧元宵,熱鬧非凡。就此意義而言,在整套表演中通過“有意識的行為”發揮效用的角色都具有表演的意義,即便其并非以傳統秧歌隊的表演進行展示。如樂大夫、貨郎、箍漏匠等角色在進入家廟時,所做的一切相關的祭拜動作,其寄托著人們莊重而嚴整的集體信念與意識,確認角色社會身份的同時,在不斷的重復中強調了角色的象征意義。因此,其祭拜行為同樣也是角色表演的行為。
三、社會表演中的角色表演
在人類表演學的觀點中,“這些社會表演要求每個人要根據自己的社會角色,設計自己的形象、服裝,規定的行為方式”[1]。人們分化為不同的小團體,各司其職,在社會的場域中進行角色的表演。換句話說,在海陽秧歌的生活圈中,除了在海陽秧歌的儀式表演中直接發揮效用的角色之外,還有一些發揮“隱性作用”的表演群體同樣在表演活動中扮演角色并發揮效用,其主要分為四種類型的團體。
首先是政府扮演“統籌”的角色,起到主導、指引的作用。在海陽秧歌的儀式表演中,常常由政府進行通盤籌劃,在全局的視野下進行方向上的指引與規劃,從而發揮“統籌”的作用,而政府的相關部門積極響應政策,并付諸實施。20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民間表演更多的是將以上層建筑為基礎的社會意識形態作為藝術表現的核心。因此,該階段海陽秧歌的表演受到了國家意志敘事表達的影響。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中國大地,國家經濟制度由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革推動著社會觀念變化的同時,也使歸屬于小傳統的民俗藝術有了新的生存空間。最直接的體現就是1981年決定編輯、出版《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系列叢書,并成立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編輯部,動員藝術工作者下田野向民間傳統藝術學習,進行資料的收集、整理、歸納。除此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相關政策的出臺也推動了傳統民間藝術的發展與衍傳。而海陽秧歌更是乘上了第一波東風,于2006年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契機下,當地的相關部門諸如文化館、非遺中心等在政府的統籌規劃下,積極響應并付諸行動。比如非遺中心舉辦了一些非遺活動的演出,并推出了一些獎勵政策,幫助海陽秧歌保存生命力的同時保障了藝人的生活。
其次是“二老藝人”扮演“紐帶”的角色,起到中介、執行的作用。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里面,特別是明清時期,社會大體由官吏、鄉紳和鄉民這三個自上而下的社會階層所構成[4]。換句話說,鄉紳階層在社會關系圈層中發揮著紐帶的作用,連接著官吏與鄉民兩個階層。其不僅表現為對官方話語的解釋與說明,同時更是在其中協調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地域內部的團結與文化認同,增強族群的集體意識。后隨著社會的變革,鄉紳階層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在當地依舊有一批人具有話語權威,在村子與外部之間扮演“紐帶”的角色,起到中介的作用。這一批人就是“二老藝人”。所謂“二老藝人”,主要是指不同時期各地方的舞蹈工作者。“在新中國文藝發展方針的指導下,對于當地民間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調查、學習、挖掘、整理,并運用到舞蹈藝術的表演與創作中。”[5]在海陽秧歌中,以張蔭松為代表的“二老藝人”對于其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為其不僅深受當地文化的浸潤,還緊隨我國相關文藝政策的指導,一方面對內深入挖掘、保護、學習;另一方面對外積極發揮其自身的中介作用,將長期收集的資料出版發行、整理為教材等,增強了海陽秧歌的文化影響力。
再次是民間藝人扮演“演員”的角色,起到表演、塑造人物的作用。演員指的是某個角色的扮演者,通過對話、唱詞、肢體動作塑造角色,展露人物的性格與內心情感。在海陽秧歌中,主要由知名的民間藝人扮演角色。所謂“民間藝人”,是指特殊舞蹈技藝的民間舞者。他們生長在遠離城市的鄉村,其所在的宏觀身份群體在當地統稱為“農民”。他們的技藝源于從父輩那里傳承而來的自由養成的身體記憶,是一種有在場共鳴的集體性的技術系統,有著鮮明的地方性身體知識特點,最終融化為個性表達[6]。海陽秧歌的角色眾多,如充當指揮的樂大夫;集體表演的花鼓小嫚;雙人對舞的貨郎、翠花,箍漏匠、王大娘,丑婆、傻小子等。其中又以民間藝人顏明玉扮演的箍漏匠、王玉里扮演的扇女、王發扮演的王大娘等最有特色。誠然,這里所闡述的民間藝人角色扮演實際上囊括了傳統意義上秧歌隊進行的角色表演。這也說明了社會表演與傳統表演之間沒有實然的界限,而應當持有闕限的視角、相對論的觀點思考問題。
最后是觀眾扮演“審美接受”的角色,起到接受、反饋、共情的作用。在民間海陽秧歌的儀式展演中,由當地的民眾擔任觀眾的角色,其不僅是審美主體,同時更是在審美的過程中重溫文化記憶,通過在場的反饋與演員的表演形成交流的循環,從而強化當地民眾的文化認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集體記憶與地域聯系。總而言之,海陽秧歌作為一場社會表演,不同的群體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對其傳承與發展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角色扮演的背后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相互關聯中此消彼長、相互影響。
四、結語
在人類表演學的理論視角下,筆者對傳統民間藝術海陽秧歌中的角色表演進行了再思考,重新思考了“角色”以及“表演”的內涵。不僅將角色定位在秧歌隊的表演中,更是延伸至整個秧歌儀式的行為中,將秧歌儀式置于社會表演的視閾下,對其“隱性”的角色表演進行功能的分析與闡釋。由此不難發現,在海陽秧歌的發展與衍傳的過程中,并非某一群體單獨的功用,而是在不同群體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穩定的關系網絡,才使民間藝術得以源遠流長。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對于傳統民間藝術的保護與傳承而言,需要多方合作,共建保護網,各司其職,扮演各自的角色,履行相應的職能。而在履行其職能之前,需要不斷強化民族集體意識,唯有如此,才能使傳統民間藝術更加生機勃勃。
參考文獻:
[1]理查德·謝克納.人類表演學的現狀、歷史與未來[J].孫惠柱,譯.戲劇藝術,2005(5):4-9.
[2]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
[3]理查德·謝克納.什么是人類表演學?(上)[J].俞茜,譯.中國戲劇,2008(8):62-64.
[4]徐祖瀾.鄉紳之治與國家權力:以明清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為背景[J].法學家,2010(6):111
[5]李卿.論“二老藝人”在鼓子秧歌發展中的價值與意義[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8(4):85-90.
[6]劉建.中國民間舞的本質與價值認知[J].民間文化論壇,2014(6):82-90.
作者簡介:
張舒祺(1999—),女,漢族,湖南衡陽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