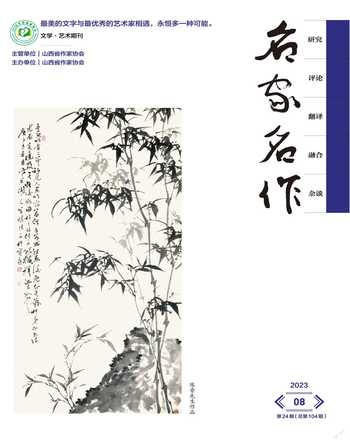《海的盡頭是草原》的影像敘事分析
[摘要] 爾冬升執導的影片《海的盡頭是草原》,以在內蒙古發生的“三千孤兒”的真實歷史為背景,講述了一段動人的愛情和拯救故事。這部影片從細節中看到了真實,從溫馨中看到了歷史,從一個小小的家庭的背后看到了一個國家偉大的愛。這部影片對于現實主題的選擇,最初更多地是出于一種吸引人的質樸與描摹之美,通過鏡頭與觀眾達成一種高度共鳴,從而達到審美的目標。它給中國電影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對民族電影的創新和發展、民族團結的可貴精神,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 鍵? 詞] 影像敘事;紀錄片;攝影語言;《海的盡頭是草原》
《海的盡頭是草原》是一部全新的電影,于2022年9月公映,是一部以“三千孤兒入內蒙”為題材的電影,講述了一段動人的愛與拯救的故事。導演爾冬升用影像敘事的方式,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了“國家的孩子”杜思珩在內蒙古的動人事跡,并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贊賞了一種跨越時空、跨越山海、跨越民族的大愛之情。
影像敘事場是由影像技術層、影像表意層、影像敘事層等多個層面共同構建完成的。其中,影像敘事層是影像邏輯和結構的重要部分,也是容易吸引大眾關注的部分,影像的敘事層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它可以將觀眾牢牢地鎖閉在故事之中,從而完成對觀眾的占有。[1]本文擬從電影的敘述風格、敘述題材、敘述手法、敘述表現四個角度來詳細地剖析這部電影。
一、影像的敘述方式:紀實美學風格
《海的盡頭是草原》是一部具有鮮明歷史色彩的電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這部電影描寫了上海與內蒙古兩個家庭的悲喜,透過上海老人不平凡的尋找親人的旅程,細致地重現了杜思珩作為“國家的孩子”,在內蒙古生活中所經歷的動人故事。它肩負著兩大使命:一是把觀眾帶入歷史,帶入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創造一種真實的歷史感;二是把歷史放進當代的文化背景中,去發現它對當代人的影響,去發現它所描述的時間在被描述的時間里所具有的特殊價值和啟示。所以,對于歷史影像的敘述,導演尤其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題材的真實,二是風格的真實。
爾冬升的電影一直以對現實的觀察和對人性的細致關注而聞名于世。該片采用客觀寫實的拍攝方法,以電影的形式來講述歷史,既從整體方面,也從細節方面,把歷史還原出來。
紀實風格的電影大多是從客觀現實入手來真實反映社會問題的。由于導演有發現問題、反映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魄力,并賦予現實故事以哲理性,所以,紀實影片更像是生活的“苦咖啡”。[2]這部電影就是基于一段令人心酸的真實歷史,即“三千孤兒入內蒙”。20世紀60年代初期,一場天災橫掃了整個中國,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在上海、浙江、江蘇這些地方,孤兒院的孤兒人數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增長。他們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偷偷帶到了孤兒院,為的就是“尋找一條生路”。但是,由于當時的社會情況并不樂觀,孤兒院收留了很多兒童,這些兒童不但吃喝成問題,就連疾病也都是依靠自身抵抗力才能抵御,在這困難之際,內蒙古自治區對他們伸出了援助之手。最后,這些兒童被合格的牧戶領養。《海的盡頭是草原》這部電影的編劇,就是將這些真人真事凝聚在一起,與觀眾形成一種共鳴。
爾冬升為了還原這段歷史,再次前往內蒙古,拜訪了許多當時事件的親歷者,聆聽他們的故事。盡管60多年過去了,原型人物對兒時的細節都只剩下了一些零碎的記憶,但他們的情緒沖擊還很強烈,很容易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
在拍攝的過程中,劇組一直都是“求真”的,對真實的畫面有很高的要求,對真實的畫面有很高的要求,也有很強的紀實感。上海在20世紀60年代恢復起來并不困難,但要拍攝到真實的草地就很困難了。這部電影將牛、羊、馬、駱駝,甚至是真正的狼都融合在一起,在這片廣袤的大草原上,讓年輕的漢族演員在真正的草原美景中學習騎馬,與動物共處,努力將草原人對民族的熱愛和仁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影像敘事主題:成長主題與民族團結的雙重母題
在影片《海的盡頭是草原》中,“海”是上海,“草原”是內蒙古。三千名“孤兒”來到了草原,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環境,一個新的家庭,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們在他鄉的時候,很難適應新的生活,但好在草原上的人們從來沒有拋棄過他們,他們的痛苦都在一種感人的愛中得到了緩解。這樣,影片就形成了“成長”和“民族團結”兩大敘事主題。
電影是隨著杜思珩的長大而慢慢展開的。小時候,杜思珩是個固執的小姑娘,由于不適應大草原的生活,常常會做出一些任性的行為,但是薩仁娜、額吉一家都默默地容忍著她。杜思珩害怕去大草原,薩仁娜與那木汗就專門給她搭建了一間茅房;由于丟失了生母送給她的小浴巾而產生了矛盾,那木汗與同伴們就在廣袤的大草原上尋找杜思珩的浴巾……畫面記錄了杜思珩的成長過程,同時也將她的叛逆表現出來,最終讓她徹底融入了這片大草原。
這是一部用愛抗災、用愛熬過饑餓、用愛解開心結的電影,它是一部從“海”到“草原”的電影,從廣闊到廣闊的電影,正如電影所歌頌的家國情懷、民族團結、大愛無邊無際,完美地詮釋了一種生命的延續和責任的傳遞。
三、影像敘事方式: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
在現實生活中,那些被牧民稱為“國家的孩子”,在災難中成長起來,并得到了草原上父老鄉親們無私奉獻的愛心。在“大歷史”的背景下,導演爾冬升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法,將“小個體”的“大故事”轉換成了“小故事”,將社會問題轉換成了“家族倫理”的敘述。在這部電影中,導演采用了宏觀和微觀的敘述方式來表現這一民族情緒。
(一)對話敘事再現民族歷史書寫
《海的盡頭是草原》圍繞著“成長”這一主題,構建了一種對歷史和現實,蒙古族和漢族的一系列復雜的集體情感敘述。通過運用自然的主題視角,作者在時間上展開了一次回溯式的敘述,在空間上構建了一次“蒙漢”家族的“對話敘事”,這是一次兩個民族的“對話”。本片借由這一特定的漢和蒙古兩族歷史的“再寫”,用“對話”的方法,突破了民族史書寫的種族、地域的局限,將民族史“再寫”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
本片中主角尋找親人就是一個不停地“對話”的過程,同時也使本片在深層次的結構中達到了一種復合式的敘述。“對話”的主題和內涵并不局限于男女主角杜思瀚和杜思珩,也包含杜思珩的蒙古族養父母、弟弟和司機兄弟,在電影里,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感情裂縫,而在這一次尋找親人的旅程中,卻追尋著彼此的感情回憶,最后達到了一種親情的契合。
(二)主旋律基調下的“傷痕文藝”敘事
影片中所涉及的歷史敘述,均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傷痕文藝”的語調,而“傷痕文藝”的敘述卻意外地與主題式的民族大一統的敘述形成了一種文化表達上的矛盾。“上海”,這個3000多個孤兒的起源地,在那個時代,它已經不是一個待救的意象,而是一個在全球化背景下,與內蒙古大草原意象相提并論的具有代表性的都市空間,它不僅是孩子們長大后尋找親人的地方,更是他們在生活抉擇中迷茫的地方,也是他們成長的地方。這種“傷痕文藝”基調的歷史敘事,在很大程度上對上海的快速發展與內蒙古毅然伸出援手的難能可貴之處進行了對比,進一步加深了民族團結這一宏觀主題。
這部電影用細節去表現真實,用溫暖去洞察歷史,在一個個小家后面展示了一種偉大的民族情感。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的評價可謂切中肯綮:“這是一部大美的影片,它的美不僅僅在風景,更在于人性和人情。這個電影尋求創新表達,把一個宏大的敘事轉化成了微觀敘事,把社會問題轉化成為家庭倫理敘事,通過一個尋親的故事,帶著觀眾進入到草原,真正地與觀眾達成共情、共鳴、共振。”[3]
四、影像敘事的表現:色彩和場景交織的鏡頭審美
鏡頭語言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段,也是大眾媒體傳遞感情和意圖的一種符號系統,是表達風格、訴說情感的關鍵。它的獨特美學原理在于以再現機制為主激發自由情感。鏡頭美學對影片的藝術呈現、意義生成等都起著重要作用,其色彩運用、光線配置、畫面構圖、角度、景別等都是鏡頭美學中重要的審美元素。[4]
下文主要從景別和顏色兩個方面來分析該片如何用鏡頭美學來進行歷史影像敘事。
(一)景別:兩極鏡頭的反復運用
在影片中,通過多種景別的交替使用、場景調度和鏡頭調度的復雜多變,導演和攝像人員都能增加影片的表現力,對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思想情感的表達、人物關系的處理,都能達到游刃有余的效果,從而提高影片的藝術感染力。
不同的景物會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俗話說:“遠景出氣氛,特寫出情緒。”遠景鏡頭具有廣闊的視野,它多被用于表現時間、環境、規模、氣氛等事件的發生,比如自然風光、群眾場面、戰爭場面等。在這部影片中,一望無際的草原、原始的蒙古包、駿馬、綿羊構成了一幅優美的圖畫,導演采用遠距離的拍攝手法,使其成為一部風光紀錄片,雄偉壯闊,使人們對蒙古草原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內蒙古雖然遠離大海,但是天廣地大,那動人心魄的美麗景色卻都集中在了“海”上。
遠景圖在展示廣闊場景的同時,也注重營造氛圍、表達情感。這部電影將大范圍的自然風景和點狀生活融合在一起,藍天和青草下的溫柔生靈、漆黑的夜色中的一盞油燈,以及一個在沙塵暴中迷失方向的少女,通過全景和遠景的組合,將小主角的思鄉之情展現得淋漓盡致。
特寫鏡頭是五個景別鏡頭中最重要的鏡頭,同時,還會對面部特征進行放大,以達到推動劇情發展的目的。就拿這部電影的高潮部分來說,杜思珩也是從南方來的,他和伙伴馬正元從草原上逃出來,但是因為沒有經驗,他和馬正元都掉進了流沙里,電影中用了很多鏡頭,特別是臉部的鏡頭,將人物的每一個細微動作都展現出來,將他們的心情和情緒都表現得淋漓盡致,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視頻里,弟弟對杜思珩說的最后一句話也漸漸沉入了沙子里,將悲傷和緊張的氣氛推到了頂點。
(二)顏色:與暖色和冷色相襯
整部影片都是用插敘的手法來講述杜思珩的經歷,而前面的幾個場景,導演用了很大的顏色對比,給人一種很有視覺沖擊力的感覺。電影中,杜思瀚所處的那個時代,大部分背景色都是以低飽和度的冷光為主,講述了一個母親在饑荒年代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孩子,經歷了太多的痛苦和內心的掙扎,在那個時代,那些場景都是昏暗的,但在平時,那些場景都是鮮活的,而且,那些場景會越來越亮,就像是一段漸漸淡去的記憶。
影片在色調處理上進行了細致的考究,一方面,通過色調區分交織的情節線索;另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向觀者呈現出“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壯麗草原景象,從而詮釋出溫情大愛的主題。
杜思瀚在尋找親人的過程中用了一種很普通的色調來表達現在的劇情。杜家人的回憶被打上了一層朦朧的濾鏡,再加上低飽和度的顏色,讓人無法忘記內心深處的回憶。杜思珩在來到內蒙古之后,對草原的描述,采用了一種淡淡的黃色,與遼闊的草原、人物的簡單服飾,以及麥色的皮膚形成了鮮明對比,既襯托出了杜思珩在草原上生長的溫暖氣氛,又突出了內蒙古草原上特有的美麗風景。片尾處,兩對母女的背影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里,在黃昏的云層里,顯得幽深而富有詩意。
影片利用鏡頭語言進行敘事,不僅形象地完成了對民間故事的講述,還利用視聽語言傳遞了信息,并產生新的意義,從而體現出電影獨特的審美特點。
渾然天成的紀實風格成就了影片畫面的真實質感,成長主題與民族團結的雙重母題恰到好處地凸顯了杜思珩被大愛感化的心路歷程;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相結合精妙絕倫地再現了漢和蒙古兩族牽手的感人事件;考究的色調處理、大小景別的適時運用勾繪出一幅高級的美學畫面。但說到影片的精巧,歸根結底還是一位少女,在她的角色互換中,實現了“愛的連接”,跨越了兩個時代。唯有“愛”,才會給人一種家的感覺,有家的地方,才會有家。就像電影的宣傳片里說的那樣:愛的遼闊,跨越山海!
參考文獻:
[1]劉婷.影像敘事[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2]朱俊威. 論紀實風格電影的蒙太奇思維及其藝術特征[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1.
[3]饒曙光,尹鵬飛.《海的盡頭是草原》:少數民族電影的共同體敘事新探索[J].當代電影,2022(10):11-13,2,184.
[4]廖茜.電影鏡頭再現美學的獨特魅力[J].青年記者,2014(5):52-53.
作者簡介:
朱雪嘉(1999—),女,山東淄博人,碩士,研究方向:廣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