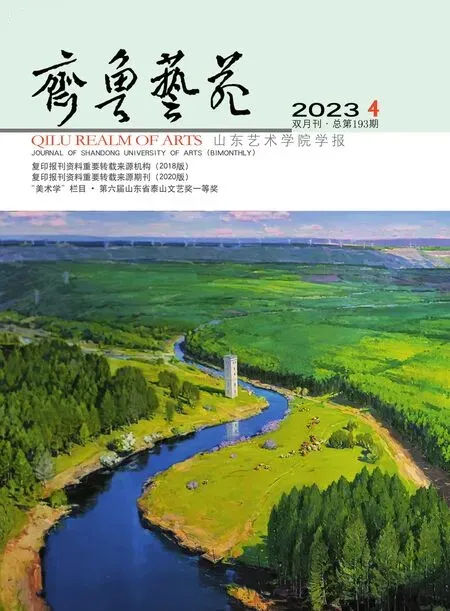論孔子對西周樂教的重構
張小雨
(文山學院,云南 文山 663000)
儒家樂教,簡單來說,便是“以樂為教”。它是將音樂舞蹈作為一種教育方式,通過開展音樂活動,在無形中影響參與者的情感志向、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并使其逐漸符合于教育開展者的期望,是一種面向人內心情感道德塑造、充分利用藝術資源的綜合性教育模式。故與今日的素質教育、藝術教育相近。孔子是儒家創始人,也是儒家樂教思想的奠基者與開拓者。從當時的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發展脈絡來看,他具備雙重文化身份:首先,出于對混亂社會現狀的深刻擔憂,他積極提倡堅守、恢復西周古制來應對時局,并做出“抑鄭崇雅”等實踐活動。因此,他與同時代的子大叔、子產、單穆公等人一致,首先是以一位維護西周舊制、積極闡述禮樂教化時代價值的賢士大夫而登場的。但是,孔子對西周文化的闡述,并未局限于原始本義,而是以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與方法進行。正如侯外廬先生所說:“孔子在西周‘維新’傳統的約束力,一方面依據對于西周制度的正義心而自認為儒(1)從原著來看,侯先生此處所謂“儒”與“儒者”與后世“儒家”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指在西周體制下,在鄉學中以教書相禮為職業的一批教師,而后者則是由孔子開創的一大學派。,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儒者的形式化與具文化,以現實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為主要任務,這就使得他在講解《詩》《書》《禮》《樂》上注入了系統的道德觀念,而并不局限于西周古義。”[1](P133)按楊伯峻先生之統計,在《左傳》中,“禮”字出現429次、“仁”字出現33次。但在《論語》中,“禮”字出現75次,“仁”字卻有109次。如果再考慮到《左傳》在文字篇幅上數倍于《論語》,則可知孔子對仁的重視遠超于前人。楊先生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孔子批判地繼承春秋時代的思潮,不以禮為核心,而以仁為核心”[2](P16)。筆者認為,孔子以繼承恢復周禮為己任是清晰的,他之所以強調仁,主要是將其作為“系統的道德觀念”注入西周禮制,是將仁視為禮樂教化的價值基礎與心理本原。從哲學體系來看,仁確是其特有概念,以仁釋禮樂,是他區別于諸位賢士大夫的獨特方法。后世諸儒在此基礎上其不斷深化,最終使得孔子獲得儒家學派開創者這一文化地位,也使得仁成為整個儒家“一以貫之”的核心觀念與根本主張。
一、“以仁釋樂”的內在轉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其內涵卻很難被定義,因為在《論語》等反映孔子學說的文獻中,他往往是以問答的形式,針對不同學生的特點而“因材施教”地闡發其仁學主張。綜合來看,仁大概有三方面內涵:1.愛人為仁。例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3](P131)朱子注曰:“愛人,仁之施。”[4](P131)愛人即對他人的敬愛、親愛、愛惜等,是一種道德情感,是仁之“施”——具體施行,即仁在情感這一維度的具體彰顯。儒家所強調的愛是以“親親”為起點,從孝順父母的親情推己及人,擴大到社會領域。繼而,對父母親人的孝悌之情,是人之為人所自然具備的情感能力,故仁完全出自主體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并非外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強制,是人主體意識與自在能力之體現,具備極強的人文內涵;2.忠恕近仁。例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5](P88-89)朱子注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6](P89)忠恕是仁之“方”,即踐行仁之具體方法。仁的內涵不僅僅是一種愛人的情感,它還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它存在于物我之間、人人之間,是一種以個人為出發點且普遍面向他人的、具有極強現實指向性的道德倫理概念;3.克己復禮為仁。例如:“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7](P125)“克己”即約束、克制自己之私欲;“復禮”,即使言行復歸于禮。儒家認為,禮乃天地運行之規則,合禮便是合天地,是人實現先天所賦之性的過程,復禮也就是復性。復禮的實踐維度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仁是主體自覺自愿去復禮之后的最終結果,是人對其天性的全部落實與彰顯。可見,孔子之仁,至少有三個不同層次:1.仁是人之為人的最高道德準則、精神境地與價值理念,可以作為統攝其他一切道德條目的道德本體而存在。愛是此本體之“施”,忠恕與克己是此本體之“方”,義、禮、智、信等具體道德名目都能夠由其統攝,可泛指一切道德條目;2.“仁”還常與“人”連用,組成“仁人”或“仁者”等指代主體的概念,是指在形下世界中,通過踐行道德實踐從而實現先天所賦之性的成人、完人,即是朱子所說“全其心之德”后的有德之人、道德完人;3.仁還是一種形下的具體道德條目,它與義、禮、智、信并列,是從對父母親人的親親之情擴展而來的對他人的普遍之愛,即愛人之情、相親之情。這可能是“仁”字的初始含義,因為許慎《說文》解“仁”字曰:“仁,親也。從人,從二。”[8](P365)在孔子看來,實現仁的重要路徑是遵禮,這樣一來,禮(自然也就包括樂)便借由仁獲得了一種道德本體式的合理性依據。
孔子首先通過將禮界定為主體實現道德涵養與復歸天性的必然選擇,繼承了春秋諸位賢士大夫的基本觀念,即削弱禮樂侍奉神靈的宗教目的,也不只是一種西周政治體制下對個人言行的強制要求,而是從哲學角度特別是自然宇宙論與道德形而上學出發,強調禮所具備的形上意義與道德意識,實現了在周代初年周公“制禮作樂”后,禮樂制度的再一次人文化發展;其次,既然仁是禮之終極目的,且它根基于個人的血緣親情,那么仁就不是空洞的道德本體與道德條目,而是融情于理的、同時指向情感與行為的價值依據與心理本原。尊禮而行實際是主體自覺的情感需求;最后,孔子將此心理本原,作為評判人各種情感的終極標準,要求人之情感抒發必須符合仁之準則。《論語·里仁》載孔子語:“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9](P68)仁成為人是否能樂之前提,而人心深處是否能樂,又是其是否能進行樂舞活動的基礎條件,故仁實際成為禮樂之根源。自此,孔子及儒家對西周禮制的具體規定之解讀,便開始主要從情感、意愿等主體要素出發,而相對擱置其宗教與政治內涵。例如,《論語·陽貨》曾記載,孔子弟子宰我對古禮之中的三年之喪產生了困惑,認為時間太長,一年足矣。孔子卻反問他“女安乎?”朱子注曰:“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10](P168)孔子將三年之喪的正當性直接歸結為親子之愛,認為父母去世后子女為其守孝是個體情感的自然流露,本不用禮規定。但守孝期限不可能無限延長,故由圣人定以三年之限,因為子女生三年,然后才能免于父母之懷。三年之喪的禮制規定,就是子女這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的體現,因為有此愛,故有此禮,此禮之目的是將此愛進行具體彰顯。孝悌之情便成為此項規定的心理本原,遵守此項規定也成為人自覺的情感需要。愛親之情是禮的內在依據,只有遵此禮而行,才能使此情獲得正當地、合理地抒發,發而得當之情才是符合道德要求之正情,才能獲得樂這一道德情感,最終才能上升至仁之高度。一年之喪是情發而不足,三年以上是其情發而過分,三年之喪才是符合情感自然需要的“天下通喪”。
孔子繼而說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11](P166)朱子注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12](P166)禮樂是內在之敬與和的外在抒發,內在之正情為禮樂之本。孔子致力于實現禮樂價值的內在轉向,并為禮制的合理性做出說明,使之成為人人皆需要自覺履行的規定。樂教開始走向與西周強調制度性、階級性不同的內在化、自覺化方向。這也正是儒家樂教與西周樂教的一大區別。禮樂教化不再僅是西周政治制度中鄉學、國學的學校教育,而是可以在社會上廣泛推行的社會教育,甚至可以成為個人修身養性、表情達意的自主選擇。因此,孔子特別強調要通過樂舞活動探知作樂者、奏樂者的內心世界。例如:“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13](P97)朱子注曰:“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后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14](P97)歌唱成為個人抒發內在情感思想的途徑,孔子從中意識到歌者之善,愿使其反之,并與其唱和之,從而詳細了解。這一過程無任何的宗教因素與政治色彩,完全是道德精神之交流。朱子謂孔子是“氣象從容”,便是無任何外在強迫而全為主觀意愿的活動。樂舞成為主體性自由意識的體現,也只有在此自由中,才能真正實現情感抒發與藝術創作。當禮樂教化獲得仁這一基于個人情感、血緣、親情的內在本原后,教化便不再只是外在的禮節儀式,也不只是政治強權下的官方意識形態教育,接受它們便是一種自覺的情感需要與道德追求。在孔子看來,雖然部分內容需要“因時損益”,但西周禮樂制度,便是一種能使情發而中節的方法。因此,即便沒有政治強力,遵守西周禮樂制度仍然是必須的。孔子從內外兩方面同時論證西周禮樂制度的合理性及當代價值,故侯外廬先生說:“孔子關于春秋時代禮樂的批判,并不是掌握著新內容以否定舊形式,而是相反,固執著舊形式以訂正舊內容。”[15](P142)其實存在不足。嚴格來說,孔子應是掌握著新內容——仁,從而發現舊形式——禮樂,仍有符合現實的價值。故舊形式自其價值內涵來說其實并不舊。可見,與同時期的幾位賢士大夫類似,孔子對西周禮樂制度的提倡與維護,首先是從哲學角度進行的。但他卻不是從本體論層面界定樂之本,然后論證其價值,而是通過“以仁釋樂”,實際是為外在禮樂規范找到了主體內在的自覺意愿,從而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下,為世人論證了西周舊制的內在合理性,是孔子在理論方面的建構。此外,孔子還以實際行動重塑西周樂教。
二、“抑鄭崇雅”的實踐運動
在《論語》中,孔子對音樂的專門敘述其實并不多,但他卻兩次提到鄭聲,其一是在《論語·衛靈公》,原文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16](P153-154)其二則是在《論語·陽貨》,原文曰:“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17](P167)朱子注解鄭聲曰:“鄭聲,鄭國之音。”[18](P167)籠統來說,鄭聲即是流行于鄭國的音樂。由于地域、人口、風俗原因,鄭國民間音樂主要受商朝遺風影響,加之鄭國處于天下之中,交通發達、土壤肥沃,商業發展水平較高,故產生以娛樂為主,帶有“藝術商品”性質的鄭聲。其主要特點是注重音樂的藝術性與娛樂性而非道德教化。按《禮記·樂記》等儒家文獻可知,孔子指責“鄭聲淫”,僅稱其為聲,而不為樂,是因為在當時,這些概念存在嚴格界限,稱其為鄭聲,不是說它在音樂形式的復雜程度上不如樂,而是從價值與道德角度給予否定,認為其配不上樂之稱謂。從文獻記載來看,《左傳·昭公元年》中還有鄭衛之音這一概念,應當與鄭聲同義。它產生于繁復的演奏手法及宏大的樂隊規模。在《左傳》中,醫和認為不可嘗試演奏五聲音階之外的音樂,為了獲取與五聲不同的新音階,就會使用到繁復的手法,發出過分的音調,影響主體內心,使其失去中正平和之情。從考古成果來看,新鄭市出土的一套鄭國編鐘10余架,共計260余枚,其中一組6枚甬鐘的音域超過三個八度,具備完整的七聲音階,它們樂律和諧,音品動聽,能夠演奏出極其多變的調式及旋律。鄭國更多繼承商代“五音俱全”的傳統,并由此取得進一步發展,實現“七音俱全”加“三重變調”,與同時代的周朝編鐘存在根本不同。此處之“淫”字,首要的含義是過分而不加節制,并非淫蕩之義。鄭聲在演奏時,多使用繁復的手法、精美的樂器、龐大的樂隊,演繹出過分多變的音階樣式和起伏過大的旋律曲調。這與儒家乃至西周樂教所竭力提倡的和平中正原則相背離,故遭到孔子斥責。
與鄭聲相對的概念是雅樂,《論語》此處將“雅”與“樂”二字連用,組成“雅樂”一詞,可能是其首次出現,而不見于《尚書》、《周易》、“三禮”、《春秋》等古文獻。但《詩經》中有《大雅》《小雅》,說明其淵源有自。雅樂的內涵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共有3層含義:首先,雅樂最初是指周人之樂或周地之樂。在《尚書》中,周人多次自稱為“有夏”“區夏”。按孫作云先生考證,“夏”字和“雅”字二者在當時同音通用(2)參見:孫作云.說雅[J].文史哲,1958,(1)。。周人自稱夏,實際上也能說是自稱雅。雅言既是周本土之語言,也可稱之為周言、夏言。雅詩即周本土之詩,也可稱之為周詩、夏詩。《詩經》的《大雅》《小雅》便是周地之詩。在一開始,雅樂只是就地域與民族角度講,指在故商統治時期,在其盟邦周內,由周人用其語言、樂器等制作而成的周民族音樂。在武王伐紂,周成為天下共主后,雅樂產生第二層含義。周公通過“制禮作樂”,自上而下禁止商人音樂當中注重娛樂性的“巫樂”“淫樂”,而僅留下像《大濩》這類商代圣王之樂,而且還對前代之樂進行了損益。此時的雅樂是指周公所制作之樂,或經周公損益的前代圣王之樂,《周禮》所說的“六樂”。它們被頒行天下,作為周王室與各個諸侯國宮廷之樂與學校教學之樂,用以取代故商音樂。這展現出雅樂從一地之樂,慢慢演變為一國之樂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雅樂產生第三層含義,即在價值上的含義。雅被解釋為正,即西周正樂,周人以此樂去正定故商宮廷、民間的不正之樂,而使得周之教化澤被天下。它們成為西周樂教制度的具體承載。所以鄭玄曾說:“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后世法。”[19](P880)此三層含義決定了雅樂有三大特點:其一,雅樂的配樂歌詞,即唱詩,是用西周王畿之地(即今天陜西省寶雞至西安一帶)的地方語言而作,在語音、用字、句式乃至樂器、舞蹈、舞具等方面,都會和商代音樂有極大的不同;其二,雅樂與周禮一樣,具有嚴格的等級規定,不同等級之人,能夠聆聽的音樂,能擁有的樂器、樂工、舞蹈隊伍等有著嚴格的規定而不能僭越;其三,制作、聆聽、演奏雅樂的一個重要目的,不是像商人特別是紂王那樣是為娛樂,而是為了接受西周教化。自此之后,雅這一概念逐漸取代了前文所說“古樂”的“古”,并逐漸獲得了一種官方的、合乎規范的、高尚優美的含義。后來,雅樂與鄭聲的對立,逐漸衍生為雅與俗的對比。雅與俗也逐漸成為了中國美學史上最為重要的一組概念,但此處不能將其展開。孔子對雅樂推崇備至,強調治理國家要“樂則韶舞”。可見,《韶》樂便是雅樂的代表。
按《論語·八佾》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20](P68)邢昺曰:“《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盛德又盡善也。”[21](P50)朱子注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22](P68)“韶”與“紹”通,意為繼承。因為接受堯禪讓的舜能夠承繼堯之德行,故其音樂被稱為《韶》樂,又稱之為《韶》舞。《論語·述而》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23](P202)朱子《論語集注》引范氏之語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如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24](P202)《韶》在內容與形式上做到了“盡善盡美”,得到孔子的極度推崇。朱子認為,“盡善盡美”指的是:“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25](P68)舜通過接受堯的禪讓而和平得到天下,又能繼承堯之事業,開創出新的治世。其盛德表現在樂舞上,是《韶》樂在音樂形式上具備“聲容之盛”的高超藝術水平,同時又在音樂的內涵上,即唱詞的中心思想上充分歌頌了舜之道德。因此《韶》舞是文質彬彬、名實相副的雅樂典范。與鄭聲不同,《韶》舞不是以娛樂為導向,從而一味追求音樂的外在形式美,而是意在以恰如其分的形式,將舜之全德進行完滿地呈現。舜之“道德之盛”——善,《韶》舞的“聲容之盛”——美,二者互為表里、相得益彰。它之所以能達到“聲容之盛”的原因,主要不是樂官伶人娛樂、獵奇思想的實踐,而是由舜之道德決定的,是百姓對于他那種無比崇拜的情感,在音樂上的自然抒發。故聆聽《韶》舞,其首要目的,是在以音樂的形式歌頌舜之道德,從而打動人之感情,使之體會到此全德,并從情感上萌發出一種對舜之崇敬及提升自我道德水準的期盼。孔子能“不知肉味”,是借由《韶》體會到舜之德,實現超越自然感官意義的道德精神境界滿足。《韶》遠早于周民族音樂,但在周代建國之后,周人對《韶》加以繼承,并將其作為西周雅樂的一份子而推行天下。孔子稱贊其是“盡善盡美”,實際上就是視之為整個雅樂之典范代表,它與孔子的音樂理想和樂教主張高度相合。此外,《韶》舞之“舞”字,有學者認為應寫作“《武》”,指的是周武王之樂。它是在武王伐紂之后所作。因為武王所行興兵伐紂之事,乃上順天意、下合民心,故人們創作這首歌曲來歌頌其盛德。但興兵得天下始終有所殺傷,不如接受和平禪讓,因此,《武》樂雖然在形式上極美,但其歌頌的對象,即武王討伐之事,卻未能盡善。如若按照此種觀點,則《論語》原文還可以寫作“樂則《韶》《武》”,即以《韶》《武》為代表去指代全部的雅樂,應該翻譯為:國家開展樂教就應使用舜之《韶樂》、周武王之《武樂》這一類的雅樂,而不應是鄭聲。
由孔子“抑鄭崇雅”“盡善盡美”可知,其音樂思想與同時代的季札一致,強調中正和諧、美善一體。孔子評價《關雎》時,還提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26](P66)(《論語·八佾》)這一準則。朱子注曰:“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27](P66)孔子在評價音樂之時,其實也對人的情感表達提出要求,認為情感抒發應適度而不過分,即可樂但不可過樂,可哀而不可過哀,過樂則淫,過哀則傷。孔子的樂教思想實際是以音樂為媒介,試圖通過對音樂音階、旋律、節奏等的節制,從而實現對個人感情抒發在程度上的控制。因此,鄭聲在演奏上的不加節制不是一個可以被忽略的小問題,而是會引起主體心靈出現不正之情、有損心身甚至淪喪道德的一個誘導因素。淫、傷等無節制的情感,是動物情性情感,儒家之所以要求節制情感實際上是強調人之為人應該具備的,控制情感的能力,體現的是人的理性與社會性。過分而盲目地追求情感表達,其實于己之身心、他人之生活皆有害無益。這體現出孔子樂教思想深刻的人文性、現實性價值。在殷商時期,樂舞主要面向天神與祖先靈考,其目的是通過樂舞來娛樂神明祈求其能賜福于人間。當時樂教的核心目的不是道德涵養而是宗教信仰。但經過周公與孔子的兩次人文化轉向后,儒家樂教才真正成為一種道德教化。孔子之樂教思想,是在周公之后更高一級的人文精神之覺醒,是人的“道德自律”。
孔子將音樂提高到了“為邦”的高度,可見他極其重視禮樂制度在維護國家秩序時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他強調音樂的政治性、社會性,故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28](P159-160)有德天子成為開展禮樂教化、制定禮樂規則的唯一主體,包括其在內的天下諸人皆要遵守之。因此,當孔子看到季氏能“八佾舞于庭”時,才會感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國家要維持穩定和諧,必須采用禮樂制度來維系人的內心及行為,人的感情要“發而中節”、行為要“尊禮而行”。首要的是,感情宣泄要在不傷害自己身心,又能與他人保持和諧的前提條件下進行。對此,音樂的誘導熏陶效應就顯得很是重要。樂教以一種感性的、直觀的形式,在無形之中,塑造著人們的感情,從而進一步影響其思想、行為,最終營造社會氛圍、改變風氣。孔子對于音樂社會功用的論述主要表現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29](P166)朱子注“興”為“感發志意”[30](P159-160),即通過聆聽樂曲、體會歌詞,引起聯想,使得自己在思想、精神、情感等方面受到感染和熏陶,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與外界接觸,凡有所接觸,便不得不受到外物在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從而產生自身對外物的某種感應。這種感應的程度有所不同,細微的感應一時間難以察覺,而當日久天長,這樣的感應就會積少成多,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個人對外物的某種情感、思想、態度。音樂的一大作用,就是將還很細微的感應興發出來。而這種興感作用,往往是“同類相感”的,即有何種之樂,往往就能引導出何種之情。音樂內容的思想性,就顯得極為重要,好的音樂應該是誘導人們生發出積極向上之情志。朱子注“觀”為“考見得失”[31](P166)。邢昺疏曰:“《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32](P270)人可由一地之詩了解一地之政。朱子注“群”為“和而不流”[33](P166),此處就詩歌音樂來說,即音樂與民眾的關系應是“和而不流”。和是指音樂能夠成為不同地方、種族、階級的人共通的紐帶,他們都可以通過音樂來表達、交流情感,并體會對方的思想感情,從而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交往。可對于正樂來說,決不能一味地迎合民眾的情感宣泄和娛樂要求而流于世俗,也不能將維持民眾關系的和諧作為終極的目的,而是要保持一種相對獨立的地位繼而起到引導輿論、改變風氣、提升道德等教化作用。保障音樂不會流于低俗的一大方法即是以禮節制樂,《論語·學而》載:“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34](P53)朱子注曰:“徒知和之為貴而一于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35](P53)在儒家看來,樂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但真正的和必須是有禮節之,它并非是一種流于世俗的迎合,也不僅是人與人之間表面關系的和氣,而是在禮樂配合、情理融合下的國家向心力、民族團結力的整合。在這種和的環境中,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感情,人人都能通過別人情感的表達,來了解與關懷對方,從而實現與維護一種真正和諧的人際關系。這樣就自然要求給予這些表達及熏染以程度上的限制,使其不至于過分或者不及,既不傷害自己又不影響他人。國家通過制樂、傳樂、奏樂、賞樂,實際是將政治教化及道德倫理意識傳播四方。進而,人們通過欣賞正樂,在潛移默化中使得其情感被誘導至中正平和,便能實現其政治的、社會的功用。有樂而無禮之和,是一種流于世俗、沒有秩序、無關教化之和;有禮而無樂之和,是一種不群之和,它是毫無生氣的空洞教化,而嚴重欠缺情感基礎與思想共鳴。從根本上說,這兩種情況都不能稱之為和,更不是群。在孔子看來,音樂必須要對個體性與社會性都有所照料,同時還能作為推行教化之工具,這就和今天一些人把音樂只歸于一種藝術形式,從而更多追求其藝術性、娛樂性有極大的不同。朱子注“怨”為“怨而不怒”[36](P166),它是指音樂詩歌可以表達作者的不滿,但是需要對不滿之情加以約束。孔安國注曰“怨刺上政”[37](P270),表明這種不滿主要來源于國家政策的失當。詩人可以通過詩樂,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向君上進諫,即是所謂“諷刺”“事君以禮”,突出表現儒家詩教的“溫柔敦厚”,即臣下一般不以直接過激的方式進諫君主、批評他人。以此反觀鄭聲,可以發現它極大地違背了這些要求。《鄭風》《衛風》中有大量詩歌是描寫由于當政者的無能、荒唐、淫亂導致的國家混亂,從興、觀的角度來看,它們更多的是使得讀者體會到鄭衛之國家的衰亡、政策的失當,二國之政治面貌完全不足以觀。更有甚者,它能興發讀者產生一種可能本不應產生的,對于自己所處環境的不滿和對于社會的抱怨,而非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情志。從群、怨的角度來看,鄭聲感情發而無禮節之,怨而怒、樂而淫、哀而傷,故又不足以群、怨。孔子對流行于天下的音樂進行取舍,認為必須要將鄭聲放逐之,即不將其用于祭祀、宴會等重大場合,而要使得《雅》《頌》各得其所,以《雅》《頌》之正樂來正不正之鄭聲,故提出“樂則《韶》舞”“放鄭聲”等主張,目的就在于利用音樂的政治、社會功用,來實現孔子理想中的國家和諧狀態。
孔子對于音樂、感情的“節制”,并非否定人應有的感情表達,也不是盲目扼制個體的情感需要,更不是一種落后而保守的音樂思想。他是從個人情性、身體健康和國家穩定和諧出發,強調理性對感性的收束、個人對集體的責任,要求個人情感的表達要在不傷害自身情性和他人生活下進行。孔子之所以反對鄭聲,不是因為其民間音樂、地方音樂的地位,而是因為鄭聲為追求極致的藝術性與娛樂性,對于樂器制作、演奏手法、感情抒發不再加以節制,這可能造成——人從通過理性節制情感從而成全其作為社會性的人,淪落為靠放任情感沖動發展而無所不為的“禽獸”。音樂不正體現的其實是人心不正,對于音樂藝術性的過分追求,實際上是戕害人性,也是傷害音樂自身,這種做法使得音樂從感化人心,讓心情復歸平和中正劣化為助長人欲、放縱情感而傷人害己。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對于鄭聲的批駁,存在著一種深刻用意,即認識到音樂藝術中可能出現的人欲泛濫問題。對于音樂藝術性、娛樂性的追求,不應過分無節,反倒為人欲所支配,從而可能導致一系列不良后果。雅樂和鄭聲的最核心區別,并不是現代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雅樂出自于奴隸主階級,是對于奴隸制度的維護工具。鄭聲出自于民間,是完全正當的對于民眾生活的寫照。二者的真正區別在于:雅樂基于道德,目的在于以符合道德之正情來引導民眾之好惡歸于中正,從而使國家和諧有序。鄭聲出自于人欲,目的在于滿足人們的享樂需求、伶人的生存需要,不具備更加深層的意義和價值,其在音樂技巧上的追求反倒是褻瀆音樂自身。“德欲矛盾”是孔子樂教思想中的核心議題,孔子強調音樂必須具備道德,藝術存在是非善惡,道德是鑒別音樂價值的最高標準。相比之下,音樂制作者、演奏者、聆聽者的民族、階級以及樂器規模、演奏技巧等,與其價值高低無必然聯系。由此反觀今日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玩音樂”等觀念,可發現當下之音樂已迷失在追求藝術水準、個人情感宣泄、個人技巧展示等錯誤的方向中,實際抹殺音樂本來應該擁有的價值。因此,孔子樂教思想對于今人解決這一現實問題,仍具備一定參考意義。
三、“孔門樂教”的具體施行
為了打擊鄭聲、重塑西周禮樂教化,孔子在魯國宮廷開展了一場“刪詩正樂”運動,《論語·子罕》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38](P108)朱子注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39](P108)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結束“周游列國”返魯。當時詩、歌、樂、舞還未完全分化,所謂“樂正”其實應該包括詩歌與樂舞兩方面。在詩歌方面,傳說孔子對西周傳承至今的諸多古詩進行編訂,“取可施于禮義者”(《史記·孔子世家》)共300余篇匯集成《詩經》一書。在樂舞方面,則是禁絕鄭聲在宮廷、祭祀等重大場合的演奏,并嘗試恢復西周禮樂體系。在思想理論方面,孔子通過“以仁釋樂”,賦予了西周樂教仁這一全新的價值基礎與心理本原,開啟了樂教發展史上又一次人文化發展與內在化、自覺化轉向。在政治實踐方面,孔子通過“抑鄭崇雅”,以及與之配合的“刪詩正樂”實踐試圖將魯國宮廷音樂恢復至西周舊制,并對當時甚囂塵上的縱樂傾向作出深刻批判。但是,其理論與實踐主張面臨的社會現實卻是“道將不行”“無人用我”的尷尬局面。于是,晚年的孔子退而著書立說、創辦私學,實際推行其禮樂教化主張。
孔子所創辦的孔門私學,其特點是繼承西周國學體系,以“六藝”為主要內容,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科目培養學生。孔子對“六藝”之教有一著名論述,按《論語·泰伯》載:“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40](P100)朱子注解“興于詩”曰:“興,起也。詩本情性,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41](P100)詩本源于人之情性,是人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興,即是興起內心之情,但情感的興發有過與不及、善與邪之分。需要以道德標準評價詩歌,通過對詩歌思想內涵的剖析以達到分別善惡之目的。進而,再通過反復吟唱與感受,使詩歌蘊含的積極思想打動主體內在。學者通過詩學教育可以識得是非、向善而行,這是學問進取的基礎階段。此外,孔子還講“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說明詩學教育,還是語言與思維教育,它著重培養受教者的語言表達、志向涵養與邏輯思維。在當時,詩歌不僅是文人士子抒發情感志向的途徑,還是國與國交往的政治語言。在外交場合,人們通過賦詩言志來實現交流,故詩學教育有著極強的基礎教育意味,它是個體進入文明社會、具備知識道德的入門之徑。朱子注解“立于禮”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于此而得之。”[42](P100)禮學教育是通過學習演練一系列禮儀流程,從而培養起受教者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水平。學者能敬心體會、一心遵循其背后的價值基礎與心理本原,便能卓然立基于此而不被動搖,最終實現歸禮、復性。從此,學者完全以天道運行規則作為自己行為處世的根本原則,能夠不為外物所動,自覺做到言行舉止符合禮之規定。它塑造出以仁道為基礎的個人精神獨立性,從根本上決定為學進取是“在己”而非“由它”,即是所謂“大本已定”“立其根本”。禮學教育著眼于行為規范,是為學境界的高級狀態,達到此種境界后,原先看似外在的禮儀規定,全部內化為人自身進德修業的主動需求。接著,人能樂此不疲,終于進入“成于樂”階段,是為學進取的最終結果。朱子注解“成于樂”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于義精仁熟,而自和順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43](P100)其中的“查滓”二字值得玩味,“查滓”又可寫作“渣滓”,指人不合于天理的私心私欲,人如果能清楚認識其弊端,不安于由其擺布,并真下一番功夫加以去除,則樂是實現進德修業的一種有效途徑。其功效必須建立在人自身,對仁道已有深刻認識與堅定守護的基礎上,即“興于詩”“立于禮”后。樂教不僅是對歌唱技巧、舞蹈形式和樂器技藝的學習,更是將情感的體驗和陶冶作為重心,提出要利用音樂與人情的密切關系,對內在與人道不合之處進行“打磨消融”。一方面,它是在守住大本后進一步提升并日臻完善的高級階段,從而與詩教在基礎上先對是非善惡有所區分不同;一方面,它著眼于培養人的心靈、情感,是由內而外地改變突破,從而與禮教強調外在行為規范,要從規范中認識體貼天理不同。不難看出,三者實則達成完美的互補與配合——“成于樂”要以“立于禮”為前提,“立于禮”要以“興于詩”為前提。達到“成于樂”,即意味著人自內心思想情感到外在行為語言,無不符合于教化之要求,人得以真正成為仁道的踐行者并實現功夫大成。最重要的是,這一境界不是外力強制的結果,而是個人樂于此、安于此的主動選擇。此時,音樂已內化為主體的情感——安樂、快樂。人能完全安于對人道之體貼與實踐,同時從中獲得快樂。故這種快樂之情,不單是音樂的聲音形式所激發起的主體自然情感,同時也是其內涵中的精神價值對人修身養性的道德啟示,以及人將其實現后的道德滿足,是一種復雜的道德情感。孔子所以能“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實則是內在道德意愿與外在道德規范和諧共生,人實現內外打通、樂此不疲之道德修養境界的審美反映。所以,在《論語·雍也》中,孔子才會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44](P186)內在主動性的地位得以彰顯,而音樂恰是培養并實現樂之情的重要途徑。因為人在進行歌舞活動時,其歌曲的唱詞、曲調,舞蹈的俯仰、屈伸等,不僅是一種藝術呈現,還是參與音樂活動的主體內心情感狀態、思想道德的真實反映。詩教所指向的語言與禮教所指向的行為,都可能被受教者采取掩飾、虛偽等,在某一特殊階段暫時表現得符合于禮之要求。但樂卻是個人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它從深層次上展現出主體沒有言說卻很難掩飾的內心世界,所謂“唯樂不可以為偽”其實就是“唯情不可以為偽”。“成于樂”還是成于真實、成于自然,它以音樂為媒介直接訴諸本心、影響情感,剝離一切偽裝掩蓋,呈現出受教者真正達到的道德境界,是施教者衡量自身工作的依據。
孔子也是當時著名的“音樂家”,《詩》三百,他皆能“弦而歌之”(《史記·孔子世家》),其弟子們也時常浸潤在音樂中,甚至將孔門樂教在地方實踐。《論語·先進》中有著名的“侍坐篇”,其中有“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詠而歸”等語句,即可見出音樂在孔門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孔子與弟子論志時,有曾點于一旁鼓琴。《儀禮·鄉射禮》記載了西周民間舉行射禮時的音樂使用細則,其中不難看出,西周樂教重在面向集體,是有明確制度流程的。但在此處,孔門卻將音樂面向個體。孔子贊賞曾點之志,這也是孔子本人及前輩圣人之志,是孔子所向往的精神境界。此時,人已經實現情感與理性、內在與外在、個體與社會之和諧統一,達到人格完滿的道德境界,獲得了自我人格自由的最大抒發。而這一切,卻又是曾子在音樂的熏陶、浸潤當中娓娓道來。由此可見孔門樂教之大成階段,那是一種很難以學術語言描述,而需要讀者直接訴諸內心情感從而加以感受的境界。此外,按《論語·陽貨》載,樂教還成為孔門弟子子游治理武城的具體工具,他命人在城墻上演奏雅樂。這是對西周禮樂制度的重建,同時也是改良。因為嚴格按照目前已知西周樂教制度的規定,普通百姓很難如此直接接受樂教。所以,與部分學者提出的,西周樂教隨著其王朝覆滅而宣告失敗不同。本文認為,西周樂教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理論重構及具體實踐,才真正開始成為人人得以接受的教化形式。西周的禮樂,就從今日可見的文獻中觀之,其性質主要是一種政治制度,目的是用來維護西周的血緣宗法等級制度,文獻中更多記載的是國家為開展樂教而設立的制度保障。而由孔子開創的孔門樂教,其性質主要是一種與其余“五藝”并列的教育門類或方式,目的是引導學生通過欣賞雅樂來規制其情感,并促成道德涵養。西周更多是禮樂制度,而儒家則是禮樂教化。自此之后,音樂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用以表達情意、涵養性情乃至結交知己的工具。樂教也開始從一種國家層面的教化制度,演化為面向個體的、能體現其個人情感類型及表達的藝術培訓、情感教育。于是,自春秋后,琴瑟、簫笛一類“個體樂器”地位逐漸提升,鐘磬一類“樂隊樂器”則逐漸沒落。為人熟知的俞伯牙、鐘子期二人“高山流水遇知音”,便發生在春秋時期。后世甚至出現了“以琴表志”“以琴知人”“以琴會友”等現象。這其實皆開端于孔子樂教,是其對西周樂教所作二次人文化、內在化轉向的結果。
結語
綜上,本文詳細考察了孔子的樂教思想,核心結論是:孔子通過“以仁釋樂”,將主體內在之仁,樹立為外在禮樂制度的最終依據,實現了西周樂教的第二次人文化轉折,建立了儒家樂教。舊有的西周樂教更加強調外在制度性,其核心目的是為維護西周血緣宗法等級制度,故更接近于一種禮樂制度而非禮樂教化。與此相比,孔子樂教則更加強調內在心性基礎,最終目的是以樂在內的六藝教化,幫助主體彰顯內在之仁。孔子還以“抑鄭崇雅”、創辦私學等實際行動,踐行其禮樂教化主張,最終使得音樂成為文人士大夫用以表達內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