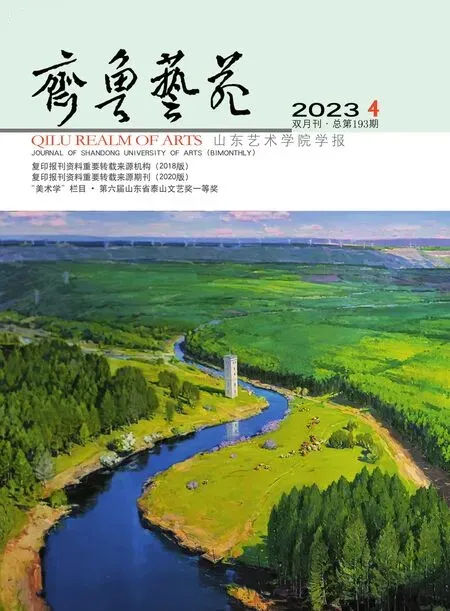重大歷史時刻的想象再現與話語重述
——建黨題材電影作品的敘事策略與言說機制
葉 凱
(山東藝術學院《齊魯藝苑》編輯部,山東 濟南 250014)
關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諸多因子構成的集合,謂之“歷史”。如果從表層外觀延展的現象學視域來看,“時間”與“空間”的“二重性”恰是構建其認知框架的邊界椽體,二者組成縱橫交織的坐標象限,讓歷史能夠擁有標注自我位置,且可以抓取靜像存在的被認知性。但歷史本性是一種綿延的流態,是不間斷之運動,而其與人的認知相遇時,變成了某些暫時的穩固之物。不過,即便經由人的主觀參與而限定的領域,歷史仍舊顯現出明顯的流質形態,因為“記載”與“言說”的必要路徑,使它總在尋找確定性時,走向不確定,而可架構其矛盾形態的緣由,在于人們始終追求的某種可被理解與解釋的邏輯關系,它通常被稱為“因果”,而這種關系指向的目標,則是普遍哲學意義上的“合法性”命名,遷延到社會學層面,與道德倫理、政治觀念等概念相合,便是帶有相對“目的性”的話語。梁啟超曰,“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1](P3),則是概括了史學認知的一般價值與應有之義。
既然歷史被視為人類社會活動在時空構筑的維度內集成的總和,那么它作為物質實存,與人的精神內在連接,便構成了人的主觀見之于客觀的行為,即通過記憶書寫、講述,把稍縱即逝的實存留影,轉換為虛擬性的文化痕跡,于是其才真正完成了自身本體性構成的完滿與流轉,而且就此成為一種有實用價值和持續存在的機體。歷史運作的機制在于這種描述動作的運動性和其實存對象的選擇度,其核心意義在于尋求經由描述后的虛擬體與原有實存之物之間的零度感,也就是對“真實性”的絕對追求,它是任何歷史書寫行為證明其“合法性”的根源,即便是虛假的偽造,也是追求以將自己裝扮成真實的面目,來謀取關于“正確”判斷的命名。然而,即便排除掉“虛假”與“偽造”的主觀動因,極力追逐“真實”的終極性,人的認知、描述與傳播的一系列流程運作之后,被加工成信息的物質實存,亦不過是最大限度保留其原有映像的擬態之物;即便是攝影術誕生之后的新型媒介載體,被視為一種最好的可以摒棄人的主觀精神銹斑影響,而最大限度還原實存在時間流動中之原貌的電影記錄方式,在安德烈·巴贊眼中,也不過是無限接近現實的漸近線[2](P193),之于讓·鮑德里亞的“后現代性”觀念,不斷被消費的歷史“真實性”,則進一步退行為“堆積的內爆”[3](P147),而消解了其“神圣性”。類比電影與現實的關系,遷延到歷史與真實本身,就可以看出,人的描述與傳播行為,完滿了歷史價值發揮其功用的最后拼圖,卻也無可避免地因為這一注入,而使其與絕對真實隔離開來。承認和接受歷史描述的相對性真實,才能理性地判斷虛構交融于其中的意義。再者,從人類認知實踐的效能來看,理解事物的過程及之后將其再描述的機制,總是部分而非全部采集、整理客觀實存的信息,都是經由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加工、合成,形成某種實質的想象性再現,正如魯道夫·愛因漢姆試圖用完型心理學解釋電影時空敘事機制時,所闡述的容易被忽視的常識論斷,“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滿足于了解最重要的部分;這些部分代表了我們需要知道的一切。”[4](P46)而歷史信息本身經由漫長歲月的磨礪,本就會損失相當多的細節,對其書寫與再述的實踐,必然會讓人們充分運用完型想象的連接,進行可能憑借聯想的虛構性補充,它運用因果邏輯思維補足實證之間的裂隙,從而形成相較完整的全貌顯現。
如果說歷史因其描述、記錄與傳播行為,而實現自身功效價值的動態系統構成,使得追求復現時空框架中的“真實性”目的,注定摻雜主觀性的虛構填充,變成一種話語重述行為的話,那么藝術,特別作為綜合而復雜的門類形態的電影,則與“歷史”內在實質——話語言說及外在表象——事件敘述一起,形成了互為鏡像的對稱關系。除去作為特例存在的紀錄形態,電影的主體存在形式——故事片,是以虛構性的想象敘事為基本的創作共識與認知前提的,即以藝術的假定性復現世界的真實性,是將喪失了鮮活性與時代感的逝去之物的遺跡,重新予以補足而修復其歷史的光韻,并滿足當下追憶與抒敘精神訴求的一種言說機制。[5](P227)同樣作為話語抒敘功能存在的歷史書寫與電影創作,便由此達成了共通,直指路易·阿爾都塞所描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6](P630)之定位,而顯影出一條經由歷史事件的表象再現之路徑,而延展為一種時空流程擇取選編的方法。滿足形塑與時代匹配的主流價值觀念的目標訴求,尤其是基于重大歷史時刻與重要歷史事件的題材再述而形構的故事文本,在這一功效價值的實現層面則更為集中突出,它將政治話語縫合于歷史與電影、真實與虛構的淆雜語境,混合意識形態表達、文藝審美實踐、商業消費運營等多重力量的場域共振,以回顧歷史的名義隱晦性地指涉當下,完成主流價值觀念的再度整合與二次重述,主體的意義便在承繼性的時間流程中得以實現它的言說機制與敘事目的。
一、敘述偏移:人物視角的著意選擇與事件篇幅的詳略得當
以近現代以來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為故事內容的作品,可以說是貫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電影藝術創作的全部發展歷程。從“十七年”“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7]的文藝創作方法與指導原則的提出到占據主導地位[8](P121),由此遷延到題材領域的“革命英雄敘事”盛行及其延續成為“前30年(1949—1979)”一種普泛存在幾乎被視為電影全部表現內容的藝術現象,甚至到商業消費主義盛行產業化大發展之后,它仍舊通過話語更迭與敘事重構,而成為贏取高額票房的關鍵。[9](P267)及至1987年2月4日,有關部門成立領導機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10](P77),以更為直接的方式推進該類影視作品的創作傳播。我們討論的建黨題材電影作品中的首部《開天辟地》(1991),就是這一政策背景的直接產物,它上承“十七年”革命英雄敘事的傳統,下啟新世紀之后“新主流大片”的源流,成為新時期“獻禮片”生產的肇始,也就此確立了“紅色影視”創作的某種中繼延續性地位。
涉獵建黨題材的電影創作,這里主要以《開天辟地》(1991)、《建黨偉業》(2011)、《1921》(2021)為例展開探討,其實可能需要厘清兩個相關概念:“紅色電影”和“獻禮片”。前者是題材的規定性,雖理論學界對其概念多有爭議,但主要指向“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革命戰爭過程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歷史事件”[11],它確認了電影藝術本體敘事內容所涵蓋的歷史時空節點;后者是創作的目的性,“是中國電影文藝工作者,為了慶賀、紀念、標志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發生的具有重大轉折性意義的里程碑式歷史事件,而拍攝的具有明確指稱意義的宣傳性影片”[12],它緣起于1958年夏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提出的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的電影創作議題[13],涵蓋了文化生產實踐外部的功用性價值。兩者分別對應的“文本內核”與“生產語境”,串聯起了電影內外世界的歷史時空,即電影講述的年代與電影生產的年代,它們之間的距離構成的張力,成為探究藝術敘事與話語言說的根本來源,也遵循我們前述的概念范疇所涉及的“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現實—真實”與“浪漫—虛構”、“文本—敘事”與“生產—話語”等諸多層面對應的復雜關系,包括理論認知、創作方法與文化功用等多種因素的糾纏扭結。
交織在電影作品文本內外時空中的事實陳列連接與話語言說表達,構成一種雙重敘述的語境,它在“歷史—藝術”構建的維度混沌間,將史實講述與虛構敘事的邊界加以模糊,而提純出來的共性表征唯有“人物”和“事件”以及兩者的編排秩序與分配比例。從中國史學書寫傳統觀念來看,這兩大因素也是分別構建不同體例的撰史方式依托的標準,即“紀傳體”與“編年體”,前者的代表作是《史記》《漢書》,后者則是《春秋》《竹書紀年》《資治通鑒》。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例,其“人物”指向的是“帝王將相”等左右歷史進程[14](P77),特別是政權更迭的“英雄人物”,體現的是某種“精英史觀”,長期以來被視為“正史”的書寫范例[15](P14)。編年體例則以“事件”發生先后順序記載歷史流程[16](P508),但在史學傳統中,通常被視為非官方認定的“別史”看待[17](P79),或許因為其泛化的記載相對具有“去中心化”的傾向,而顯現出某種哲學意義上的“主體間性”特質,它由“單一主體”向“集體主體”轉化[18](P148),形構了話語言說的多視角與多聲源。
建黨題材電影作品就內容對象而言,就是圍繞中國共產黨建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展開敘事言說的創作實踐文本,其中最為核心的標志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也是歷史事實本身及黨史的話語規定性所確立的,那么以其為目標的歷史講述,顯然是就“事件”及其發生的時空序列為范例的敘述,在史學書寫的范式層面指向“編年”體例。就意識形態相關的哲學認知論出發,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認同者,中國共產黨所主張的歷史觀是一種群眾史觀,即把人民群眾及集體精神作為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19](P221),其治史觀念顯然與切近歷史宏闊整體性展開的“編年”模式更契合。具體到“建黨”與“一大”召開的歷史事實而言,牽涉其中的人物眾多,予以藝術性呈現時,也較為適合在年代的時序展開中,顯現出群像式刻畫的波瀾壯闊與豐厚濃郁,是“歷史—藝術”之維的內在需求。
《開天辟地》《建黨偉業》《1921》三部分別誕生于不同歷史時期,分別向中國共產黨誕辰70周年、90周年、100周年“獻禮”的電影作品,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編年”體例,作為該段歷史的主體敘述框架,只是在具體呈現方式上,之于相關人物視角加以著意選取,而將歷史事件的脈絡流程,或延伸拓展,或凝縮收斂,在下筆著墨的篇幅之上,在鏡頭影像敘事的段落之間,詳略揮灑,力求得當。于是,“編年”體例敘述的總體框架之內,人物對象則突出重點,嵌入“紀傳”著史的優長,在群像縱覽、群峰畢現的流動質感中,謀求突出“核心”與“線索”人物的經歷刻畫,實現作品文本對于歷史講述與電影敘事雙重層面的期待預想。
《開天辟地》運用歷史現實主義思維與嚴肅的“正史”書寫觀念,以“編年體”為主體時間框架,以左右歷史的核心人物之行動形成“紀傳體”式串聯為脈絡,第三人稱旁白凸顯權威全知敘事視角,直觀凝聚在重大社會歷史政治事件及其中心話語的因果必然性邏輯之上,構成關于歷史書寫的正統言說。《建黨偉業》則實現了“去中心化”,多重散點透視的“編年體”寫作,將歷史的時間線拉長,全知視角隱沒在客觀敘事的自然流程之后,均衡的“人物”與“事件”敘述篇幅比例分配,將歷史的時空向量溢散在“凝縮性”與“碎片化”的歷史細節剪影中,依靠“正史”敘寫的因循縮減與傳奇性營造,“稗官野史”成為填補影片敘事豐滿的商業消費動力,利用藝術本體所當然應有的虛構想象特質將其充盈。《1921》將更為直接地拋卻了宏大敘事的全知視角及“編年”體例的全時段用力,緊緊圍繞中共“一大”核心事件的運行,運用以往歷史加載與文藝敘事并不關注的線索人物貫穿,接近其主觀視角的客觀敘述,更為隱藏了“主體”所在的位置,將“集體”記憶裝扮成“個體”陳述的私密絮語。
二、風格顯影:正統質樸與浪漫渲染的兩級遷變與折中漫溢
三部“建黨”題材的“獻禮”電影作品,雖然其生產出品的年代相距甚遠,但是卻不約而同地選擇近似的開篇方式,顯示了“紅色電影”之意識形態話語對黨的歷史來源認知及其藝術選擇的“統一性”。三部電影作品的序幕開端,都以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作為講述起點,以黑白影像定格及舊有照片定幀剪影式組接的畫面,結合年份數字、事件名稱、簡要結果等字幕配合的形式,浮光掠影、一筆帶過的重要時代節點標注,構筑了影片整體敘事的“編年”體例時空框架,作為歷史背景烘托的前情提要,其充滿藝術性的鋪陳渲染,呈現了自近代以來,面對外來侵略而國勢日益衰敗的危難之際,無數仁人志士探求救亡圖存、復興中華的艱辛探索與英勇斗爭的過程。正統寫史的要求對于核心事件掌控及電影藝術視聽融合的顯在方式之于年代氛圍的營造,在方寸把握的尺度間,力圖構建一種基于常態而開拓創新的書寫范式。作為慣例近似的開篇之后,三部電影作品在事件詳略與人物擇取的敘述脈絡走向上,卻各不相同。
《開天辟地》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試圖將20世紀初期中國大地亟待醞釀一場翻天覆地變化的紛繁,集中落墨于代表中國千年文化傳承的古都北京一隅,由巴黎和會激發的“五四”愛國運動為起點,順序展現了其時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愛國抗議、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探索救國出路而引進與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歷程;下篇則將鏡頭段落轉向外來文明與現代文化交織的上海,圍繞工人運動開展實踐以及在此基礎上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完成建黨前的組織預備,進而籌備及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細節,有序遞進,娓娓道來。影片依托宏闊時代背景,以重大事件的呈現為骨架,將一種對歷史漸進推動力量的社會學言說熔鑄于時序性的史實延展之中,體現出煌煌大氣般的寫史功力。事件“編年”順述與重點核心人物行動軌跡的“紀傳”密切結合,細膩豐滿的筆觸,搭建公共空間到私人情感的適度比例分配與書寫,不動聲色地突出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行動與作用,全片洋溢著一種質樸、中正、沉穩、肅穆的敘述節奏與年代氛圍。宏觀全知視角、畫外點評轉場、群體刻畫與個體描繪結合,節制個體情緒之激進迸發,始終把握某種“歷史現實主義”平淡客觀的風格,是其符合當時文化生產外部語境的必然選擇。
然而,即便是全片始終保持樸素寫實的正統歷史敘事風格,電影作品本身受到創作自律法則的制約,在具體人物生活場景與家庭關系的細微描摹之處,仍舊依據“藝術真實”思維指導下的細節完型想象,以未必能夠考證而相對虛構的方式,填補相關橋段的情節。一種基于浪漫主義的風格嵌入的基因片段,如清風徐來般地縈繞漫溢而出,于宏大歷史敘事主聲部的間奏之隙漸顯,從而準確拿捏創作風格的分寸感覺,避免因為過度強調正統寫史的使命,而喪失藝術本身靈動鮮活的核心所在。于是,在“歷史—藝術”維度的二元平衡中,以“真實—虛構”交迭存在的創作方法,完成正統主導下的浪漫想象填充,便是在保持電影本體敘事價值基礎上,不使作品淪為純粹紀錄工具的必然路徑。
在《開天辟地》這部作品中,這一思路主要被運用在描述核心人物主線革命活動之外的個人生活場景,比如李大釗與家人郊外踏青,美輪美奐的景色中,映襯著小女天真爽朗的笑聲以及李慈祥親切的目光;窮街陋巷的都市夜色里,深陷父子沖突而內心矛盾的陳獨秀,買下街邊老媼蒸煮的一鍋茶葉蛋,讓其送去辛苦勞作的兩子住處,自己卻悄然躲在街角處默默望向那燈光下的期盼;古香古色的街頭市井,毛澤東、何叔衡、楊開慧聚集于“文化書社”的店鋪,何將一雙精致的嬰兒虎頭鞋交予楊手,以祝福這對年輕夫婦早生貴子。一系列看似與“建黨”主線敘事毫不相關的閑來之筆,卻是力求在藝術虛構填充細節的浪漫寫意中,塑造更加豐盈立體的人物形象,進而從“歷史—藝術”哲學的本質認知論出發,“把鏡頭對準事件與歷史中的人,進而揭示人性、人本和人的深層精神世界。”[20](P323)其時關乎個體命運與歷史進程的關系思考,也是新時期以后文藝創作思潮中所熱烈討論并付諸藝術創作,踐行“人性、人情與人道主義”[21](P212)精神的集中呈現。
相較《開天辟地》基于“正史”書寫的直抒胸襟,一種政論間奏夾雜其間的直白表達,且圍繞核心人物立體刻畫,而推進重大歷史事件線索展開的正統抒敘而言,之后的兩部建黨題材“獻禮片”因歷史再生產語境的時過境遷,而顯現出迥乎不同的面貌。直觀通透的意識形態表達,構筑的夾敘夾議之寫史與政論旁白,某種小說式敘事夾雜散文式評價及趨近于紀錄片的紀實手法,被完全閉環的虛構性電影本體敘事所取代,商業消費美學與類型書寫滲透于史實事件縫隙之間,形成一種鋼筋混凝土式的澆灌凝固。
依然不離“歷史—藝術”糅合的雙重維度,《建黨偉業》一片,寫史本身比《開天辟地》更加偏向于宏觀視角下的均等價值判斷,既有承繼正史書寫對于基本歷史事實考究的正本清源,又在敘事時間向度上較為合理均衡分配。以“主體間性”觀念指導的總體哲學史觀,“拒絕單中心論,強調主體之間的相互溝通和理解”[22](P73),將歷史人物、講述者、受眾視為行走在時間長河中的平等主體,強調冷靜的言說態度。在更為嚴格的“編年體歷史中去尋找戲劇性,并且在這個基礎上選擇必要的時間節點”[23],這個歷史本身與故事敘述的時間,被創造性地進行延展,作為敘事主體組成的節點,被前置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初,并在開篇30—50分鐘之后,才真正開始講述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密切相關的新文化運動及“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它與以往歷史書寫與文藝創作所認知的時間線明顯不同。影片對于最為核心的中共“一大”會議,也僅僅用了最后30分鐘凝練陳述。一種時間的延展與漫溢,或可是一把敘述路徑的“雙刃劍”:一方面,散淡的筆墨更顯自然而不露痕跡,猶如歷史的光韻躑躅于前,靜默留下投影;另一方面,主線敘事的追光似乎在全景敞開的大時代光圈中,遺忘了本想言說的核心。
之于電影藝術本體層面敘事結構選擇的技巧,《建黨偉業》的創作團隊采取了“正史”之外插入“稗官野史”,甚至某種未經驗證“逸聞”的方法[24](P471),來構置情節細微之處的豐富性,而這一風格策略的應用,多著落在關于“建黨”歷史之外的非核心事件與旁支人物的敘寫上。譬如蔣介石受陳其美指派,暗殺政敵——光復會首領陶成章的段落,在醫院行動的動作場面,就是明顯的依據某種傳說加以藝術想象虛構的具現,有借鑒“諜戰”類型作品的橋段調用與旨趣訴求;張勛復辟后在紫禁城的大殿之上覲見皇帝時奴顏婢膝的丑態,經藝術的虛構維度展開,演化為小皇帝溥儀將風箏系在其辮子之上,而令之于大殿之外奔跑取樂的場景,既有藝術形式本身純粹的諧趣美學之源,又有指向歷史本身的隱喻與反思,暗諷其是一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荒誕政治鬧劇;“一大”上海會議因租界巡捕搜查而臨時休會后,驚魂未定的陳公博夫婦在旅館電梯里,遭遇攜槍而來的不明男女,其主觀心理的緊張與劇情轉接而來的動因,形成希區柯克式的驚險懸念張力,而隨之證實只不過是與主線敘事無關的旁置枝蔓,一對殉情自戕的男女戀人,卻在此被加以藝術重現式的放大,而構成電影類型橋段與商業消費美學功用的嵌入與凸顯,產業化布局下電影作品的市場訴求與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復調變奏,融合于故事文本的“真實—虛構”雜糅的抒敘行動。影片風格的再度自我重塑,包含著來自于“十七年”時期革命浪漫主義美學的淵藪;新世紀文化產業大整合與電影“全球化”語境中,主流意識形態與商業消費目的混成合謀,而結構出的新型美學修辭與敘事范式[25](PIX);中國文藝敘事的美學傳統與“史補”觀念[26](P63);中國電影早期創作實踐形成的影像傳奇敘事慣習[27];它們集歷史記錄與藝術敘事的差異與共性,在正統史學書寫之外,融入浪漫主義式的想象再現與完型填充,完滿了電影文本之于“真實—虛構”維度的二元融合。
作為主創團隊時隔十年之后,就“獻禮”建黨周年慶典推出的同一題材作品,為避免雷同而有意尋求新的角度,似乎是藝術審美追求獨創性,而非復制性的內在本質要求使然,也是歷史話語在其核心價值不變的情況下,如何實現講述方式的自我更替,以適應時代本身變化的必然。有基于此,《1921》采用了與《建黨偉業》迥乎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物視角與敘事策略,它不再是全知視角下“編年體”式漫長歷史縱貫線的自然光效呈現,而是選取了“個體化、日常性”[28]的角度,試圖拋卻“歷史”本身的駁雜,回歸到“以人為中心來敘事和表情達意”[29]。影片一改前作向歷史無限敞開的自然主義光韻,而敘事寫史的中心完全凝縮移置,變成了僅就中共“一大”召開的前后,鋪展開來的單線敘事,以組織者李達和其妻王會悟的日常生活及為會議籌備所作的努力為情節線索,具有極度接近個體敘述的主觀視角,那么電影文本及其寫史功能的呈現與傳遞,也就近乎個體口述自我經歷的平凡事件。宏大敘事的基調看似被降維,但其仍舊是一種集體記憶,不過是由個體講述而已[30](P144),而這種講述,不僅無損于其權威意義,反而可以成就話語佐證的邏輯,變為具有活性的神話傳承,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言的“神話—歷史”:“只有口耳相傳的傳說,卻同樣也被宣稱為歷史。”[31](P58)
個體生活體驗的零度介入形態呈現,力圖彰顯歷史事件背后濃郁的生命質感,神話敘事及權威話語的隱逸與散落,為其與“日常性”疏離的偏振化閃現,營造了藝術想象性再述的空間留白,它不必擔憂會對被普泛認同的公共史實產生僭越與冒犯,反而由于自我的輕盈圓潤釋放的善意美好,而獲得了一種自在盎然的詩意共鳴。關于清新與純真的書寫與定義,重新厘定與呈現了藝術浪漫主義風格的內涵與外延,而對其恰當應用的二度生產實踐,也是創作團隊力求避免過度商業化消費的油膩渲染,剝去歲月侵蝕后的斑斑銹跡,還原歷史本身所處年代原初樣態,同時滿足當下審美認知訴求的復合型探索。
《1921》在著意塑造一種貫穿全片的“氛圍”,它并非完全指向時代考證的歷史還原,也不是僅僅依賴浪漫情懷主導的懷舊想象與當下詮釋,而是恰恰混合著影像空間質素延展與人物精神狀態顯現的某種“感覺”,也就是“感覺的現實主義之氤氳”氣質。歷史時序展開的片段影像空間中,“人物”與“景致”作為內容承載其內,構筑特殊影像審美視聽感知的狀態。室內低飽和度照明近似夜景,而以黃灰色調形成高對比度的明暗相間,倫勃朗式典型布光“利用光照角度創造出立體感……喚醒影像生命”[32](P169),監獄內鐵柵相隔的陳獨秀與李大釗,主觀抒情的音樂伴以低沉磁性的嗓音,發出“時代使命即將降臨”的宣言;戶外則以明亮的青藍色調構置精巧的運動鏡頭,年輕的毛澤東搭載有軌電車并將身體探出車外,主客觀視角切換的活動畫面間,閃現一個青年眼中繁華的十里洋場的時尚光鮮,而《新青年》雜志的廣告招牌并不突出地矗立于街邊,意喻新時代的思想浪潮正在悄悄萌發。一種頗具后現代性的歷史“情境”的轉移再現[33](P229),反向輸出的“詩意現實主義”手法,極致抒情中的浪漫主義書寫[34](P106),但卻充滿了積極樂觀的熱情與純真。而這一貫穿全片的“人景合一”的感覺狀態,正是用審美的精致浪漫,試圖營構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言說,一群致力于救國救民的年輕人如何開啟他們理想之路的故事……
三、意圖蘊藉:歲月鋪陳的邏輯交叉點與內在傾抒的粘合劑
時值周年慶典紀念的重大時刻推出的建黨題材系列電影作品,除去之于作品內容與創作行為的雙重層面構建對其認知的“歷史—藝術”維度,還潛藏著一層關乎“文化記憶”的隱含維度。正統歷史現實主義的樸素書寫,輔之以人性化的細節描摹;延展的時間線索中消減主體敘事的強度,而填充商業消費性傳奇軼聞的類型合成;個體化、日常性視角寫史構建集體認同的“感覺現實主義氤氳”與詩意共鳴;敘事策略應時而變,似乎與時代語境密切相關,或許是對其“獻禮”功用的“文本—生產”定位的呼應,也是揚·阿斯曼關于“文化記憶”功能的表述,即它有除去日常狀態的另一重“非常”時間——“節日及儀式慶典”的價值,以補足常態世界中被忽略刪減的部分維度[35](P57)。
“非常”時間牽涉紀念的意義,與過去及現在的二元性對照相關,正如伊曼努爾·列維納斯所認知的以逝去區分的將來與現在,而將來必須于現在出場,才能抵消逝去對于時間意義的消解,那么兩者必須直面彼此的論斷[36](P69)。“過去—現在—未來”的全方位覆蓋,指向“文本內容—生產語境—建構意義”三重動作,三者之間環環相扣乃至順序鏈接,兩兩之間又因不同的界域阻隔,而形成復雜的相互指涉關系,因此在這類交織的淆雜中,要找到某種統一性,以防止彼此割裂抵牾,而從所謂內在精神領域入手,也許是更為妥當的選擇。
由精神內在的維度切入其中,它又涉及如下幾個方面:柯林伍德提出的歷史哲學的“主觀性”,指向歷史書寫或講述的思想知識體系[37](P5);杰弗里·丘比特認為的歷史與個體記憶的功能性類比,即歷史作為個人記憶的社會對等物[38](P45);貝爾納·斯蒂格勒所持的觀點則是技術體系是人類記憶的載體,而歷史的記憶是關于逝去之人的故事,擁有其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所在[39](P177)。由此綜合而言,歷史書寫可以是在主觀知識系統觀照下,由個體記憶形成集體認同,并通過一定的技術體系講述既往逝去的實踐,而其中較為重大的節點,則需構筑時間意義上的儀式加以不斷重述,從而證明自我的存在價值與神圣意義。
作為人的精神生產的話語言說機制運作,實質上是在持續模擬一個人的訴說與被訴說的狀態。而電影創作本身又是集大眾性、通俗性與虛構性為前提的敘事行為,復現世界的訴求凸顯藝術“模仿性”特質,特別是對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模仿[40](P410)。那么,“歷史—藝術”文本自身,同樣可以“人”的模擬形態出現,即以擬態畫像的方式被賦予“人格化”,而后研究本文本身被視作一個怎樣的人,以及在某個重大歷史時刻,如何述說自己的故事與故事里的自己。在這種頗具藝術浪漫性的想象思考中,“人格化”的策略并非明確指向講述者、敘述視角或被呈現的人物、時間與世界,而是根據需要在幾者之間自由轉換,甚至是囊括所有的一種融合于人的形象的綜合,是關乎審美者的心意與物象統一的“意象”[41](P258)。建黨題材電影文本的“人格化”意象,可以按照年齡區間畫像的人物形態出現,代表作品完成言說與被言說的功用。
《開天辟地》可以被虛擬為中年“人格”,它涵蓋了影片文本內容包含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及片中出現的系列人物形象。影片整體上保持了一種正統敘事的成熟穩重風格,政論性的旁白如歷史教科書般工整標準,而場景視覺設計、情節重心把握亦在中規中矩間顯現出理性思考的平穩節奏。把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階層狀況、歷史重大轉折事件、新興思想活躍傳播等宏大背景沿時間線順序展開,娓娓道來的講述,有一種紀錄紀實的風格內在追求隱含其間。尤其是影片涉及的眾多歷史人物的角色人選,大多都是當時具備比較優秀演技的中年演員充任,而并非之后流行的商業性票房明星及新世代網絡流量擔當。相較而言,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電影創作生產的運行機制與核心理念,仍舊在相當程度上,維持著將電影視為嚴肅文化作品功用的基本認知,文以載道的教化思想與經典現實主義還原歷史的反映論依然占據主流,而且牽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選題,又恰逢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的關鍵時刻,而意圖推出的“獻禮”慶典之作,自然更為重視如何經由一種權威性的文藝敘事,完成時代意識形態所要求的正統話語表述,呈示從歷史之源走來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主體合法性地位。而站在精神文明建設的高度,20世紀90年代文藝創作的指導思想,所提倡的“主旋律”意識,亦“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42](P119),也契合中正持重的“中年”人格化塑造品格。同時,電影作品制作上映的1991年,正是中國面臨復雜的國際格局演變,需要穩住陣腳,確立后續發展道路與目標的關鍵階段,而牽涉歷史大背景下的時代意識形態話語再述行為,卻是要求文藝創作在書寫“黨史”之時,必須顯現出一種正統審慎的態度與尺度。
《建黨偉業》則力圖呈現一種時間向量延展中的“老年”人格視角。該片是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而推出的經典力作。壽齡九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稱為“鮐背之年”,其表層含義來源于魚背后的斑紋,意指高壽老人身體與精神上深深烙印的歲月痕跡,也是泛指人歷經歲月滄桑之后寧靜安詳的智慧與淡然,以及回眸一世走來的從容不迫與良多感懷。在現代數學計數的“十進制”體系中,九也為極致之數,代表著質變來臨前的量變峰值。從年齡階段界定的“人格化”定位來看,《建黨偉業》的電影文本形態,恰恰體現出了“老年”性狀的“擬人化”特質。當一個人處于老之已至的狀態,則似乎更有回憶少時往事的祈愿。這部作品的時間線,是以比較久遠的“武昌起義”為起點,這一設定也是與該年同時是“辛亥革命”勝利100周年的歷史計時刻度相關,雙重時間價值迭加的紀念實踐,以回憶往昔、不忘初心的隱藏點題,確立其內蘊精巧的敘事策略。全片情節節奏與影像氛圍始終處于一種時斷時續與朦朦朧朧的狀態中,像極了輕睡老人模糊的意識里那歲月繾綣的倒影。相較于《開天辟地》那人到壯年時處世的中正至大與一絲不茍,《建黨偉業》則顯現出了老者智慧的圓融通透與舉重若輕,它可以不動聲色地容載不同性質的復雜信息,并在巧妙處理其比例體量與兼容關系時,實現多重復合的訴求價值。這部影片誕生的2011年,也正是需要整合一些復雜因素完成創作文本的年代,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文化廣泛傳播的創新目標,產業化快速推進大背景下電影創作面臨的市場化競爭任務,都要求此時的創作實踐如要同時完滿歷史書寫、藝術審美、商業回報的多重場域表述,唯有形構一種多智近妖的“老辣”謀斷。影片采用了當時比較盛行的“全明星”戰略,演員皆為來自世界各國、兩岸三地成名已久的“大牌”從業者,周潤發、趙本山、王學圻、范偉、馮鞏等“老戲骨”,或主演、或客串,其表演似蜻蜓點水、波瀾不驚,似乎也與電影作品本身內含的老年“人格”畫像恰巧吻合。
《1921》相較前面兩部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在立意上就試圖規避以往較為常用的宏大敘事視角,而傾向于核心事件集中呈現的個體性與日常性敘述,從片名就可以看出,它改變了某種直白的先在主體規定性,而使用了年代指稱的中性客觀命名。影片相對應的人格畫像,則指示為一種時代文化流行趨勢所推崇的“少年感”,更像是以主流獻禮名義呈現的另類青春電影書寫。電影作品視聽語言敘事的調性、人物角色的演員配置及動作表情的表演規定性設置,都顯現出了一種盎然勃發的青春氣質。正如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所言:“少年強則國強”[43],《1921》試圖從更為世俗化的角度,講述一群“自強少年”如何于百年前的青蔥歲月中相聚匯集,立志改變老大帝國的落后面貌,尋求救國強國之路的故事。影片大量使用年輕人所耳熟能詳的生活場景,以符合日常體驗感知的情節橋段,連接構置“一大”召開前籌備階段的歷史情形想象,比如李達訓練王會悟應對軍警盤問的多組鏡頭切換組接,王急速奔跑的畫面插入了輕快版《國際歌》配樂,在完成主體情節推進的同時,將充滿活力的年輕夫婦之間的小小情趣生動展示出來;青年毛澤東邁著歡快的腳步,想要進入在滬法國人節日狂歡的隊伍,卻被租界巡捕趕出領館大門,而后他于上海街頭夜色中盡情狂奔的寫意鏡頭,穿插著其少年時期在湖南老家的山林間,被父親追打的場景,依然輕快旋律的主觀配樂與升格攝影慢放間,意寓著一代青年人從反抗封建父權到走上反帝革命道路的激情成長,也以個體化形象的浪漫書寫,指涉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最初誕生的生命歷程。對于電影文本外的2021這個年度而言,它首先直接面向的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慶典這一重大歷史時刻中的重大事件,是非常態的慶典時間里呈現逝去時代的平常生命體驗。在電影作品誕生的2021年,時代語境決定了它的敘事話語策略的不同,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兩個一百年”交匯的時間節點,總結過去、把握現在、展望未來的形象化書寫,是新的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綜合話語表述[44],作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啟的肇始,呈現一種全新的符合其年齡隱喻指涉的“青春”少年人格化敘事,也是理解其核心精神的應有之義。從世界格局演化的角度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的提出,同樣預示著中國共產黨面臨時代機遇與挑戰的背景下,團結中國人民,保持發展活力的光榮使命與任務。這也是電影作品《1921》重啟“少年中國”意象敘事的多重話語因由所在。影片亦體現出了強烈的指向未來的象征,百年前段落出現的李達夫婦居住地點附近鄰家少女的形象,呼應百年后尾聲段落呈現的小學生群體參觀“一大”會址的情景……孩子的意象不斷復現,意味著一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傳承……
結語
建黨題材電影作品于特定年度的持續再生產,是以“獻禮”的名義構筑公共歷史記憶空間的藝術實踐,它作為一種典型的儀式慶典,首先要滿足的是基于題材內容設定的歷史書寫價值,即圍繞“人物”與“事件”的節點與編排比重,形成的寫史方法與體例應用;其次是遵循電影本體藝術規律的創作方法與風格特色的限定,即運用“真實—虛構”雙重維度之間的張力,構建正統現實主義主體與審美浪漫主義填充的二元關系;再次,需要探討文本內外的話語生產語境,它亦關注情節內容涉及的時代與電影創作出品的時代之間的量差,而將文本內外所涉及的講述人、敘寫視角及人物角色混合而成的“人格”畫像,是理解該題材序列作品所包含的眾多復合性指涉關系及其電影作品敘事策略與話語言說機制的便捷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