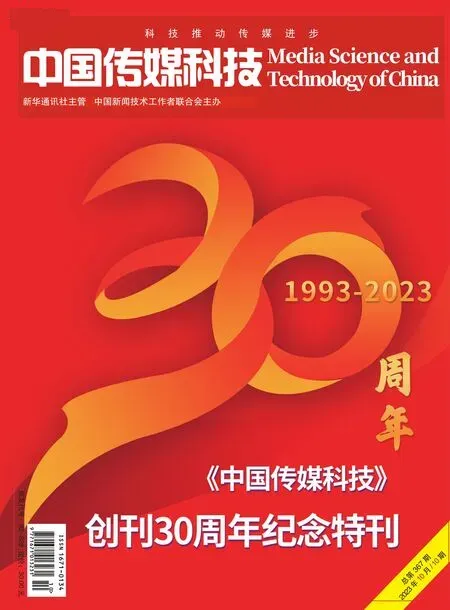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受眾對于科普信息接收方式的研究
呂 豐 辛夢茹 謝 地 張文慶 何 文* 胡漢昆*
(1.武漢大學人民醫院藥學部,湖北 武漢 430060;2.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藥學部,湖北 武漢 430071)
1.研究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2021 年6 月,國務院發布《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 年)》,強調“建立完善科技資源科普化機制,不斷增強科技創新主體科普責任意識,提升科技工作者科普能力”。[2]作為藥學工作者,在數字化媒體盛行的當下,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創作并高效推廣科普內容責無旁貸。為了更好踐行這一使命,我們有必要對新媒體時代下的科普信息傳播行為進行探討。科普信息的傳播效率依賴于受眾對信息的接收方式,深入研究適合科普知識的傳播媒介和策略,從探索、研究和總結現代社會信息傳播模式的發展和接收方式的演變入手。
2.文獻綜述與研究問題
2.1 傳播媒介和科普信息接收方式的發展
科學普及簡稱科普,是指利用各種傳媒以淺顯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讓公眾接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推廣科學技術的應用、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的活動。科普工作從其誕生之初就具有完全的社會屬性。17 世紀末以牛頓力學革命為基礎的近代科學突飛猛進,18 世紀由法國資產階級領導的啟蒙運動則是科學傳播的第一次高峰。理性思考和以人為本的科學意識逐步生根于社會意識,科普作為源流讓科學知識從少數精英科學家流向普通大眾,為日后的數次工業革命打下基礎。在我國,自1950年起,科普是“中華全國科學普及協會”的簡稱,1958 年科協與科普兩大團體合并為中國科協,1979 年“科普”一詞被收入《現代漢語詞典》成為規范化的專有名詞,以科普為前綴的組合詞匯大量涌入社會公眾視野。[3]
從近代至今,人類社會慢慢形成了通過郵局、快遞、課堂、報紙、宣傳欄、講座、科普讀物、圖書、期刊、展覽館、博物館等傳播媒介進行信息傳遞或傳播的方式;19 世紀至今逐漸出現了電報(19 世紀30 年代)、電影(1872 年)、電話(1876 年)、廣播(1903 年)、電視(1925 年)、傳真(1929 年)等信息傳遞或傳播媒介;近三十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出現與發展,網站(1991 年)、微博(2009 年)、微信(朋友圈、公眾號、小程序)等新型信息傳播媒介不斷涌現,特別是近幾年來短視頻的傳播方式如抖音短視頻、快手短視頻、YouTube 等,正在快速成為人們接收科普信息的方式。可以看出,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的科普渠道發展,正由單向、低效的傳統模式迅速轉變為雙向和互動的多元化模式。
2.2 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
① 在新媒體時代,從受眾接收信息的角度,何種媒介適合科普信息傳播?
② 不同年齡受眾在接收科普信息時,有何種行為特征?
③ 根據受眾接受信息的方式及行為特征,如何提升科普信息的傳播效果?
3.研究設計
3.1 基于5W 理論的研究框架
美國學者H·拉斯韋爾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首次提出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個基本要素,形成了“5W 模式”或“拉斯韋爾程式”。這五個要素分別是Who(誰)、Say What(說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過什么媒介)、To Whom(向誰說)、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4]“5W 模式”奠定了傳播學研究的五大基本內容,即控制分析、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以及效果分析。5W 理論為探索科普傳播過程的結構和特性提供了具體出發點和理論框架。
我們擬將5W 模式中的“Who”具象為科普信息的制作者和傳播者,準備從5W 模式中的制作者和傳播者(Who)、傳播媒介(In Which Channel)、接收者(To Whom)的角度出發,對科普信息的傳播過程、傳播內容和傳播效果進行深入分析。
3.2 基于5W 理論的研究綜述
3.2.1 科普信息的制作者和傳播者
從“制作者和傳播者(傳播主體)”的角度,根據文獻以及課題組的總結,傳播主體的可信度可分為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相對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普通的制作者和傳播者。[5]其中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主要是指政府部門、官方新聞媒體以及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等;相對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是指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企事業單位、知名學會或協會等;普通的制作者和傳播者主要是指普通大眾或有一定信息傳播影響力的知識掌握者、傳授者以及知名人物等。“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和“相對權威的制作者和傳播者”具有機構對個人進行信息傳播的特點,“普通的制作者和傳播者”則主要是指個人對個人進行信息傳播。
3.2.2 現代社會科普信息傳播媒介的分類與特點
現代社會科普方式已由科學知識的單向線性傳播轉變為公眾和科學界等多主體平等、雙向互動的過程,更強調以受眾為中心的科學教育。[5]這里的“互動”具體指“信息的制作者和傳播者”發布信息之后能夠收到信息接收者的反饋和評價。現代社會信息傳播方式幾乎都有不同類型和程度的互動方式。傳統媒體例如:報紙、圖書,可通過讀者和作者書信來往的方式實現有時間差的互動,而現代的新媒體方式例如微博、微信(朋友圈、公眾號、小程序等)、短視頻,通過評論、留言、私信、彈幕、彈窗等方式實現即時互動。研究認為,只有實現了互動的傳播才能被視為真正的有效傳播。[6]
現代社會新傳播媒介根據受眾的需求分為精英新媒體和大眾新媒體。[7]其中精英新媒體主要指以擁有前衛傳播意識,掌握一定的財力、智力、算力等傳播資源的受眾為主體的新媒體。譬如MOOC 慕課平臺、學習強國App、專業技術論壇等。而大眾新媒體則以大眾傳播為特征,通過信息展示(靜態)和推送(動態)的方式,提高信息傳播效率,降低信息傳播的成本,譬如:短視頻平臺、今日頭條、微博、微信公眾號等。[8]然而以短視頻平臺為代表的大眾新媒體因創作者的專業層次不同而存在科普作品質量良莠不齊的情況,在更高的傳播效率下,摻雜某些商業目的或過于夸張的“標題黨”可能會產生知識誤區造成誤導,這是值得注意的。
3.2.3 科普信息的接收者分類及其媒介偏好和行為特征
課題組根據接收科普信息后反饋的具體情況,把接收者分為被動接收者、主動接收者或互動接收者。被動接收,指接收者沒有主動搜尋目標信息,而是被動接收傳播媒介傳播的信息,并且沒有對信息進行反饋。主動接收或互動接收,是指科普信息的接收者主動搜尋信息并接收,且對信息進行反饋。不同的信息接收者處理信息的行為和信息接收偏好是不同的,因此對受眾進行細分,針對不同種類的受眾設計差異化的科普策略,可有效提高科普信息的傳播效率。
4.受眾對科普信息接收的行為與習慣
課題組根據信息接收者的年齡和行為能力特征,把現代社會人群信息接收者大致分為老年人群(60 歲以上)、中年人群(45~59 歲)、青少年人群(13~44歲)和嬰幼兒人群(12 歲以下)四類。由于嬰幼兒人群信息接收自由度受監護人控制,不作為本項研究的研究對象。
4.1 老年人群
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2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60 歲及以上非網民群體占非網民總體的比例為41.9%。我們推測:由于老年網民頻繁使用手機上網、網絡購物等與生活相關的網絡應用,導致了較大增幅。老年人群中使用率最高的五類應用依次是即時通信(90.6%)、網絡視頻(84.8%)、互聯網政務服務(80.8%)、網絡新聞(77.9%)和網絡支付(70.6%)。此報告還表明,網絡新聞在老年人群中大受歡迎,其使用率較整體網民高3.2%。[9-10]基于上述數據,可以歸納出三個特點:(1)老年人群瀏覽網絡信息的時間相對充足;(2)老年人群關注信息的途徑逐漸從報紙、電視轉向網絡;(3)生活類、健康類科普內容更易被老年人群接受。對于我國老年網民人數激增的現象,我們推測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我國人口結構老齡化日趨增加,導致這部分人口基數逐漸龐大;其次,由于疫情的影響,老年人群外出娛樂活動減少,需要一些可替代的娛樂活動來消磨時間;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老年人群信息接收手段從以前的接收廣播、翻閱報紙、收看電視的信息傳播,轉向通過手機、電腦等新傳播媒介;最后在心理層面,因為疫情導致老年人群社交的局限性,其更容易產生孤獨感,因而更容易依賴新型的傳播媒介來獲取信息,并因其豐富的內容以及時效性而更容易產生用戶黏性。
那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老年人群在新媒體形勢下的信息傳播效率呢?筆者總結為以下兩點:①居住環境極大地影響著老年人群的信息接收行為。據董夢飛等研究報道,城市老年人群有強烈的學習信息技術,提升信息素養,融入現代生活的意識[11];而農村老年人群使用新媒體的主要原因是加強和外界的聯系。[12]經濟收入和文化程度對老年人群使用新媒體終端的普及率有影響,其中文化程度是核心變量。[13]②身體狀態和認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老年人群信息接收行為。老年人群因為體力、視力,或接收設備操作門檻等,在接觸新媒體時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礙。[14]
4.2 中年人群
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在不同年齡人群中表現出明顯的偏好差異,中年人群作為主要信息受眾,對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接受占比均較高。“收視中國”王平的調查顯示,在被訪者接觸占比相對領先的媒介中,電視接觸占比隨被訪者年齡提高而提高,中年人群中,僅有50.8%的人每天都會在家里接觸電視,而老年人群每天在家里接觸電視的人數占比達到了96.5%;此外,中年人群在家里上網的比例則為51.7%,而老年人群在家里上網的比例則降低到22.6%。此外,上述調查還指出,中年人群通過上網獲取信息的目的前三名分別為社交、新聞和視頻。[15]然而在應對新媒體帶來的信息接收方式變革時,中年人群也存在著一定的困境。在另一項調查中,以微信為例,中年受訪者在選擇“日常使用微信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一題時,89.3% 選擇了“微信功能操作運用不熟悉”一版,位列第二的困難為“甄別信息方式尚不明確”,有 63.9% 的受訪者選擇此選項,表示“曾被子女說不要盲目相信這些文章,但又不知道到底該相信哪個、不相信哪個,或者可以轉發什么、不要轉發什么”等。[16]朱紅濤等以使用信息平臺的中年用戶為問卷對象,調查中年人群的信息瀏覽特征和習慣。結果顯示,中年人群主要通過智能手機來獲取信息,信息閱讀頻率較高但時間有限,多為碎片化閱讀。[17]
結合我國社會現實和上述調查,可將中年人群的媒介偏好與行為特征大致歸納為兩點:①碎片化閱讀時間。由于中年人群既要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還肩負著撫養下一代的責任,其時間也主要花費在工作上,閑暇之余主要通過手機等移動端設備接收信息,多為碎片化閱讀。而碎片化閱讀主要體現在閱讀內容和閱讀時間的碎片化兩個方面,具備很強的互動性。[18]②高品質信息偏好。中年人群作為社會活動的中流砥柱,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各行各業知識儲備的差異,對于科普知識的需求還是相當廣泛的。因此,如何通過中年人群信息接收特點來創作和輸出高品質科普產品,是科普創作者應該關注的重點。
4.3 青少年人群
青少年人群在信息接收方面同樣體現出明顯的主題偏好和閱讀特點。在謝興政等人對福州六所高校大學生的問卷調查中,九成以上大學生習慣每天觀看短視頻,其中,每天觀看1 小時以上的大學生占比87.20%。[19]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發布數據,超過70%的青少年在熬夜時刷短視頻。[20]從青年人群的觀看行為上,視頻、圖片、文字、音樂是青少年最喜愛的表達元素[21],半數以上學生通過觀看短視頻來獲取各種趣味資訊。[19]但是在權威信息方面,超過80%的青少年更相信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由此可以看出“習慣接觸的信息接收方式”和“信任的信息接收方式”并不一致。[21]此外,72.7% 的受訪青年表示一般不會主動搜索信息,而是建立在某一兩次主動搜索基礎上的被動被推送,這是基于大數據算法的個性化推薦。[20]但是陳瀅通過問卷方式發現,用戶認為推送內容同質化嚴重,不能準確推送符合用戶需求的信息,對“個性化推薦精準”的認同度不高。[22]
基于上述研究,對于青少年人群的媒介偏好與行為特征可以做如下總結:青少年人群的時間主要花費在學習或工作上;在閑暇時間,主要通過手機接收信息。由于思維活躍以及網絡工具的使用能力較強,其信息搜尋模式的主動行為多于被動行為,交互的媒體互動方式居多。同時由于工作與學習占據較多時間,青年人群對碎片時間的利用率也較高。[23]
5.提升科普信息傳播效果的策略
5.1 優質科普信息的傳播媒介和內容特點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新興的媒介形式凸顯,科普信息傳播的媒介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科普信息傳播不再局限于如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微信(包括公眾號、朋友圈)、微博和網絡短視頻平臺等傳播媒介的融合協作為科普信息的傳播與分享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同時,對媒體傳播形式的評價也從傳統的收聽率、收視率等指標轉變為播放(閱讀)量、點贊量、彈幕數量、評論量、收藏量、投幣數量、轉發量、有償購買的銷售量和金額等指標。[24]通過綜合衡量某個主題內容的傳播效果,能夠更加準確地對受眾的信息接收行為和瀏覽偏好進行描述,以便科普生產者以此為依據優化科普產品,滿足不同年齡段受眾的需求。[25]
目前科普類微信公眾號數量龐大,相關主題的微博也是信息量巨大的開放平臺。微博兼具媒體和社區屬性,具有用戶草根化、滿足傾訴要求、內容微小化、“背對臉”式信息交流、傳播碎片化、傳者和受者地位平等的傳播特點。[26]然而,陳曉華的研究顯示,17~33 歲年齡段的用戶是微博用戶的主力人群,占比為 79%。[27]如前所述,這個年齡段有科普閱讀習慣的受眾,以碎片化閱讀為主,閱讀目的性較強,往往只瀏覽自己的微博主頁中刷新出來的微博,不去主頁瀏覽,且據報道,學歷越高、年齡越大這個趨勢越明顯。[28]在2012 年8 月,微信公眾平臺正式推出,提供了一種公眾號發布信息、個人用戶收聽訂閱模式。與微博的傳播特點相比,微信公眾號具有點對點的大眾傳播方式、干擾較少的傳播過程、真實且實時接收的觀眾、受眾篩選后的選擇性、強大的信息擴散能力等優點。[27]微博和微信是新媒體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科普承載媒介,以靜態信息(如文字和圖片)的呈現形式為主,適合有一定閱讀習慣和閱讀偏好的受眾,以中年人群為主。
短視頻平臺與其說是一種科普信息的傳播新媒介,不如說是在媒體融合大背景下的一種接收門檻較低的信息體裁,目前幾乎在各大主流平臺均有短視頻欄目。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為10.44 億人,較2022 年12 月增長1380 萬人,占網民整體的96.8%。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10.26 億人,較2022年12 月增長1454 萬人,占網民整體的95.2%。[10]短視頻以其傳播主體多樣化、受眾龐大、沉浸式體驗和即時互動性一躍成為受眾參與科普傳播的最主要渠道之一。[29]在短視頻傳播效果的研究方面,很多學者從不同的理論出發,研究短視頻傳播效果的影響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①短視頻的標題,運用設置懸念、刺激互動等特殊策略來撰寫標題[30]、標題的“互文性”(即與系列短視頻標題相似,使接收者產生觀看聯想)對短視頻傳播效果的正向作用[31];②短視頻的時長和畫面比例;③短視頻的內容,以正能量傳播、主題宣傳、知識普及為主題,形式短小精悍,感情色彩強烈,配以背景音樂的抖音短視頻易成爆款[32];④有固定的科學傳播者,注重與用戶的互動,采用情景劇、動畫等創意形式的科普視頻往往具有更高的傳播力[30],且視頻創作者身份的權威性更易獲得受眾關注,帶來視頻熱度。[33]另外,楊達森等人通過研究發現,短視頻有企業認證會對傳播效果起抑制作用。[31]
5.2 提升科普信息傳播效果的方法
在新媒體時代,基于社交平臺和短視頻平臺,推動科普傳播提質、增效、擴容,對于助力科技創新,提升全民科學素質具有頗為深遠的意義。基于前文對受眾及其信息接收方式的綜述和思考,筆者將提升科普信息傳播效果的方法總結如下:①內容引人入勝,出鏡者顏值較高,字幕標題醒目;理解門檻較低,淺顯易懂是普及的前提,在此基礎上的科學內容要有專業審核和把關。②應更多利用較短的閱讀或觀看篇幅(約60~180 秒)來呈現科普內容。③美工和渲染包括音樂等呈現元素要具備一定藝術美感,杜絕形式上的粗制濫造和低俗庸俗。④根據科普內容對受眾進行媒體區分,在偏好人群中選擇播放量高,關注多,轉發多,點贊多,評論多,有互動的平臺上進行內容投放。⑤科普主題應該有連續性,作為長期具有持續曝光量的科普內容更能引人入勝,從而激發受眾更高的認可和熱情。
結語
科普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公眾的科學素養,是依靠多種媒體形式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實現的。伴隨著更強的互動性,更廣的傳播性、更大的信息量和更低的傳播成本,新媒體傳播形式的發展日新月異,也為新時代科普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基于新媒體的信息傳播模式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越來越多地依賴微信、微博和短視頻平臺。作為科普資源的創作者和傳播者,應順應新媒體時代的大潮,積極探索提高受眾信息接收效率的手段,讓更加準確有效的科學話語從信息的洪流中脫穎而出。
本文運用拉斯韋爾的“5W”模式對新媒體時代科普信息傳播進行媒介分析、受眾分析和效果分析,通過聚焦于不同年齡受眾對信息接收方式的特點和差異,綜合分析了老年人群、中年人群和青少年人群的生活習慣、閱讀行為、信息接收偏好和反饋手段等因素對最終信息接收效率的影響。對于老年人群,獲取閱讀時間相對充足,獲取手段也逐漸從報紙、電視轉向網絡,其中對生活類、健康類科普內容尤其偏好;對于中年人群,由于閱讀時間的碎片化,則對于高品質、專業針對性強的科普內容需求更高;對于青少年人群,則更多利用閑暇時間的手機移動端獲取信息,新穎的題材和表現形式更能引起這部分受眾的關注。基于不同的信息傳播媒介提出了優質科普信息的內容呈現方式和傳播手段,通過對目標受眾人群的細分,采取各具特色的傳播策略,打造個性化高品質的科普傳播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