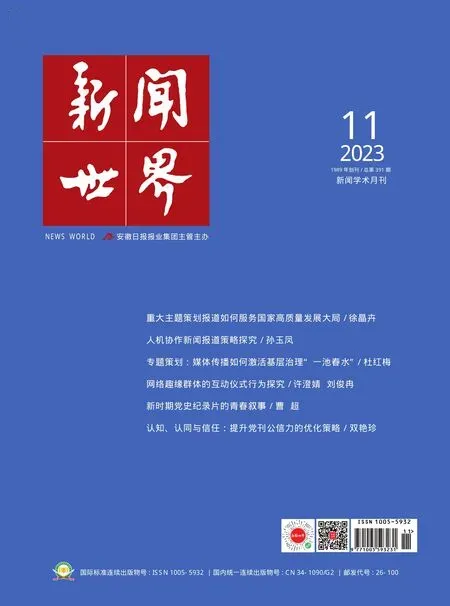新媒體語境下農村地區健康傳播研究
——以皖西地區L村為例
○張 蕊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進政策。國民健康狀況不僅關乎個人和家庭,也是國家富強、社會繁榮的重要標志。“健康傳播是一種將醫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的健康知識,并通過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個社區或國家生活質量和健康水準為目的的行為。”[1]更為廣義的概念認為凡是人類傳播中涉及健康的內容,都屬于健康傳播。健康傳播研究興起于上世紀70年代,隨后得到迅速發展,健康傳播的方式也隨著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而更新。健康傳播旨在提高公眾的健康素養,通過改變和提升公眾對健康知識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從而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最終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是“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為健康傳播提供了更為多元的形式和渠道,新媒介技術被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健康傳播中。借助微博、微信、短視頻等平臺,結合文字、圖片、音視頻等形式,一批主流媒體、專業類的健康傳播機構以及自媒體在新媒體時代走上了健康傳播之路,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目前有約5 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相較于城市,我國農村地區受到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水平影響,農村居民的健康素養相對較低。“2021 年健康素養監測結果顯示,全國城市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30.70%,農村居民為22.02%”[3]。加強農村地區的健康傳播,提升農村居民健康素養,改善農村居民健康水平,不僅關系到廣大農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那么,在新媒體語境下,農村地區健康傳播現狀如何?新媒介技術在農村地區健康傳播中的應用情況如何?存在什么問題?是何原因?有何對策?
L 村位于皖西地區,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村莊,常駐人口約2000 人,以中老年和兒童群體為主。本文以L村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訪談法,探究新媒介技術在L 村的應用情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而思考其原因和對策。此外,由于我國農村地區人口流動性大,L村有一半以上人口常年在外務工、求學,考慮到外出務工、求學人員健康知識獲取受到外界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對L村在地居民的調研展開。
二、新媒體語境下農村地區健康傳播現狀及問題——以皖西地區L村為例
新媒介技術拓寬了健康傳播渠道,豐富了健康傳播的方式,這種影響同樣觸及廣大農村地區。在大眾傳播領域,移動短視頻的低門檻性及內容的豐富性,使其超越了其他媒介形態,成為農村居民獲取健康知識的新渠道。在人際傳播領域,家庭微信群成為人口流動時代子代對親代進行文化反哺的重要媒介,在代際交往中促成了健康傳播。在組織傳播領域,基層組織在健康信息的傳遞和發布中對新媒介技術的利用程度較低。
(一)移動短視頻中的健康內容:自媒體助力鄉村健康傳播
根據第51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3.08億,占網民整體的28.9%。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10.12億,占網民整體的94.8%[4]。移動短視頻操作便捷、收視成本低、內容通俗且娛樂性強,成為新媒體時代公眾獲取信息、娛樂休閑的重要媒介形態。在這一背景下,短視頻成為健康傳播的新途徑,各主流媒體、專業的健康傳播機構、自媒體等紛紛入駐各大短視頻平臺。基于前述移動短視頻的優勢,在農村地區,“刷短視頻”同樣是農村居民的高頻行為,短視頻為農村居民獲取健康信息提供了新渠道。
移動短視頻在助力農村地區健康傳播的同時,也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網民在媒介使用中主動性不夠,健康類信息的獲取具有隨機性。盡管農村網民熱衷于“刷短視頻”,但是缺乏主動搜索意識,較少去主動搜索與自身相關的健康類信息,更多情況下是被動地接收網絡推送的內容,既沒有固定關注的健康領域,也沒有穩定關注的健康類賬號。二是農村網民更易受短視頻中的偽健康信息干擾和誤導。由于內容生產制作門檻較低,把關相對缺失,移動短視頻的內容良莠不齊,尤其是UGC模式下生產的內容,大量偽健康信息充斥其中,如“吃碘鹽防輻射”“憋氣可以檢測肺癌”“紅棗紅糖可以補血”等,這類偽健康信息干擾了農村居民對健康知識的認知和接收。
(二)家庭微信群中的健康信息:社交媒體時代的代際反哺
代際關系即親子關系,代際溝通對于農村中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認知和接收具有重要作用。在農村地區,受到生活環境和數字鴻溝等因素的影響,子代比親代能夠更多更好地接收健康知識,健康素養相對更高。然而,受到外出求學、務工等因素影響,我國農村地區人口流動性大,農村普遍存在老人留守現象,親代與子代的空間隔閡給代際溝通造成了阻礙。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微信在農村被普遍使用。社交媒體跨越了代際溝通的空間距離,為親代與子代之間的信息交流和情感鏈接提供了平臺和載體。借助家庭微信群,子代通過向親代轉發疾病防控、養生知識、醫療科普等鏈接和視頻,完成了代際反哺,實現了健康傳播。
借助社交媒體,遠離家鄉的子代成為健康傳播的主體,拓寬了親代獲取健康信息和知識的渠道,但是其是否達到了子代所期待的傳播效果?根據健康傳播中的經典“知信行”理論,健康傳播效果的實現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是認知層面,即接收、獲取健康知識;其次是態度層面,建立對健康知識的信念,形成積極的態度;最后是行為層面,即被傳播對象調整行為方式,踐行健康理念。在“知”這一層面,家庭微信群中的健康傳播行為,盡管拓寬了親代接收、獲取健康知識和信息的渠道,但親代對家庭群中的健康信息存在選擇性接收的傾向。受到親代時間精力、原有的知識儲備、親子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子代轉發的鏈接、短視頻并不總是被親代點擊觀看。在“信”和“行”層面,盡管親代對家庭群中子代所傳播的健康知識認可度較高,但長期以來的生活理念和行為習慣較難改變,很難真正踐行,導致健康傳播的效果更多是停留在“知”的層面。
(三)基層組織在健康傳播中對新媒介技術的利用程度較低
組織傳播是指某個組織憑借組織和系統的力量所進行的有領導、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傳播活動[5]。作為一個統一系統,L村組織中的領導者和組織成員之間離不開信息的溝通和聯系,領導者需要向組織成員發布通知,組織成員需要向領導者表達訴求,從而完成組織任務,維系組織運作。作為基層組織,L村的健康信息傳播主要依靠宣傳單、大喇叭以及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對新媒介技術的利用程度較低。L村唯一的移動政務平臺是一個名為“L村衛健群”的微信群。該群管理者為該村婦女主任,群成員共159人。群公告顯示:本群主要宣傳計生衛生政策和健康教育。筆者加入該群后,通過線上參與式觀察發現,群內主要發布健康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安排,如疫情防控期間查驗核酸、購買醫療保險、婦女宮頸癌篩查等。作為L村在政務宣傳工作中僅有的新媒體傳播方式,L村在衛健工作的開展中開始適應新媒體傳播語境,但是其所伴隨的問題也較為明顯,如傳播渠道單一,除微信群外別無其他新媒體平臺;傳播內容較為狹隘,僅是對相關政策的宣傳和工作任務的安排,沒有對健康理念、知識的進一步宣傳,且發布頻率不高;傳播形式較為枯燥;信息流向單一,群內活躍度較低,互動性不強。
三、農村地區健康傳播存在問題的原因探究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不論是在大眾傳播層面,還是在人際傳播或組織傳播層面,新媒體傳播方式對農村地區的健康傳播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拓寬了農村居民接觸健康知識的渠道,但是其傳播內容較為駁雜,傳播效果不顯著。基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本文認為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居民的新媒介素養相對較低,以及社交媒體所構筑的虛擬人際交往制約了代際反哺所產生的實際效用。
(一)農村居民的新媒介素養有待提升
媒介素養即公眾接觸和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新媒介素養是指“公眾接觸、解讀和使用新媒介及新媒介信息時所表現出的素質與修養。”[6]新媒介時代的到來,對網民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新傳播技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方式,在帶來便利的同時,要求公眾具備更高的數字能力。另一方面,相較于主流媒體的層層把關,網絡媒體中把關人角色相對缺失,大量自媒體入駐短視頻平臺,UGC模式下生產出來的內容真偽難辨,更加挑戰農村網民對媒介內容的辨識能力。
與此同時,囿于文化和經濟水平的限制,包括基層組織干部在內的農村地區居民新媒介素養相對較低,尤其是農村的老年群體幾乎淪為互聯網時代的數字難民。一方面,農村居民對新媒介的接觸和使用能力相對落后。農村居民的媒介接觸和使用較大程度上是基于娛樂休閑的需求,對于媒介內容往往是被動接收和隨機獲取,在新媒體的使用中缺乏主動性。加之健康素養較低,不懂得也不善于利用新媒體主動搜尋健康知識和求醫問藥。另一方面,農村居民對自媒體內容的辨識能力相對較弱,易受失實信息干擾、誤導,從而阻礙了新媒介技術在農村地區健康傳播中的應用,也影響了新媒體平臺中健康傳播的效果。
(二)社交媒體中的虛擬交往制約傳播效果
如前所述,代際傳播對于農村老年人健康信息的認知和接收具有重要作用,但農村地區人口流動性較大,阻礙了代際關系中的面對面交往。微信的普遍使用,雖然為代際交往提供了一個虛擬平臺,加強了代際溝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親代交往中的缺失部分,并在此過程中幫助農村老年群體獲取更多的健康信息,但虛擬人際交往始終無法達到面對面交流的效果。究其原因,社交媒體中健康知識的有效傳播,既受制于親代原有的知識儲備,也受制于親代對被“反哺”的意愿。部分農村中老年群體受教育程度較低,“數字鴻溝”使其對于子代所轉發的鏈接“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空間的隔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上的疏離,影響了親子關系的親密度,進而影響了親代接受數字反哺、文化反哺的意向。缺少了子代對網絡內容的進一步“解讀”和對親代行為上的“督促”,健康傳播的效果往往止步于“接收”層面,也削弱了代際反哺的實際效用。
四、結論及對策
新媒介技術拓寬了農村地區健康傳播的渠道,豐富了健康傳播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村居民的健康素養,但是也伴隨著傳播內容質量參差不齊、傳播效果不顯著、基層組織對新媒介技術的利用程度低等問題。
面對以上問題,本文基于基層組織的視角,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在衛生健康工作領域,加強對新媒介技術的投入使用。在現有政策支持下,加強對政務微博、微信、短視頻等的利用,打造“互聯網+政務”,發展農村地區移動政務。第二,借助外援,加強對優質健康傳播賬號以及縣級衛健政務微信平臺的宣傳利用。第三,對基層計生干部、村醫等展開培訓,率先提升這類人群的健康素養和新媒介素養,打造農村地區健康傳播輿論領袖。通過輿論領袖,帶動村民健康素養和新媒介素養的整體提升。此外,人口流動背景下的代際交往,更需要子代的主動關懷和耐心反哺,為親代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和數字化幫扶,在彌合“數字鴻溝”的同時,更好地幫助親代提升健康素養,提高生活品質。
注釋:
[1]張自力.健康傳播研究什么?論健康傳播研究的九個方向[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5):45-50+2.
[2]人民網.健康傳播是構建工位體系重要一環[EB/OL].(2020-07-28)[2023-07-06].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0/0728/c14739-31800304.html.
[3]央視網.國家衛健委:2021 年全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達到25.40% [EB/OL].(2022-06-08) [2023-07-06].https://news.cctv.com/2022/06/08/ARTIEGrbIaab0K4CfQaJDEgb220608.shtml.
[4]中文互聯網數據資訊網.CNNIC: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23-03-24)[2023-07-06].http://www.199it.com/archives/1573087.html.
[5]魏永征.關于組織傳播[J].新聞大學,1997(03):31-34.
[6]余秀才.全媒體時代的新媒介素養教育[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2,34(02):11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