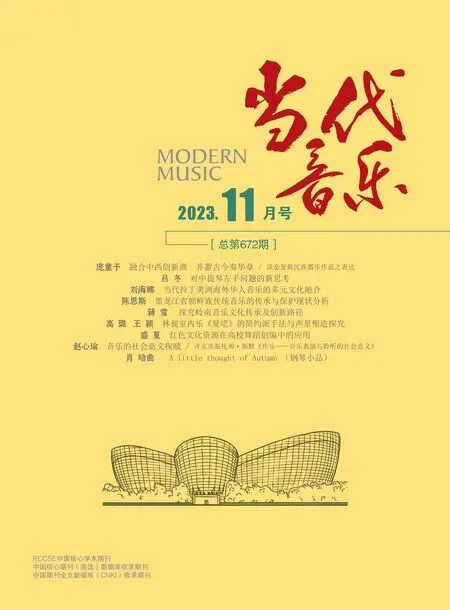淺析海頓在弦樂四重奏中的喜劇性風格
朱家玉
一、 音樂中的喜劇性風格
喜劇, 是美學范疇的重要形態之一。 喜劇性的外部特征是 “笑”, 以引起聽眾發笑、 感受到輕松活潑的氛圍為主要目的。 音樂中的喜劇美通常通過兩種表現方式得以體現。 一種是外在的表現手段。 外在音樂中的喜劇性常常用標題、 文字的形式提醒觀眾, 表現喜劇性這一風格。 例如, 德沃夏克的 《幽默曲》 和圣·桑的 《動物狂歡節》 等這一類的標題音樂。 聽眾在看到標題時便可一目了然作品的喜劇性風格特點。 與之相對應的另外一種是內在的表現手段, 即通過音樂語言表現出來的純音樂。 純音樂的喜劇性主要借助于音樂語言中的和聲、 織體、 節奏、 力度和速度等要素得以體現。[1]相對于外在手段借助標題、 文字的提示, 純音樂中的喜劇性色彩需要聽眾具有較高的音樂素養和音樂欣賞能力, 這樣才能更加容易地理解和領悟作曲家的真實意圖。
二、 海頓的喜劇性風格發展歷程
海頓一生共創作了68 首弦樂四重奏, 正是由于他在弦樂四重奏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貢獻, 因此被世人稱作“弦樂四重奏之父”。 海頓早期的音樂創作大多繼承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特點, 并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在中期的音樂創作中才逐漸形成鮮明的喜劇性風格特點, 在他的弦樂四重奏作品中得以體現。 海頓對于弦樂四重奏這一體裁的確立和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開創作用。
海頓早期音樂創作處于萌芽和發展時期, 喜劇風格開始形成有作品9、 17、 20 這幾首作品。 其中, 在他的早期十首作品中主要效仿嬉游曲的性格特點。 在中期的音樂創作時, 處于海頓喜劇性風格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 海頓創作出了具有成熟的喜劇風格的弦樂四重奏第33 號作品。 其中, 第50 號作品采用了具有探索性的喜劇手法。 在作品54、 55、 64 這幾首作品中, 發展繼承了這種獨特的喜劇風格。 在海頓晚期的音樂創作中, 這種喜劇風格逐漸地退隱消失, 主要是對于巴赫復調作品的致敬, 或者具有浪漫主義傾向, 例如作品71和74。 在作品76 中體現了喜劇創作熱情的回升。 海頓音樂創作生涯中最后的三首弦樂四重奏分別是作品77和103 (未完成作品)。
三、 海頓形成喜劇性風格的原因
(一) 啟蒙運動的產生
18 世紀的下半葉, 歐洲在經濟、 政治、 文化等各個領域均發生了重大的變革。 由于經濟和政治發生了巨大變革引起了文化思潮的強烈反響, 啟蒙運動順勢而生。對于音樂界來說, 啟蒙運動的出現對于音樂家的音樂創作有著重大的影響。 這個時期由巴洛克時期的宏偉豪華的音樂風格逐漸轉化為淳樸明朗、 自然均衡的音樂風格。 這時的音樂家們追求雅俗共賞的音樂。 一方面要求音樂語言淳樸、 質樸; 另一方面, 也注重音樂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的深度。 海頓作為維也納古典樂派的奠基人,音樂風格質樸、 幽默, 音樂內容貼近日常生活, 音樂主題取材自民間音樂, 能夠很大程度地引發大眾的共鳴,具有獨特的喜劇性色彩。
(二) 喜歌劇語言的影響
18 世紀的歐洲, 意大利正歌劇的發展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然而這時新興起來的喜歌劇卻大受人們歡迎。喜歌劇起源于正歌劇中的喜劇因素, 由幕間劇發展而來。 喜歌劇內容取材于日常生活, 貼近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大多是美好的結局, 因此頗受人們的喜愛。 喜歌劇音樂內容輕松活潑、 幽默機智, 喜歌劇語言在器樂作品中也曾出現過。 海頓在創作具有成熟的喜劇性風格的弦樂四重奏作品期間, 同時也從事著不少喜歌劇的創作,例如 《愛唱歌的人》 《藥商》 《漁婦》, 音樂語言生動活潑、 幽默質樸。 海頓所創作的弦樂四重奏這一體裁具有強烈的喜劇性風格特點, 這與18 世紀喜歌劇語言的流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三) 音樂能力的形成
音樂能力的形成離不開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 海頓的家境十分貧寒, 但幸運的是, 在他8 歲的時便獲得了去合唱學校接受音樂教育的機會, 在那里接受了樂器的練習和樂理的訓練。 1761 年, 海頓開始為親王宮廷樂隊服務。 在這任職的三十年期間, 親王十分支持海頓的音樂創作, 使海頓得到了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創作環境。海頓創作的弦樂四重奏作品大多數誕生于他在埃斯特哈奇宮廷工作期間。
海頓的父親是一名農夫, 海頓受到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音樂創作中也繼承發展的體現了農夫身上所蘊含的質樸的特點。 因此, 海頓也被世人親切地稱為 “奧地利農夫”。 大多數杰出的音樂家背后都有一個熱愛音樂的家庭。 海頓的父親也是一個音樂愛好者, 這種熱愛對于海頓的音樂啟蒙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海頓對于音樂擁有巨大的熱情和喜愛, 對于人生、 世界、 自然都保持著樂觀豁達的態度, 因此他的音樂創作風格也充滿著對于自然的熱愛、 對于生活充滿好奇、 幽默、 質樸的情趣。
四、 欣賞者聽覺審美心理分析
(一) 欣賞者的聽覺審美
波蘭哲學家、 美學家羅曼·茵格爾頓是現象學美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 《美學研究》 第二卷中發表的《音樂作品及其同一性》 是音樂美學領域的代表作品。他提出 “音樂作品是純意向性對象” 這一命題。 這種“意向性” 哲學思想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師: 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思想上。 茵格爾頓認為: 世界上存在兩種對象。 一種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對象; 另一種是依附于人的意識的意向性對象。 不可否認的是,音樂藝術正是屬于后者 “意象性對象” 這一范疇。 茵格爾頓強調音樂作品中存在著 “內在時間” 或者說 “主觀時間”, 這種內在的時間只能通過人的體驗去感知。 欣賞者在感受一部音樂作品時, 便展示出了對物理客觀時間的超越。 這種 “超時間性” 在音樂中表現是最具代表性的。 在充滿濃郁喜劇性色彩的海頓弦樂四重奏第33號作品中, 經常出現 “意外的結束” 和 “戲劇性的休止” 等音樂創作手法, 正是利用了 “超時間” 性, 使欣賞者能夠更好地領悟理解其中的喜劇效果。 音樂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 意識活動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需要我們重視起來。[2]
倫納德·邁爾的 “期待-情緒” 理論是情感心理學的主要觀點, 對于探究喜劇性風格的聽覺心理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首先, 產生期待, 接著制造和累積懸念, 最后回到人們思維中的審美視野, 即完成了 “解決”。 在解決時, 要求欣賞者對作品的內涵、 音樂語言有所了解, 才能明白理解作曲家的本意。 否則, 只是一個 “不響的包袱” 罷了。 羅小平把音樂欣賞概括為期待、 交流、 回味三個環節。 第一, 在欣賞之前欣賞者的審美經驗中的既定視野引起一種期待。 第二, 在音樂進行中音樂作品的表達和欣賞者的聆聽形成一種交流。 最后, 欣賞之后欣賞者會進行回味。 它是交流的繼續, 在這一階段能夠拓展欣賞者的既定思維, 深化審美體驗。 喜劇性是營造出一種輕松歡快的氛圍和環境, 一成不變的音樂語言是無法表達喜劇性的。 平穩和諧的音樂進行和意外的結束、 戲劇性的休止形成鮮明、 強烈的對比。 這種對比破壞了音樂發展中連貫的進行, 制造意想不到的喜劇性效果。 弗洛伊德曾經說過: 藝術品的巨大吸引力并非在于其美的效果, 而是在于其釋放了人的本能需求, 滿足了被壓抑的欲望, 消解了因壓抑這些欲望而造成的緊張。 作曲家和欣賞者都會在此過程中找到內心的平衡。
(二) 欣賞者的審美心理
喜劇性是指審美主體 (這里即指的是音樂欣賞者)所認知的主觀判斷與實際表現出來的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喜劇美學大家陳秀英這樣總結概括喜劇美:喜劇美是一種矛盾的體現, 通過不適應、 不協調的音樂語言表現出來。 在這種反常和反轉中, 喜劇性得以體現。 但是, 這里所說的矛盾沖突并非真正的不可化解的矛盾, 而是指由于音樂欣賞者以往的思維定式而引起的誤解。 正是這種誤解造成欣賞者形成緊張或期待的心理狀態。 當然, 這種誤解是可以解除的。 因此, 想要表達喜劇性這一特點的音樂創作者們需要格外注意把握這種誤解中的 “度”, 不可欠缺更不可過分。 如果誤解過當,超出欣賞者的審美認知范圍時間過長, 就會適得其反,造成荒謬、 不可理喻的效果。
音樂欣賞者的音樂文化素養和審美心理結構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對于喜劇的理解程度。 首先, 欣賞者能否理解到作曲家想要表達的喜劇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 歷史和公理標準的影響。 舉個例子, 海頓音樂創作中的喜劇性的表現放在維也納古典時期是可以令人接受的, 為大眾所津津樂道。 但是, 如果同樣的喜劇表達手法放在巴洛克時期, 聽眾只會覺得不可思議、 荒誕無比, 達不到良好的喜劇效果。 更不用說, 這種喜劇風格的創作在當時是不具備出現的條件了。 其次, 欣賞者聽覺審美同時也受到欣賞者心理結構的限制。 喜劇審美語境中的理性成分和感性成分需要處理的均衡得當。在喜劇效果中感受到的是由于誤解而造成的緊張, 并非悲劇那種壓迫感, 讓人感覺到透不過氣。 喜劇審美心理活動一般是: 原先造成的緊張得到解除和原有的期待發生逆轉, 上一秒的愕然大驚可能下一秒就會轉變成恍然大悟。 黃自把音樂欣賞分為 “情感的欣賞” 和 “理智的欣賞”。 “情感的欣賞” 指的是由于音樂語言中旋律、節奏、 和聲、 調性、 速度等要素所引發欣賞者的各種情緒和情感。 “理智的欣賞” 指的是對于音樂結構美, 即曲體美、 和聲美、 曲調美的理解。 在音樂欣賞時應注意二者的平衡, 達到兩者的統一。
毋庸置疑的是, 喜劇風格的形式美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與此同時, 在愉快的背后也通常會伴隨著一種尖銳的批判, 使人在笑聲中沉思、 感悟。 這時, 音樂欣賞者的情緒狀態會更加協調和平衡, 上升到新的審美高度,進入深層次的心靈的愉悅和豁達之中。
五、 典型的喜劇性創作手法分析——以第33 號弦樂四重奏為例
1781 年, 海頓寫下了成熟的弦樂四重奏第33 號作品。 這首第33 號作品一方面是最具喜劇性風格色彩的作品,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海頓喜劇性風格作品的集大成之作。 這首作品是海頓獻給沙皇俄國保羅公爵的, 因此取名為 “Russian Quartets”。 與此同時, 在這首作品中, 海頓創造性地用諧謔曲代替了原有的小步舞曲樂章, 因此又被稱為 “諧謔曲四重奏”。 音樂織體由原先的具有巴洛克音樂特點的華麗風格轉變為維也納古典樂派所體現的均衡明朗的風格特點。 典型的喜劇創作手法: 假再現、 喜歌劇式的寫作、 重音倒置、 雙關語、 音區的夸張對比、 突然的結束、 休止。 樂句不規整、 節奏不規范、 常規節拍、 力度的破壞等都在第33 號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出現過。[3]
作品33 之2 結束部分的主題具有鮮明的喜劇性風格特點, 整個樂章里充滿著喜歌劇般輕松愉快的氛圍。羅小平在 《音樂心理學》 一書中這樣說道: 音樂中的喜劇美可以通過模仿人的語言音調中幽默、 滑稽的因素而形成。[4]在這一樂章里, 運用大量的重復音的快速跑動和饒舌的音樂語言繪聲繪色地模仿喜歌劇中的人物。 這首作品被世人命名為 “玩笑” 這一標題, 主要是因為最后樂章中對休止符的喜劇性處理。 戲劇性的休止在不經意間出現在結尾主題中。 整個樂章在毫無終止感的進行中意外地結束。 聽眾在這里存有疑慮, 并不敢確定樂曲是否已經真正地結束, 直到演奏者放下樂器那一刻才明白, 這正是海頓的機智滑稽風格的音樂表達。
作品33 之3 這首C 大調四重奏因第一樂章中的第二主題和第二樂章中間部分使人聯想到小鳥而得名標題為 《鳥》。 這首作品一共分為四個樂章: 第一樂章是中速的快板, 調性為C 大調; 第二樂章是帶有諧謔風格的稍快的快板, 調性同樣為C 大調; 第三樂章是慢板, 調性為F 大調; 第四樂章是回旋曲結構, 為快速的急板,以C 大調結束全曲。 值得強調的是, 這首作品的終曲是一個極具喜劇色彩的樂章, 這一部分完全采用的是喜歌劇的寫作手法, 喜歌劇里的人物那種饒舌式的語言仿佛在音樂中再現, 渲染出一種熱鬧的氛圍感。 令觀眾十分意外的是, 在結尾處幾小節中, 音量逐漸變小, 這種小的音量帶給聽眾的感覺是人物與聽眾的距離漸漸拉遠,人的情感也漸漸消失在音樂的結尾中, 給在場的聽眾無盡的回味和感嘆, 發人深思。
作品33 之4 的第一樂章中蘊含著極其濃郁的喜劇性風格色彩。 這一部分的起始樂句結束處的那個很難引起聽眾注意的小動機在后面出現的音樂中多次變化再現, 這種再現帶來了強烈的喜劇效果。 正是由于這個小動機的靈活再現帶給觀眾新鮮、 新奇的聽覺效果。 高音區和低音區的音符遙相呼應, 在整個樂章迎來尾聲的時候, 四個聲部再次再現這個小動機。 這整個樂章在最后一次再現的時候, 音樂的喜劇性效果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順利圓滿地結束了。
結 語
喜劇思維實際上是一種不折不扣、 名副其實的創新性思維。 在經濟與科技高速迅猛發展的今天, 各種各樣的矛盾層出不窮, 生活中無形中伴隨著各方面的壓力。在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之下, 尤其是人們心理上的問題日益突出。 因此, 人們越來越需要喜劇性所具備的輕松愉快的氛圍。 音樂作為一種情感的藝術, 具有不可忽視的療愈功能。 音樂中的喜劇性目的是讓人發笑, 而笑可以使情緒得到發泄、 心靈得到放松, 對于音樂治療有不可忽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