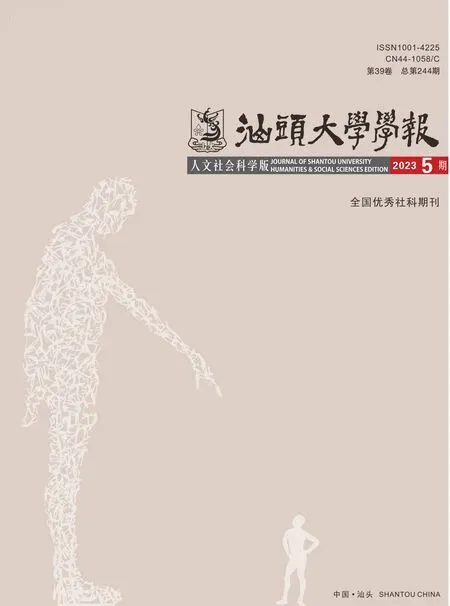從《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看錢謙益筆下晚明詩人的群體呈現
丁一凡
(蘭州大學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106)
《列朝詩集》作為一部大型斷代詩歌選本,其選人、選詩天然具有一定文學史建構、樹立典范及宣示文學主張或偏好的作用。《列朝詩集》包括乾集上、乾集下、甲前集、甲集、乙集、丙集、丁集和閏集共七個分集,內容豐富,體例完善,特別是錢謙益為所收錄詩人撰寫的小傳,除了具備極高的史料價值外,更關涉到錢氏詩學理論及詩學批評的諸多重大命題,廣受采信,影響深遠。在錢謙益撰寫的《列朝詩集小傳》中,《丁集》顯得尤為特殊:《丁集》包括上、中、下三個部分,時間覆蓋嘉靖、隆慶、萬歷、天啟、泰昌、崇禎六朝,在規模、體量上幾乎等于甲、乙、丙三集之和;同時因距離錢謙益生活時代較近,相關記載豐富且容易獲取,故《丁集》的人物小傳較之前三集而言篇幅更長、記事更詳,議論與評價部分亦更為豐富,更具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價值。在《丁集》中又以《丁集下》較為特殊:《丁集下》所收錄之人物在文壇上的活躍時間約為萬歷中后期至崇禎之初(即16世紀晚期至17 世紀早期),錢謙益要為與他同處一個時代的詩人們作傳,故此部分人物小傳多表現出一種迥異于其他部分小傳的“見證者歷史”(eyewitness history)①“見證者歷史”這一概念(eyewitness history)源自美國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小施萊辛格對當代史的定義是‘由生活在事件發生時代的人所撰寫的歷史記載’;‘見證者歷史’則指由‘親身參與所記錄的事件者’或者‘那些直接觀察了至少部分所描述事件者所撰寫的歷史記載’,它不同于僅作為‘見證者記錄’而非從歷史視角出發來撰寫的回憶錄,是當代史的一個分支。這種類型的歷史記述在修昔底德時代就已誕生,甚至可以說正是歷史撰述之源頭。小施萊辛格認為,從圭恰迪尼、馬基雅維利到培根、馬考萊、托克維爾、基佐、卡萊爾、白芝浩、班克羅夫特、帕克曼、亨利,亞當斯等,一直到19 世紀下半葉,大多數偉大的史學家都是某種意義上的見證者史家,他們參與公共事務,而不僅僅是學問家;他們認為史學家應當根據自身的直接經歷撰寫歷史……”詳參談麗:《小阿瑟·施萊辛格史學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256 頁。“見證者歷史”(eyewitness history)相關定義之原文,可參見The Historian as Participant,Daedalus,Vol.100,No.2,Century(Spring,1971),pp.339-340。的書寫視角與書寫方式。《丁集下》凡127 條目,共收錄詩人151 位,其人物的排布及呈現具有顯著的團塊狀、集群式的特征。錢謙益以地域、交游社集關系為主要串聯線索,輔之以族親、師承、科考仕途等多維關系,于人物、詩作的刪選操作及小傳文本撰寫中,完成了對于晚明詩壇的全景式展現及相應的晚明詩史建構與詩學批評表達。學界過往涉及《列朝詩集小傳》的研究,大多將小傳作文學史、文學批評材料視之并用于佐證錢氏詩學的某些具體問題,但對小傳文本的結構層次、行文邏輯、敘事手法,乃至《列朝詩集小傳》整體的設計架構等方面缺乏關注,亦忽視了對小傳歷史記述的視角、方式以及這種視角、方式造成的影響與效用的探討。針對于此,本文選取《丁集下》這一價值獨特的部分加以重新審視與分析,嘗試對其中晚明詩壇人物的集群式呈現及隨之衍生而來的相關詩學問題有所解釋及補充。
一、以“嘉定四先生”為核心的吳中文士集群
這一集群從第一條“松圓詩老程嘉燧”至第二十六條“倪學究鉅”,算入附見詩人和與之關系密切但散見于其他各處的“王編修衡”、“米山人云卿”,合計三十七人。此三十七人中,位列前四的“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唐時升、婁堅、李流芳最為關鍵,其余諸人基本皆為吳中文士,可視為“四先生”之交游圈得以呈現。白一瑾曾在《論〈列朝詩集〉的吳中詩學本位觀》一文中指出:“錢謙益對明代詩學流派,實際上是以吳中詩學為中心,以詩學流派與吳中詩學的‘遠近親疏’來進行品第的”[1],此處位居《丁集下》之首的吳中文士群,可謂是整部《列朝詩集》中最重要的,錢謙益最意圖彰顯的文士集群——縱覽整部《列朝詩集》的人物分布,其中隱藏著一條鮮明的吳中詩學傳承線索及代興脈絡:從明初的“吳中四杰”,到永、宣朝的邱吉、瞿祐,到弘治朝的沈周、史鑒,到正德朝的“吳中四才子”,到嘉靖朝的長洲皇甫兄弟,最后落在晚明的“嘉定四先生”這里完成收束。
崇禎元年(1628 年),嘉定縣令謝三賓合刻程、唐、婁、李四人詩文,名之曰《嘉定四先生集》,自此有“嘉定四先生”之名。在錢謙益的筆下,程嘉燧為“四先生”之魁,不過《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婁堅之《學古緒言》時,其提要曾指出“嘉定四先生”中的程嘉燧實為附名,且對其評價不高,其余三人實以婁堅為冠冕:“(婁堅)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名,本非善類,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稱。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為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余焰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頹瀾,延古文之一脈。”[2]提要中說程嘉燧“本非善類”、“蒹葭倚玉”,可謂是很嚴厲的貶低,不知提要中的此番論斷,是否是受清初文士對錢謙益推尊程嘉燧太甚而引發的普遍反感所致。嘉定今屬上海市行政區劃,位于長江三角洲南岸,西接昆山、太倉,東鄰寶山、普陀,南依吳淞江(古稱松江),北面即為長江入海口。嘉定一縣,僻居海濱,民風質樸,清代的嘉定學者錢大昕曾在《習庵先生詩集序》中總結說:“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樸魯,仕宦無登要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后黃忠節公文章節氣,照映千古。國朝則菊隱、樸村、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3]錢謙益早年醉心王、李,癡迷復古:“《空同》、《弇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紙。搖筆自喜,欲與驅駕,以為莫已若也。”[4]1347不過在結識了“四先生”之一的李流芳并進一步受到程嘉燧開示啟發后,錢謙益幡然醒悟,自此確立了以“古學”為根抵的治學及詩文創作取向,逐漸發現了復古派理論的弊端并加以反思與批判:
為舉子,偕李長蘅上公車,長蘅見其所作,輒笑曰:“子他日當為李、王輩流。”仆駭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長蘅為言唐、宋大家,與俗學逈別,而略指其所以然。仆為之心動,語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數年,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僱賃之病……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為文之阡陌次第[4]1347。又《陳百史集序》云:
余未弱冠,學為古文辭,好空同、弇州之集。朱黃成誦,能闇記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模倣,以為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長而從嘉定諸君子游,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傳習其風流遺書。久而翻然大悔,屏去所讀之書,盡焚其所為詩文,一意從事于古學[5]676。
錢謙益晚年尤喜追憶與嘉定四君交游往事并暢談自身學術和文學轉向之事,如“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轅易向”[4]1359云云,不勝枚舉。正因為嘉、隆間諸君“敦尚古學”并對錢謙益產生了關鍵的導向性影響,故錢謙益置“嘉定四先生”于《丁集下》之首并予以極高的評價,且小傳文本的體量乃至與之匹配的選詩,皆遠超《丁集下》中其他人物,推尊之意表露無疑。
接“四先生”而后,即為歸有光之季子歸子慕。歸有光出現在《丁集中》相對偏后的位置,距離《丁集下》之首的“嘉定四先生”和歸子慕比較接近。錢謙益將歸子慕設置在此,除了有呼應《丁集中》“震川先生歸有光”的作用外,更意圖凸顯“嘉定四先生”和歸有光的師承關系。這一曾師承關系,是錢謙益所力圖彰顯的吳中詩學傳統,乃至整個明詩史建構中的重要一環:將“嘉定四先生”這一小集團,尤其是錢謙益最為推尊的程嘉燧,接續在前三集已經確立的高啟、李東陽等明詩正脈主流之上,除了賦予了“嘉定四先生”集團以合法性之外,更是將這一集團所代表的吳中詩學體系提到了一個很高的位置。同時,此舉亦暗中排斥了復古、竟陵之流,也可以理解為錢謙益對于自身詩學觀點和立場的一次重申,可謂一舉多得。關于“嘉定四先生”與歸有光的師承關系,除了“唐處士時升”小傳里“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門,故熙甫之流風遺論,叔達與程孟陽、婁子柔皆能傳道之,以有聞于世。”[6]580的表述之外,錢謙益在其詩文之中亦多有提及,如《初學集》卷三十二《嘉定四君集序》:
嘉靖之季,吾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禰唐,傾動海內。而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者也……二十年來,司宼之聲華燀赫、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熙甫之文,乃始有聞于世。以此知文章之真偽,終不可掩,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討論之。如唐與婁,蓋嘗及司宼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問學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瓣香于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7]921。
此外還有“余惟吳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底,嘉定之遺老宿儒,傳習王常宗,近代歸熙甫之舊學,懷文抱質,彬彬可觀。”[4]929等等,不一而足。不過于此尤需辨清的是,歸有光之于“嘉定四先生”的師傳并非親炙①今人黃仁生在其《明代嘉萬之際的文學演變與嘉定派的醞釀過程》一文中就明確指出“四先生”實皆未從歸有光受學:“唐時升之父名欽堯(1501-1556 年),字道虔,長于歸六歲,也早于歸在嘉定授學,但二人的確頗有交情。今見于《震川先生集》卷七的《答唐虔伯書》,就是在嘉靖二十三年為張貞女伸冤時寫給唐欽堯的。三十五年,欽堯以貢生授撫州訓導,明年死于赴任途中,歸有光為之撰《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和《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志銘》,皆以‘友’相稱,敘及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著有‘《易說》及詩文數十卷’。但唐時升在歸妻王氏逝世這年才出生,至欽堯死時,年僅六歲,所謂‘早登有光之門’,根本無從說起……至于年齡小于唐時升的婁堅、程嘉燧,則更不可能從有光受學,而李流芳則是在歸逝世后四年才出生。”參見陳文新、余來明主編:《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136 頁。,錢謙益可能是想突出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進而建構其明詩發展脈絡及進行文學史意義的確定,因而于此故意語焉不詳,模糊處之。
二、以曹學佺等為首的金陵詩社集群
這一集群自第二十七條“胡山人梅”至第三十七條“沈布衣野”,另加上散見于《丁集下》其他各處的如陳邦瞻、葛一龍、王醇、吳稼竳、梅守箕、程可中、焦竑等,總數約為二十人。錢謙益選錄金陵詩社諸人并將其集中呈現,一個直接原因便是編纂《列朝詩集》過程中所獲得的文獻基礎:“戊子中秋,余以鋃璫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編。”[6]463——《金陵社集詩》為萬歷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606-1607 年)由曹學佺所主導的金陵社集中詩人之作品合集①據《千頃堂書目》卷三一“總集類”載:“《金陵社集詩》八卷,曹學佺、臧懋循、陳邦瞻及一時名士唱和作”。對照曹氏《石倉詩稿》及其交游人物各自別集中的相應詩作,此記錄當確信無誤,而錢謙益采詩所見之本,恐非全帙。關于《金陵社集詩》的版本、卷數情況,可參看北京大學孫文秀博士學位論文《曹學佺文學活動與文藝思想研究》第45-47 頁相關考證。,這批詩人一部分以合傳形式出現在《丁集上》“李臨淮言恭”條目附見之“金陵社集諸詩人”中(合計有九人:王嗣經、張正蒙、陳仲溱、吳文潛、程漢、姚旅、臧懋循、梅蕃祚、胡潛),另一部分則是集中安排在了《丁集下》比較靠前的位置,即此處所拈出的以曹學佺為首,以柳應芳、吳兆、吳夢旸等人為核心成員的金陵詩社集群。
金陵(南京)歷來為人文之淵藪,六朝如此,明代亦然。成祖于1420 年遷都之后,南京作為留都,原有政府機構仍然保存,僅在人數上略有簡省。南京除了發揮一定政治行政方面的功能外,“也有調節人事之作用。南京六部尚書與都御史官職,成為朝廷官員升遷降謫的‘旋轉門’。”[8]59此外,“作為江南文化中心、第二京城的金陵,又逐漸形成了與封建中央政權‘離心力’極強的第二文化中心,很多文人名士,失意官宦在這里聚集。也有很多高僧及外國傳教士也在這里辯論講學,使這里養成一種愛好議論、集團結伙的風氣。”[9]由于職務上的相對清閑和江南文化風氣的浸染熏陶,往來南京的各級官員在政務之外,多有詩酒集會、吟詠唱和的習慣,如《丁集下》“韓國博上桂”條中有“留都舊京,賓朋翕集,戶履填咽,詩酒淋漓”[6]587之類的描述,足見昔日之盛況。另《丁集上》“李臨淮言恭”條附見“金陵社集諸詩人”,對百年間金陵文士社集吟詠之活動更有詳細的介紹: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夸為仙都,游談者指為樂土。弘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墠;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歙集,風流弘長。嘉靖中年,朱子價、何元朗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幼子(于)、百榖以勝流而至止。厥后軒車紛沓,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為領袖。臺城懷古,爰為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6]462-463。
錢謙益在此段文字中梳理了金陵詩壇自弘治、正德年間以來的發展脈絡,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為弘、正之際的顧璘、王韋、陳鐸、徐霖;嘉靖時期的朱曰藩、何良俊、金鑾、盛時泰、皇甫汸、黃姬水等人。這批詩人共同締造了金陵詩壇的“初盛”局面。萬歷初期的陳芹,以及后續的張獻翼、王稺登等人,重振昔日輝煌,至于“軒車紛沓,唱和頻煩”,是為“再盛”之景。另《丁集上》“陳寧鄉芹”小傳對此亦有所補充:“卜筑新林別業,近新林浦謝玄暉題詩處,又于桃葉淮清之間,起邀笛閣,招延一時勝流,結青溪社,每月為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金陵文酒觴詠之席,于斯為盛。相延五十年,流風未艾。”[6]460此處言及金陵“青溪社”,自嘉靖末來由顧璘、朱曰藩、何良俊等人主持,至萬歷之初經由陳芹大為擴張,規模頗為可觀。其實“金陵社集諸詩人”中所述詩人集群之代承脈絡,也大致相當于青溪社①郭紹虞先生《明代文人集團》一文曾引朱孟震《停云小志》,對青溪社作了詳細考證:“‘青溪自后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陳明府芹即其地為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致。歲辛未,費參軍懋謙約余為詩會其上,于是地主則明府,次則唐太學資賢、姚典府涮、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先后游而未人會者,則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鸞、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邵太學應魁、周文學時復。癸酉(萬歷元年)復為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每月為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同心投分,樂志忘形,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錄詩若干刻之,命日《青溪社稿》,許石城先生序其首;續會錄詩若干,吳瑞轂序之……后方民部沆,葉山人之芳入焉。’此文紀述源流甚詳,考朱孟震《玉笥詩談》,所載亦均青溪社事,社中人物與當時倡和之作,大率在是,茲不備述。”參見陳廣宏、鄭利華選編:《抉精要以會通》,商務印書館,2018 年,第28-29 頁。的發展過程,不過,錢謙益始終未提及“青溪社”之名,有論者指出“其目的可能是為其‘山人文學’張本”②張清河:《晚明江南詩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7 頁。更進一步地,作者以朱孟震之說與錢氏言論相對比指出:“朱孟震等似乎認為,從隆慶五年(1571)首次社集可見,本籍或者仕宦于金陵的‘世家’曹僚在詩社中居于主導地位。如縣令陳芹、參軍費懋謙等,由他們來形成影響、擴大規模,而山人僅僅充當“參與者”的角色(到了曹學佺組社的時候,隊伍變得很混雜,難以一概而論了)。顯然,朱孟震的敘述與錢謙益有很大差別。這一點,清初的黃虞稷看得很清楚。黃虞稷等認為,錢謙益考證紕漏,‘錢氏考之未得其詳。“青溪社”集,倡自隆慶辛未,而非萬歷初年也’。然而筆者認為,錢氏是蓄意混淆視聽的。他之所以這么做,顯然是為了制造一種晚明文學一開始就‘以山人文學為主流’的假象。錢謙益一再強調:青溪社的主體是山人。比如,他認為介于山人與世家之間的陳芹是青溪社的主盟者(‘復修青溪之社’):而山人莫是龍、張文柱是該社的核心成員(‘廷韓及張仲立,皆翩翩佳公子,青溪社中之白眉也’):山人金鑾、盛時泰等是詩社的耆舊(‘在衡、仲交以舊老而蒞盟’);山人張鳳翼、王稺登是青溪社的勝流(‘以勝流而至止’),至于其他人是不足道的(‘厥后軒車紛逐,唱和頻繁’)——總之,在錢氏眼中,‘青溪社’簡直就是一個‘山人俱樂部’。”見《晚明江南詩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119 頁。——不管小傳此番操作是否出于為“山人文學”張本的目的,錢謙益通過《列朝詩集》的編選和排布初步完成了金陵詩社脈絡的梳理與建構:顧璘、王韋、陳鐸、徐霖四人被集中收錄于《列朝詩集·丙集》靠后的位置,朱曰藩、何良俊、金鑾、盛時泰等人被集中收錄于《列朝詩集·丁集上》,而承接金陵詩壇“初盛”、“再盛”繼起的,就是涌現于曹學佺任職金陵期間(1599-1608 年),以曹學佺為首,臧懋循、陳邦瞻、吳兆、吳夢旸等人為代表的“極盛”詩人群體。這一批代表金陵“極盛”的詩人群體,是錢謙益于《丁集下》中所力圖突顯和推尊的,僅次于以“嘉定四先生”為首的吳中詩人集群的一個重要詩人集群。
錢謙益于此集群之展現中首推閩人曹學佺,這一方面是曹學佺確為當時金陵詩社之執牛耳者,另一方面則是錢謙益消解、分化、削弱閩詩一派的文本策略。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三月,曹學佺左遷南京大理寺,與同僚陳邦瞻、陳宗愈多有唱和來往。《陳大理詩序》謂:“己亥歲,予左遷南大理,棘下有二君子稱詩,其一為高安陳德遠,一則新會陳抑之也……”[10]據曹學佺《石倉詩稿》卷一《金陵初稿》之詩作及許建崑《萬歷年間曹學佺在金陵詩社的活動與意義》等現代研究成果來看,此年之中與曹學佺有交游往來的人物尚有龍膺、茅國縉、祝世祿、范允臨,以及焦竑、李贄、利瑪竇等人。次年元旦,曹學佺邀請沈野、柳應芳、胡潛等人游覽棲霞寺、靈谷寺、雞鳴寺、燕子磯等名勝,三月復召梅守箕、柳應芳、臧懋循、陳仲溱、魏實秀等“宴集雞鳴山,眺玄武湖,撰詩甚伙”[8]68,《金陵初稿》中《金陵覽古》十首、《僦居雜述》二十首、《集雞籠山望玄武湖》等詩可為佐證。四月,“曹學佺邀請吳兆、梅守箕、程可中宴集官署后湖,分韻撰寫荷花詩”[8]69。直至此年深秋離京歸鄉安葬母親,曹學佺在南京期間的交游經歷還涉及楊時芳、張正蒙、呂叔與、盛鳴世、吳文潛、吳叔嘉、曹明斗、湯之相等人,范圍極廣。從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三月赴任,至萬歷二十八年(1600 年)秋歸鄉,這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是曹學佺南京仕宦生涯的第一個階段,此階段所進行的種種集會、交游唱和也為數年后的“極盛”局面奠定了基礎。曹學佺于萬歷二十八年(1600 年)秋歸鄉葬母,次年伙同沈野等人云游四方,足跡遍涉建州、龍巖、蘇州,并短暫停留于金陵,而后又至鵝湖、天目山、太湖等,復于萬歷三十年(1602 年)七月由南棘寺歸閩。此年下半年至萬歷三十一年(1603 年),曹學佺基本活躍在閩地詩壇,與徐、謝肇淛等閩籍詩人先后結有芝社、瑤華社等。萬歷三十二年(1604 年)二月,曹學佺同吳兆、林古度由閩中返回金陵,遷戶部郎中,此后直至萬歷三十六年(1608 年)調任四川,曹學佺基本身處金陵,此數年中各種集會、唱和接連不斷。這一時期內,尤其是萬歷三十四、三十五年間社集產生的詩作,結集即為《金陵社集詩》,也就是錢謙益所謂“戊子中秋”“采詩舊京”所見之本。據《千頃堂書目》卷三一“總集類”載:“《金陵社集詩》八卷,曹學佺、臧懋循、陳邦瞻及一時名士唱和作”[11]772,“今存《金陵社集詩》殘本,卷上為萬歷三十四年,卷中、卷下為萬歷三十五年。徐朔方《臧懋循年譜》據此將社事系在萬歷三十四年,認為社詩‘為今、明二年作’。”[12]351對照曹氏《石倉詩稿》及其交游人物各自別集中的相應詩作,此說當確信無誤。以今存《石倉詩稿》中《金陵集》一卷為例作粗略統計,便有《到金陵社集葉循父園賦答》、《閏九月九日燕子幾登高共享寒字》《元夕過桃葉渡同諸子飲》《七夕同社邀永叔集城南王氏園中》等數十首相關詩作。若結合相關交游人物之別集中的相關線索,對前后若干年中詩社活動、集會成員等作一番梳理,其規模和體量可能相當驚人——據孫文秀《晚明詩壇“金陵之極盛”雅集考論》所考證,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 年)至三十六年(1608 年)曹學佺任職南京期間,參與“金陵之極盛”階段文士雅集活動的成員共有103 人,另外還有僅存姓名而生平、籍貫等無考者65 人[13],這個數字遠遠超越之前任何時代的金陵社集活動,絕對擔得起“金陵之極盛”之名。
錢謙益如此推重曹學佺和金陵詩社集群,除了曹學佺本人的士林地位、詩文成就以及在他主導下的金陵詩社步趨“極盛”等因素外,聯系錢謙益編纂《列朝詩集》時的時代背景,其實背后更有某種現實的考量。陳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指出:
前論牧齋熱中干進,自詡知兵。在明北都未傾覆以前,已甚關心福建一省,及至明南都傾覆以后,則潛作復明之活動,而閩海東南一隅,為鄭延平根據地,尤所注意,亦必然之勢也。夫牧齋當日所欲交結之閩人,本應為握有兵權之將領,如第肆章論“調閩帥議”,即是例證。牧齋固負一時重望,而其勢力所及,究不能多出江浙士大夫黨社范圍之外,更與閩海之武人隔閡。職是之故,必先利用一二福建士大夫之領袖,以作橋梁。茍明乎此,則牧齋所以特推重曹能始逾越分量,殊不足怪也[14]963。
錢謙益是否意圖藉由曹學佺以助其復明事業,香港學者嚴志雄曾著宏文《陳寅恪論錢謙益“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考辨》專論此事,該文第二章“曹能始對牧齋有無政治利用價值?”通過一系列詩文及史實的考證梳理,認為“牧齋利用能始從事政治活動此一說法始終只是一個富有啟發性的猜想,陳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實質證據以資佐證。”[15]94囿于本文主旨,此處聊備一說,不另詳細闡發。
三、以徐氏兄弟、謝肇淛、鄧原岳為代表的閩派詩人集群
這一集群分為兩個部分出現,首先是第七十九條“徐舉人熥、布衣”至第八十二條“陳秀才衎”的六人,其次是第九十八條“謝布政肇淛”至第一百零四條“陳汝修”的八人,合計十四人。此外還可歸入不屬閩籍,但因仕宦、交游經歷而與閩籍文士關系密切的屠本畯、阮自華等若干人物。閩派詩人內部連結緊密,交游唱和頻繁,理論主張鮮明,創作成果豐富,在當時是一支不可忽視的詩壇力量:“錢謙益編纂明代詩歌總集《列朝詩集》,共收明代詩人1663 人,其中閩地詩人有104人,約占所收明代詩人十六分之一,清初另一著名詩人、學者朱彝尊輯《明詩綜》,錄明代詩人3400 多人,而閩地詩人則有260 余人,所占比例約為十五分之一……就數量而言,明代閩中詩群僅次于江浙詩人,為明代詩歌創作的一支主力軍。”[16]尤其是萬歷一朝以來,以徐氏兄弟、謝肇淛、鄧原岳為突出代表的閩派詩人,連同前面已經出現的曹學佺,通過交游結社、砥礪創作以及編纂詩集等文學活動,在當時的詩壇頗有名望和影響力。
雖然《列朝詩集小傳》中將二徐、謝肇淛、鄧原岳等人分割開來,但實際上這一批閩派詩人的活躍時間基本相當,無法也無需對他們加以嚴格的劃分。陳廣宏于《閩詩傳統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學的一種歷史省察》一書中依據閩派詩歌的代興和傳承脈絡,將鄧原岳、徐熥并舉,而把曹學佺、徐、謝肇淛三人歸為一個小集團,這五位閩派的核心人物共同覆蓋了萬歷中期直至崇禎這一階段,在晚明詩壇保持了相當長久和廣泛的影響力。據陳價夫《徐惟和行狀》記錄,早在萬歷十三年(1585 年),徐熥就與陳價夫、薦夫兄弟及鄧原岳、謝肇淛等閩地詩人有過交游來往:
是歲,試省闈,主司已擬入格,將魁,閩士會有阻之者,竟不果錄。惟和乃益厭習公車業,刻意攻古文詞,與陳秀才汝大、汝翔、陳山人惟秦、振狂、鄧學憲汝高、謝司理在杭及不佞價夫、弟薦夫輩數人,結社賦詩,剌來筒往,殆無虛日。[17]338-339
萬歷十七年(1589 年)夏秋之間,徐熥于紅雨樓南園中筑綠玉齋,并作《綠玉齋記》。八月,陳薦夫、陳椿、謝肇淛等人過往,多有唱和,如謝肇淛之《飲徐惟和綠玉齋得喧字》《八月十四夜同陳汝大陳伯孺集綠玉齋》[18]344-345等詩可作佐證。此后若干年間,綠玉齋成為閩派詩人舉行詩文集會的一個核心據點:“這一批詩友在此間有各自的居所用于社集,如陳椿的山齋、陳宏己的吸江亭、鄧原岳的竹林山莊、袁敬烈的南郊水亭、陳薦夫的招隱樓、陳價夫的水明樓……但不可否認,綠玉齋居于相當顯要的地位。萬歷二十年,鄧原岳轉餉遼東,便道過家,即來徐氏齋中看望;萬歷二十二年,鄧氏與曹學佺等又集徐熥齋頭;萬歷二十三年秋,徐熥、陳翰臣(字子卿)、陳薦夫下第歸,鄧原岳將奉使入浙督餉,徐將游南京,以上諸人及陳椿、陳宏己、袁敬烈等又集于綠玉齋,皆有詩,盛況空前。”[17]339除綠玉齋各次集會之外,萬歷十七年后明確見于記載的結社尚有芝山社、烏石山之社①郭柏蒼:《全閩明詩傳》卷四十:“(徐)初與趙世顯、鄧原岳、謝肇淛、王宇、陳價夫、陳薦夫結社芝山。”鄧原岳:《西樓全集》卷十八《答李廷燁東莞》:“不佞弟無似,與惟和兄弟及諸酒狂結一社于烏石山下,篇什不少,今且付梓,秋末可得成書,當寄郵筒一求證印也。”徐熥《幔亭集》中亦有《集鄭氏烏石別墅》等詩可為佐證。等,涉及人物包括但不限于:陳價夫、薦夫兄弟、鄧原岳、陳椿、陳宏己、陳鳴鶴、謝肇淛、曹學佺、鄭琰、陳仲溱、王元等。此外,除了綠玉齋集會這樣的文學活動外,閩派詩人更在編制選本和整合地域性文學文獻方面有突出成果。約在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間(1593-1597 年),鄧原岳編《閩中正聲》成,收錄福州一地自洪武至萬歷前期詩人五十一家、詩二百六十八首,該集“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為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6]649其后不久,徐熥編《晉安風雅》十二卷增益之,收詩二百六十四家凡千余首,并通過選本的收錄操作凸顯出閩中詩學自洪、永朝林鴻、高棅、王恭、王偁,到正、嘉朝鄭善夫,再到隆、萬朝鄧原岳、陳價夫、陳薦夫、謝肇淛、徐諸家的傳承譜系和發展脈絡。通過一系列選本的編制及推廣,鄧、徐二人意圖為地域文學張本,并借此凸顯閩地宗唐的復古詩學取向及相關理論——而這,或許恰恰是導致錢謙益對閩派總體持論不高的主要原因——試觀鄧原岳小傳中對閩派所倡“唐音”的批判:
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匯》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觀其持論,則汝高之詩從可知矣。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后來庸靡之病歸咎于林子羽,蓋有見于此。[6]649
為何閩派重視的“正聲”及“唐音”,在錢謙益看來就不是“唐人之唐”呢?《牧齋初學集》卷七十九的《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或許給出了一個比較詳盡的解答:
夫文之必取法于漢也,詩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為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為唐者矣。知所以為漢者而后漢之文可為,曰為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為漢可知也……自唐、宋以迄于國初,作者代出,文不必為漢而能為漢,詩不必為唐而能為唐,其精神氣格,皆足以追配古人……彼不知夫漢有所以為漢,唐有所以為唐,而規規焉就漢、唐而求之,以為遷、固、少陵盡在于是,雖欲不與之背馳,豈可得哉[7]1701。
錢謙益指出,如據遷、固學漢,據少陵學唐一類的方法,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當下之時代無法完全再現漢、唐的社會環境與思想文化,那么也就注定了從結果層面加以模仿、復刻,只能是觸及皮毛,不得精髓。所以《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接下來強調:
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為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為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仿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為宗祖。承訛踵偽,莫知底止[7]1702。
錢謙益這一種頗具有進化論式的文學史觀及相關認知,正是他批判復古派的核心邏輯。據此考察閩詩流變及其理論宗旨,自然會將膚淺的宗唐歸結為晚明閩派“庸靡之病”的緣由——“觀其持論,則汝高之詩從可知矣”一句,既點明了閩派一貫秉持的詩學路徑,也暗示著正是這樣的詩學路徑的局限性,導致了閩派最后墮于“柔音曼節,卑靡成風”。[6]180更進一步地,錢謙益將閩派與在《丁集下》之前就已強烈抨擊、貶低的竟陵派相聯系,從而完成了對于閩派的降格與消解:
(“謝布政肇淛”小傳)在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伯谷,風調諧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伯谷者為多。在杭之后,降為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鐘、譚,風雅凌夷,閩派從此熸矣[6]648。
從小傳文本和《丁集下》中閩派詩人的分布特征來看,錢謙益對待閩派的態度是頗有些矛盾的:一方面錢謙益一定程度上認可閩派詩學的地位及成就,于《丁集下》中給予了閩派詩人足夠的重視(如收錄曹學佺詩83 首,徐詩47 首)和相對中肯的評價;另一方面出于回護、褒舉吳中詩學的私心,他又不希望看到另一個在規模、數量上壓過吳中一頭的地域性詩人集群的存在,故于《丁集下》的詩人排布和安置上,將閩派諸人分散、拆解,從而達到削弱、淡化閩派存在感及詩史意義的效用。前文論及的曹學佺更是一典型例證,作為閩派關鍵人物的曹學佺并不以閩派面目示人,反而出現在了金陵詩社集群之中,而此處閩派被分為兩截分別加以呈現,則更是錢謙益潛藏其詩史建構意圖的一種文本策略。
除了曹學佺、二徐、謝肇淛、鄧原岳外,《丁集下》中還有一小撮較為隱蔽的閩派人物,那就是第一百一十七條“張童子于壘”至第一百二十條“林隱士春秀”的九人。此九人皆由徐徐興公串聯——張于壘,漳州府龍溪人,“友人燮字紹和之子也”,“年十四,紹和攜之入閩,與徐興公諸賢即席分韻,童子倚待立成,四坐閣筆。”張于壘二十二歲早逝,錢謙益收錄他,著墨寥寥,重點在于記錄其父張燮張紹和:“紹和以文章自命,所著詩文集凡數百卷。余驚怖其浩汗,不能錄也。錄童子詩一首,使人知紹和有子,如古之九齡與玄者,亦因是以存紹和云。”[6]660接下來的“周隱士如塤附見陳龠”二人,皆為閩籍隱士,生平無考,因“徐興公與其孫鴻游,得其遺稿”[6]661,故存而錄之。此數人與錢謙益無甚交集,錢謙益經由徐而了解到他們的存在,并以五人合傳的形式記錄下來。另徐小傳曾經提及:“崇禎己卯,(徐)偕其子訪余山中,約以暇日互搜所藏書,討求放失,復尤遂初、葉與中兩家書目之舊。”[6]634如此看來,錢謙益與徐有過直接的碰面交流,應該是藉由此契機得知上述諸人并收錄于《列朝詩集》之中。
四、其他小規模集群與獨立人物
除了上述三個相對集中呈現的詩人集群之外,《丁集下》中尚有不少組織和體系相對較小的詩人社集或團體。它們在錢謙益的詩史、文脈勾勒中,往往以十人以內的規模分散出現,不具備如核心集群那樣鮮明、緊密的、或是有特定地域范圍的功能性線索,也相對缺乏如長久、定期的集會唱和、乃至作品匯編、合刻等等文學活動。錢謙益對這一部分詩人的處理仍以交游線索展開,不過這種線索相較于前文所論若干集群而言,其文學性聯系相對薄弱,而多表現為同年、同鄉、同僚或親屬等非文學系關系。另需說明的是,其中人數規模過少者,如第八十九至九十一位“張舉人民表”、“秦秀才鎬”、“阮徵士漢聞”三人,世稱“天中三君子”,此種情況姑且算作“并稱”現象,并不作詩人集群視之。
小規模集群的典型代表,如以虞淳熙、馮夢禎等為首的勝蓮社。這一集群主要包括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七條的“徐推官桂”、“虞稽勛淳熙”、“馮祭酒夢禎”、“朱主事長春”、“黃少詹輝”、“陶祭酒望齡”、“焦修撰竑”、“馮庶子有經”八人。此八人彼此交好,均有功名,交游廣泛,閱歷豐富,此處將其視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主要依據勝蓮社這一層面的人物聯系。勝蓮社是萬歷二十二年(1594 年)成立于杭州西湖的一個具有濃厚佛教背景的文士社團。晚明文人崇佛風氣盛行,蘇杭一帶尤甚,以至于“江南之人奉放生教者,十家而五。”[19]40除了與僧人的交往之外,平日禮佛行善亦是文人崇佛行為的重要部分,故此時之西湖多有集會放生之舉,勝蓮社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勝蓮社主要由屠隆、虞淳熙、馮夢禎三人發起,由虞淳熙執筆之《勝蓮社約》云:
西湖,南宋放生池也。豐碑屹立道上,第飛泳亭廢耳,亭以飛泳名,將取山光悅鳥,濠游魚樂。然異熟果成樊籠鏑釜中,幾許能全,即不幸復投網罟,猶冀重贖更生,便令折翮困鱗,隨放隨滅……此后至社者,必攜飛泳之類來,所費鍰錢,自一銖至累鎰無量……社定錢湖舟中,閑詣上方池、凈慈萬工池、昭慶香華池,期以每月六齋日,會首傳帖,醵金授典座,自修供具。凡會首認定,開后坐以齒緇素,各為行三寶前,不必讓遠客。[20]498-499
勝蓮社專為放生活動而組建,并且設立了明確的與會章程,組織頗為有序。綜合藍青《晚明杭州勝蓮社考論》、李小榮《晚明虞淳熙西湖結勝蓮社諸問題補論》等今人研究成果,勝蓮社的核心成員主要有:袾宏、馮夢禎、虞淳熙、虞淳貞、邵重生、屠隆、朱大復、徐桂、陸振奇、葛寅亮、鄭之惠、謝耳伯、吳之鯨、楊中麓、黃汝亨等合計三十人。勝蓮社雖以行放生積善為主業,但文人集會,自然也少不了游覽山水和詩文吟詠(西湖的風景名勝也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條件),勝蓮社成立之后十余年間,可考的詩文集會包括但不限于:萬歷二十六年(1598 年)十一月,吳之鯨主持,馮夢禎、楊中麓、黃汝亨、虞淳熙等人參會;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七月,韓敬主持,袾宏、馮夢禎、虞淳熙、虞淳貞、張孺愿、柯紹皋、卓云等參會;萬歷二十九年(1601 年),馮夢禎主持,費元祿、虞淳熙、虞淳貞、潘之恒、吳二水、吳德符、吳之鯨等參會;萬歷三十年(1602 年)閏二月,恰逢虞淳熙五十歲生日,馮夢禎、屠隆、朱長春等人集會并為虞淳熙祝壽等。諸次集會所涉具體詩文作品,過于龐雜繁多,本文不再一一羅列。
《丁集下》中有不少地位顯赫的詩人可以歸入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的集群中,但同時也存在著相當一部分較為獨立的人物,隨意而零散地出現在《丁集下》之中。這一批詩人多為某某“山人”、“隱士”、“居士”、“秀才”,他們或直接與錢謙益本人有過某些交集,或與被收錄在《丁集下》的其他詩人有過短暫的結識、會面,還有可能是錢謙益在編纂時輾轉聽聞,然后抱著存人記史的目的予以收錄。此類獨立人物的小傳大多極為簡短,生平履歷亦殘缺無考,需將其單獨摘出加以討論。如第四十一位“王遺民鏳”,其小傳云:
鏳,字叔聞,金壇人。恭簡公樵之諸孫也……丙戌之十月也,年已七十矣。叔聞送人下第詩有“一夕殘秋帶客還”之句,吾友于中甫見而激賞之,命其二子從之游……丁亥冬,過金壇,得其詩于御君,篝燈疾讀,俯仰太息。當吾世有叔聞而不能知,且叔聞或知余,而余不知叔聞,余之陋則已甚矣!……若夫叔聞之晚節,又當與謝皋羽、鄭所南齊名于千載之后,后之君子頌其詩,論其世,將有如吳立夫、程克勤者,采而錄之,余又淺之乎知叔聞矣。[6]612-613
以錢謙益筆鋒之嚴苛挑剔,能讓其“俯仰太息”且感慨“余之陋則已甚矣”之人,恐怕在整部《列朝詩集》中也屈指可數。錢謙益不僅另為《王叔聞先生詩鈔》作序,還存錄了王氏九十首詩作,這個數量介于“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唐時升和曹學佺之間,位列《丁集下》第四,較之排列在“王遺民鏳”前后的其他詩人而言可謂“鶴立雞群”,足見錢謙益對其重視程度。對于王鏳之詩,《明詩綜》錄其一首,《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錄其七首,和《列朝詩集》收錄九十首相比,差距極大,錢謙益的個人偏好在“王遺民鏳”這里表現得非常明顯。其次,錢氏本人的族親也常獨立出現,如第七十八條“錢山人希言”。常熟錢氏奚浦一脈,相傳為吳越王錢镠之后,自五世祖錢泰始,地位日顯,成為常熟望族:“錢泰有五子,分別是元祿、元祮、元禎、元祥、元祾。錢希言的祖父錢表本是元祮季子,元祾無后,遂以為嗣……錢希言的曾祖元祾與錢謙益的高祖元禎同出錢泰一脈,錢希言與錢謙益之父錢世揚同輩,兩家過往甚密。”[21]220錢希言年少遇家難,旅居在外,顛沛流離,故難以專心舉業,約在萬歷二十年(1592 年)徙居蘇州后徹底成為“山人”。除了小傳里的介紹外,《牧齋晚年家乘文》亦略有補充:“強識多聞,詩筆繁富。為人傲兀任性,不諳世務,而好學干謁,所至輒抵戾其詩,取投贈悅俗,遂無可傳。”[5]158-159錢謙益因感慨“蓋棺之后,其書未削稿者盈箱溢帙,今皆散佚不存矣,惜哉”故而“詳著之”[6]633。據錢希言所著《松樞十九山》等相關史料可知,他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 年)后遍游皖、浙、楚等地,交游圈涉及湯顯祖、屠隆、袁宏道、申時行、江盈科、馮夢禎、鄒迪光等人,亦不妨視為吳中詩學集群的外延人物。
余論:再從收詩數量談起
粗略來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中詩人集群的設定、排布及最終呈現的文本面貌似乎缺乏規律可循,但若將其重置于《列朝詩集》的分卷體系中,并結合《丁集下》選錄人物之收詩數量這一項因素加以審視和考察,錢謙益對于晚明詩壇的認知、判斷及勾勒、描繪,其實更寄寓著某些深層次的關于詩史建構和詩學批評的表達訴求。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所覆蓋的范圍,對應《列朝詩集》卷十三(上、下)、十四、十五、十六合計四卷的內容。其中,《列朝詩集》的“丁集第十三之上”有程嘉燧、唐時升、婁堅3 人,收詩數量分別為215、107、41 首,此3 人收詩數量均極多,且恰好形成了一個逐級遞減的近似等比的數列。“丁集第十三之下”自李流芳至于胡梅共28 人(其中“鄭秀才胤驥”條附見徐允祿、龔方中2 人,“王提學志堅”條附見“弟志長、志慶”2 人,僅存名,未收詩,不納入統計),其中只有李流芳一人收詩數量較多,為41 首,與婁堅相同,其余人收詩數量均維持在十余首的水平,和“嘉定四先生”無法相比。“丁集第十四”自石沆至王鏳合計14 人,此卷人數并不算多,但平均單人的收詩數量則較多(這或許也和《金陵社集詩》的文獻基礎有直接關系)——暫以30 這一接近《丁集下》中人物收詩數量的中位數為衡量標準,此14 人中有石沆、吳兆、吳夢旸、曹學佺、柳應芳、范訥、吳鼎芳、葛一龍、王醇、王鏳這10 人收詩數量超過了30 首,在《丁集下》中收詩數量大于30 首的總共18 人中占據了過半比重。“丁集第十五”自李蓘至吳拭合計46 人,此卷中除李蓘、黃輝、陶望齡和徐收詩較多外(4 人收詩數量分別為44、33、50、47 首),其余人物收詩較少,且相當一部分人物的收詩數量低于10 首。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卷中人物的小傳文本,相較于卷十三、卷十四人物小傳詳實清晰、整飭有序的文本面貌,更為細碎簡短,體現出蕪雜、分散的文本特征。“丁集第十六”自董其昌至傅汝舟合計51 人,此卷中大部分人物的收詩數量僅為個位數,各自小傳文本的碎片化特征更為明顯,甚至多處出現僅存名而無傳文的情況。更進一步結合前文所論詩人集群觀之,《丁集下》中晚明詩壇的呈現特征及隱藏于其中的詩史建構、詩學批評意圖則漸趨顯露——吳中詩人集群大致對應卷十三,金陵詩社集群大致對應卷十四,這兩卷所收錄人物及其各自小傳,較之卷十五、十六而言,脈絡和體系更為嚴整,規模和體量更為龐大,持論以正面肯定為主基調,當是錢謙益力圖推尊、凸顯的部分。第十五、十六兩卷的小傳內容及其收錄人物,則相對零散、破碎、雜亂,其中既無可與吳中、金陵詩社相抗衡的集群,也缺乏收詩數量較多、詩壇地位重要的個人。唯一有可能在規模上和吳中相抗衡的閩派,還遭到了錢謙益暗中消解、弱化的處理。這兩卷中的很多人物,或出于《列朝詩集》存人記史的編纂目的而得以納入,他們在錢謙益的詩史架構和批評體系中往往只起到鋪墊、陪襯的作用。
在《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展現的晚明詩壇全景式畫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自吳中詩派,到金陵詩社,再到閩派乃至其他小型群體、獨立個人的關乎地位、意義及重要性的遞減階梯。在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刪選取舍、次序排置以及人物小傳的撰寫中,常熟人錢謙益力圖傳揚、彰顯其家鄉詩學,特別是推尊對自身詩學路徑、詩學理念有決定性影響的“嘉定四先生”群體。更進一步的,若拓展至《列朝詩集小傳》的整體架構及詩學批評語境,結合錢謙益對于復古、竟陵兩派的駁斥及批判,《丁集下》中這套主次分明、等級森嚴的詩壇立體圖景,更凝聚著錢謙益確立以吳中詩學接續李東陽而下之正統地位的迫切期冀,甚至于說是某種野心。秉承刪述傳統精神的選本型總集《列朝詩集》,其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層面的意義及功能,正體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