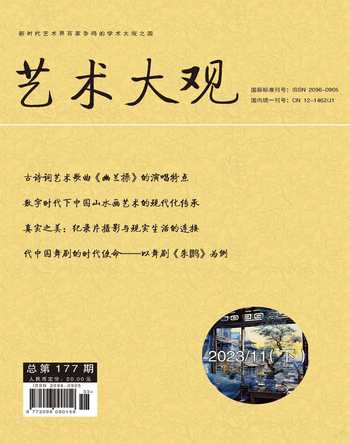露天戲臺與劇院
陸晗笑
摘 要:觀戲曲起源和發(fā)展的千年歷史,其演出場所從露天戲臺逐漸豐富到現(xiàn)代性的劇場。露天戲臺孕育和奠定了戲曲的藝術(shù)個性和不同于其他藝術(shù)樣式的本質(zhì)特征,而劇場使戲曲有了更高的藝術(shù)審美和創(chuàng)作要求,同時也給予了戲曲藝術(shù)跟隨時代發(fā)展的力量。本文主要論述兩種演出場所各自在戲曲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和不可撼動的影響,分析其在當(dāng)代應(yīng)用于戲曲演出的現(xiàn)狀,最后提出應(yīng)當(dāng)對兩種演出場所辯證看待,二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關(guān)鍵詞:戲曲;演出場所;劇院
中圖分類號:J814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33-00-03
戲曲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文藝樣式,從其萌芽時期的藝術(shù)形態(tài)可以看出,它誕生于民間。露天戲臺是孕育戲曲的搖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劇院的誕生,它的演出場所逐漸從藏于民間的各類戲臺變成了瑰麗壯觀的劇院劇場,戲曲也自此進(jìn)入了更加“專業(yè)”的時代。宏觀來看,戲曲的演出場所按照空間特點可以分為兩大類:無遮蔽的開放露天戲臺和四面封閉的劇院場所。兩者在戲曲發(fā)展和傳承的過程中各司其職,對戲曲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而如今,民間戲曲演出日漸減少,露天戲臺也日益荒廢,更多的戲曲創(chuàng)作誕生于劇院場所。因此,分析不同演出場所的功能特性及其對戲曲藝術(shù)形式和內(nèi)容的影響,有助于優(yōu)化二者在當(dāng)代的應(yīng)用,以更好地傳承和發(fā)展戲曲。
一、露天戲臺孕育戲曲演出的基本屬性
(一)民間性
戲曲萌芽于早期人們的勞作生活,并在朝代更替和社會變化所帶來的生活習(xí)性改變中發(fā)展。周秦時期,民間百姓依靠祭祀先祖來期盼一年勞作的風(fēng)調(diào)雨順,從而形成了多用來祭祀的歌舞。到了宋代,雜劇、南戲形成,其演出形式更加完善,演員人數(shù)也隨之增加。文人作家對于故事情節(jié)的設(shè)置更加跌宕起伏,大多仍取材自民間生活,如富家千金與窮書生的愛情故事、目連救母的親情故事等。無論哪個時代,戲曲劇目的創(chuàng)作圍繞各個時代的人們所生活的環(huán)境為背景,在實際生活中尋找故事靈感。周貽白先生在《中國戲劇史長編》一書中也提到:“一切事物的形成,追本溯源,有一個不易的原則,即產(chǎn)生文化的行為,無一不是為著幫助實際生活而起源于勞動,沒有勞動,便不會有文化。[1]”戲曲誕生于民間,在人們?nèi)粘谧魃畹耐寥乐形侦`感、日漸強壯。最早的戲班也是在民間組織中形成的,其演出的場所多種多樣,如露天高臺、集會廣場等。這些露天戲臺的演出形成了一種“一體化”的觀演關(guān)系,讓本就來源于民間的故事更加貼近觀眾,這與當(dāng)時人們的生活條件和方式也息息相關(guān)。古代的交通不便使購物場所形成了聚集的姿態(tài),因此有了“集市”“廟會”,人們大多在固定的時間一齊前往購買。趕集和逛廟會是當(dāng)時人們的重要日子,從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便可以看出。所以,人們常常會在集、會場合設(shè)置露天演出,以增加熱鬧氛圍,這也是早期戲曲的主要社會功能。劇目的選擇與周圍環(huán)境中攤販的吆喝聲相適應(yīng),使觀眾的情緒更加高漲,也更能與戲中人物共情,實現(xiàn)近距離觀賞。這也與戲曲“實際生活的藝術(shù)反應(yīng)”這一根本屬性相吻合。
(二)夸張性
戲臺推動戲曲的露天表演開始有了更多的藝術(shù)特征,同時也反映出戲曲的劇目演出具備了更完善的演出體系和更強的可看性。早期的露天沒有遮蔽的演出場所,遇天氣惡劣便無法進(jìn)行演出,如果仍要繼續(xù)進(jìn)行,演員的妝發(fā)也會遭到破壞,從而大大地影響了演出的整體效果。戲臺帶來的遮蔽性給演出呈現(xiàn)帶來了很大的保障,讓戲班開始有更多在“行頭”上下功夫的機會。由于觀演距離的拉開,觀眾在視覺和聽覺上的接收效果有所減弱。這讓戲曲演員不得不開始使用更加夸張的妝容和區(qū)別于日常的服飾,來加強視覺上的沖擊來維持演出的觀感,并用更加特殊的唱腔和音樂,以區(qū)別人們在觀區(qū)日常的交談聲,在嘈雜的環(huán)境中得以凸顯。不同的角色在戲中也會對應(yīng)設(shè)計不同的服飾,以此來加深觀眾的記憶,達(dá)到可以讓觀眾清晰地了解其所扮演的角色在劇中的地位、身份的目的。戲曲“夸張”“寫意”的特征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進(jìn)一步得到了發(fā)展。如元人胡祗遹《朱氏詩卷序》記載:“危冠而道,園顱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則駿奔走,魚笏則貴公卿。[2]”可見,在戲曲演出體系的完善和可看性的驅(qū)使下,其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角色標(biāo)簽”。另外,由于觀眾大多僅能在戲臺正面進(jìn)行劇目觀看,戲臺較高,演區(qū)與觀區(qū)拉開了距離,這也是我國“觀演分離”演出關(guān)系的雛形。
(三)通俗性
通常來說,露天戲臺的戲曲演出具有強烈的通俗性。這不僅僅受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所影響,同時也與露天演出場所的特性相關(guān)。首先,露天戲臺一般除了中間的演出區(qū)域,觀眾可以隨意在演區(qū)外圍成一圈進(jìn)行觀看。戲臺的周圍時常聚集著各式各類人群,或者說這些場所大多處于人來人往的地理位置,而這里的觀眾密集程度大且多為婦女老人等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群。他們常以趕集的心態(tài)——哪里熱鬧哪里湊,來臺前觀看。深奧復(fù)雜的演出不利于在鬧市進(jìn)行,這直接導(dǎo)致了露天演出劇目首要的目的是制造氣氛,以“叫”“喊”等夸張的表演形式為主,依靠“熱鬧”來留住觀眾,因此只能設(shè)計簡單的劇情和容易理解的詞句。其次,雜劇的繁榮興盛與飛速發(fā)展,開始使它的創(chuàng)作群體更加大眾化,許多平常書生趨之若鶩,紛紛開始成為“編故事的人”,而他們憑借并不高的文化水平創(chuàng)作出來的劇目通俗易懂。從通俗性這一方面看露天戲臺的演出為戲曲發(fā)展帶來的影響,可以看出,戲曲的成熟,先以俗眾的形式走進(jìn)人們的日常生活,讓民眾廣泛參與其中,使戲曲成為人們飯后茶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也為戲曲日后發(fā)展成為最能反映人們思想情感的藝術(shù)樣式之一奠定了基礎(chǔ),為往后不勝枚舉的文人、劇作家紛紛投入創(chuàng)作、以此來抒發(fā)抱負(fù)和志向做了鋪墊。在劇院出現(xiàn)前的幾百年間,人們習(xí)慣于在嘈雜環(huán)境中欣賞在自己土地上逐漸具備藝術(shù)特征的戲曲,它也成了民間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文化。
二、劇院強化戲曲演出的觀演關(guān)系
(一)劇院提升戲曲演出的觀賞度
宋代繁榮的商品經(jīng)濟(jì)給百姓帶來了空前發(fā)達(dá)的娛樂文化,需要“付費”才能進(jìn)入的封閉式演出場所已經(jīng)初見雛形。市井看客們的娛樂生活日漸豐富,常常為了看一出戲揮金如土。元代散曲家杜仁杰在《莊稼不識勾欄》套曲中寫道:“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個木坡,見層層疊疊團(tuán)圞坐。”這直觀地體現(xiàn)出了在當(dāng)時戲曲演出已經(jīng)成為一種平民化和常態(tài)化的演出項目,人們想看戲也不必等到以前固定的祭祀、集會之時,只要花錢就能隨時觀看。伴隨著這樣可觀的經(jīng)濟(jì)效益,戲班們也開始為觀眾打造更加“好看”的戲曲演出,其中至關(guān)重要的一項就是讓花了錢的觀眾不被“外人”打擾,即建造固定的演出場所。《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篇中記錄了由“路伎人”演出的雜劇表演,已經(jīng)開始有相對固定的演出場所:“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不以風(fēng)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3]”這里提到的所謂的“棚”,在當(dāng)時即被叫作“勾欄”。根據(jù)《國劇畫報》中對勾欄的描述記載,勾欄為四面封閉的演出場所,僅一個出口可供人出入。如此有了固定的演出舞臺,并將演員和觀眾集中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更大程度地提高了觀眾對于演出內(nèi)容的“接收率”。
首個封閉式的劇院建于16世紀(jì)的英國。國內(nèi)早期劇院于清朝建造,時稱城市劇院。隨著劇院的出現(xiàn),更加專業(yè)的舞臺設(shè)備和演出配套設(shè)施,讓戲曲如西方戲劇一般登上了“大雅之堂”。劇院內(nèi)的戲曲演出帶來最直觀的影響就是劇目的藝術(shù)性和觀賞性提高了。它不僅表現(xiàn)在演員創(chuàng)造能力的提升和藝術(shù)手段的增多,而且無打擾環(huán)境也提升了觀看的舒適感。據(jù)記載,清代知名戲班開始對戲曲演員進(jìn)行遴選,名角制也在此時開始產(chǎn)生,戲子伶人的地位也開始上升。在劇院環(huán)境的作用下,此時創(chuàng)作的戲曲劇目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來看,都更加適合觀眾全身心地投入觀賞,更接近于藝術(shù)呈現(xiàn)。
(二)劇院挖掘了戲曲演出的創(chuàng)作深度
露天戲臺的戲曲演出風(fēng)格是通俗和夸張的,劇院的劇場演出則是精致和有深度的。劇場時代創(chuàng)排的戲曲劇目大多具有思想性、戲劇性。從元曲四大家的各個經(jīng)典作品到“臨川四夢”,再到當(dāng)代優(yōu)秀編劇創(chuàng)作的劇本,這些稱得上文學(xué)作品的戲曲劇本產(chǎn)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戲曲演出場所的成熟而引起的社會對優(yōu)質(zhì)劇目需求的增加。與此同時,劇目題材也更加豐富,現(xiàn)實性立意逐步增強。早期多以喜慶劇、道德劇、神仙劇為主,到了近現(xiàn)代,各種歷史劇、時事劇、愛情劇等題材大量涌現(xiàn),像京劇樣板戲的出現(xiàn)就是戲曲劇目題材拓寬的例證。戲曲的思想性和批判性也隨之越來越強。同時,劇院的環(huán)境特點決定了舞臺中的演出調(diào)度是可創(chuàng)造的。舞臺方寸之地,變幻才會好看。豐富的調(diào)度打開了藝術(shù)家的思路,也為戲曲插上了“精致”的翅膀。許多經(jīng)典的戲曲劇目在劇院條件越來越現(xiàn)代化之后,也開始紛紛創(chuàng)排適應(yīng)劇場舞臺演出的版本,如越劇的《花中君子》《琵琶記》《荊釵記》等。這些都是不錯的新編案例,符合戲曲規(guī)律的老戲新唱是一種劇目傳承、適應(yīng)時代的好做法。多樣的舞臺設(shè)計和技術(shù)手段更容易調(diào)動演員的情緒,比如更多樣的音樂渲染和更有層次的燈光設(shè)計,都很好地提升了劇目的吸引力。不可否認(rèn),讓劇目演出變得更有深度是劇場助力戲曲邁出的一大步。
三、劇院和露天戲臺共同發(fā)展的重要性
露天戲臺孕育了戲曲千年發(fā)展所形成的藝術(shù)個性和不同于其他藝術(shù)樣式的本質(zhì)特征,演出在戲臺上展現(xiàn)時具有先天的優(yōu)勢,是戲曲藝術(shù)最直觀的呈現(xiàn)。而發(fā)展是必然的趨勢,劇院的戲曲演出所呈現(xiàn)的是其適應(yīng)時代的成果,具有更強的藝術(shù)性,在助力戲曲發(fā)展的過程中也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二者不應(yīng)以勝敗而論,也不該此消彼長。
劇院的出現(xiàn)使創(chuàng)作者和觀眾都產(chǎn)生了新的思維方式、審美習(xí)慣和審美偏好,這也是時代帶給藝術(shù)家們的新命題。但這兩種演出場所卻不該有“新舊更替”的觀念。如越劇《王老虎搶親》,就是在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元宵節(jié)的民俗文化上創(chuàng)作出的經(jīng)典作品,時至今日也常常在元宵節(jié)慶會上被搬演。它是對人們?nèi)粘I畹目坍嫸Q生的藝術(shù)作品,并非以展現(xiàn)高級藝術(shù)技巧為出發(fā)點的創(chuàng)作。其中所包含的濃郁節(jié)日氛圍和熱鬧的百姓生活,在露天戲臺上被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而在劇院這種封閉的演出環(huán)境中演出就略遜一籌了。再如近年來新編的小劇場蒲劇《俄狄王》、越劇《春琴傳》等劇目,它們需要結(jié)合舞臺來呈現(xiàn)驚艷的整體效果,像專業(yè)燈光的配合、巧妙設(shè)計的舞美烘托、音質(zhì)豐滿清晰的音響設(shè)備等各個部門共同展現(xiàn)劇目中的美學(xué)和思想。可見,在戲曲不斷發(fā)展的長河中,開放和封閉兩種演出場所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并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戲劇理論家張庚先生曾指出:在遺產(chǎn)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新戲曲,就是要在一個劇種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發(fā)展,要老百姓能接受[4]。作為戲曲工作者,“戲曲作品不是做給小部分人看的”是時刻都應(yīng)謹(jǐn)記的道理。近年來,戲曲似乎陷入了“劇場熱”,創(chuàng)作者一頭熱地扎進(jìn)劇場耕耘,對露天下鄉(xiāng)演出有所冷落。面對劇場舞臺的專業(yè)性,有的人認(rèn)為在這里演出,要時刻記住“雅”。于是設(shè)計出很多獨特、抽象的調(diào)度和手法,刻意為了制造神秘莫測的“高級”表演,來吸引小部分喜歡“研究”藝術(shù)的人,甚至丟掉了很多戲曲自己的表演語匯,如鑼鼓省略、妝容平淡、服裝寫實等。有些甚至連“舞臺方丈地,一轉(zhuǎn)萬重山”的程式都打破了,企圖跳出這些“露天戲臺演出的限制”。這就得不償失了。即使當(dāng)下對“讓戲曲跟隨時代發(fā)展適應(yīng)劇場演出”的呼吁不絕于耳,但將戲曲本質(zhì)特點的忽視和抹去卻并非讓戲曲向前發(fā)展的良方。在過去,露天演出座無虛席,時常“鑼鼓一敲,全村報到”,如今“劇場熱”卻出現(xiàn)了觀眾寥寥無幾的現(xiàn)象,這是值得深思的。露天演出是戲曲的土壤,它孕育了戲曲的藝術(shù)個性和從古至今觀眾對戲曲的情懷。戲曲需要藝術(shù)上的深度,但也更得守住自己的根脈。
于戲曲工作者而言,未來要在繼續(xù)挖深劇院戲曲緯度的同時,重新重視露天戲臺的演出,利用和發(fā)揮好露天戲臺的作用。在創(chuàng)作新編劇目時,不僅要創(chuàng)作適應(yīng)劇場規(guī)律的作品,也應(yīng)兼顧適合露天演出的新劇目。天地大舞臺,舞臺小天地。舞臺藝術(shù)的真實性來源于社會環(huán)境和百姓生活,這正是戲曲在露天戲臺環(huán)境中發(fā)展積累的。另外,要鼓勵專業(yè)院團(tuán)多下鄉(xiāng)演出,這不僅是戲曲根脈的回溯和延續(xù),也讓青年戲曲演員在切身感受中更通曉戲曲所包含的文化價值。農(nóng)村山居至今仍保留著節(jié)慶、年俗搭戲臺演大戲的風(fēng)俗習(xí)慣,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即使相較于古代變得少見,但這種力量不可忽視。近年來,部分劇團(tuán)的下鄉(xiāng)惠民演出就大有可觀。演出時拿出家喻戶曉的經(jīng)典劇目,座無虛席,各個年齡段的觀眾都有,也有小販的叫賣聲夾雜其中,依稀可見早期戲曲成熟時期的演出盛況。顯然,露天戲臺作為伴隨戲曲發(fā)展千年的演出場所,其所形成的觀演關(guān)系扎根于人們文化觀念之中,并與民族文化相適應(yīng)。
四、結(jié)束語
演出場所是戲曲呈現(xiàn)的載體。當(dāng)代要傳承和發(fā)展戲曲,首先,應(yīng)該尊重和保留它的本質(zhì)和特征。露天戲臺成就和積淀了戲曲千年以來的藝術(shù)個性,戲臺演出承載著戲曲的“根”,是其最本質(zhì)的展現(xiàn)。其次,也應(yīng)并重戲曲在當(dāng)代的適應(yīng)性發(fā)展,劇院場所精細(xì)化了戲曲的演出風(fēng)格,讓其更具有藝術(shù)性和當(dāng)代審美性,為戲曲提供了更多的“雅”。無論是劇院還是露天戲臺,都應(yīng)重視它們的不同作用,在未來兼顧適應(yīng)于兩種場所特征的劇目創(chuàng)作,相輔相成,共同助力戲曲發(fā)展的力量發(fā)揮到最大化。
參考文獻(xiàn):
[1]周貽白.中國戲劇史長編[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2]胡祗遹.胡祗遹集[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3]周貽白.中國戲劇史長編[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4]胡芝風(fēng).戲曲舞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規(guī)律[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