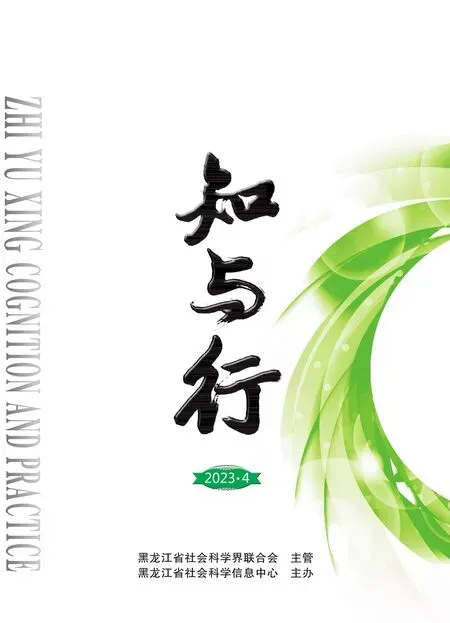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及啟示
劉 潔,劉文蕾
(華中科技大學(xué)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xué)院,武漢 430074)
“儀式”(ritual)是一個(gè)古老而又嶄新的議題。“古老”體現(xiàn)在儀式研究所積淀的豐厚歷史上,“嶄新”則源于其歷久彌新的特質(zhì)。1986年,美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學(xué)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出互動(dòng)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論。2004年,該理論在《互動(dòng)儀式鏈》(InteractionRitualChains)一書中被正式提出,并被認(rèn)為是西方社會(huì)學(xué)理論新發(fā)展的重要成果。該書自2006年由我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學(xué)者翻譯引介,在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受到廣泛關(guān)注。在前人基礎(chǔ)上,柯林斯引入情感社會(huì)學(xué)的概念,將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看作儀式的核心機(jī)制,認(rèn)為情感能量的流動(dòng)和理性選擇催生了互動(dòng)儀式鏈的形成。不同的鏈條環(huán)環(huán)相扣,其所承載的社會(huì)空間越來(lái)越大,最終形成宏觀的整體社會(huì)。[1]152-155柯林斯的洞見(jiàn)在于他將情感、個(gè)人行動(dòng)、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納入同一個(gè)理論模型中,并以情感為橋梁來(lái)連接個(gè)人與社會(huì),從微觀的互動(dòng)情景解釋“社會(huì)何以可能”的問(wèn)題。
進(jìn)入21世紀(jì),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較為完備的模型框架為我國(guó)的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國(guó)內(nèi)的經(jīng)驗(yàn)和材料也為該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與之相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產(chǎn)出更是逐年增加。特別是近年來(lái)互聯(lián)網(wǎng)的迅猛發(fā)展,微博、微信、抖音、嗶哩嗶哩等在線社交平臺(tái)日益成為學(xué)界尤其是新聞傳播學(xué)科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似乎也在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獲得了新的闡釋“活力”,成了一個(gè)“萬(wàn)能”的理論工具。但正如學(xué)者張濤甫所指出的那樣,“作為人的智性的產(chǎn)物,理論的發(fā)現(xiàn)和表達(dá)也是語(yǔ)境性的,存在偶然性和條件約束”,并且理論的傳播也離不開語(yǔ)境的規(guī)約,理論“一旦走出其原生語(yǔ)境,進(jìn)入另一種語(yǔ)境,就會(huì)面臨脫域的挑戰(zhàn)”[2]。通過(guò)梳理新聞傳播學(xué)界近年來(lái)的若干個(gè)案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作為知識(shí)的西方概念或理論資源在向中國(guó)擴(kuò)散的過(guò)程中伴隨著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即本土不加批判地簡(jiǎn)單挪用、照搬、移植西方概念或理論,出現(xiàn)偏差與誤用;第二種情況是西方概念或理論在本土面臨著碰撞、抵抗,出現(xiàn)意義的爭(zhēng)奪或話語(yǔ)的協(xié)商,如《烏合之眾》中的“群眾觀”在中國(guó)不同歷史語(yǔ)境需要下的兩次被定義[3];第三種情況則是西方概念或理論在本土的語(yǔ)境下發(fā)生“變異”[4],以至被直接綜合或馴化,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如學(xué)者劉海龍用場(chǎng)域分析方法討論了“文化工業(yè)”到“文化產(chǎn)業(yè)”的語(yǔ)境變遷。[5]
一、研究設(shè)計(jì)
(一)研究方法與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文獻(xiàn)計(jì)量分析方法,將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ce(版本號(hào)6.1.R6)作為主要計(jì)量工具。CiteSpace的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功能用來(lái)挖掘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國(guó)內(nèi)傳播與接受過(guò)程中的著眼點(diǎn),從橫向內(nèi)容維度展現(xiàn)高頻詞匯和熱點(diǎn)議題間的關(guān)聯(lián);關(guān)鍵詞突現(xiàn)功能則可以從縱向時(shí)間維度展現(xiàn)該理論整體的發(fā)展演進(jìn)脈絡(luò)。不過(guò),有研究者提出單純的知識(shí)圖譜分析只是研究結(jié)果的羅列,結(jié)論過(guò)于淺薄。因此,在知識(shí)圖譜的基礎(chǔ)上,本研究同時(shí)采用關(guān)鍵文本細(xì)讀方法,以呈現(xiàn)2006—2022年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路徑以及被想象和使用的圖景。
(二)數(shù)據(jù)來(lái)源與處理
樣本數(shù)據(jù)的質(zhì)量直接決定研究結(jié)論的科學(xué)性,根據(jù)布拉德福文獻(xiàn)離散定律,某一學(xué)科或研究領(lǐng)域的大部分關(guān)鍵成果集中于數(shù)量較少但質(zhì)量較高的核心期刊之中。[6]因此,為保證數(shù)據(jù)的權(quán)威性,我們選擇中國(guó)知網(wǎng)(以下簡(jiǎn)稱CNKI)學(xué)術(shù)期刊數(shù)據(jù)庫(kù),以北大核心和CSSCI收錄期刊為數(shù)據(jù)來(lái)源。鑒于本文聚焦國(guó)內(nèi)學(xué)界,而在SSCI數(shù)據(jù)庫(kù)中查閱的與本主題關(guān)聯(lián)性較強(qiáng)、由國(guó)內(nèi)學(xué)者獨(dú)撰或合撰,且位于JCR分區(qū)Q1、Q2的文獻(xiàn)較少(1)筆者在WOS-SSCI數(shù)據(jù)庫(kù)中以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或Randall Collins為主題進(jìn)行檢索,共計(jì)得到155條結(jié)果,手動(dòng)統(tǒng)計(jì)每條結(jié)果與本研究?jī)?nèi)容的關(guān)聯(lián)性、作者來(lái)源和構(gòu)成、權(quán)威性,僅有7篇符合要求,被引頻次均較低。檢索的截止時(shí)間為2023年4月24日。,因此SSCI數(shù)據(jù)庫(kù)不包含在此次數(shù)據(jù)選擇范圍內(nèi)。本研究在保證文獻(xiàn)質(zhì)量的基礎(chǔ)上,為了兼顧研究的全面性,將文獻(xiàn)篩選范圍擴(kuò)大到CNKI碩博士學(xué)位論文庫(kù),并于必要時(shí)進(jìn)行單獨(dú)分析。
文獻(xiàn)檢索與數(shù)據(jù)處理過(guò)程如下:在CNKI中選擇高級(jí)檢索模式,分別以“互動(dòng)儀式鏈”“儀式鏈”“互動(dòng)鏈”“蘭德爾·柯林斯”為主題或關(guān)鍵詞進(jìn)行精確檢索核心期刊文獻(xiàn)并導(dǎo)出。再以“互動(dòng)儀式鏈”“蘭德爾·柯林斯”為主題單獨(dú)檢索碩博學(xué)位論文,兩次檢索均勾選同義詞擴(kuò)展,起始年不限制,結(jié)束年設(shè)置為2022年。第一輪統(tǒng)計(jì)共得到295篇核心期刊論文以及301篇碩博學(xué)位論文。為保證數(shù)據(jù)的有效性,筆者對(duì)已選數(shù)據(jù)進(jìn)行二次篩選。人工核驗(yàn)并剔除重復(fù)、信息不全、弱關(guān)聯(lián)、內(nèi)容不符等無(wú)效文獻(xiàn),同時(shí)使用Citespace軟件的Remove Duplicates(去重)功能清洗,最終得到共計(jì)557條有效樣本數(shù)據(jù)。其中,核心期刊論文257篇,碩博學(xué)位論文300篇。數(shù)據(jù)采集的截止時(shí)間為2023年3月15日。為兼顧樣本的說(shuō)服力和可操作性,本文以被引量為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抽樣處理,分別選擇了排序前10位的10篇核心期刊論文和10篇碩博學(xué)位論文,統(tǒng)計(jì)時(shí)間為2023年3月29日。在所選20篇論文中,絕大部分來(lái)自新聞傳播學(xué)科,經(jīng)濟(jì)管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教育學(xué)各1篇。
二、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
(一)起點(diǎn):以“譯叢”身份“打包”進(jìn)入中國(guó)
20世紀(jì)80年代,柯林斯的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正在醞釀成型,我國(guó)大陸社會(huì)學(xué)也恢復(fù)重建。歷來(lái)重視移譯世界各國(guó)學(xué)術(shù)名著的商務(wù)印書館從1981年開始出版“漢譯世界學(xué)術(shù)名著叢書”,該項(xiàng)翻譯任務(wù)也是我國(guó)自有現(xiàn)代出版以來(lái)最重大的學(xué)術(shù)翻譯出版工程。其中,“社會(huì)學(xué)名著譯叢”占了重要的比例,由社會(huì)學(xué)家蘇國(guó)勛教授主持出版。他在叢書總序中指出:“對(duì)社會(huì)學(xué)來(lái)說(shuō),所謂增強(qiáng)學(xué)科意識(shí),除了參與、觀察變革社會(huì)的實(shí)踐之外,就是要提倡閱讀經(jīng)典研究大家,舍此別無(wú)他途。”[7]可見(jiàn),彼時(shí)我國(guó)翻譯西學(xué)著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鑒吸收、為我所用。正如學(xué)者周飛舟所認(rèn)識(shí)到的:“中國(guó)社會(huì)學(xué)發(fā)展的百年過(guò)程中,大量引進(jìn)西方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理論的兩個(gè)高潮期是五四運(yùn)動(dòng)以后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各約20年的時(shí)間,這兩個(gè)時(shí)間段分別面臨著救亡圖存和百業(yè)待興的重大歷史使命,很多西方理論被奉為救亡和發(fā)展的秘籍、經(jīng)典而引入中國(guó)。”[8]在上述背景下,柯林斯在2000年應(yīng)邀到中國(guó)講學(xué)并發(fā)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系列演講;2004年,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林聚任等在獲贈(zèng)《互動(dòng)儀式鏈》英文版后決定翻譯該書;此后,中文《互動(dòng)儀式鏈》一書分別于2009年、2012年和2021年出版三次,并被納入商務(wù)印書館“社會(huì)學(xué)名著譯叢”。據(jù)了解,“漢譯世界學(xué)術(shù)名著叢書”的出版考核標(biāo)準(zhǔn)之一為“選題上一定選取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xué)術(shù)經(jīng)典著作”[9]。可以說(shuō),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正是基于中國(guó)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起點(diǎn)下從大洋彼岸而來(lái),在國(guó)家發(fā)展需要和學(xué)術(shù)進(jìn)步需要的雙重動(dòng)力下,以著作的翻譯引介、納入譯叢為擴(kuò)散的媒介,逐漸被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了解、吸收和發(fā)展。
(二)路徑:時(shí)間、學(xué)科及內(nèi)容
從時(shí)間路徑來(lái)看,國(guó)內(nèi)圍繞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學(xué)術(shù)研究于2006—2022年總體呈上升態(tài)勢(shì),核心期刊文獻(xiàn)與碩博學(xué)位論文的數(shù)量變化趨勢(shì)基本一致。具體而言,引介初期只有零星文獻(xiàn),自2011年開始緩步提升,2016年到達(dá)研究的第一次小高峰,文獻(xiàn)量達(dá)到10篇及以上;2017—2021年增速較快,核心期刊及碩博學(xué)位論文分別攀升至57篇、81篇,可以推知此時(shí)學(xué)界對(duì)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呈高度集中的關(guān)注趨勢(shì);2022年碩博學(xué)位論文數(shù)量雖有較小回落,但相關(guān)討論仍舊熱度不減。綜上,可將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大致分為三個(gè)時(shí)期:引介期(2004—2010年)、攀升期(2011—2016年)和爆發(fā)期(2017—2022年)。
從學(xué)科路徑來(lái)看,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傳播主要集中于社科領(lǐng)域。不同學(xué)科對(duì)該理論的吸收度存在差異,其中占比最大的依次為新聞傳播學(xué)、教育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科下的碩博學(xué)位論文、核心期刊論文占比遙遙領(lǐng)先,分別約為61%、36.6%,是該理論發(fā)端學(xué)科——社會(huì)學(xué)的近12倍和5倍。這與學(xué)者張振亭等的研究結(jié)論相契合,他們發(fā)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傳播研究繁盛的語(yǔ)境下,新聞傳播學(xué)學(xué)科交叉性大幅增強(qiáng),2006—2017年間“引用的知識(shí)中近一半來(lái)源于其他學(xué)科”[10],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知識(shí)占比較為顯著。
從內(nèi)容路徑來(lái)看,首先借助CiteSpace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功能(2)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將257篇核心期刊論文的數(shù)據(jù)導(dǎo)入CiteSpace,以1年為一個(gè)時(shí)間分區(qū),系統(tǒng)自動(dòng)選取2006—2022年的數(shù)據(jù);使用Labels功能調(diào)節(jié)Keyword按By Freq呈現(xiàn),文獻(xiàn)節(jié)點(diǎn)標(biāo)簽數(shù)量(Threshold)設(shè)置為2,手動(dòng)刪除勾選頻數(shù)≤1的關(guān)鍵詞,其他參數(shù)設(shè)置保持默認(rèn)選項(xiàng)。可得與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相關(guān)的核心期刊文獻(xiàn)關(guān)鍵詞共現(xiàn)網(wǎng)絡(luò)圖譜,共生成539個(gè)節(jié)點(diǎn),920條連線,密度為0.0063。,不難發(fā)現(xiàn):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國(guó)內(nèi)的研究與使用中,“情感能量”和“互動(dòng)儀式”是兩大最核心的高頻詞。關(guān)鍵詞“情感能量”與“短視頻”“抖音”“網(wǎng)絡(luò)社群”“情感動(dòng)員”聯(lián)系緊密,關(guān)鍵詞“互動(dòng)儀式”則與“文化認(rèn)同”“集體記憶”有著較高的關(guān)聯(lián)度。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成為研究者分析在線互動(dòng)、認(rèn)同與動(dòng)員的常用視角和理論資源。借助CiteSpace關(guān)鍵詞突現(xiàn)功能(3)關(guān)鍵詞突現(xiàn):在篩選功能中將γ設(shè)置為0.3,Minimum Duration設(shè)置為1,選擇前20位突現(xiàn)詞。,可以推知:2015—2018年,“情感傳播”和“社會(huì)認(rèn)同”是學(xué)界關(guān)注的前沿內(nèi)容。尤其是2016年的“帝吧出征”事件,“情感動(dòng)員”“國(guó)家認(rèn)同”成為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探討的焦點(diǎn)。隨著短視頻行業(yè)的火爆以及主流媒體的紛紛入駐,2019年學(xué)界關(guān)于“抖音”平臺(tái)、“媒介儀式”、“彈幕文化”的研究迅速增多,“抖音”成為突現(xiàn)強(qiáng)度最高的詞。同時(shí),當(dāng)話題度和熱度兼具的多檔選秀綜藝陸續(xù)推出,以及“AO3”(Archive of Our Own,同人作品托管網(wǎng)站)事件的發(fā)生,碩博研究生紛紛將目光投向了“粉絲文化”與“偶像養(yǎng)成”議題。2020—2022年,突如其來(lái)的疫情防控讓居家成了常態(tài),“直播帶貨”“慢直播”成為學(xué)界關(guān)注的又一重點(diǎn)話題。
總體來(lái)看,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傳播的內(nèi)容路徑呈現(xiàn)出與時(shí)間路徑和學(xué)科路徑較高的關(guān)聯(lián)性。在引介期(2004—2010年),社會(huì)學(xué)議題占主導(dǎo),如少數(shù)民族、宗教儀式、學(xué)校教育等;攀升期(2011—2016年)和爆發(fā)期(2017—2022年)則以新聞傳播學(xué)議題為主,短視頻平臺(tái)、游戲、彈幕網(wǎng)站、直播空間、網(wǎng)絡(luò)社群等最受關(guān)注。上述議題雖各有側(cè)重,但都觸及了儀式、情感、認(rèn)同(包括社會(huì)、文化、國(guó)家及身份認(rèn)同)等內(nèi)在維度。
(三)條件: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問(wèn)題涌現(xiàn)
賽義德(Edward Said)認(rèn)為,理論或觀念“向新環(huán)境的運(yùn)動(dòng)絕不是暢行無(wú)阻的。它勢(shì)必要涉及不同源點(diǎn)的表征和體制化過(guò)程”[11]400,這關(guān)系到他所提出的被移植的理論得以被引進(jìn)、接納甚至抵制的條件。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被引介后,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師生們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接納以及如何使用這個(gè)理論的?
經(jīng)過(guò)對(duì)20篇樣本論文文本的細(xì)讀,可推知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被中國(guó)的研究者接納主要伴隨著三個(gè)條件:第一,研究田野不斷拓展。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技術(shù)的進(jìn)步以及國(guó)內(nèi)各種新媒體產(chǎn)品的涌現(xiàn)使互聯(lián)網(wǎng)新生代的在線社交需求有了實(shí)現(xiàn)的可能,這一網(wǎng)絡(luò)社交化趨勢(shì)天然地契合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對(duì)于人際“互動(dòng)”問(wèn)題的探討。同時(shí),行業(yè)內(nèi)社交產(chǎn)品的垂直細(xì)分化、場(chǎng)景化等為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應(yīng)用提供了豐富且廣闊的研究田野。第二,研究對(duì)象愈發(fā)全面。全球化背景下社會(huì)包容性的提高、年輕人思想的轉(zhuǎn)變使網(wǎng)絡(luò)亞文化在中國(guó)擁有了相當(dāng)程度的發(fā)展空間,ACG文化族群、飯圈粉絲等長(zhǎng)期被忽視的亞文化群體逐漸顯性化,在網(wǎng)絡(luò)空間形成了一種新奇而特殊的互動(dòng)現(xiàn)象。第三,研究情境逐漸豐富。一方面表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群體性事件的頻發(fā),理清其內(nèi)部互動(dòng)機(jī)制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治理的關(guān)鍵;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在“網(wǎng)紅經(jīng)濟(jì)”“粉絲經(jīng)濟(jì)”和“社群經(jīng)濟(jì)”的繁榮,“互動(dòng)”成為消費(fèi)者注意力變現(xiàn)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
(四)使用目的:政策和行業(yè)導(dǎo)向?yàn)橹?/h3>
我們將所選樣本論文分為三類,即現(xiàn)象探究導(dǎo)向、政策和行業(yè)建議導(dǎo)向以及人文關(guān)懷導(dǎo)向。以現(xiàn)象探究為目的的論文旨在借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闡釋組織內(nèi)部的運(yùn)轉(zhuǎn)、互動(dòng)機(jī)制,加深對(duì)某一群體、現(xiàn)象、事件的理解,如有樣本論文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框架指導(dǎo)下厘清了“帝吧出征FB”事件中表情包的情感動(dòng)員路徑和能力。[12]以政策和行業(yè)建議為落腳點(diǎn)的論文則更希望在明晰互動(dòng)過(guò)程的基礎(chǔ)上為政府、行業(yè)、市場(chǎng)主體、媒體、群體等建言獻(xiàn)策,如有樣本論文通過(guò)對(duì)斗魚TV游戲直播平臺(tái)里參與者互動(dòng)狀況的分析,以期挖掘出構(gòu)建平臺(tái)黏性的因素,為平臺(tái)良性發(fā)展、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價(jià)值提供借鑒。[13]以人文關(guān)懷為導(dǎo)向的論文更在乎借具體的微觀互動(dòng)儀式思考人機(jī)關(guān)系、人際關(guān)系等議題,如有樣本論文透過(guò)移動(dòng)社交媒體的互動(dòng)儀式探討傳播的本質(zhì),思考新媒介技術(shù)與人的關(guān)系。[14]綜上可見(jiàn),國(guó)內(nèi)研究者對(duì)于為什么要應(yīng)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有著不同的考量。值得關(guān)注的是,政策和行業(yè)建議導(dǎo)向占比最大,說(shuō)明研究者更在乎成果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指導(dǎo)意義。
(五)“形變”:虛擬在場(chǎng)的挑戰(zhàn)
理論傳播的最后一個(gè)步驟是“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納(或吸收)的觀念因其在新時(shí)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11]400-401。學(xué)者陸揚(yáng)對(duì)此有相同的看法,認(rèn)為“理論旅行”是指理論在傳播、發(fā)展、接受過(guò)程中,自身發(fā)生的形態(tài)、力度、指向的變遷。[15]我們將這種現(xiàn)象概括為“理論擴(kuò)散的形變”。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遭遇的“形變”主要表現(xiàn)在使用條件上,其中,“身體在場(chǎng)”要素面臨著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虛擬在場(chǎng)”的替代挑戰(zhàn),超過(guò)80%的樣本論文不約而同地對(duì)該理論提出了疑問(wèn)和修正:親身在場(chǎng)是必要的嗎?柯林斯在《互動(dòng)儀式鏈》的“序言”中也意識(shí)到了相關(guān)質(zhì)疑,不過(guò)他認(rèn)為:“身體的聚集使其更加容易,但由遠(yuǎn)程的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的關(guān)注和情感連帶也許是可能的。但我的假設(shè)是遠(yuǎn)程儀式的效果會(huì)是較弱的。”[1]15可見(jiàn),柯林斯本人對(duì)于“虛擬在場(chǎng)”持保留意見(jiàn),而有論文就提出了電子媒體通過(guò)模擬人的生理表征來(lái)實(shí)現(xiàn)互動(dòng)儀式鏈運(yùn)轉(zhuǎn)的預(yù)設(shè),認(rèn)為隨著“可穿戴設(shè)備、物聯(lián)網(wǎng)、VR技術(shù)、無(wú)人機(jī)”等的發(fā)展可以“達(dá)到完全浸入式的親密互動(dòng)和逼真的‘在場(chǎng)感’”[16]。簡(jiǎn)而言之,技術(shù)、時(shí)代、文化語(yǔ)境的變化使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面臨著條件是否適用的檢驗(yàn),拓展了研究空間,當(dāng)然這還有待進(jìn)一步論證。
三、結(jié)論與討論
若以柯林斯在2000年應(yīng)邀到中國(guó)講學(xué)并發(fā)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系列演講為起點(diǎn),該理論至今已引入中國(guó)20余年。從文獻(xiàn)計(jì)量的結(jié)果來(lái)看,乘著“大量譯介西學(xué)著作”的東風(fēng),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經(jīng)歷了從引介期(2004—2010年)到攀升期(2011—2016年),再到爆發(fā)期(2017—2022年)的擴(kuò)散過(guò)程。該理論雖于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提出,但在中國(guó)的新聞傳播學(xué)研究中獲得了長(zhǎng)期且顯著的存在感。圍繞理論中“互動(dòng)儀式”“情感能量”兩大核心詞,由在線社交媒體平臺(tái)搭建的虛擬空間成為新聞傳播研究者們深耕的田野。碩博研究生們則進(jìn)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間,延伸到網(wǎng)絡(luò)游戲、粉絲社群、虛擬偶像和虛擬主播等較為熱門的年輕化產(chǎn)品和領(lǐng)域中,“粉絲文化”與“偶像養(yǎng)成”議題成為研究熱點(diǎn)。以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為視角或框架,國(guó)內(nèi)研究普遍觸及了情感動(dòng)員、集體記憶、媒介儀式、認(rèn)同(包括社會(huì)、文化、國(guó)家及身份認(rèn)同)等內(nèi)在維度。從關(guān)鍵文本分析的結(jié)果來(lái)看,該理論的接納與應(yīng)用背后伴隨著研究田野、對(duì)象、情境三個(gè)條件的拓展和豐富。研究目的呈現(xiàn)為現(xiàn)象探究、政策和行業(yè)建議以及人文關(guān)懷三種導(dǎo)向,提出建議是研究者們最常見(jiàn)的目的。把該理論作為研究視角或理論框架的個(gè)案和實(shí)證研究涌現(xiàn),但基礎(chǔ)性研究不足。此外,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還面臨著“身體在場(chǎng)”這一條件要素被“虛擬在場(chǎng)”替代的挑戰(zhàn)。
一直以來(lái),國(guó)內(nèi)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面臨著本土化和自主性的焦慮。由于知識(shí)生產(chǎn)長(zhǎng)期跟隨或沿用西方舶來(lái)的理論資源,理論的內(nèi)生動(dòng)力不足,經(jīng)常陷入“西方理論,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二元框架的迷惘。[17]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確對(duì)待西方理論成為論爭(zhēng)的焦點(diǎn)。通過(guò)觀察、分析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的傳播路徑、被想象和使用的過(guò)程,筆者發(fā)現(xiàn)了其中存在的若干問(wèn)題,主要表現(xiàn)在研究時(shí)間的滯后性、研究議題的同質(zhì)化以及理論使用的套路化上。
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初入中國(guó)時(shí),學(xué)術(shù)界問(wèn)津者寥寥,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直到2016年才在線上空間嶄露頭角,研究時(shí)間上呈現(xiàn)出明顯的滯后性。同時(shí),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的繁榮期(2017—2022年),研究議題呈現(xiàn)出顯著的集中趨勢(shì),這背后除了時(shí)代背景的因素,也不排除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的“亦步亦趨”化問(wèn)題。在具體使用上,似乎只要和“互動(dòng)”有關(guān)的網(wǎng)絡(luò)現(xiàn)象都可以用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框架來(lái)解釋,有時(shí)還會(huì)出現(xiàn)與其他相似理論如“傳播儀式觀”“儀式傳播”等混淆使用的情況。究其根源,作為眾多西方經(jīng)典著作之一,《互動(dòng)儀式鏈》是以譯叢的身份被“打包”引入國(guó)內(nèi)的。換句話說(shuō),其譯介并非由解決實(shí)際問(wèn)題的需要推動(dòng),而是由“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大思潮驅(qū)動(dòng)。在這種“先學(xué)習(xí)-后應(yīng)用”認(rèn)知定式下,便容易形成直接將西方理論資源套用到具體問(wèn)題上的慣性,因?yàn)椤皩W(xué)了就要用”,久而久之涌現(xiàn)眾多“精致的平庸”之作,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成為流水線作業(yè)。蘭克(Leopold von Ranke)認(rèn)為:“從特殊性出發(fā),我們可以拾級(jí)攀登到普遍性,但從宏大理論出發(fā),我們?cè)僖不夭蝗ブ庇X(jué)地了解普遍性了。”[18]131學(xué)者李金銓對(duì)此表示認(rèn)可,認(rèn)為向西方學(xué)習(xí)是必經(jīng)之路,但是在方法的實(shí)踐上,他推崇的是韋伯式現(xiàn)象學(xué)路徑,即“先從華人社會(huì)的生活肌理和脈絡(luò)入手,尋找出重大問(wèn)題的內(nèi)在理路,然后逐漸提升抽象層次”,到達(dá)一定高度后自然會(huì)與西方理論產(chǎn)生對(duì)話。最后,勾連理論與實(shí)際問(wèn)題的最佳點(diǎn),有時(shí)甚至需要再創(chuàng)理論。[18]104-105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以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duì)西方理論的條件下,互動(dòng)儀式鏈理論在中國(guó)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運(yùn)用僅停留在借用階段,缺乏對(duì)理論的基礎(chǔ)性研究和基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的理論創(chuàng)新,甚至出現(xiàn)誤用和濫用現(xiàn)象。此理論傳播個(gè)案提示我們中國(guó)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建立本土話語(yǔ)體系和提升國(guó)際話語(yǔ)權(quán)任重道遠(yuǎn)。
簡(jiǎn)而言之,對(duì)待西方外來(lái)理論,要具備全球視野,更要立足在地經(jīng)驗(yàn),要走“特殊性-普遍性”而非“普遍性-特殊性”的路徑。在增強(qiáng)學(xué)術(shù)自主性和話語(yǔ)權(quán)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味拒斥西方學(xué)術(shù)成果,而是從本土實(shí)際問(wèn)題出發(fā),同時(shí)打開視野,在合適的維度自然而非刻意地與西方理論對(duì)話、互鑒,做到“不忘本來(lái),吸收外來(lái),面向未來(lái)”[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