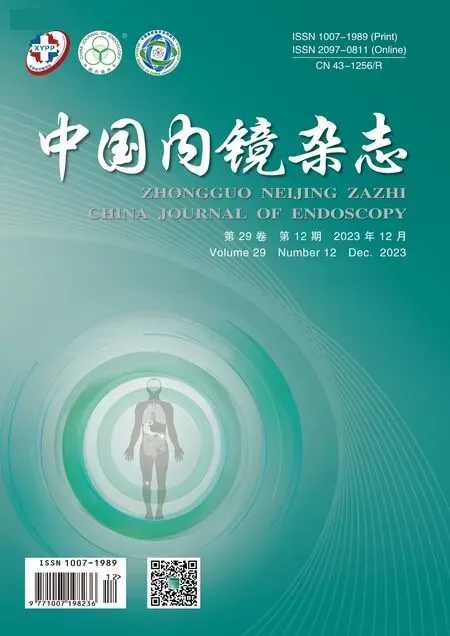不同吻合方法應用于腹腔鏡全胃切除術食管空腸吻合重建中的對比研究
龔磊,喻晶,覃相志,李敏,黃斌,任明揚,田云鴻,彭洪
[南充市中心醫院(川北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1.胃腸外科;2.肛腸外科,四川 南充 637000]
腹腔鏡治療早期胃癌,行遠端胃切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被證實[1]。中國CLASS-01 研究和韓國KLASS-02-RCT研究,為腹腔鏡下微創手術治療局部進展期遠端胃癌,提供了高級別的循證醫學依據。表明:腹腔鏡外科手術在治療局部進展期遠端胃癌,遠期療效確切,患者獲益顯著[1-3]。隨著胃近端癌的發病率逐年上升,腹腔鏡全胃切除術的比例越來越高[2]。然而,腹腔鏡全胃切除術操作難度大,對技術的要求也非常苛刻。腹腔鏡下全胃根治性切除后的難點在于消化道重建,即食管和空腸的吻合,而食管空腸吻合的方式眾多,哪種方式更好,當前仍無定論。常見的吻合方式有圓形吻合法和直線吻合法。圓形吻合法,根據釘砧座置入方法的不同,分為:反穿刺法、OrVil 法和荷包縫合法;直線吻合法包括:overlap法和π形吻合法。2009年日本學者OMORI等[4]將反穿刺法應用于腹腔鏡全胃切除術,該方法克服了釘砧座置入的難題。隨后多位學者相繼將食管-空腸π形吻合用于消化道重建中,并在腹腔鏡全胃切除術中成功應用,進一步推動了π 形吻合在臨床中的應用[5-11]。本研究通過比較腹腔鏡全胃切除術食管-空腸π形吻合法與圓形吻合反穿刺法的可行性、安全性和術后近期療效,旨在為胃外科醫生在選擇食管-空腸吻合方法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收集75 例臨床確診為胃癌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55例,女20例。75例中,27例行食管空腸π形吻合進行消化道重建,為π形吻合組(n=27);48 例行食管空腸圓形吻合進行消化道重建,為圓形吻合組(反穿刺法組)(n=48);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和術前臨床分期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納入標準:1)接受根治性腹腔鏡全胃切除術的胃癌患者;2)位于食管胃結合處(Siewert Ⅲ型)和胃體部的腫瘤;3)術后病理證實為胃癌者;4)食管-空腸吻合在全腹腔鏡下完成。排除標準:1)腫瘤浸潤至齒狀線以上的Siewert Ⅰ型和Ⅱ型食管胃結合部腺癌;2)有腹腔相關手術史,腹腔內臟粘連嚴重,中轉為開腹手術者;3)術中探查腫瘤浸潤周圍組織,器官無法切除,或廣泛轉移者;4)患有其他系統性疾病,不能耐受全身麻醉和手術者。患者及家屬均簽署相關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由同一手術團隊實施腹腔鏡全胃切除術,術者有豐富的腹腔鏡手術經驗,且均有至少50 余例腹腔鏡胃癌根治術的經驗。麻醉滿意后,患者取平臥“人”字位,頭部及左側體部均高于水平線15°,足稍低位。主刀醫生通常位于患者左側,第一助手站在右側,扶鏡醫師則位于雙腿間。建立氣腹后,觀察孔用10 mm Trocar建立于臍下,采用5孔法進行手術操作。建立氣腹后,臍下建立觀察孔(10 mm Trocar),主操作孔位于左上腹腋前線肋緣下2 cm 處(12 mm Trocar),其余三孔分別位于臍水平左側腹直肌旁(5 mm Trocar)、右側腹直肌旁(12 mm Trocar)和右側腋前線肋緣下 2 cm(5 mm Trocar)。按照日本《胃癌處理規約》,行胃癌D2 根治術,即:腹腔鏡全胃切除+D2 淋巴結清掃,并離斷十二指腸,用3/0 PDS 線荷包包埋十二指腸殘端[12]。腹腔鏡全胃切除后的消化道重建,均采用全腹腔鏡下Roux-en-Y吻合,分別為π形吻合和圓形吻合(反穿刺法)。
1.2.2 π 形吻合 游離腹段食管7~9 cm,若腹段食管較短,可打開左右側膈肌腳,擴大食管裂孔,用束扎帶結扎食管胃結合部,以屈氏韌帶為起點,至20 cm 以外的空腸處,用臨時縫合絲線做標記,經上腹取標本口提出。體外離斷空腸系膜縱行血管1 至2支,使吻合口上提無張力,再游離和離斷空腸,直至距遠端空腸斷端約50~60 cm。理順系膜后,先與近端空腸做空腸-空腸側側吻合,并關閉系膜裂孔。重建氣腹,由巡回護士插入普通胃管后,由一助醫師向左下腹牽引束帶,顯露出腹段食管,再用電凝鉤或超聲刀工作面于食道右內側壁開窗以待吻合(圖1A),上提遠端待吻合空腸,觀察系膜、腸管張力和血運良好后,用腔管長為60 mm的直線型切割閉合器,將食管和空腸做側側吻合(圖1B),于腔鏡下檢查該吻合口完整且無出血后,用1枚釘倉即可關閉食管空腸共同開口,并離斷食管(圖1C和D)。為了減小吻合口張力,常在吻合口前后壁分別全層縫合加針,以避免閉合不全(圖1E和F)。

圖1 食管-空腸π形吻合的操作過程Fig.1 Operation process of π-shaped esophagojejunostomy
1.2.3 圓形吻合(反穿刺法)先由洗手護士取一根長約10 cm的牽引線,系于管徑25 mm 的管狀吻合器的抵釘座的尾部后,經上腹取標本切口放入腹腔。重建氣腹,游離腹段食管5 cm,用束扎帶結扎食管胃結合部,在胃管支撐下,于食管右側壁用超聲刀切開一3 cm小口(圖2A),將抵釘座完全置入食管,外置牽引線位于食管切開線近口端(圖2B)。用腔管長為60 mm 的直線型切割閉合器離斷食管(圖2C),牽引絲線,將抵釘座中心桿輕柔地拖出食管(圖2D),解除氣腹后,完整移出標本。與π 形吻合組方法相同,體外完成近端與遠端空腸的側側吻合,并關閉系膜裂孔。由遠端空腸斷端放置管型吻合器主體,并距空腸斷端5 cm 穿出待吻合,用手套制作簡易約束帶,約束吻合器處空腸,重建氣腹,在腹腔鏡監視下,避免空腸系膜扭轉,管狀吻合器主體與抵釘座對合后,完成食管空腸端側吻合(圖2E),保留距吻合口3 cm左右空腸后,遠端空腸斷端用直線型切割閉合器離斷(圖2F)。食管空腸吻合口前后壁間斷包埋。

圖2 食管-空腸反穿刺法吻合的操作過程Fig.2 Operation process of esophagojejunostomy by reverse puncture
1.3 觀察指標
1.3.1 術中情況 包括:手術時間、食管空腸吻合時間、術中出血量、淋巴結清掃總數、術中食管空腸吻合相關并發癥(吻合口閉鎖、吻合口狹窄和吻合口撕裂)等。
1.3.2 術后情況 術后食管空腸吻合口相關并發癥(吻合口出血、吻合口狹窄和吻合口瘺)。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或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等級資料比較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比較
75 例胃癌患者均完成了腹腔鏡根治性全胃切除術,無中轉開腹手術。π形吻合組手術時間和食管空腸吻合時間分別為(221.5±8.8)和(34.7±3.7)min,與反穿刺法組的(246.9±5.6)和(47.2±4.6)min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15.19,t=11.81,P<0.05)。兩組患者術中出血量和淋巴結清掃總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surgic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2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2.2.1 術中并發癥 反穿刺法組發生術中并發癥2例,包括:食管空腸吻合口閉鎖1 例,吻合口撕裂1例。行食管空腸吻合時,將空腸遠端系膜側黏膜釘合在吻合口上,術中測漏時,胃管不能通過吻合口,經術中胃鏡證實為吻合口閉鎖。于腹腔鏡下沿右側吻合口切開,直至被釘合的對側黏膜被切開,在胃管支撐下,用倒刺線連續縫合切開的吻合口右側壁。吻合口撕裂為吻合口黏膜及肌層撕裂,術中胃管注入美蘭,發現有美蘭從空腸系膜側漏出。于腹腔鏡下拆除原吻合口,繼續游離食道殘端,手工完成荷包縫合,空腸做7 cm 長的儲袋,完成食管空腸儲袋吻合。經過上述處理,2例患者術后均順利恢復。
2.2.2 術后并發癥 反穿刺法組發生術后并發癥3例,包括:吻合口狹窄2 例,吻合口出血1 例。吻合口狹窄發生在術后3~6 個月,在胃鏡下擴張治療,癥狀緩解。吻合口出血發生在術后3 d,給予藥物止血等對癥處理后,好轉。
3 討論
3.1 腹腔鏡全胃切除術的臨床應用
隨著腹腔鏡器械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全腔鏡下消化道重建是腹腔鏡全胃切除術的必然趨勢,尤其是對于肋弓夾角狹小、腫瘤位置高和有肥胖癥的患者,其優勢更為明顯[13]。全胃切除術后,全腹腔鏡下吻合的安全性,一直是廣大外科醫生最為關注的問題。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的高低,決定該手術安全與否,以及其能否在臨床推廣應用。腹腔鏡全胃切除術消化道重建首選Roux-en-Y吻合,但何種吻合方式更佳,尚無定論。根據食管空腸吻合器械的不同,分為:應用腔內直線型切割閉合器行食管-空腸側側吻合,以及應用圓形吻合器行食管-空腸端側吻合[12-18]。
3.2 腹腔鏡全胃切除術不同吻合方法的應用
3.2.1 食管-空腸吻合 目前,臨床常用的腹腔鏡下食管-空腸功能性端端吻合(functional end-to-end anastomosis,FETE)是OKABE等[19]在原FETE基礎上改良而來的。吻合前,先將食管和空腸分別離斷,于兩斷端分別開口,分別置入直線型切割閉合器,行食管-空腸的側側吻合,再用腔內器械關閉其共同開口[19]。王自強等[20]于2007 年提出完全腹腔鏡下食管-空腸側側吻合。該方法與UYAMA 等[21]的吻合方法區別在于:小腸食管均未離斷,可以將食管向下牽拉,避免食管縮回胸腔,有利于吻合。該方法也就是自牽引,后離斷,即π形吻合前身。2016年,KWON等[22]提出π形吻合,也稱三合一技術,即用直線型切割閉合器離斷食管和空腸,同時關閉共同開口。蒿漢坤等[23]報道了100 例腹腔鏡全胃切除術后,應用π 形吻合行食管空腸重建,臨床效果明確,進一步證實了π形吻合的安全性。
3.2.2 開展π 形吻合的經驗 本團隊開展π 形吻合的初步經驗如下:1)離斷空腸系膜縱行血管1至2支,以減小食管空腸吻合口張力;2)從共同開口常規檢查吻合口有無出血;3)在食管空腸吻合口的最高點,前后壁間斷加強縫合;4)在吻合口下方5 cm處,將空腸漿肌層和右側膈肌縫合,減小吻合口張力;5)術畢,經胃管注入美蘭,檢查有無吻合口滲漏。π形吻合組手術時間和食管空腸吻合時間分別為(221.5±8.8)和(34.7±3.7)min,與反穿刺法組的(246.9±5.6)和(47.2±4.6)min 比較,π 形吻合行消化道重建的時間,比圓形吻合器(反穿刺法)重建更短,更適宜臨床推廣應用。
3.2.3 反穿刺吻合法 2009 年日本學者OMORI等[4]首次報道了反穿刺法,該方法解決了釘砧座放置困難的問題,使得管狀吻合器行全腔鏡食管空腸重建變得容易。本中心將反穿刺法應用于全腔鏡下食管空腸吻合口重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1)在胃管支撐下,切開食管右側壁,只有一個危險三角,而傳統的方法是在食道殘端中心穿出,有兩個危險三角,術后吻合口瘺的概率會相對大一些;2)避免牽引線夾入直線型切割閉合器中;3)若腹段食管斷端預留的穿引孔洞較小,切忌暴力拖拽牽引線,如果牽引線拉斷后,抵釘座完全滯留于食管中,可嘗試借助腔內扁頭彎鉗的支撐力,將預留孔洞小心撐開至可拖出抵釘座中心桿為止[24];4)食管空腸吻合口前后壁漿肌層間斷加強,間斷包埋漿肌層空腸閉合端;5)術畢經胃管注入美蘭,檢查有無吻合口滲漏。本中心曾用反穿刺法行食管空腸吻合,遇到空腸較細,伸入25 mm吻合口器較為困難的情況,通過在吻合器機身外涂抹石蠟油,注射解痙藥物后,完成了食管空腸吻合[24];然后,在經胃管注入美蘭,檢查有無吻合口滲漏時,發現吻合口系膜側有美蘭滲出,切開空腸側系膜,可見吻合口撕裂,只有外面漿膜層完整,拆除原吻合口,行空腸儲袋和食管吻合。
綜上所述,全腹腔鏡下食管空腸π形吻合和反穿刺法吻合均是安全、可行的。在食管空腸吻合時間方面,π形吻合重建時間更短;當腫瘤位于胃體和胃上部,腫瘤未累及齒狀線,小腸較細,伸入吻合器較為困難時,π形吻合優勢較為明顯。由于π形吻合是先吻合后離斷,不能判斷近切緣有無侵犯,特別是黏膜下浸潤的腫瘤。所以,當腫瘤為浸潤至齒狀線以上的SiewertⅠ型和Ⅱ型食管胃結合部腺癌,不推薦運用π形吻合,推薦反穿刺法,使用管狀吻合器重建。臨床可根據患者具體情況和各中心的吻合經驗,做出個體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