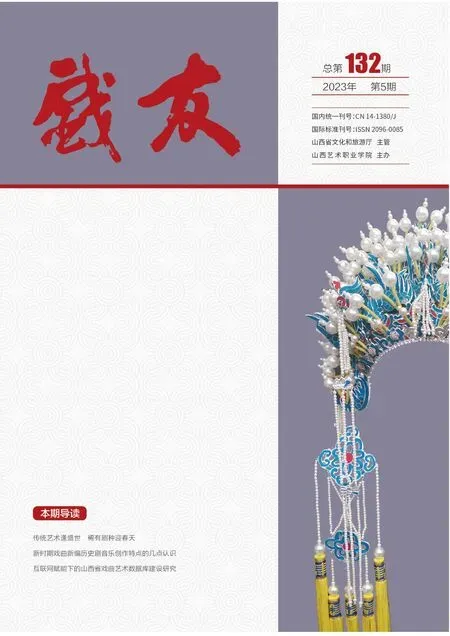舞劇《粉墨春秋》回望
成 瀟
舞劇這一舶來藝術品,傳入中國已百余年,是舞與劇的高度融合,其不止表現(xiàn)為具有舞蹈的典型特征,更多的是與戲劇內(nèi)容的結合,使得舞劇體現(xiàn)出強大的戲劇內(nèi)涵。

舞劇在中國百年的發(fā)展中受到中國文化的大力影響與浸潤,逐漸融入了中國特色和中國元素,成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式舞蹈藝術。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近些年來,我國不斷排演出各種傳統(tǒng)文化、紅色文化等不同題材的舞劇,如《永不消逝的電波》《草原英雄小姐妹》《粉墨春秋》《精忠報國》等,深受觀眾的肯定與青睞。
《粉墨春秋》是眾多舞劇中傳播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優(yōu)秀作品。2011年,山西藝術職業(yè)學院華晉舞劇團全力打造而成。講述了民國初年一個梨園戲班中三個師兄弟人生經(jīng)歷的榮辱起浮。其通過戲曲的不同行當,演繹人生百態(tài),并借用“戲中戲”的形式再現(xiàn)了世間的恩怨情仇。《粉墨春秋》不僅展現(xiàn)了舞蹈自身的魅力,還在“劇”的闡釋上下足了功夫。劇中充分借用中國戲曲故事來表達本劇主題,利用舞蹈與戲曲元素的融合,凸顯中國傳統(tǒng)藝術,如古典舞中“身韻”與戲曲“身段”的結合,舞蹈 “技巧”與戲曲“武功”的結合,戲曲“蹺功”“髯口”與舞蹈劇情的水乳交融,使本就有著相同根脈的藝術形式完美地貼合在一起,這種獨特的創(chuàng)意手段,造就了《粉墨春秋》形神兼?zhèn)洹忭嵣鷦拥臍赓|(zhì)與形態(tài)。
一、立意宏大的創(chuàng)作構想
山西是戲曲大省,被譽為“中國戲曲的搖籃”。據(jù)統(tǒng)計,山西現(xiàn)存戲曲劇種38個,無論從數(shù)量、形式、表演特點而言,都令人驚嘆。如此繁盛的戲曲文化為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深厚的藝術底蘊和可挖掘的歷史資源。《粉墨春秋》選用戲曲作為戲核,便是深刻地掌握了山西文化的精髓,這一運用既是對傳統(tǒng)戲曲藝術的普及和傳播,也是對山西文化在全國乃至世界的力薦和推廣。因舞劇與戲曲本身不同,戲曲具有較強的地域性,由于各地方言與語音的差異,致使唱腔這個戲曲的核心在傳播中受到一定局限。舞劇則沒有唱腔的限制,不受限于國界與地區(qū),避免了因語言而造成的溝通困難,這也是舞劇自身具備的優(yōu)勢之一。以此為創(chuàng)作理念,該劇打通了傳統(tǒng)文化傳播的壁壘,對于讓世界了解山西文化、了解中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引發(fā)了觀眾在歷史與現(xiàn)實中的呼應、在傳統(tǒng)與當下間的思考。
二、特點鮮明的表現(xiàn)形式
《粉墨春秋》作為一部以戲曲故事來串聯(lián)舞蹈形式的舞劇,可謂視角獨辟蹊徑。劇作以古典舞為核心,吸納了戲曲表演元素,無論從內(nèi)容到外延抑或表現(xiàn)形式、舞蹈語言、行為內(nèi)涵等無不流露出其獨特的個性特質(zhì),使這部劇具有了更強的凝練性與新的高度和意義。

首先,本劇抽拔出了戲曲中“行當”這一概念。戲曲行當是戲曲表演長期積累的產(chǎn)物,具有極強的程式性。本劇選取了武生行當中三個不同的人物特點,大師兄長靠武生、二師兄短打武生與三師弟撇子武生,用行當來扮演人物。通過戲曲行當這一特殊的戲曲表演形式,使人物富有強烈的身份意義,在舞蹈表演的同時,展現(xiàn)形象與身體語匯,在戲曲程式中展示舞蹈形態(tài),在藝術構建中實現(xiàn)本土表達,使本劇形成了獨特的美學特征與個性化的戲曲范式創(chuàng)作。
其次,在本劇的表達上極大地融入了戲曲的五法與表演技巧,即手眼身法步與戲曲特技。戲曲乃是以歌舞演故事,因此戲曲與古典舞蹈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在《粉墨春秋》中體現(xiàn)得很是突出,其細枝末節(jié)中,無不體現(xiàn)著戲曲元素,但始終緊貼著舞蹈這一主題。如本劇中,借用了著名京劇武生戲《挑滑車》《殺四門》等來拉近戲曲與舞蹈的關系,如長靠武生大師兄,就是選用了《挑滑車》片段來刻畫人物的英勇善戰(zhàn);如二師兄扮演的短打武生,則是利用了《殺四門》片段來呈現(xiàn)命運多舛的角色性格。
《粉墨春秋》中對戲曲技巧的運用更是一大亮點。具體表現(xiàn)在髯口舞、水袖舞與蹺功舞的運用上。拿水袖舞來說,水袖在舞蹈的身韻課程中是必修課,但所用水袖袖長較短,學習和掌握起來相對容易。該劇借用了戲曲旦角演員的長袖袖長與技巧,用兩米五長的水袖進行表演。一方面袖子較長,不易控制,拋撒方向難以把握;另一方面,水袖滑軟,揮灑高度和技巧也不易掌握,對演員來說是個挑戰(zhàn),但對演劇效果來說確是極大的烘托。不僅如此,如髯口舞也是在京劇的基礎上增加了晉劇極具爆發(fā)力特點;蹺功則承襲了女性不登臺、用男演員來表演等特點,從這些角度來說,戲曲技巧的添加使該劇呈現(xiàn)了“舞與技”的完美嫁接,是“舞與戲”的深度結合,也是不同藝術門類的融合傳承。
三、對中國舞蹈文化的建設意義
《粉墨春秋》可以說是一部具有民族性的舞劇典范之作。其在舞蹈化的進程中對舞劇的表演方式、審美追求都是一種深入與延展。他對傳統(tǒng)戲曲的成功借鑒,使劇作保持了獨特的文化個性與特色。特別是將其作為中國當代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其也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與意義。從其自帶的文化厚度與其傳播的廣度而言,《粉墨春秋》強化了傳統(tǒng)文化與民族特性,也在豐富中國“古典舞”的表演實踐中寫下了濃墨華彩的一筆。特別是在當下舞蹈化與現(xiàn)代化的快速融合進程中,古典舞在某種程度上丟失了民族文化特色,《粉墨春秋》逆流而上,對傳統(tǒng)古典藝術進行吸納并揚棄繼承,將戲曲元素浸透其中,對當下舞劇創(chuàng)作給予了一定啟示與方向。
舞劇的核心是舞,但如何撐起核心、如何演繹核心、如何表現(xiàn)核心,是需要舞蹈人不斷探索的。而從《粉墨春秋》的成功上演也不難發(fā)現(xiàn)一條通向成功的道路,即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舞劇藝術表演,這或是可資借鑒和參考的一種模式、一種體裁以及一種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