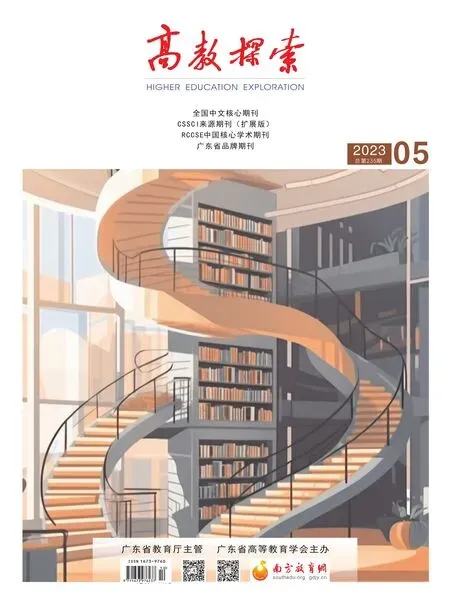李書田與近代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現代變貌*
何 睦
就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現代化進程而言,李書田是一位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李氏既是知名的水利工程專家,也是民國時期工程類大學校長的優秀代表。由于時代因素,其高校履職經歷豐富但又曲折,抗戰前曾任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原唐山交通大學,以下簡稱“唐交”)和北洋工學院(原北洋大學,以下簡稱“北洋”)院長,抗戰期間先后籌組和執掌國立西北工學院等6所高校,抗戰勝利后又任復校后的北洋大學工學院院長。其中,李氏在1930-1937年執掌唐交和北洋兩校時期,按照當時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最新趨勢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不僅成功使當時正遭瓶頸的兩所老牌名校重煥活力,而且事實上推進了中國早期工程類高校向兼具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功能于一體的現代大學的轉型。由于種種原因,教育史學界關于李書田的系統性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雖然經過部分學者的努力,學界在李氏高等教育思想及科學成就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宏觀性共識,但對其工程教育實踐中最為華彩的“唐交—北洋”時期,尚欠缺一次深入史料并基于全局性視角的剖析。從教育史的角度來說,這也是我們深度觀察中國高等工程教育“近代—現代”轉型細節的難得機遇。在當前建設新工科和雙一流大學政策疊加的背景下,我國高等工程教育再次面臨調整與煥新。本文或亦可為探索解決新時期工程類大學發展和規劃一系列問題,攢聚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
一、民國最年輕大學校長的成長歷程
在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中,李書田保持著一項紀錄,其出任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時只有30歲,執掌北洋工學院時也僅32歲。雖然由于當時人才稀缺,青年學者擔任大學校長的情況并非孤例,但李書田能在剛入而立之年主政兩所知名大學,顯然曾為同輩翹楚。他既具國際視野,同時又有站位國家社會經濟整體發展思考的全局意識,自身亦是出色的工程專家,最重要的是胸懷一腔熱忱的工程教育救國理想,這一切都與其充實且豐富的求學和執教經歷息息相關。
李書田于1900年出生于直隸省盧龍縣新房子村(現屬河北省昌黎縣),其胞兄李書華亦為著名物理學者。李氏家鄉位于灤河和青龍河交匯之處,由于近代以來河道年久失修,經年泛濫,少年時李書田便已確立投身水利工程事業之志。1917年,李書田從冀東名校直隸省立第四中學畢業,如愿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并于兩年后升入土木工程科正科學習。北洋大學立校于1895年10月,為近代中國高等工程教育之肇端。創校人盛宣懷為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在甲午戰前已在津創辦北洋電報學堂、水雷學堂等若干“中體西用”的洋務學堂,初步培養了一批近代工業人才。但甲午之敗使其認識到:“日本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設學堂……制造槍炮開礦造路諸工、皆取材于機器工程科、地學、化學科矣。”[1]即中國欲求富國強兵,也必須完整引進西方高等教育學制,培養高級工程人才才能達成。因此,“北洋大學堂”首設的“礦務、工程(土木)、機器、律例”四科中三科為工科,辦學目標直指培育能夠引領產業自主發展的技術精英。可以說,李書田日后對辦學定位毫不妥協地堅持,以及工程技術救國等思想,與北洋或者說高等工程教育最初所背負的歷史使命有著緊密的承繼性關聯。
就在李書田入學的同一年,教育部敕令北洋大學法科與北京大學工科互換,北洋就此成為了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純工科大學。不僅師資幾乎全為高水平外教,學業要求亦極為嚴格,由時任校長著名教育家趙天麟提出的“實事求是”校訓,更是初步明確了高等工程教育的學術特色。在這樣的環境中,李書田度過了聞雞起舞的大學生活。據曾與其同宿舍的水利專家張度回憶:“每天凌晨我起身較早,但他起得更早,盥洗后,他早就去大樓繪圖室了。晚餐后他仍去教室或繪圖室學習,總是很晚了才夾著大量的圖書回來。學校規定夜十一時熄燈,電燈熄了,他往往點燃上一只小煤油燈,繼續攻讀或寫作。”[2]由于刻苦努力,李書田在校期間取得了令同輩望塵莫及的成績。1923年,李書田本科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庚款留學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深造。這段孜孜以求的求學經驗,也促進其日后高標準人才觀、師資觀的形成。
對于李書田來說,赴美留學的意義并不僅僅限于個人學位的獲取,更是其接受并把握國際高等教育理念和發展動向的關鍵時期。進入20世紀以后,綜合化和服務社會已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界的共識。以李書田留學的康奈爾大學為例,對大多數近代中國留學生來說,該校以農工科技著稱,是美國工程類大學的代表,甚至北洋和唐交都曾因專精工科而獲“東方康奈爾”之譽。但實際上彼時的康奈爾大學隨著文學、歷史學、醫學等專業的成功開設,業已作為高水平綜合大學而聞名全美。另一方面,該校建校伊始的“康奈爾宣言”本身便是美國大學服務社會理念的首聲,且隨著美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和完成,原本居于鄉村小鎮的康奈爾校方也開始向城市社會靠攏。尤其是該校于20世紀20年代在紐約曼哈頓創建完成的醫學院體系,成為李書田日后在天津市中心規劃北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的重要啟示。[3]總之,在美所見所聞,皆促使李書田從廣闊的社會視角來思考高等教育問題,其博士論文也以偏重經濟管理的《鐵道管理工程經濟》(Engineering Economics of Railroad Operation)[4]為選題。1926年畢業后,他進入了世界著名工程師瓦代爾的公司,從事橋梁設計工作,這段工作經歷為他積累了珍貴的實際工程經驗。
1927年秋,李書田受時任北洋大學校長劉仙洲邀請回母校任教。劉仙洲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極具遠見卓識的工程教育家,其執掌北洋時期,制定了學校歷史上最初的長期發展規劃。在李書田日后的高等教育思想中,劉氏規劃中提出的擴充學系、理工并行發展等[5]思路均有跡可循。不過由于時局動蕩,劉仙洲的規劃沒能付諸實施。劉氏于1928年去職后,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接任北洋校長。茅以升一生勤勉,在掌校期間每周“騰出三天時間(包括星期日)搞科學研究”[6],其對科研活動的重視態度亦在全校形成垂范。從趙天麟到劉仙洲、茅以升,三位早期工程教育家從不同角度對李書田形成了積極引領,也喚起其關于高等工程教育現狀的“問題意識”。
1930年5月,李書田受各界推薦,出任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時名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正式開啟大學校長生涯。1932年8月又在時任北洋工學院院長蔡遠澤的舉薦下回到母校,接替抱疴請辭的蔡氏出任院長,直到抗戰爆發。這一時期是李書田高等工程教育思想成型和實踐的重要時期。此前由于各種原因,兩校正不同程度地面臨辦學方向、學生就業、辦學經費、學科建設等等問題。此外,兩校還分別各有棘手之題。唐交在民國前期原以“唐山交通大學”聞名于世,并獨立發展。但國民政府成立后,將原上海、北平、唐山的交大三校再次合并為一校,以上海為本部,北平、唐山為分院。①但“交大三院,歷史各殊,優點大異,教程風氣,亦不盡同”[7],這就使唐交亟待厘清自身定位,并確立新的發展方向。而“老北洋”更是由于沒有滿足國民政府“三院九系”[8]以上方能稱為大學的新規定,被迫于1928年更名為“北洋工學院”,令師生校友痛心疾首。作為當時歷史最為悠久的工程類大學,兩校的困境也昭示了中國高等工程教育已走到調整轉型的關口。
此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京津冀地區淪為抗日前沿,也促使李書田從更高層面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的定位問題。他曾于多種場合闡辟了“以高校建設維系主權之存在”的宗旨。如在擴充恢復北洋大學的問題上,他提出:“天津數載以來,儼如危城……倘只顧充實腹地大學,勢必長窺伺之心”[9]。同樣,在回應唐交是否遷校問題上,他明確指出:“唐山在余長院時,已大加擴充與充實……大家都知道唐山的特殊環境……此為確保唐山為我國土的決心之重要表示”[10]。而在談到高等工程教育之于抗日救亡的意義時他又鼓勵師生:“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大學之責任愈大……尤其以應用科學為國家富強樞紐之現代我工程學院,所負之使命愈大。”[11]可以這樣說,民族危局尤其激發了李書田推動中國高等工程教育大跨度發展的緊迫感和決心。
二、李書田的高等工程教育實踐
如前所述,李書田掌校后所面對的是老校積弊,因此其主要辦學實踐可以概括為“革舊布新”。所謂“舊”,即漸為滯礙的早期大學辦學思路和機制;所謂“新”,即引進全新的現代高等教育理念。并且作為青年大學校長,其深層次的教育思想又是在革舊布新的摸索過程中同步萃取出來的,因而特別散發著實踐的光輝。其主要舉措,可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明確人才培養目標,錨定辦學層次
李書田認為,現代工程實踐是具有高度復雜性的系統社會活動,因此受過大學教育的高級工程人才不應只是技術工匠,而應是集技術供給、項目組織、資源調配等多種角色于一身的“工程師”,而師資相對完備的國立大學更應向社會輸出具有項目領導力的“工程領袖”。1935年,他在總結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高等工程教育之“五端”,“即(一)培養深厚的科學基礎;(二)訓練實際的工程技術;(三)訓練組織與管理的能力;(四)培養創業與刻苦的志氣;(五)培養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興趣”[12]。這套育人方針突破了工程技術一隅,將現代工業建設中所需的統籌領導作用、主觀意志力、創造意識和能力等要素納入人才素質范疇,不僅使中國高等工程教育有了清晰的高級人才目標,而且錨定了一流工程類大學的辦學層次。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學者多將李書田的人才思想定評為“精英教育”,難免令人產生小眾化之聯想。然其亦曾明確指出:“工科大學生每年畢業生人數不過千人而已。以中國之有待建設及急需工業化,今后中國之技術人才需要,自日益增加。中國之工程教育,在今后半世紀中,當因需要而繼長增高。”[13]換言之,其工程教育理想非僅從一校辦學優劣出發的“小而精”,而是立足全國人才需求,符合現代高等教育規模化發展趨勢的“大而精”。
以育成“卓越工程師”為目標,李書田對既有人才培養體系進行了調整。一方面,在延續兩校較為嚴格的治學傳統基礎上,加強課程的社會應用性,使學生除具備牢固的專業知識以外,還要掌握“管理上和組織上的學識”[14]。以其先后在兩校創辦水利工程專業為例,他強調:“除關土木工程及水利工程之基本科目必須教練外,經濟學科、農業學科以及水利行政、水利法律,亦應盡量設置授習”[15]。另一方面,高度重視社會實習,將實習視為連結大學課堂知識與生產實際的重要環節。他在執掌兩校期間,陸續與唐山開灤礦務局、啟新洋灰公司[16]、天津市工務局、濟安自來水公司[17]等知名企事業單位建立了實習合作關系,以切實提高學生的技能素養。此外,為了讓學生緊跟產業發展動態,李書田還盡可能邀請地方企業的一線技術專家進行講座,如當時任職于天津永利堿廠總工程師的侯德榜,便曾受聘北洋“特約講師”,來校講演“工業用水”等產業實際問題。[18]通過加強產學結合,使畢業生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據水利專家常錫厚回憶,李書田掌校時期北洋畢業生一改20年代末“畢業即失業”的情況,“不用托人情、行賄賂、走后門,專憑學識才能就可得到就業機會,這在當時真是難得之事”[19]。
(二)對接國際標準,打造一流育人環境
作為育人環境的組成部分,李書田高度重視師資和設備的引進,以及管理機制的建全。首先,他將師資水平的提高與推動學術本土化進程相結合,一方面接軌國際標準,將教師的聘用門檻提高到博士;另一方面以留學生為引進師資的主要目標,一改中國大學近代以來對外教的依賴,在保證師資水平的情況下,逐步實現了本土化高水平師資隊伍的建設。唐交的土木專家王華棠、朱泰信,北洋的水利專家周宗蓮、徐世大、冶金專家魏壽昆等一批知名學者,均在這一時期受其延攬回巢執教。由于留學生熟悉國情,愿意通過融合本土案例、編輯本土教材等手段將國外的理論知識充分“中國化”,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學生甚至發出了“愿北洋的教授都是留學生”[20]的愿景。
其次,對于實踐性較高的高等工程教育來說,先進設備的重要性不亞于師資,且如李書田所言,由于“充實設備與添建校舍是不可分離的”[21],還需要增建實驗樓等必要的建筑,這在民國政府教育投入有限且極不穩定的情況下,對于工程類高校是巨大的挑戰。對此,李書田一方面依靠對專業發展形勢的準確判斷,盡可能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將設備引進的重點放在能夠帶動學科質變的尖端儀器上。如唐交從美國購置的形變分析儀,是構造工程學的最新發明,當時全亞洲僅有三臺,由此成立了國內唯一一間構造工程實驗室。[22]又如北洋花費巨資添置的風洞設備,成為飛機制造及相關專業起步的基礎。[23]另一方面開源節流,通過發動校友捐贈及社會贊助等多種渠道集資,完成了唐交圖書館的擴建,以及北洋工程學館和實驗館的建設。同時“盡量少用職員,盡量減少消耗費用,盡量減少不必須之開支,樽節所得,悉用以增置實驗設備,圖書及有永久性之建設”[24]。這一原則即便在抗戰艱難辦學時期,李書田也一直堅持。
此外,制度化和公開化是現代高校管理的基本原則,但也是早期中國大學的短板。李書田自到任唐交后,便立即致力于修訂學則以整飭校務,兩年間通過了《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專章》等多達31項規程[25]。執掌北洋時期又先后制訂了《院務會議規程》《事務會議規程》《參觀旅行規則》《實地聯系規則》等多種治校章程。[26]并仿照西方高校的校長會議,組織包括院長、總務長、教務長、教授等的院務會議,作為討論審議院內重要事務的機關。[27]同時,他重視《交大唐院季刊》《北洋周刊》等校刊建設,并將之作為信息平臺定期公開校務,“各項重要公牘,院務進行情形”[28]等校務情況向師生公示,不但體現了現代大學的管理特點,而且其中所含的規則意識、流程意識,暗合工程學科的專業精神,于校園文化具有潛移默化的建構意義。
(三)營建科研組織平臺,開創研究生教育
科學研究是現代大學的重要功能。民國前期,雖然已有大學成立了若干研究機構,如北京大學研究所(按文、理、法三科分設)、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等,但從全國總體上看,工程科學方面的科研活動還是主要限于個別學者,缺乏組織性和規模性。有鑒于此,李書田掌校唐交后,便多次力請交大本部在唐交設立研究所。1930年10月,“交通大學研究所唐山研究分所”獲準設立,李書田任所長,成員包括羅忠忱、顧宜孫等當時在校的知名教授。唐交所的組建是中國大學工程研究向組織化邁進的重要一步。但該所初期所面臨的“人少課多”[29]之困,也使李書田意識到,要想充分發揮大學的科研功能,必須從根本上營建出利于激發教師科研潛力的工作生態,為此他在掌校北洋后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身體力行,親自進行科研示范。李書田自回國任教之始,便同時開展科研與教學工作。即便擔任行政職務后,也沒有因為身份的改變而遠離科研,陸續完成了《對數圖解河水流量計算法》《關于為河北省農田水利開發自流井之調查研究》等多項研究。根據1935年的統計,其論文發表數量居北洋教授之首,起到了很好的科研表率作用。[30]第二步,削減教師授課量。早期的大學教師無不背負了沉重的教學任務。據茅以升回憶,北洋大學的教師“不論本國人或美國人,教務均甚繁重,每星期授課二十小時以上”[31],李書田剛回國時也只能在教學間隙尋覓空當進行科研。有鑒于此,他加大了師資引進力度,每系增聘教授2人,同時配合教職員專任制度,以減輕教師任課負擔。[32]這就使教師在授課以外進行自主科研活動獲得了時間條件。第三步,建構覆蓋全校教師的科研組織平臺。他先于1933年在校內組織成立了礦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并于翌年將兩所合并為“國立北洋工學院工科研究所”,成員覆蓋全校所有學系教師。李書田親自出任研究所主任,要求每個教師都要在“切實授諸生以學,督諸生求學”以外,還要“自家精勤研進學術”。[33]
由此,學校的科學研究活動出現了蓬勃的態勢,許多專事教學多年的教師也被激發出了科研活力和熱情。為配合教師科研成果的發表,李書田又創辦學術期刊《北洋理工季刊》,至抗戰爆發前共刊載了170篇學術論文,[34]在全國工程學界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在組織基礎成熟后,李書田又于1935年再接再厲,開工科研究生教育之先河。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首批3名研究生畢業,被授予碩士學位,成為最早的一批工學碩士,于中國工程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四)加強“學科集團”建設,規劃具有工程教育特色的綜合型大學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起步階段,由于學科建設的理論準備尚不充分,加之專業設置不斷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預,無論唐交還是北洋都存在學科相對不足的問題。如唐交在李書田接手時僅有土木工程一個學科,學校時名“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被國民政府定位為專事培養鐵道工程人才。但李書田認為唐交歷史悠久,全國馳名,理應發展為學科齊全的一流大學。為此,他在接受任命后便制訂了《對于發展交大唐院之將來計劃》,提出增設學系、研究所等一系列計劃。[35]在他主政的短短兩年間,唐交恢復了一度撤銷的礦冶工程科,并在土木工程科下增設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兩門(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交礦冶科復設本不在交大本部計劃之列,但李書田認為唐山本是礦業之都,礦產又是工業基礎,因此力主恢復,并籍由學科增設,成功呈請更校名為“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36]為學校日后的發展提升了更廣闊的格局。此外,考慮學校“距離當時中國最大的北寧、津浦兩大路機廠近在咫尺”,且“學校土木與礦冶兩科有需于機械的地方太多”[37],李書田還試圖增設機械電機工程系,雖未獲本部批準,但李書田結合屬地產業發展,多學科協同建設的思想,已初步明確。
在執掌北洋后,李書田又在既有的土木、礦冶、機械三個學科基礎上,根據天津新興產業的發展特點和城市建設需求,陸續添加了水利衛生、航空、冶金、電機等多個系組。②經過多年實踐,李書田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建設思路逐漸清晰。1937年初,他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提交了《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詳細闡述了其將新北洋大學建設為綜合性大學的構想。他在計劃書中首先指出一流大學綜合化的必要性:“獨立學院學生,只是囿于一隅,課外孤陋寡聞,文化熏陶,嘗試灌輸,均事倍功半,而高級人才之訓練,并不限于所研習之專門學術,綜合大學,優點在此。”[38]在具體規劃方面,李書田計劃在北洋既有工科專業基礎上再擴建電訊、化工等關聯專業,構建包含11個方向的“大工科”體系。同時參照美、英等國理工學院的形式,優先建立與工科教育緊密聯系的理學院。在理工齊備的基礎上,還將陸續設立醫學院、文學院和法學院。這些學科之間亦非孤立存在,“理學院添設生物及生理學系及藥物學系,俾資與醫學院密切聯系;而生物學復與工學院醫學院將開設”[39]。東西方語文則為“學習、讀作、演述之工具,并為法學的恢復基礎”[40]。法學院恢復后,在最初基礎上,還將下設經濟學系,與工程管理等方向形成對應聯系。也就是說,李書田的規劃中,各學科之間將形成相互聯系的閉環,對此李書田使用了“學科集團”一詞來描述,實際對應當前的學科群概念。
顯然,該方案不僅是北洋一校的規劃,而且凝聚了李書田對于工程類高校發展方向的理解。按照這一思路,新北洋大學將是以工科為中心,包含工、理、醫、文、法五學科大類,具有工科特色的綜合性大學,且理學院和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的籌備也已在抗戰前夕幾近完成,[41]惜抗戰爆發使這一進程戛然而止。
(五)構建現代校城關系,取助社會資源辦學
推進工程類大學與屬地社會的融合,是李書田研究中易被忽視的方面。如前所述,李書田對于當時國際高等教育領域中校城關系日益緊密的趨勢有著充分認知,這一點尤其體現為其執掌北洋時期,對學校與所在地天津這一民國工商業中心城市關系的推動上。
北洋因八國聯軍之亂遷于津市北郊的西沽。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空間的距離與國立大學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使學校和天津社會形成一定疏離,也造成其在地方資源獲取、協同發展等方面明顯不足。為改變這一現狀,李書田采取多方舉措加強學校與地方社會的互動。
首先,推動校內教師發揮科教專長,投身社會事務。李書田本人帶頭走出象牙塔,以北洋工學院院長的身份兼任《大公報·科學周刊》主編[42]、天津三八女子中學校董[43]、整理海河委員會委員[44]等社會職務,在科學普及、女子教育、城市水治理等社會熱點領域現身服務。在其引領下,校內學者紛紛通過掛職政府企業、接受科研委托等形式參與城市產業和市政發展。如土木系主任張潤田(字倬甫)受聘天津市政府顧問等職,并提案《津市工程三年計劃》,在《北洋周刊》上獲贊為“本院學術貢獻津市之第一聲”[45]。
其次,學校辦公益,開設“工友補習學校”,為社會工人補習文化知識。該校開辦于1933年4月,由北洋學生輪流擔任授課,校方撥出教室和圖書館作為教學場所[46],被市內來賓盛贊“為中國大中小學之創舉”[47]。
再次,推動學生校園活動的社會化。李書田掌校后開始向部分學生社團提供資助,鼓勵其與社會聯合開展活動。如長城抗戰期間,“國劇社”就曾邀請津門梨園名流“合臺義演,所得慰勞抗日前線”[48]。李書田尤其重視體育,為此他推動學校加入天津體育協進會,并制定了專門辦法獎勵在社會賽事中獲獎的學生。[49]凡此種種,北洋學生文體訊息頻頻見諸《大公報》等城市媒體,提高了社會對學校的認可。
最后,加強學校與社會的空間交流。早在唐交時期,李書田便曾嘗試向社會開放校園,在春假、暑假接待社會參觀。[50]掌校北洋時期,他又定期撥款對學校附近的西沽桃花堤進行維護[51],數年間竟成津門名景,每到賞花季節,“院內院外,桃花林下,布滿游人蹤跡,各校旅行團,結隊來游者尤眾”[52]。顯然,通過主動營建校園周邊城市景觀,不但使校城在空間上融為一體,而且推動了大學師生與市民之間的直接接觸。
良好的校城關系為李書田爭取地方資源支持學校發展獲得了便利。譬如,在籌建北洋圖書館時,學校得到了天津通成公司、伊文思圖書公司、興華公司等天津市內企業近千元捐款;[53]在為飛機工程系籌措研究經費時,得到天津中國銀行支持,獲得經費資助3000元,[54]并得到市內博物館主動捐贈飛機一架,[55]確保了中國第一臺自制飛機發動機研發成功;在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籌備過程中,更是得到時任天津市長張自忠積極協調幫助,以及社會名士盧木齋、婁魯青的慨然讓地。[56]總之,在李書田的努力下,北洋工學院與天津地方社會形成了一種緊密并帶有互助性的現代校城關系。這一經驗,在抗戰期間也成功支撐起其在貴州、西安等地的辦學活動。
三、李書田對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歷史貢獻及啟示
從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整體發展脈絡來看,經過19世紀末肇始后近40年的演進,無論從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還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內在需求出發,都亟待一輪與時俱進的變革。而李書田作為這一進程的推動者和實踐者,至少在四個方面做出了重要歷史貢獻。
第一,明確了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養的定位和地位。正如李書田所言,工程類學科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初階段,與其他學科同歸于寬泛的西方“高深學問”[57],育人目標和特色并不清晰。而國民政府成立后,又將一批專科層次的專門學校升格為本科。但囿于辦學基礎和思路的限制,新晉本科高校多將工程教育定位于“職業教育”,這就出現了人才目標矮化的趨勢。在高等工程教育面臨分水嶺的時候,李書田從現代工程建設的實際情況,以及唐交和北洋的辦學歷史出發,提出了以卓越工程師為目標的“五端”人才育成戰略,并圍繞這一思想對兩校的課程體系、師資設備、管理制度等軟硬件進行了全面更新,不但具體回答了現代高等工程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層次問題,而且非常及時地確立了工程教育在中國高等教育整體版圖中的地位。
第二,完善科研體系,奠定研究型大學的基礎。由于早期中國大學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教學,科研活動多限于學者的個體行為,科研功能體現得非常有限。不過,按照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當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階段后,直接照搬外來科技已經無法滿足本土產業界的需求,勢必要求高校發揮科研服務功能。對此,李書田不僅敏銳察覺到“大學與工業之聯絡,屬近年之進展”[58],而且從全局的高度將之視為學術獨立的契機,如其言“不知進取,即學術永無提高之機會,永無獨立之機會,永無創造之機會”[59]。他在總結唐交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科研組織、制度、期刊等平臺的搭建,在北洋工學院構建了全校性的科研體系,及至研究生教育的開展,推動了工程類高校從教學型大學向教學科研型大學的轉型,為嗣后研究型大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第三,論證并實踐了工程類大學的綜合化發展之路。對于工科院校是否發展非工學科,是中國工程教育領域一直以來的爭議。特別是辛亥以后,教育界一度受德國“學”“術”分離思想的影響,工科被認為是“術”的范疇,而多以單科大學的形式發展。前述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的學科互換事件便是代表,也為日后北洋的發展埋下了隱患。而李書田以其廣闊的國際視野,在參考康奈爾等國外先進大學發展動向的基礎上,成為工程類大學多科化、綜合化的堅定推進者。在他所制定的《對于發展交大唐院之將來計劃》和《國立北洋大學籌備緣起及分期完成計劃》中,既有理工科內部不同專業方向的“小綜合”,也有工科與醫學、文法等其他學科大類的“大綜合”,構建成為以工科為中心的學科群。這實際上同時回答了工科院校要不要綜合化,以及怎樣在綜合化進程中保持工科特色的雙重命題。
第四,推進高校與屬地社會新型現代關系的建構。從西方大學發展的歷史來看,經歷了從古典時期大學與城市社會互不來往,到近代產業革命背景下相互依存的變化。這一現代校城關系的核心一方面植根于高校與屬地城市產業發展的緊密結合,另一方面也在于大學在城市建設、文化體育、社區治理等各領域與屬地城市的深度融合。對此,五四運動以后,中國教育界在整體轉向以美為師時,已發覺其“服務社會”的理念并有所接受。③但如何實際推動這一轉變的落實,還要取決于高校管理者對這一趨勢的具體理解和經營辦法。如前所述,李書田一方面在教學、科研、學科設置等方面推動兩校與津唐兩地產業界的對接,已初具現代產學研合作模式的雛形;另一方面根據中國社會實際情況,將“服務社會”發展為“融入與取助”社會,積極推動大學師生參與城市公共事務、文體事業,乃至在辦學資金、校園空間等方面與城市社會分享資源,從而獲得廣泛認可和回應,為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的在地化發展做出了示范。
綜上所述,20世紀30年代,李書田在把握國際高等教育變革趨勢的基礎上,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通過實踐為中國工程類大學找到了正確的發展方向。雖然歷史不能簡單復制,但以筆者淺見,其高等工程教育思想中所蘊含的若干精神遺產仍可引為當下之鑒。
其一為一流意識。這是李書田高教生涯中始終不變的追求。當前,我國工程教育規模已經位居世界之首,隨著總量增加,突出一批一流專精的院校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國家高教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頭部高校須把握工程學科發展的最新形勢,樹立一流人才培養理念、創設一流科研平臺、引進一流軟硬件,方能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學科和一流高校。
其二為變革意識。正如李書田以大刀闊斧地“革舊布新”回應了產業升級進程對高校內涵和功能提出的新要求,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4.0建設的關鍵時期,工程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對人才格局的要求越來越高。高等工程教育不可墨守成規,應積極探索新工科自主發展路徑,大膽調整學科結構和培養機制,拓寬專業基礎,變專才教育為素質教育,變面向行業甚至崗位的教育為面向新型工業化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教育。從這個角度來說,工程類大學的建設也應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領域的先鋒。
其三為學科群意識。多科化、綜合化是現代高等工程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千校一面。當前,一些高校在綜合化的路徑問題上有所躊躇,如能參考李書田為唐交和北洋的長遠統籌,以自身優勢專業方向為中心,打造復合型學科群,則有利于在保持學校原有特色的基礎上完成多科化、綜合化的進程。
其四為共同體意識。工程類高校更應主動擁抱地方社會,不可閉門造車。這其中既包括在人才育成、科研方向、專業設置等環節充分與地方產業結合,深化產學研合作,也體現在行政、經濟、人文交往、空間建設等方面充分考慮社會因素,形成全方位的發展共同體。
最后為品牌意識。正如李書田在唐交和北洋取得的成績,建基于其對兩校歷史傳統的尊重和賡續,工程類大學在“務實”發展的基礎上也不應忽視“務虛”,盡可能在治校理念中凸顯文化積淀,在發展規劃中體現歷史定位。這既有利于高校自身的發展,也是我國在理工科領域打造世界知名大學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注釋:
①1921年交通大學建校,在北京、上海、唐山分設院部,原唐山工業專門學校被編為唐山學校,1922年各部成為獨立大學建制,直到1928年9月,國民政府頒布《交通部直轄交通大學組織大綱》,再度將三校合并,并于翌月移交新組建之鐵道部轄屬。由于內外部各種因素,從三校合并后至李書田到任前的兩年間,唐交三易校長,校務亟待穩定整飭。參見汪啟明:《西南交通大學校史(第二卷)》,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
②1929年起,按照教育部要求,正科改為本科,科下各學門改稱學系,系下分組。1935年北洋工學院共設四系七組,包括礦業工程學系(采礦、冶金)、土木工程學系(土木、水利)、機械工程學系(機械、航空)、電機工程學系。參見李書田:《北洋大學之過去五十三年》,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編輯室:《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天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408頁。
③1921年,蔡元培考察英美教育時,在美國伯克利大學發表演說,將中國的大學理想闡述為:“孔墨精神加上英國之人格教育、德法之高深研究、美之服務社會”。其中,“美之服務社會”顯然為蔡氏此次考察的收獲。參見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國學生會演說詞》//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