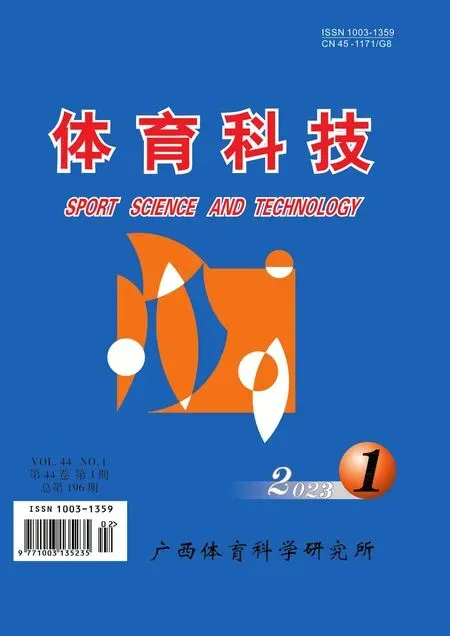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策略研究
趙迎輝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策略研究
趙迎輝
(山西工學院 通識教育學院, 山西 朔州 036000 )
具身認知理論強調認知與身體、環境是一體的,與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的教育內涵相吻合。文章簡述具身認知理論實際運用研究和國內外研究狀況等,分析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的現狀,提出牢固樹立以身體為主的教學理念、營造身體生成的俱樂部教學情境、豐富教學手段,培養體育精神等策略,旨在助推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的學術、實證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具身認知;俱樂部教學;策略
立德樹人是高校的根本使命,也是高校的靈魂和立身之本[1]。2006年,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聯合提出啟動“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計劃,力圖改變學生體質健康下滑趨勢,同時也對學校體育教學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二十年來,關于高校體育教學模式改革的探討一直不斷,其中“俱樂部”制體育教學模式改革在全國各高校試運行的較多,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學生參加運動的積極性。但是,隨著教學實踐的不斷深入,高校俱樂部體育教學的不足也愈加凸顯,俱樂部體育課也成為一些學生眼中的“水課”“放羊課”“躺贏課”,學生“喜歡體育,不喜歡體育課”的現象依然存在。在致力體育教學模式改革的同時,我們應該反思:受“身心二元論”影響的傳統體育教學思維能否適應俱樂部體育教學模式的發展。
1 具身認知理論意蘊
1.1 具身認知理論概述
20世紀50年代歐洲興起的第一代認知科學,旨在強調“身體與心智的分離”“離身認知”“把認知與人的身體相分離”,認為人的大腦只是計算機,認知只是符號的加工,且加工的地方只存在于大腦,無論是符號加工還是聯結主義都認為人的認知與身體無關。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笛卡兒、洛克、康德等人的哲學思想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20世紀末期,生成語義學、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創始人喬治·萊考夫和美國哲學家、認知科學家馬克·約翰遜以17世紀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為學術指引,提出思維基于身體、源于身體,思想范疇和概念隱喻都是身體感覺運動經驗造成的學說,對心智與身體的一體化特征進行了系統的論證,在學術界逐漸興起了有望取代認知信息加工范式的第二代認知科學。雖然目前有關巨神理論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但學者們對具身認知已達成了共識:具身認知理論既不主張身體一元論,也不贊成身心二元論,它強調一體論;認為心智在大腦中,大腦在身體中,身體在環境中,心智、大腦、環境是一體的;身體調節及影響人的思維、判斷、情緒、動作和動機等心智過程,身體與環境是耦合關系。
1.2 具身認知理論的實際運用研究
所謂具身,就是一種人對身體的獨特體驗。身體是經驗的主題,是經驗者,而不是被經驗的客體[2]。隨著西方哲學領域對身體經驗的“變更”,認知科學領域也迎來了由“離身”到“具身”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計算機科學、語言學和人工智能學科的影響,心理學領域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行為主義的認知革命運動。隨后,認知科學領域開始發生由“離身”到“具身”的細微轉變。到20世紀80年代初,過度追求實驗室數據和實驗室假設的認知心理學,因脫離實際生活、游離于社會文化視野之外而備受批評。傳統的“大腦就是計算機,思維就是計算機,認知過程猶如計算機的表征和運算過程”等認知心理學的元素主義傾向遭到心理學家的悍然抨擊;擁有情境性、具身性和動力性首要特征的第二代認知科學逐漸走進學者的視野。第二代認知科學與第一代認知科學的明顯區別在于,第二代認知科學更注重認知過程的情境性和動力性特征,強調認知依賴于身體、認知依賴于環境。20世紀90年代,意大利帕爾馬大學的神經生理學家賈科莫·里佐拉蒂和同事們在恒河猴大腦皮層中發現了一種新的視覺——鏡像神經元,引導第二代認知科學進入更加深入、實際的研究,給后來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認識心智的新視角。
2012年,學者斯諾巴在《Dance as a Way of Knowing》文中介紹到怎樣用舞蹈進行知識教學的實踐案例,作者不是傳統的把舞蹈作為一種身體鍛煉的方式,而是把舞蹈作為一種知識表達和知識探索的方式進行;舞蹈練習的過程就是身體學習的過程,在這一特殊的過程中,通過身體的動作解釋了一種與生俱來的身體語言,而在這一學習過程中,練習者的身體、心智、環境和大腦組成了聯系緊密、融為一體的體系[3]。斯諾巴倡導的這種學習是基于具身認知的,是一種具身學習。2012年,學者戴維斯等人研究了具身認知研究的應用前景,提到了在司法、文學和藝術領域運用“具身認知”的學說。亞利桑那大學SMALLAB、隔離比亞大學IGENERATION和TABA教學策略研究是國外關于具身認知在教育領域研究中的代表,側重于學前教育、老年教育和信息技術方面的研究應用。
國內學者楊丹滋的《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教學方式變革理論探討》、秦安蘭的《具身認知理論及其對幼兒教育的影響》、楊少芳的《具身認知理念指導下自閉癥兒童音樂治療方向的個案研究》、劉儀輝的《基于具身認知的教學設計研究》等對教學策略、教學設計都在理論層面有貢獻。劉欣然、范婕的《從身體哲學匯總尋找體育運動的哲學線索》、顏榮的《大學體育教學巨神認知意蘊及優化策略研究》、張慈軍、周惠新的《高校體育教學中融入具身認知理論研的研究》、焦宗元的《身體視域下體育認知的轉向研究》、周惠新的《身體哲學視域下現代體育教學的具身認知》、何紹元等人的《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體育教學轉向研究》等研究,將具身認知這一理論運用到體育領域進行研究和論證。
2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現狀
2.1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彰顯主體性
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指出,“人的意識能操縱身體,但身體是主體的,意識只是身體的一部分。”身體的動作是身體意向性的表達,而不僅僅是意識的表達。高校體育突出育體和育人,強調教育的本質,是一種以身體教育為手段,培養全面人的教育。體育作為一種特殊的身體活動參與樣式、主體的身體活動的教學形式,在教學實施過程中凸顯了具身性,這也是體育的特殊性。受到傳統體育教學模式的影響,師生在觀念上皆認為體育技能的教學較為重要,而忽視教學的實施過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的實施,對調動學生參與體育學習、體育鍛煉的積極性有顯著提升作用,實踐證明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有良好的體育技能學習效果和育人功能。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能很好地激發學生興趣,培養學生個性,從而促進體育學習效果[4]。
體育教學的過程是倡導以人的身體參與學習、技能獲得為特征的實踐過程。在學習的過程中,人體參與學習的各個機體之間有相互交流和碰撞,并在交流和碰撞中不斷提高和完善,激發了生命肉體的原始動力,讓身體生命價值重新建構,使體育教學的本意得以彰顯。在體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注重學生個體、重視學生主體特征、尊重學生獨立性和差異性,對學生積極性的提高有推動作用。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在俱樂部會員分層次教學中,注重因人而異、因材施教的“處方”教學,注重學生的身體先天條件、心理感受,從身體的認知特點入手,倡導“身體合作”“身體參與”,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身心兼顧,為提高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打下良好的基礎。
2.2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缺乏情境性
情境性教學是建立在真實情境問題或以解決真實事件問題的教學,有一定的模式性和角色扮演性,由美國學者Jean Lave和Etienne Wenger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現行體育課教學遵循強調先講授(教授)運動技術層面,學生模仿練習、教師糾錯、學生練習強化,之后進行某一個大環節的技術授課,學生進行強化練習,學期末組織課內小型比賽的模式進行。這種傳統的授課方式看似無縫銜接,但是卻忽略了實用性。學生發現在比賽中運用技術動作時很難和課程學習建立有效的聯系。這是因為在傳統體育課堂授課過程中缺少角色對抗和場景模式。具身認知理論強調,知識技能的來源依賴于環境。高校體育環境場景的設定或模擬,有利于學生學習運動技術動作、建立自身心理、進行有效溝通,卻抑制了學習者內在學習動機。
2.3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缺失人文精神培養
高校體育教學在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方面有著特殊的育人價值。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實現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近幾年,高校體育教學的重心逐步由技術層面轉向學生的身心全面發展,但大多停留在教會、教懂、教樂等層面,對于學生內心層面的觸動時有時無,在立德樹人等人文精神方面的培養存在諸多問題。目前,國內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多數依舊建立在傳統的體育課堂教學基礎上,學生在上課時間、上課項目和任課教師實現了相對的自主選擇,教師在教學大綱、教學內容、教學設計等具體實施環節也有了對應的改革,但是對于國家提出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教體藝〔2002〕13號)、《高等學校體育工作基本標準》(教體藝〔2014〕4號)對學生德育、人文精神以及心理健康方面要求的達標度,依舊停留在教學大綱的一紙文件上,教師的重心依舊停留在俱樂部學員技術層面,俱樂部學生(學員)熱度于項目層面。開設俱樂部課程教學時,學生(學員)的學習動機缺乏,教師在課堂上缺少與學生心靈的碰撞。
3 具身認知視域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策略構建
3.1 從“離身認知”到“具身認知”:牢固樹立以身體為主的教學理念
體育教學的過程是倡導以人的身體參與學習、技能獲得為特征的實踐過程。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的模式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學生實現了上課時間、上課項目和上課教師的自主選擇,學生的學習激情較傳統體育教學高,學習效果好[5]。體育課是較為特殊的課程,強調身體參與,教育和引導學生進行“身體思維”,讓學生在知、情、意、行等方面有很好的表現。具身認知視域下的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的教學組織過程不死板,在師生互動、重視學生的水平差異等彰顯學生主體地位方面有著先天優勢。
3.2 從“講授技術”到“構建知識”:營造身體生成的俱樂部教學情境
目前,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過程依舊走“重技術”的淺層教學路線。強調運動技術的習得本身沒有問題,忽略學生對體育學科或某一單項術科的深度知識加工,是目前俱樂部教學所欠缺的。在實施體育俱樂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對教學大綱、教學日歷和教案進行精心設計,重點設計和謀劃技術動作與技術動作之間的銜接、技術單元與技術單元之間的銜接,在教懂、教會、教樂的基礎上考慮學生的理解與體驗,合理設計教學情境、角色扮演、情境設定、以賽促練等環境,促使學生融入特定的情境中,激發學生學習的內驅力,增加俱樂部教學體驗感。在教學實施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的學習理解和學習體驗,引導學生對已有知識和運動技能的整合、深加工;結合使用過程性評價,在模擬特定的比賽場景下,引導學生對已有運動技能與多學科知識的融合,真正獲得屬于自己的運動技能和綜合知識,為學生終身體育奠定基礎;引導學生在特定的教學情境中與自身“對話”,在身體實踐的基礎上進行反思,將認知心智、身體和環境融為一體。
3.3 從“技術鑄人”到“立德樹人”:豐富教學手段,培養體育精神
“講授——示范——模仿——練習——糾錯——再練習”的體育教學過程是培養學生堅韌意志、永不言棄的良好品質的重要手段,也是運動技術習得的必經階段。但是,如果停留在技術習得層面,不能深層次地將體育與德育和學生品格意志、價值觀、人文精神等方面融合的話,這依舊是停留在傳統的體育課堂教學層面。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要合理運用現代教學手段設計特定的教學情境,引導學生融入教學情境,注重觀察學生的體驗感受,不是僅停留在技術層面,還要銜接好對運動項目的文化、精神的引導,正遷移至已有的知識結構、生活環境、學習環境、社會環境中。在技術習得的過程中,引導學生進行感悟生命、敬畏生命,在模式比賽中引導學生進行團隊合作,合理宣泄比賽中成功與失敗情緒;多層次設計教學實施環節,讓學生在學懂、學會、學高興的基礎上體驗角色轉變、團隊力量、人際交往等,為進一步培養學生健康的體魄和健全的人格夯實基礎。
4 結語
具身認知視域下的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在調動學生參與運動的積極性、彰顯學生主體地位方面有很好的促進作用。在具身認知視域下探討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通過合理設計教學情境、豐富教學手段方法,引導學生進行身體思維、自我認知,在運動技能習得、體育精神培養方面拓寬路徑,助推高校體育俱樂部教學模式的學術、實證研究。
[1]李力,金昕.新時代高校立德樹人的內涵、難點及實現路徑[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149-154.
[2]葉浩生.具身認知的原理與應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3]葉浩生.“具身”涵義的理論辨析[J].心理學報,2014,46(7):1032-1042.
[4]焦宗元.身體視域下體育認知的轉向研究[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17,36(5):65-69.
[5]顏榮.大學體育教學具身認知意蘊及優化策略研究[J].池州學院學報,2019(3):91-93.
[6]姜勇,馬晶,趙洪波.基于具身認知的體育與健康學科核心素養意蘊與培養路徑[J].體育學刊,2019(4):88-93.
[7]陳忠菊,曹紅敏,楊輝霞.基于具身認知理論的體育教學“立德樹人”路徑探析[J].池州學院學報,2021(3):115-118.
[8]章翔,林秋菊,李斌,等.安慶師范大學公共體育課堂俱樂部制教學模式探討[J].體育學刊,2021(6):118-122.
Research on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ollege Sports Club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ZHAO Yinghui
( Shanxi College of Technology, Shuozhou 036000, Shanxi, China)
山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重點項目(項目編號:SSKLZDKT2020078);山西省高等學校教學改革創新項目(項目編號:J2021918)。
趙迎輝(1987—),碩士,講師,研究方向:高校公共體育教學、體育教育訓練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