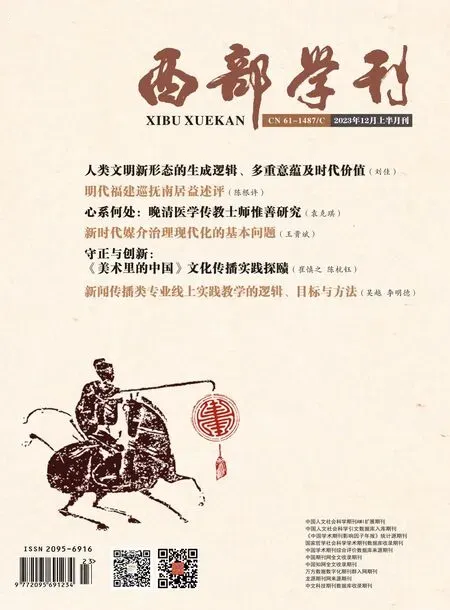試論宗教信仰的變遷對蒙古族制度文化的影響
王 璐
(內蒙古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呼和浩特 010020)
蒙古族是一個非常注重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在其文化中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所以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宗教的作用[1]。一方面,宗教是統治階級管理國家、控制民眾精神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對于保持蒙古地區的長治久安和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蒙古民眾的精神食糧,豐富了蒙古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成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形成了蒙古民族獨特的生活習慣和文化。
一、蒙古族早期的宗教信仰——薩滿教
薩滿教是在原始信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民間信仰活動。因為通古斯語稱巫師為薩滿,故得此稱謂[2]。蒙古社會曾信奉薩滿教,受其“萬物皆有靈”[3]觀念的影響,產生于宗教信仰的約孫(蒙古語,意為“禮”“理”。編者注)主張敬畏神靈,主要體現在敬畏火神、勿踏門檻、敬仰長生天(1)長生天是蒙古民族的最高天神,即蒙哥·騰格里(突厥語是Mangu Tangri,蒙古語是Mongke Tangri,讀作“騰格里”)。因蒙古人以蒼天(蒼穹)為永恒神,故謂長生天。和偶像崇拜。
隨著蒙古人的興起,這一原始的部族信仰緊隨政權的充實和壯大不斷對其發展和決策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薩滿教首領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建立蒙古帝國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薩滿教在這樣一種人民心理普遍脆弱和缺乏安全感的社會中起到了維系蒙古人民同心合意、共御外辱的積極作用,并在落后的草原經濟條件下形成了一種全民信仰的精神狀態[4]。
二、多教并存的蒙古帝國時期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后,薩滿教處于鼎盛時期,其領袖闊闊出經常假借長生天的名義,挑撥成吉思汗兄弟的感情,后被成吉思汗處死[5]。這次政變事件,使成吉思汗統治帝國的法制思想發生了變化,他雖然信仰薩滿教,相信長生天神說等闊闊出的一派言語,但此后他不使一教掌權,不讓其參與政治,制定和增補了禁止人們偏崇一種宗教,要敬重一切宗教的法律規定。這種規定雖然沒有廢止薩滿教,但無疑是一種變革和進步。因為薩滿教畢竟是一種原始宗教,而成吉思汗所征服地區的宗教諸如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的傳入,無疑豐富了蒙古帝國的宗教文化內容,使人們尤其是蒙古族貴族階層的眼界放寬、思路開闊,從而更有利于他們對帝國的統治[6]281。
三、黃教在蒙古地區逐漸起主導作用
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俗稱)在蒙古地區傳播,迅速為蒙古貴族和廣大牧民所接受,北元時期佛教文化興盛和發達起來,甚至貴族子弟也出家為僧,比如衛拉特和碩特部有首領拜八嘎斯的義子咱雅班弟達,出家后成為著名的一代蒙古高僧[6]282。蒙古全民信佛始于阿勒坦汗,他與明朝停止戰事,達成互市協議,使蒙古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為發展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他尊崇佛教,以佛教作為統一社會的精神紐帶,使廣大阿勒巴圖(蒙古語音譯,意為“承擔賦役的人”,平民。編者注)和哈剌出(蒙古語,意為平民、下民。編者注)牧民皈依佛門,行施善事,俯首聽命于阿勒坦汗[6]92。
黃教影響了蒙古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文學、史學等各個方面,為其注入了新的內容。十六世紀末,以阿勒坦汗為首的蒙古右翼統治集團為了提高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地位,滿足建立政教并行政權的需要,頒布了一部法典,即《阿勒坦汗法典》,該法典對有效維護阿勒坦汗的統治、促進黃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以及蒙古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并對蒙古后世立法和法典編纂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153。按照該法典的規定,不論寺廟僧侶還是牧民百姓,凡事必須遵守戒律,不得違背。蒙古族統治者吸取了依法守戒的經驗,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就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所以北元時期是蒙古族封建統治者制定草原法最多的時期,也是特點最突出的時期[8]。
同時,藏傳佛教登上了歷史舞臺,改變了蒙古人的政治觀和思想意識,不論寺廟僧侶還是牧民百姓,凡事都必須遵守戒律,不得違背戒律規定。黃教的“轉世論”突破了薩滿教“天賦論”,有利于各封建統治者的統治和發展壯大各自的勢力。蒙古封建統治集團頻頻向西藏達賴喇嘛求得賜號,尋找前世,以便從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共同的宗教信仰密切了蒙藏兩族的關系,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加強了蒙藏文化的交流,促進了蒙古文化的發展。
四、宗教信仰對蒙古制度文化的影響
(一)蒙古政權由盛轉衰
成吉思汗時期,受薩滿教的“長生天”觀、偶像崇拜觀影響,蒙古人確信成吉思汗是受“長生天”之命來治理百姓的,確立了大汗獨尊、汗權至上的時代特征,并且推動當時的蒙古統治者不斷地用武力征服世界。蒙古帝國是一個典型的崇尚武力的軍事帝國,從大汗到臣屬均崇尚一種泛武精神。成吉思汗身邊依靠的重臣“四杰”——博爾術、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溫均為一代武將。“尚武”總是和戰爭聯系在一起,戰爭是早期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活內容之一,社會通過戰爭得到了強化管理,人民通過戰爭才明確了自己所負擔的義務,早期的蒙古法幾乎都與戰爭密切相關,戰爭也已成為蒙古法文化的重要方面之一[9]21。
隨著對各地的征服,蒙古統治者接觸到各種宗教信仰,他們逐漸放棄了落后野蠻的原始宗教,接納各國不同的宗教形式并為己所用,逐步改變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用文治觀念治理國家。
清朝統治者為了征服蒙古地區,對其采取“分而治之”“眾建而分其勢”的分化政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宗教政策,注重同蒙古封建貴族的聯姻,特別是最早與努爾哈赤建立關系的科爾沁部,“恩威并施”拉攏和撫綏蒙古上層貴族,保留和承認他們的特權,并給以優厚俸祿,封以崇高爵位,使他們成為清朝統治者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可靠力量[10]。在蒙古地區建立盟旗制度的同時,實行封禁政策,禁止各蒙古部落之間以及蒙古牧民與內地漢民的經濟文化交流,禁止蒙古人學習和接觸漢文,禁止內地人出關經商和種地。為了防止蒙古部落聯合反抗而崛起,清朝統治者把蒙古各部完全封閉起來,不僅使蒙古各部之間缺少溝通和交流,也阻斷了蒙古各部與外界先進文化與制度的接觸[11]。同時,在蒙古地區進一步提倡和推行黃教,把黃教成為控制蒙古的精神工具,黃教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教義讓曾經強悍的民族變得順從、忍讓、失去血性,削弱了民族斗志,逐漸失去了勇猛善戰的素質和尚武的精神[12]。
清朝征服蒙古各部時,喇嘛教(黃教)早已在蒙古各地傳播。清朝統治者開始時并不信仰黃教,但當他們了解到黃教的教義后,把它當作統治蒙古族民眾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提倡和推行黃教,以達到軟化蒙古社會的作用。清廷籠絡和利用黃教上層,指任和確立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喇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編者注)、活佛,擴大黃教的影響和吸引力,興建寺廟,鼓勵人們出家當喇嘛,免除喇嘛的兵役、徭役和賦稅,鼓勵廣大平民棄俗從僧,使大批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圖云集廟宇、念經修佛。底層民眾安于現狀,將希望寄托于虛無縹緲的來世,王公貴族則是傾其所有以換取來世幸福,特別是進藏熬茶,致使大量財富流入喇嘛之手,而不是用于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造成蒙古社會的貧困化。財富畸形分配,僧侶不事勞作、不交賦稅的代價就是蒙古族再也無力與清朝一爭高下,還因為青年男子都向往成為喇嘛,致使人口逐步減少。
(二)蒙古文化由單一到多元
蒙古族文化有以下特點。第一是開放性。因為單純的游牧文化不能充分滿足人們對精神財富的需求,蒙古民族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并將其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第二是剛毅性。游牧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順應自然,形成了保護環境、圖謀生存的頑強性格和宏偉氣魄。第三是崇德性。蒙古民族繼承和發揚了古代北方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即講公共道德、講禮儀、講信譽、真誠樸實。
在元朝的建國之初,蒙古法文化表現出的主要特點是“草原中心主義”。顯然,這是要把草原游牧文化強行推廣到中原農耕文化地區,以游牧生產方式取代農業生產方式,開歷史的倒車,這代表了最早一批蒙古貴族南下中原的真實心態[9]117。但在蒙古族不斷征服世界的過程中,他們不斷接受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進步思想和文化,思想觀念越來越開放、包容。成吉思汗尊重各個宗教教派,與道教的長春真人丘處機“龍馬相會”論道三日,并接受他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孝道、行善止殺、平治天下的建議。被稱為“治天下匠”的耶律楚材歸附成吉思汗,用中原儒家傳統思想逐漸影響蒙古統治者,使他們意識到想要治理中原地區,僅靠《大札撒》(《成吉思汗法典》)是不夠的。為了籠絡漢族士大夫,維護和鞏固對漢族地區的統治,元朝實行了一些采行漢法的做法。尤其在元代建國之初,曾試著實行任用漢官、實行漢法的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二月發生的“李璮事件”[13](李璮是金末山東軍閥李全之子,后策動叛亂,被元廷鎮壓后處死,該事件進一步促成元世祖政權對華北各地統治的集權化過程。編者注),忽必烈非常信任和重用的王文統參與該政變,動搖了忽必烈對漢族臣僚的信任。自此,元朝統治者逐漸疏遠漢族臣僚,重用回回人,從而使元朝統治者放棄了原本正確的民族政策,實行了民族等級政策,眾多漢族儒臣多年的努力功虧一簣[14]。但不論如何,蒙古統治者走出了“蒙古至上主義”的禁錮,不斷接納和學習中原法,形成了蒙古法與中原法互相影響交融的二元特色法文化。
(三)民族融合、共同發展
正像馬克思所講的:“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15]當蒙古法進入中原并試圖擴大其適用范圍、強化其法律效力的時候,文明程度的差異性使蒙古統治者反倒開始逐漸適應被征服地區形態穩定的法文化模式,盡管這種消極的適應——毋寧說是“順應”——仍然帶有相當大的保守性和抵觸性。如蒙古統治者以各種方式抵制來自中原傳統法文化的影響,并力圖永久保持屬于帶有自己特色的蒙古法文化內容,表現為在一定范圍內對蒙古法的繼承和沿用,甚至積極地推向漢族或者其他民族,有的幾乎維持到終元,或者采取措施形式上中斷中原傳統法文化的延續。但若從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總體發展趨勢來把握那個時代互為交錯的矛盾的法文化關系,則這種表現為對某一方面的抵制或對另一方面的維持,最終并不會成為一種絕對穩定的態勢,而只能是在謀求一種相對穩定的格局中,實現一方對另一方的妥協,或者說是自然地追求一種協調的狀態。當然,中原傳統法文化一方的主體以被征服者的地位而言是不應存在主動妥協問題的,反倒是以蒙古統治者為代表的蒙古法文化一方,在堅持自身的一貫性過程中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讓步,終于形成了中國傳統法文化發展長河中的獨具特色的元朝法文化[9]111。
蒙古汗國到元朝,是蒙古族發展的鼎盛時期,既保留了游牧民族傳統習慣法律制度,又推行漢法,起用漢族官僚,大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養份,加快漢化速度,不斷豐富蒙古族文化。為了更快地拓展和鞏固勢力,達到統治的目的,蒙古統治者實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16]。北元(2)北元(1368年—1635年)是明軍攻占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統治后,元朝皇室退守漠北與明朝對峙的政權。時期蒙古族由盛轉衰,政治、經濟實力日漸衰落,蒙古文化發展受到制約。元廷北遷后,因明蒙戰爭和東西蒙古間內訌迭起導致十四世紀末到十六世紀中葉止幾乎沒有留下什么文字性史料,蒙古文化進入了“黑暗時代”[7]143。經歷了對不同宗教信仰的歷程后,在蒙藏精英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蒙古族最終走向了與藏傳佛教融為一體的道路[16],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宗教信仰的變更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選擇,而是時代、歷史的選擇,可以說宗教信仰的變遷使蒙古社會步入正軌,推動了蒙藏政治、經濟、文化的廣泛交流和蒙古地區的繁榮發展[17]。
蒙古族為何從薩滿教改信喇嘛教,佛教真能讓戰斗民族變得文弱不堪?答案是否定的。宗教信仰的變遷不是蒙古民族由盛轉衰的唯一原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由盛轉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用單一、片面的視角看問題。一個國家或民族經歷由盛轉衰的過程,導致這樣過程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統治者的原因、有宗教的原因、有民族矛盾、有起義和戰爭的推動、有歷史的發展,也有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最終融合的因素……正如費孝通先生主張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指出的,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發展,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斷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時也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人[18]。各民族就是在這樣經常性的變動中形成人類的共同體,形成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和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思想是貫穿所有民族共同的歷史傳統[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