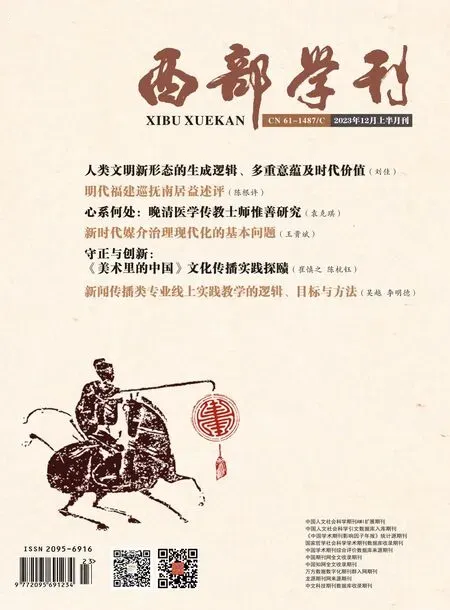“情理”在裁判文書中的說理應用
——基于相關裁判文書的分析
高 燕
(南京醫科大學康達學院,連云港 222000)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印發《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和《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要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重視并規范“情理”的使用。在撰寫裁判文書過程中,法官應對“情理”部分進行充分論證以增強“情理”運用的正當性及判決結果的合理性,從而讓當事人接受并認可判決結果,真正實現案結事了。
“情理”作為國人特有的文化基因,其在裁判文書中使用狀況如何?產生效果怎樣?面臨什么困難?如何審視這些問題?如何調整并合理規制“情理”的使用?本文擬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對裁判文書的梳理與分析,觀察“情理”在司法說理中的運用情況與發展趨勢。通過對樣本裁判文書的深度挖掘分析,窺見當前司法說理中“情理”應用的現狀,發現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出癥結,進而提出改進措施以規范“情理”的使用。
一、裁判文書中“情理”運用的研究分析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
以北大法寶網司法案例庫作為數據庫,以“情理”一詞為全文檢索關鍵詞,以最高人民法院為檢索法院層級,截至2022年7月20日,共檢索到以2018年至2022年為審結年份的裁判文書333份。通過人工識別和精細篩選,排除內容重復的裁判文書21份、模板相同且有關“情理”表述一致的裁判文書37份,剔除“酌情理由”“情理費”無關搭配以及出現在優秀案例編者按部分的裁判文書4份,最終得到有效樣本271份。為方便研究,使用Excel數據分析軟件作為數據分析工具,將樣本中關于提出主體、具體表述、含義類型、功能效果的關鍵信息逐一提取,利用篩選、統計、制作圖表等功能進行整合處理和量化分析。圍繞樣本中“情理”的使用場景、方法,使用時所指的含義類型、使用的效果和作用等方面展開研究,得到如下分析結果。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1.案件類型
就案件類型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情理”運用主要集中于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在271份樣本中,民事案件170件,行政案件38件,執行案件34件,刑事案件0件。民事案件中,合同糾紛案件達到126件,主要包括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計算機軟件開發合同糾紛、借款合同糾紛等。就審理程序而言,申請再審審查案件165件,二審案件59件。
2.使用主體
根據樣本的統計結果顯示,“情理”的提出主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審理案件的法官——審理的一方,一類是參與案件的訴訟參加人,即被審理的一方,包括當事人、第三人、訴訟代理人等。在271份裁判文書中,法官作為提出主體的有133份,訴訟參加人作為提出主體的有140份(1)有2份裁判文書中最高院和訴訟參加人都使用了“情理”。。法官作為提出主體的裁判文書中,有的是引用原審法院關于“情理”的表述,有的是“本院”提出。其中,最高院法官采用“情理”說理并作為提出主體的文書有101份。訴訟參加人作為提出主體的裁判文書中,有的是陳述原審當事人關于“情理”的表述,有的是再審申請人或上訴人提出。
3.常見含義類型
“情理”發端于斷獄之司法要求[1]。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其內涵不僅包含常情常理、世情社情、道德禮俗、風俗習慣、家法族規、鄉約行規等宗法農耕文明社會中庶民百姓所普遍認同的內容,還包括諸如“親親”“尊尊”“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等反映儒家倫理精神層面的規范[2]。如今,學界關于“情理”內涵的觀點甚多,卻尚未形成一致意見。本文通過案件分析,大致歸納出三種常見的含義類型,分別是客觀理性規則、日常生活法則和社會美好風尚。
(1)客觀理性規則。包括客觀規律、邏輯規則。
(2)日常生活法則。包括經驗知識、民間風俗、交易習慣。
(3)社會美好風尚。包括道德風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分析發現,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書中的“情理”內涵相對固定集中,最常使用的是日常生活法則,客觀理性規則次之,社會美好風尚使用較少。值得說明的是,裁判文書中關于“情理”的具體指向鮮有說明,往往呈現出一種神秘感,需要結合語境分析體會,因而本文總結的三類常見含義類型帶有一定的主觀性。
4.功能與作用
(1)加強說理,增強服判力
判決案件講求以情動人、以理服人。相較于冰冷陌生而又晦澀的法律條文,“情理”是有生命力的樸素鮮活之理,是社會大眾共同理解和遵循的道理[3]。因此,“情理”的使用對息訴平爭具有超乎尋常的作用。裁判文書中,使用者圍繞案件的證據材料、事實經過等相關內容展開敘述,輔助闡明案件情況。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通過“情理”論證,對證據、事實或者判決提出確認,加強說理效果,說服他人認可自身觀點。
(2)法官自由心證的重要判斷依據
自由心證,是指對于證據的取舍、評價以及事實的認定,法律原則上不預先規定,而是交給法官自由判斷的原則或者制度[4]。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照法律規定,運用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進行判斷,并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情理”包含邏輯推理、日常生活經驗法則等義項,是法官自由心證的重要判斷依據。
(3)填補法律漏洞,解決疑難案件
當今社會,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鮮事物層出不窮,新型案件不斷涌現,法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無法窮盡實踐中面臨的各類疑難問題。當法律無章可循而法官又不得不作出審判時,“情理”的應用便顯得尤為必要。在某種意義上,“情理”可以成為一種法律以外的具有正當性的補充,不僅可以填補立法漏洞,還有助于拉近司法與公眾的距離,增進互信,強化司法權威。
二、裁判文書中“情理”使用存在的問題
(一)“情理”使用格式化
承辦法官在使用“情理”時存在填充式、格式化的說理現象,有的承辦法官在書寫裁判文書時采用流水作業批量生產的方式,先提出觀點,再將證據簡單堆砌或是簡要描述事實,后籠統以“(不)符合情理”收尾,最后寫下判決結果。整個裁判過程沒有體現出個案分析和針對性說理,僅一句“(不)符合情理”就可以讓一切順理成章,根本不多加解釋,但這樣無法真正解開當事人的心結,化解矛盾。誠然,“情理”是一種以大眾的“集體記憶”的形式保留在人們的思維中[5],是長期共同生活在同一環境下形成的共同認知,當使用者論及“情理”時,聽眾可以一點就通甚至心照不宣。但是,當立場不同、利益矛盾時,“情理”就無法讓所有人都心領神會,需要使用者加以闡釋,讓“聽眾”信服。
(二)回應當事人不當
通過樣本分析,發現有部分裁判文書未回應或者遺漏當事人提出的“情理”問題。樣本呈現的案件多為再審申請案件或上訴案件,當事人提出“(不)符合情理”所指向的問題恰恰是當事人不服判的原因,也是爭議的焦點問題。承辦法官應當重視且謹慎對待這些問題,詳細闡明其中緣由,讓當事人心服口服。然而,實踐中仍存在個別裁判文書自說自話,不理會雙方提出的“情理”問題,當某些問題較為棘手時,回避回應當事人;或問題過于簡單時,不屑回應當事人。還有的裁判文書未考慮到雙方當事人的知識儲備,默認雙方為專業人士,跳過其提出的“情理”問題,不予解答。有的承辦法官雖然對“情理”進行回應和說明,但對專業問題簡單數筆帶過,未充分闡明理由,導致當事人無法完全理解,從而提出再審申請。譬如在一起政府強拆引起的賠償案件中,再審申請人對原審法院結合“情理”等因素酌定的數額不予認可(2)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賠申1326號行政裁定書。,原審未充分說明酌定金額的依據使得一方提起再審申請。如果司法機關不能在思想上加以重視這些問題,長此以往司法系統會在大眾心中留下冷漠疏離的印象,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三)“情理”使用技巧生澀
在司法說理中,法官對于“情理”的使用略顯生澀。首先,對“情理”的使用存在局限。有的法官在使用“情理”進行說理時,僅局限于個別客觀邏輯和日常經驗,言辭模糊,效果一般。其實“情理”的內涵十分豐富,觀察的角度也很多,法官應當充分知悉、了解社會習慣、風俗人情,從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中挖掘“情理”的內涵[6]。其次,說理方法不專業。裁判文書的說理主要采用演繹法,但承辦法官在采用該方法進行說理時較少對大小前提進行深入分析,在論證時不能運用發散思維,從不同角度展開論述,而是簡單套用“三段論”,說服力度不夠,或者過度分析,大段說教,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還暴露出邏輯漏洞。通過對271份裁判文書的整理分析發現,當事人對于“情理”的使用更為隨意,問題也更多一些。最后,“情理”的錯誤援引。“情理”援引的經驗法則應當是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正面的、積極的,彭宇案便是一個錯誤示范。在民事領域,法律不能以惡意揣度他人,否則只會加劇社會的不信任,產生道德危機。正如姚建宗教授[7]指出的,如果表達的思想與實踐內涵對于具體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言,不具有積極意義和正面作用,而是具有消極意義和負面作用,這些不成文的規范或格言、諺語就不被視為法律常識。
三、裁判文書規范使用“情理”的建議
“情理”的使用通常只是一種輔助,法律規范的適用才是第一位的。此時“情理”作為裁判理由而非裁判依據,起到增強論證、錦上添花的作用。必須申明的是,絕不能以“情理”替代法律或否定法律。因此,當案件為一般案件,適用法律明確時,“情理”作為輔助說理手段置于法律規范之后;若案件為疑難案件,適用法律不確定或法律規范出現漏洞時,“情理”可以在必要時以法律條文為基礎融入司法說理。需要注意的是,當“情理”作為裁判依據使用時,務必事先窮盡一切法律手段。換言之,只有在法律規范或事實證據存在缺陷或者爭議時,訴訟參與人才可以使用“情理”。
首先,司法說理中的“情理”應當具備最低限度的公理性,即司法說理中的“情理”應當是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即使大家個性不同、追求不同,但在“情理”的認識上能夠達成最基本的一致。在司法說理中,使用者在使用“情理”前,應當判斷其主張的“情理”是否能夠得到社會中多數人的認可,是否經得起推敲和換位思考,能否達到法律所期望的一般人所應有的理性。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司法說理中的“情理”應當符合正面積極的主流價值觀,能夠傳遞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裁判文書作為司法機關向公眾發聲的窗口,是傳遞價值觀的重要渠道和直接媒介,大眾通過研讀判決主文領會司法精神和態度,并預測和調整未來行為。裁判文書中的“情理”說理部分是價值觀輸出的主要陣地,也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因此,作為價值引領的重要工具,“情理”應當傳遞出一種正面、積極、向上的能量。
其次,當司法說理中“情理”發生沖突時,應有一套衡量標準,以保證裁判的正當性和一致性,也便于案件的回溯和監督。參照法理的價值位階,“情理”的沖突可以分為同位階沖突和不同位階沖突。當“情理”的位階相同時,可以作出如下順位:生命利益大于健康利益,健康利益大于財產利益,生命利益不分高低,財產利益可以按照價值區分高低。當“情理”位階不同時,應當遵循社會本位原則,個人利益讓位于公共利益。同時要兼顧比例原則,降低損害,實現利益最大化。
最后,多元論證強化說理效果。“情理”說理的過程應當呈現出解釋、推理、論證等多階段的樣態,語言表達上應盡可能準確簡潔莊重,論證方法上盡可能多角度充分。一方面,“情理”的含義類型指向應當明確,使用者應清楚闡釋“情理”的內涵,并結合案件具體分析,進行推理并論證。“情理”說理的語言表達上應盡可能避免夸張、反問等帶有強烈情緒的修辭手法。司法說理尤其是裁判說理應當是嚴肅的、莊重的,關鍵在于規范性。只要內容上通俗易懂,邏輯上清晰嚴謹,最終能夠實現說理效果即可。另一方面,“情理”說理的過程應當是完整的、多階段的,而非機械使用三段論。值得注意的是,“情理”說理的角度應盡可能多樣,從利弊關系的考量、立場維度的切換、后果影響的預測等多角度展開論述,使論證更加充分,更有說服力。